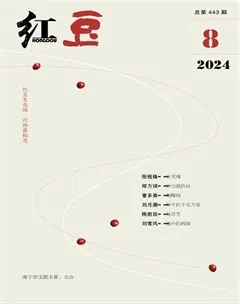孤云独鸟川光暮
2024-09-18李沛芳
唐朝诗人李嘉祐有一句写景之诗——“孤云独鸟川光暮”,意思是孤独的鸟儿和云朵映衬着暮色中的河川;但这句诗还有另外一层人生含义:在宏大的背景下,个体显得渺小而坚韧,正如孤云和独鸟奋力在黄昏的余晖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番意境很适合阐释小说《马芬芳》中的人物形象马芬芳。
《马芬芳》讲述了“我”在乌拉斯台遍地马粪的薄草地遭逢“贵人”马芬芳。她因为年轻时美丽动人而被一个小组长王耀武看上,又因拒绝他而在特殊年代被造谣污蔑为“破鞋”。马芬芳备受屈辱,一气之下来到草原上以捡马粪为生,住在一个简易的棚子里孤独且坚韧地生活。“我”随马芬芳的妹妹而来,妹妹的一句“王耀武死了”,虽然让马芬芳有大仇得报的轻松感,但“一辈子不回去”的誓言仍丝毫未变。“我”从中嗅到了文学的养分,写了一篇文章得了奖,拿着文章“我”又去寻找马芬芳,结果再也找不到她。失落的“我”只好为小说编了一个结尾,以寄托某种希冀。
小说刻画了一个遭逢贞洁困境的女人——马芬芳。因拒绝而被造谣本该是一场小的困境,揭开真相还她清白,事情很快就可以画上句号。但小组长王耀武却利用了众人对于女人贞洁的极端重视心理,最终演化成马芬芳的悲剧和一生的逃离。这不得不令人唏嘘!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她)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以死捍卫身体的贞洁是对女人的无理要求,也就是说,在贞洁面前,死不值得一提,这种拿女性贞洁和死亡相较的观念造就了多少悲剧。祥林嫂的悲剧仍历历在目,她本是一个健壮的、有活力的女人。第一次死了丈夫被卖时,被抓走,反抗过,后来从了,生下一个男孩,被狼叼走了。第二个丈夫也死了。祥林嫂再一次回到鲁四老爷家,越来越多的“看客”出现了,看客虽是带着国民劣根性的冷漠使祥林嫂的处境愈加艰难,但真正使祥林嫂内心坍塌的是“慈善女人”柳妈。柳妈说:“我问你:你那时后来怎么竟依了?”“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这个大罪名就是“没有为贞洁而死”,它瞬间点醒了祥林嫂,她恐惧起来。这种大罪名的后果甚至到了阴司都不能摆脱,她仍然是一个不贞洁的鬼。以当下眼光看祥林嫂,何其可笑!祥林嫂和周边的男性、女性竟把女性贞洁演绎到如此自欺欺人的地步。
同样的,马芬芳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来自千百年“贞洁观”的渗透和社会舆论的负面效应?当然小组长对于时代、观念、社会舆论的利用和操纵是根本原因。马芬芳是美的化身,如阿芙洛狄忒女神;她纯洁美好,富有才情。然而“美”,从来不是“苦难的免死金牌”,反而常是“美好易逝”“红颜薄命”的命运阐释。美素来与危险处境、多舛命途挂钩。因为美容易吸引眼球,存在诱惑性,在被欣赏和追逐的同时,也容易被迫害、被利用。马芬芳就是众多被迫害的“美人”中的一个。当然,如果仅仅是小组长王耀武毫无根据的一面之词,掀不起舆论的大风浪。然而这一面之词与根深蒂固的“贞洁观”挂上了钩,舆论的海浪顺势就翻滚起来,开始侵袭无辜的生命。马芬芳对“我”说:“嘴是会杀人的呀。让你天天挂个鞋,你能愿意?”文本虽没有具体描写马芬芳如何在被造谣、被抨击、被侮辱中一步步走向自我惩罚式的生存处境,但透过“王耀武的死都难以平心头之恨”和马芬芳一生的逃离和流放,我们也能掂量出当时她所受的灾难与侮辱有多沉重。当然,马芬芳也“中毒”颇深,对自我形成了反噬。马芬芳的妹妹曾不无惋惜地说:“我姐就是太好面子了。”马芬芳的重面子并非虚荣,而是受“贞洁观”荼毒颇深,莫名其妙的罪推她走向莫名其妙的罚,“一辈子不回去”的誓言是赌气,是自证,更是对自我的惩罚。关键是她何罪之有,却要一辈子受罚?这种荒诞的“罪与罚”的内在逻辑是:当舆论的刀朝向她时,她把自己的刀也朝向自己。没有什么比自我阉割更加痛苦,在自证与无法自证中她备受折磨,只好走向逃离。逃离到一个没有亲人、没人认识的荒原中,在那里她认为或许有重新开始的可能。然而,内心无法和解就永远深受其扰,再加之生存之艰难,她的处境只有更加凄凉。
文本中妹妹为马芬芳推荐一本书,并指明书中的主人公与她有相似的处境命运,这本书正是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河岸》讲述了特殊年代中的一对父子,父亲库文轩本应因烈属身份备受优待,然而一个神秘的烈士遗孤鉴定小组竟将其定为河匪的后代。母亲迅速与父亲划清界限,库文轩与儿子库冬亮自此过上了自我阉割和流放的生活。尤其对于库冬亮而言,母亲在岸上,父亲在船上,分裂和离散充斥在库冬亮成长的精神世界中。“岸”与“河”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河”是流动不定的,象征着自由和接纳;“岸”是坚实不可摧的,象征着权利话语。因莫须有的罪名或者主流话语权被无端操纵,库文轩父子被排除在权利话语之外,不得不漂泊和流放。他们只能以船为家,渐渐失却岸上的一切。加之库文轩对于身份和身体的执念,库冬亮撕裂扭曲的成长环境,这对父子在苦痛中挣扎,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河岸》作为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和解读,影射了那个年代中离散的家庭关系和荒诞的世情人心。《马芬芳》和《河岸》的故事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马芬芳与库文轩父子因犯了“不被认可的罪”而被主流话语所排斥,被迫走向了“流放”。马芬芳走向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栖身于一间简易的棚子;库文轩父子走向漂浮不定的河流,安身于船上。大草原蓝天白云,辽阔飞扬,是诗意的生存空间;河流神秘、洁净而有力量,同样弥散着浓浓诗意。但诗意的背后是贫瘠的生活、艰难的生存环境、孤独漂泊的心灵。对于主流话语权的掌握者而言,这是他们这些“罪人”的流放地,是他们接受惩罚和自我赎罪的空间;对于马芬芳和库文轩父子而言,这样的生存空间意味着逃离与赎罪,也意味着接纳和自由。
同为对主流话语空间的逃离,库文轩父子有着更为复杂的缘由和心境,内中所涵盖的身份认同、血脉确认、家庭关系、心灵成长和社会权利结构命题有着多元的探索空间。而短篇小说中的马芬芳是单纯逃离被排斥、被侮辱环境的女性,她想证明自身的清白,追求一方接纳自己和能够自洽的天地。文学中有太多的“女性逃离”:娜拉女性觉醒式的逃离,《伤逝》中子君为爱对家庭的逃离,艾丽丝·门罗小说中女性对家庭、丈夫、自我心灵的逃离等,这些逃离大都因无法实现女性精神、物质的独立不得不悻悻而归。而马芬芳的逃离有别样的意义。
马芬芳的命运陷于草原,草原也托起她人格的挺立。其一,马芬芳以捡马粪为生,马粪为马芬芳赢得了活下去的尊严。用马粪换钱,马芬芳得以在大草原上生存下来,她捡着马粪,在岁月侵袭和环境盘剥下依然拥有光滑的脸蛋、有力量的眼睛、被文化熏陶过的卓然气质。反观她的妹妹皱纹横生,干瘪瘦小;小组长王耀武患肛门癌,整个肛门都切了,成天吊着屎袋子,最后也死了。其二,马粪可以滋养万物,也滋养了马芬芳。马粪作为臭味浓烈的排泄物,为人所厌弃。但它是土壤的养分,马芬芳说“用它养花,劲大得很。”它是懂马芬芳的,它吸收了马芬芳的泪水,转而温暖她的心灵。正是马粪,安放了马芬芳无处安放的灵魂。其三,乌拉斯台空中草原隔绝了人世,也隔绝了悲伤。乌拉斯台空中草原海拔很高,离天空很近,“四面八方高低起伏,让你有种不在人世间的超脱和虚幻”。正是这样一个远离人世的地方,虽孤独凄清,却让众人那“会杀人的嘴”消失了声音,将那些劈向她的乱刀挡在草原之外。马芬芳才可以遗世而独立,“突兀而自然”地活成一处风景,散发迷人的芬芳,“好像跳出了时间的轮回”一样。
“我”也是短暂逃离城市、追寻自然的年轻女性,正是这次“逃离”,我遇上了马芬芳。马芬芳和“我”的联结就如“我”和“洪七公串串香”的联结,是无限接近又无限渐远的。换言之,“我”和马芬芳是互为镜像的。“我”是一个租住在破败的机械城单间里的落魄女孩,中文系毕业却在广告公司做文员,生存的捉襟见肘,内心的自我阉割,“我”如一方贫瘠的土壤,无法培育文学的理想花朵。如马芬芳一样,在现实的挤对和压迫下,我囚禁了自己的心灵,任它一天天荒芜下去。“我”去乌拉斯台空中草原旅游,也是对自由天地向往的意愿所致。正是在这里,“我”得以邂逅马芬芳。下山时,马芬芳送了“我”一小袋马粪,让我养花。“我”非常珍视,感觉到“这是一个女人沉甸甸的一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土壤,仿佛我是年轻时的马芬芳,已经提前预知了自己未来几十年和马粪相伴的命运”。与“马粪”相伴是“我”和马芬芳共同的命运,“我俩”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相遇的两个同病相连的女人,“我们”都被社会无形的压力挤对到一个逼仄的角落,在那里“我们”的心灵不再对外界开放,“我们”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然而,在内心里依然有那么一块地方,是“我们”誓死捍卫的,那就是“生而为人的尊严”。
正因如此,马芬芳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她的命运在“我”面前预演,“我”在她身上找到惺惺相惜的感觉之时,也嗅到了文学的气息。她成为“我”小说《南山芬芳》的主人公,她的故事为“我”赢得了文学奖项。借助于此,“我”进入了文学圈,受邀参加了几次讲座,有幸碰上了灵魂高度相通的几位笔友。最重要的是马芬芳身上遗世而独立、勇敢而坚贞的人格品质给予了“我”摆脱现实困境的力量,“我”触摸到生命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被理想照耀的前行之路。无论马芬芳是“我”的一个梦,还是“我”在乌拉斯台空中草原的一次邂逅,她都如一束光,照亮了“我”孤独贫瘠的心。
小说描绘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他者”,与我们生命相连、情感相通的人儿,经由他们的人生故事和情感力量,我们得以成长。他们在苦难中奋力挣扎而开出的花就如马粪,跨越时空界限,滋养着我们贫瘠的心灵。
【作者简介】李沛芳,女,河南安阳人,文学硕士。曾在《文艺争鸣》《百家评论》《长江丛刊》等发表文章。现供职于湖北省文联。
责任编辑梁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