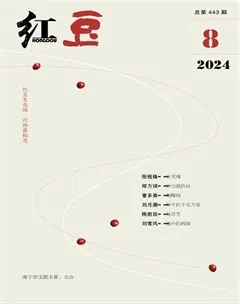蝶变
2024-09-18唐忆若
一天,我们到猫儿岩露营。那里面朝江水,山体岩石如同被刀斧劈开一般,笔直地插入百余米之下的江水中。据说站在江对岸,或者泛舟江水上,远远看这块岩石,它就像猫耳朵一般尖尖耸立。到了目的地,搭好天幕和帐篷之后,天边出现了奇特的彩云,它们排列整齐细密,好像鱼的细鳞,也像涟漪,其颜色也很奇异,色彩偏桃红,虽然已经是夕阳西下,却依然鲜艳透亮,十分好看。
半夜的雷声和风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急促的雨点打在帐篷上。狂风夹杂着暴雨恣意一夜,帐篷外那点儿可怜的篝火早已被浇灭,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闪电不断地划过黑漆漆的夜空。清晨时分我走出帐篷,外面虽是一地狼藉,但天地间却变得更加纯粹透亮,空气中还有一丝清新的泥土气息。我走到悬崖边,望着江面上厚厚的云雾,原本该一览无余的江水、对岸村庄里的房舍、村庄外的盘山公路,以及更远处的鸭池河大桥,都被这层厚厚的云雾所遮蔽。毫不夸张地说,我好像走进了一团潮湿的棉花糖中。忽然吹来了一阵风,对岸那个小山村也俏皮地钻出半个头,在白雾的映衬下若隐若现,犹如仙境,天哪,怎么这么美?
两个月之后,因为要创作一部电视剧,我来到了黔西市的化屋村调研。进村之后,我总是觉得这里莫名熟悉,我把这个疑惑告诉村里的艾星,他笑了起来,说:“那你和我们村有缘。”走到村里的民族大联欢广场上时,我忽然反应过来了,拿出手机打开之前露营那一次拍的照片给他看,我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他们村。艾星瞟了一眼之后点点头说就是他们村。他手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头,说:“你应该是在那里拍的这些照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远远的一座尖尖的像猫耳朵一般的山头矗立在江边的摩崖顶端。
“化屋”这个词来自苗语音译,意为“悬崖下的村寨”。这个悬崖下的村寨有着雄奇险峻的自然景观,风光旖旎,民族风情浓郁,清朝便已建寨,现在村里仍然居住着苗、彝、汉三个民族的村民。
在二〇〇八年以前,化屋村不通水电,不通公路,也没有信号,它就是落后的、无人问津的小山村。
那时出村的路只有一条被称为“手扒岩”或者“毛狗路”的悬崖小道。从这条路去到最近的一个镇上,得走上好几个小时。而村民组和村民组之间、这一户和那一户之间,虽然彼此都看得见,甚至大声说几句话都听得到,但如果想面对面相见,也得走上好半天弯弯曲曲的山路。
“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保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娱乐基本没有。”这些话用在化屋村上可以说是相当贴切的。当时,村里人的主要收入只有三个渠道:种植养殖业,在东风湖水库中捕捞水产品进行贩卖,外出打工。
这里地处乌蒙山区的腹地,高原山地占到了九成以上,且多喀斯特地貌。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农产品,即便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其收成也仅仅能解决温饱问题。随着长江禁渔令逐渐完善,捕捞水产品这条路也越来越艰难。村民们只剩下外出打工这条路了。
在二〇〇八年之前,化屋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八百元。贫穷、落后,自然就会想着发展,但如何发展,该从哪一步发展,又能发展到哪一步,这些对于化屋村来说,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有了问题自然就要尽快妥善地解决,为此,化屋村的村“两委”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专项工作组连同驻村工作队一起,多次分组入户,召集相关产业的村民,给渔民讲政策、讲利弊、讲发展。经过工作组频繁、不断、多次上门宣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村民慢慢理解、接受了。有些工作,说起来也就是一两句话,但真正办成可能是一两个月,甚至是漫长的一两年。就拿改造民宿这件事来说,这项工作中化屋村的村干部的辛苦付出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化屋村中百分之九十八的村民都是苗族同胞,他们世代都过着自给自足、缓慢闲适的生活。累了在山坡上打个盹,饿了去摘点野果子吃,热了跳进江水中痛快地洗个澡。运气好捕获到了野味,就做几道美食,邀请三两朋友,喝点儿自家酿的米酒,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摇摇晃晃唱着山歌回家……
村民们对将自家的老宅改造成民宿以发展旅游业有明显的抵触情绪。许多村民对老宅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担心民宿改造会破坏老宅的原貌,一些村民对民宿经营的前景持怀疑态度。通过一系列有理有据、细致入微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参与到民宿改造和旅游业发展中。到二〇二三年底,化屋村开办了四十余家农家乐、二十一家民宿,村民们纷纷当上了老板。
时任村委会主任的杨龙说,以前邻村的人都轻蔑地调侃化屋村为“火烧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因为以前的村里几乎都是茅草房,连土墙房都很少见,家家户户杂乱无章、见缝插针地紧挨着,形成了一个无序的、臃肿的村落,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化屋村的第一次搬迁是在一九九三年。当年东风水电站竣工之后,江水水位上涨,化屋村大部分人只好搬迁到了黔西周边进行安置,但也有另外一部分村民不舍故土,没有搬迁,被后靠安置,杨龙家也属于后靠安置这一部分。虽然村落是暂时搬迁了,村容村貌整体比以前也有所改善,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杨龙说了一件事,他在读初中的时候,一个关系较好的同学来找他玩,这个同学在他家的门外叫了他好几声,但杨龙屏息静气,始终不敢应答,同学又叫了几声之后,悻悻离去。之所以不敢应答,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正好是午饭时间,而他的手上就捧着一碗糙米饭。这碗夹着稻壳的米饭,仅仅加了些粗盐,再倒上一些水搅拌均匀就吃了,甚至寒酸得连辣椒面都没有。正值青春期的他听见同学的叫喊声后,出于羞耻,他的第一反应是躲起来,他害怕同学看见他手上的那碗米饭,害怕同学看见那碗饭之后讥笑他以及他的家庭。
苦日子杨龙过了很多年,到了二〇〇五年,杨龙如愿以偿考入了一所音乐院校,父母东拼西凑攒够了学费,最终他才得以踏上前往武汉求学的道路。因为家庭穷困窘迫,放暑假杨龙并没有回家,他留在城里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但是意外发生了,在打工的时候他不慎弄断了自己的手指,为了治病他只好遗憾辍学。这一变故,不仅影响了他的学业,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那一年的九月,他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在外打工几年后,化屋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家的公路早已修通,很多人开始在码头做生意,在外打工的他也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二〇一一年的年底,杨龙回到了村里。后来,杨龙成功当选化屋村村委会主任。二〇一九年,因为身体,他辞去了村委会的工作。但杨龙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业之路,现在他在村里拥有两栋民宿,年收入不低于四十万元。
如果说杨龙代表的是村里曾经走出去又选择回来的那一部分人,那么化屋村歌舞队成员杨长坤的这半辈子,则可以说是一直待在村里的那一部分人的缩影。十九岁的杨长坤因家庭条件困难,无法继续念书,只好选择辍学回家务农,以减轻家庭负担。回家后,亲朋好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两人认识没多久便结婚了。说起结婚这事,杨长坤还非常感慨,他分家时家里只有三百斤玉米,他分得了七十斤。分家后的第一个夜晚,杨长坤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他说:“当时我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为了生活下去,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三年,他在村里种植小黄姜,然后拿到黔西县(现为黔西市)菜市场销售,靠买卖蔬菜维持生计。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六年,他在东风湖中捕捞鱼虾,然后拿到农贸市场进行售卖。二〇〇六年,当地政府对化屋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补助了他一万元。有了这笔钱,他开始修缮自己的房子。一番修修补补之后,他和他的家人有了一个避风港。二〇〇七年二月,化屋村组织了歌舞队,杨长坤的歌舞才艺这时候有了舞台和用武之地,歌舞队的表演成了他的主业。杨长坤说:“我嘴巴笨,也不晓得该说些什么,但是说心里话,正因为有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村才能发展起旅游业,才能组建起歌舞队,我才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也才能成功地培养了四个孩子。”
除了杨龙、杨长坤,还有在村里开了苗绣蜡染公司的尤华忠、杨文丽夫妻,他们一起注册了游船旅游公司。还有年收入不低于五十万的尤荣学,以及在村里教授歌舞的何兰……他们的成绩,再次印证了这句话: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带领大家奋斗的是村支书许蕾。许蕾在新仁乡任党委副书记,她请缨担任化屋村的党支部书记。她是党的二十大代表。二〇二一年二月三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化屋村视察工作,她向总书记汇报了化屋村的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她深知,守好绿水青山并高效转化,辅之以乡村旅游,才是化屋村发展的根本。因此,她坚决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带领化屋村群众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许蕾在化屋村工作期间,主导组建了歌舞队、导游队,开办了长桌宴。村民们没有发展资金,她便到处奔走,帮助农户们向银行申请贷款;村民们服务水平不够,她便请来了新东方厨师培训学校和酒店管理人员给村民们进行培训……二〇二二年十月,作为基层代表参加党的二十大时,她说:“我把老百姓当亲人,把老百姓的事当家事,将会一如既往地把乡村产业发展好、生态环境保护好、民族文化传承好、社会治理效能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好。”
通过努力,二〇二一年化屋村累计接待游客超七十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三亿多元,化屋村还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荣誉,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文化旅游村。
我想,我以后不再在河对岸露营,而是来到村里,好好地住上一些日子。
【作者简介】唐忆若,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担任电视剧《花繁叶茂》《沸腾的群山》第二编剧、三十六集电视剧《星火云雾街》原编剧、电影《云上南山》编剧等。《星火云雾街》获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花繁叶茂》获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责任编辑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