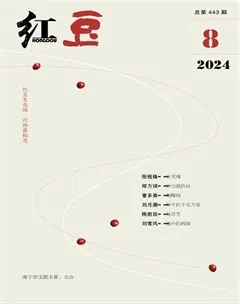作为道场的厨房
2024-09-18钱红莉
小麦覆陇黄
童年的味蕾不仅拥有着顽强记忆,而且一定充满着某种神性。每年小满以后,我总是渴望能吃到家乡的小麦粑粑。
小满过后,天一直晴朗,十天左右小麦就成熟了。某天起个大早,夜露未消,我跟我妈来到麦地,花一上午时间,将分散于各处的五六分地的麦子全部割下,挑到打麦场,脱粒,暴晒。记得我妈常捻起一粒麦子,置于上下牙间,嗑瓜子一样,便可判断麦粒的干湿度。
挑一担干透的麦子到村口碾房碾粉,意味着我们的味蕾即将享用到额外犒赏——小麦粑粑。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小麦粑粑是能吃到的唯一美味。和好面,稍微醒醒。铁锅烧热,倒入菜油,挖一坨湿面放进锅中用锅铲抹均。薄薄一层洁白的面一忽儿变身为深色,沿着锅边铲起,迅速翻身,两面均烤至金黄,起锅前撒薄薄一层白砂糖卷起。入嘴香、甜、烫,别有一番韧劲。仿佛是一种仪式,每家的第一顿新面必定是摊几张小麦粑粑。
小河边的瓠子,田埂边的南瓜,也跟着新麦一起成熟,可以吃了。瓠子可搭配新麦一起做面汤。清水和面,揪成一个个剂子。木桌擦洗干净,撒一层面粉,以酒瓶擀面,擀至刀削面那样的厚度,用刀切割成细长条,撒一把干粉,以防粘连。瓠子切丝,菜油炝炒,加水,大火顶开,面条下锅;再中火顶开,撒盐,起锅。小孩子可以连吃两三碗,连碗底汤也要一饮而尽。
除瓠子面汤,晚餐我们还吃南瓜疙瘩汤。如此吃法,大抵算急就章。妈妈做了一天农活儿,身心俱疲,随便挖适量小麦面粉,放在小盆中用清水搅得尽量黏稠一些。南瓜削皮去瓤,切滚刀块,猛火断生加水烧开后,敞开手指自盆中捞起一坨湿面轻轻攥紧。大小适中的疙瘩鱼贯而出,迅速于滚汤中成形,慢慢便都一齐浮上,熄火,调味,便是一顿美餐。疙瘩汤比面汤更有咬劲,尤其喜爱吃留在碗底的稀溜溜的糊糊。这时的南瓜块早已化为无形,深深浸润于面糊之中,一气喝下,甜糯入骨,不小心沾一滴到手上也要伸出舌头舔干净。这么多年,无论走到哪儿,再也不见我家乡的蒲团南瓜,外表麻癞癞的,颇似蟾蜍的脊背。那种糯甜口感,世间无一可比拟。它沉睡于我的味蕾之上,终生难忘。
家乡处丘陵地带,旱地极少,像我家每年收成一两担麦子已属了不得的事。整个六月是可以敞开吃上十余顿新面的,其余的要放进粮仓里珍藏起来,留待寒冬腊月换挂面吃。
家乡的挂面,齁咸,是孩子们一直抗拒的。记得我妈妈将换回的挂面头子全部揪下,和着剩饭一起煮,顶多加点儿青菜,便是一顿饭。幼小的我,最怕吃挂面头子,鼻涕一样的不说,还那么咸。每次吃到挂面头子汤饭,均恨恨的。长大后,一直不太稀罕挂面,大约小时候被齁怕了。
麦子量少,珍贵得很,连麦麸也不浪费。酷暑时节,许多人家拿它与黄豆一起烀,发酵后联袂做酱。终日蒙一层纱布防蚊虫,一天天烈日下暴晒,慢慢地变得乌金黑亮,仿佛有光。足足晒完伏天至入秋,酱成。我们家乡不称这种佳酿叫“酱”,而叫“顺应”,因此做酱就是“晒顺应”。小时候我一直不明何以如此称呼,根本想不出是这两个富于哲学意味的字。直至有一年,读到桐城女诗人白梦的一篇文章,方恍然有悟,家乡的古人有大慧。称“酱”为“顺应”,不就是顺应时节之意吗?对“晒顺应”,我妈一直不感兴趣,故我们家的那点儿珍贵的麦麸都喂了鸡和猪。别的人家煮鱼,皆以“顺应”来调色增味,唯独我们家煮出的鱼白生生的。祖先的古雅,可见一斑。偌大的中国,除了枞阳、桐城两地,也不知可有别地称“酱”为“顺应”的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全家移居小城,于华侨皮鞋厂工作过一段时日。每逢黄昏下班,我都爱去食堂排队买馒头。漫天白汽中,蒸好的馒头堆在笼屉中高耸入云。当时正值十五六蹿个子的年岁,食欲旺盛,买好馒头的我,一边往家走,一边大口解馋,除了麦香之外,还有一丝甜津津,润物细无声地遍布整个口腔。吃着馒头走在法国梧桐幽深的树荫里,我还会背海子的诗:“吃麦子长大的/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直没有声响……”
许多年没吃到如此可口的馒头了。有一次去山东,在一个小镇食堂宴席上,终于见到了一盘平凡的馒头。每一个馒头都方方正正,自带幽光,似从田间地头赶来。我掰了四分之一,一股久违的麦香冲鼻而来,无须佐菜,适合小口慢慢咀嚼,起先绵软,继而紧实有韧劲,然后是满口的甜。多年后,终于又品味到麦子本源的味道。
六月食瓜
每临酷暑,意味着家里唯一持铲的我,一年中艰辛卓绝的炼狱之旅开始启程,但我从不亏待自己,每一餐都会额外做一道喜爱的菜犒赏自己。
今生尤爱丝瓜。当地的油皮丝瓜,色泽较深,刨了皮,留下几缕绿色经络,从中间纵切一刀,再斜切成薄片。热锅凉油,先爆炒一把毛豆米,激凉水,盖锅中火焖煮三两分钟,盛起备用。净锅再热锅凉油,几粒蒜瓣爆香,丝瓜爆炒三十秒,汇入毛豆米,稍微拨拉几下,记得留一点儿底汤。以宽口白碟装盘,宛如一道艺术珍品——豆米恰似一粒粒璎珞,滴溜溜,绿茵茵。丝瓜若老玉,沁一丝浅碧,幽幽荡漾。入口滑腻,微甜。半碗米饭,吃到后来,连汤带菜浇到饭头上,百食不厌。丝瓜也是颇具佛性的蔬菜,入油锅时,不发出一丝微响,只默默承受,佛一样坚忍,不比别的菜,遇油一刹那,刺啦一声响,惊天动地,几欲跳脚咆哮:“烫死老子了!烫死老子了!!”
一日午餐,刨了两根丝瓜,做一道清汤。略微滴入一点儿花生油,几片老蒜爆香,丝瓜片汇入,炒出水,滚水没过,汆一个鸭蛋花,猛火顶开,汆小半碗肉片。起锅前倒入几滴芝麻油。这样的汤,清热、解毒、降暑,殊为清口。喝下一碗,午休片刻,午后两点高温下骑行,整个人的情绪一派宁静平和,像克莱斯勒用小提琴拉出的《幽默曲》,通透,干净,圣洁。是的,我用了“圣洁”这个词。每次吃完丝瓜,我的灵魂似乎都变得圣洁起来了。
一年四季,内火颇重,酷暑尤烈。苦瓜也是餐桌常客。偶尔兴起,做一道苦瓜酿或苦瓜炒牛肉。这两道菜滋味殊异,辣、苦、鲜,构成其主调,得青草夜露花香的神韵。人爱苦、食苦,生命似亦上了一级台阶。
两广人夏日煲汤,爱放苦瓜,能除邪热,解疲乏,延缓衰老。一次在菜市,遇见一个广东人,她教我做牛肉炒苦瓜。因为孩子不爱吃苦,故这道菜我不曾实践过。岭南还产一种节瓜,长得像冬瓜,形似瓠子,与肉红烧或煲汤。南国之地,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来煲汤的。
冬瓜也是夏日百搭菜,不管是红烧还是做汤,皆可口。把浑身裹满大粒盐的新鲜海带,浸泡、洗净、切成细丝,与老蒜瓣爆炒,直至滑腻腻的丝状物消失,盛起备用。选白皮冬瓜,削皮切成薄片,大火炝炒至断生,加开水适量,汇入海带丝,一齐倒入砂罐内,小火慢炖半小时熄火,加盐调味。喝一口,大海的咸腥气丝丝缕缕地来,冬瓜虽早已化为无形,但魂魄尚在。
一次,嫌这汤太素,画蛇添足地汆一些肉片,丢一把虾仁干进去,滋味立即打了折扣。当真是素有素的妙处,一旦沾了荤腥,原本出尘的气质被悄悄改变,不复是洁净模样。
也是奇怪,这一道平常的海带冬瓜汤,唯酷暑享用,比较惊艳。一入秋冬,再去做它,滋味大不如前。气温的变化,一定会带来味蕾感受的迥异。说到底,不过是要遵循不时不食的规律,当真有着无穷的奥义在里面。有时,着实热得失了胃口,忽然想起冰箱底层的一两块咸肉。热水浸泡,洗净,切成薄片,煸出油脂,冬瓜切块,红烧。味略微调重些,无非为了下饭。一盘咸肉烧冬瓜,粗朴而守拙,可以吃出滋味,也无非图个吃饱。
南瓜也是夏日不可或缺的一味。那种糯如板栗的南瓜,切成大块与绿豆一起煲汤。热得吃不下米饭时,一碗南瓜绿豆汤下肚,既解暑又饱胃,况且不担心发胖,一举两得。清早起来,吹了一宿空调,胃口难开。小米洗净配上老南瓜,小火慢熬,米面上浮一层粥油,略微放凉了喝,吸溜有声……南瓜的甜糯若隐若现,像午睡时的浅梦,半明半昧,一直走不到头,就咸鸭蛋,慢慢品味,又是美餐一顿。
炒鸡胸肉最需要黄瓜丁来加持。热锅凉油,干煸小米辣、青花椒、老蒜瓣,汇入鸡胸肉丁,猛火炝炒至水干,酱油适量调色,再入一把黄瓜丁,炒至断生即可,起锅前,加入适量胡椒粉、孜然粉增香。这道菜要用小勺挖来吃,鸡肉的韧杂糅黄瓜丁的脆,于口腔内崩裂,宛如二重唱,摧枯拉朽的麻辣,山长水远地来,直至吃得一头汗。
合肥有一种老品种黄瓜,半尺长的样子,滚圆多刺,皮白,老时泛黄。嫩时适合生吃,老的适宜煲汤。近年去菜市专门寻找那种越老越好的黄皮瓜。刨皮纵切一刀,掏空籽实,整条丢入汤锅中,小火慢煨。煨猪小排,整锅汤里皆荡漾着瓜的清香气,小排无人问津,喝汤则令口腔清新洁净。食完,原地坐禅,如在深山……
偶尔偷懒,一根黄瓜切成薄片与鸡蛋同炒,无须煎炸烹熘,极短时间内,也能成就一道下饭神器。倘若不讲究,可日日享用黄瓜宴。菜市买回凉皮,调好汁水,加入黄瓜丝、熟豆芽凉拌。刀削面用滚水烫熟,在凉白开中冰镇,拌上黄瓜丝、鸡丝、鸡蛋丝,加大量芝麻酱,老醋放足,又是一顿。
瓜田下过日子,说难也不难。
土豆天使
我一向对土豆缺乏敬意,只觉它淀粉含量高,食之,想必会发胖。直到十余年前,每天早晨,到幼儿园门口送孩子,当我问起口齿不清的孩子晚餐想吃什么时,他嘴里总会蹦出“土豆”两个字,心想天下小孩大抵是土豆天使派来的精灵。
烹饪领域想象力奇缺的我,无非土豆切块,同猪前胛红烧,或者醋熘土豆丝。仅此三两花样而已。最多猪肉改为牛肉,一样切大块红烧。孩子还提建议,诸如炒土豆丝,不能太烂,嚼的时候要听得响的那种。我秒懂,就是不能盖锅盖烀,必须大火烹炒,激点儿凉水,土豆丝介于生熟的中间状态,甚好。
冬天的时候,煲一锅牛筒骨做火锅底汤,涮土豆片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枚半斤重的大土豆切成片,全部进了小孩的胃。有时无心炒菜,将饭煮好,去居所附近菜店拎回一盒烫菜,羊肉片、牛肉片、西蓝花等食尽,剩下的汤,小孩是不许倒掉的。翌日,必然会下鸭血、冬瓜,最不该忘掉的还是土豆片。偶尔吃一顿牛肉火锅,孩子还得有一盘土豆片。看他自沸腾的火锅中夹出一块土豆片,蘸点儿芝麻酱,吃得头也不抬,不小心冒出一个嗝。
一次看纪录片,西北一对养羊的年轻夫妇从早忙到黑。天已黑透时,年轻的妻子自羊圈脱身,风风火火地自地窖中掏出三四枚土豆,飞也似的削皮、清洗,拿过一样魔幻的工具,土豆变成一摞土豆丝。裹上薄芡,一边的油锅已滚,挖一大勺土豆丝丢进去,土豆丝变得金黄。她的三个娃娃吃得鼻涕横流,真过瘾。
吃到最美味的土豆,是在云南。一次采风活动,走了很远的路。途中要去一个地方,过一座木桥,步行一两公里,便可抵达,但实在太累,于是原地静等大家。他们很久还没回来,急得我伫立桥头张望。就在快要失去耐心的那一刻,终于看见一个朋友的身影,隐隐约约间,她手里托了一样东西,近了看清是两个烤土豆。她笑嘻嘻地递与我,说还是热的,吃吧。我剥皮了,一入嘴,便惊呆了,原来世上竟有如此美味的土豆。
喜欢买红皮土豆。菜市有一对夫妇,他们家的蔬菜、鱼肉多自金寨县山中贩来。红皮土豆天然种植,是慢慢享用阳光雨露一点点长大的,质地紧实,每次拿来红烧,其时间远比荷兰土豆长得多,入口满嘴土豆味,喷香。这所谓的“土豆味”也是一种玄学,懂的人自然懂。
海鲜、镬气及其他
平素负责一日三餐采买,时不时逛逛超市,给孩子买一份新鲜三文鱼。孩子就着店家赠送的一小份袋装酱料,吃得欢欣异常。我喜熟食而厌生,于是平底锅一层薄油,三文鱼两面煎至焦香,佐以一点儿山西老陈醋,滋味殊异。
去年,合肥市三文鱼每斤约二百元,今年飙升至二百七十元。一小块背脊,七八十元钱不见了,实在下不了手。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一个生意人,担着两筐豆腐路过穷苦人家门前。穷人家的男人听着窗外的叫卖声,简直发狂,纠结复纠结,末了,在心里呐喊“大不了不过了”,捏几角钱挣扎着出门买一块豆腐吃,是怀着家财散尽的决心。当今太平年代,买一块三文鱼,我也不至于要到家财散尽的地步。但日子是一天天过下来的,如此高昂的物价,实在让人心里打鼓。
某日去超市,适逢三文鱼鱼排被切下,新鲜欲滴的样子,买一盒。嗯,确乎消费降级了。鱼排洗净控水,两面煎至焦黄,放适量黄酒去腥,加七八片姜片提味,加纯净水,一股脑儿倒入砂罐,熬煮。汤汁瞬间乳白,依次加半块豆腐、十余个鱼丸,小火慢炖,这个房间皆飘着来自大海的咸腥之气。
一边做家务,一边幻想着孩子放学回到家,想必食指大动。待孩子回到家,看到三文鱼汤,现实却事与愿违。在我的一番忽悠下,诸如深海鱼汤含有钙镁铁等大量矿物质啊,可以增强记忆力啊……他勉力喝下半盏。剩下大半,煮汤人含泪也要喝下去。
海鱼鲜美,讲究现食。一年秋,在上海的一次宴席上,吃到极新鲜的带鱼。自出海到餐桌大抵不超三个时辰。切成段,放一点儿酱油,姜片亦省略,清蒸上桌。入嘴,鲜香扑鼻。真是大味至简,原来这世上,竟有如此带鱼圣品。我一人默默埋首饕餮般进食,众人言笑晏晏中,我独自钟情这一味海货。东道主热情,频频劝菜,见我无动于衷,到底急了,幽默一句:“钱老师,你怎么不吃皮皮虾呢?是不是嫌它长得丑?”满桌哄堂大笑。趁众人笑之余韵,我将最后一块带鱼夹入碟中。回庐后,有大半年,我家餐桌上不曾有带鱼的身影。吃了新鲜的清蒸带鱼后,觉得唯有出水的清蒸海味,才能令沉睡的味蕾重新复活,冷冻海鱼确乎不值得吃。
有一年在温州吃到一碗海鲜面,同样觉得惊艳。温州人擅养生,开席前服务员适时奉上一小碗海鲜面,将食客的胃垫一垫,避免空腹饮酒。面对那一小碗面,彼时的我颇为犯难,得有多腥呢?试着挑出一根品咂,嚯嗬,何等鲜美!一忽儿碗底见空。那一绺面里,除了海虾还有几种贝类食材,厨师处理得恰到好处,嫩而不柴,鲜而不腥。回到家,根本不敢如此效法,我生活的城市没有大海,且离大海远矣。
一天,晚餐的菜不太够,去饭店要了一份辣椒炒肉。无论辣椒还是肉片,殊为可口,唇齿间隐约飘荡着一股特殊的镬气。所谓镬气,即是锅气。这种锅气,家常炒不出,必须有二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菜品遇热瞬间煮熟,才能保持住那种镬气。我们平常下小酒馆,纵然一盘小炒,也能吃到那种抓人的镬气。饭店煤气灶特殊制成,铁锅置上,于火力猛攻下一忽儿到达二百摄氏度左右,菜品于高温涅槃下进行一系列美拉德反应,故炒出的菜没有不可口的。
日子久了,孩子常常问:“妈妈,你怎么还不出差?”实则是他馋了。cI0xlB0g3/M0Ah6rAsltBvGh5fyxXgtRr4++RiPkD8U=我出差后,他可以肆无忌惮下馆子去,尽情享用着那遍布镬气的菜品。合肥有一家连锁餐饮店,孩子最为钟情他们家的鸡汤。我不服气,买回一只老鸡煲汤,悄悄复制店家流程,一样用矿泉水,唯不放鸡精。孩子总说比不上店家的鲜美。我的鸡汤哪一点比不上了?作为一个有好强之心的人,我不服。某日,去菜市又拎回一只老鸡,一劈为二,一半剁成小块,砂锅里慢慢煨。汤滚,去浮沫,改小火慢炖,加了若干霍山石斛、一整根美国西洋参、一小撮宁夏枸杞。慢炖三小时,香气剧增。这锅汤确乎大补,孩子喝下一整碗,抹一下油嘴,给予点评,说要是放一勺味极鲜就更完美了。
清晨,路过一处蔬菜档口,摊主极力推销他们的瓠子。我说:“瓠子要到割麦时节吃才有瓠子味。”摊主笑笑说:“你再等十几天,露天种植的瓠子就能卖了。”始终记得,小满以后,新麦打下,有瓠子疙瘩汤吃的童年。瓠子喜水,大多植于河边。我的脑子里还深深镌刻着,早稻秧在水田返青时,瓠子上市了。
菜市偶遇本地产洋葱,扁圆,胭脂紫,挑只硕大的,正好配野生鳝鱼爆炒。鳝鱼过热水,去除表皮一层滑腻的白衣子,切寸段备用。剥十余粒老蒜瓣,一小块咸肉切片待用。锅热,放色拉油少许,下咸肉、姜片、老蒜瓣,青花椒一撮,爆香,熘鳝鱼段,黄酒、酱油适量。鱼段收缩后,放入一罐啤酒,中火焖熟。另一口锅热上,猪油炝炒洋葱断生。末了两锅合二为一,将菜混合在一起,起锅前,放一点儿宁化府食醋即可。作为一名老古董,大棚种植的洋葱未曾进过家门,唯一青睐露天种植的本地洋葱。故,今日餐桌上,有了洋葱炒鳝。
顺应四时节序,不时不食。说到底,不过是留恋朴素的本源之味。
【作者简介】钱红莉,女,又名钱红丽,安徽枞阳人。出版有散文随笔集《低眉》《风吹浮世》《诗经别意》《四季书》《植物记》《河山册页》《读画记》《小食谭记》等二十余部。曾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刘勰散文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蓝雅萍
特邀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