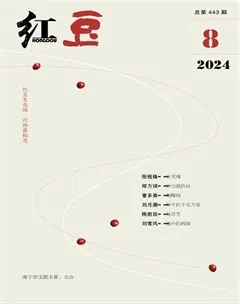一湖枯荣
2024-09-18区晓菲
“一叶知秋”这个词,有一种很悠长的韵味。叶与秋虽是不同物事,但却能由此及彼,意韵相连。有时我想,如果我们把一片片树叶收集起来,放在老旧的书本里,等树叶慢慢干去,叶面也变得平整,那一叶一叶的秋,就成为可以留存的念想,可以抚摸,可以感知,该多么有趣。我们还可以在闲暇时光里,沏一壶茶,温一碗酒,把秋天拿出来,翻一翻,晒一晒,慢慢品尝。这种知秋的历练,这种生活的滋味和情怀,给平凡的日常,平添了很多情趣。就像白居易在那个雪夜,屋里摆满冒着小泡泡的高粱酒,小火炉里炉火正旺,晚归的人们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人儿,怎不叫人心怀温暖、心生向往、心心念念呢?
“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有读者或许认为它是用来说哲理的,而我却很愿意把它当作诗,喜欢句子里扑面而来的季节感,喜欢意境里的秋寒和微凉。自然也喜欢这个叫秋的季节。
南宁太南了,一直到立秋,气温都还让人冒汗,感觉不到节气的变换,也体会不到诗词的意境。“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的氛围,这个时节是不会有的。即便到了腊月,也还是蓝天白云,满城花开。秋对于南宁人来说,是晨起的一粒露珠,深夜的一抹月色,青春鬓角的一丝白发,需要慢慢等,细细看,才能有些许的痕。秋于南宁,就好像青梅竹马的爱情,默默间,笑谈中不经意的时候,就来了。
这段时间,湖边的落叶多了起来。或黄或绿,或薄或厚,或安静或者纷飞,都自有一番景致。我喜欢这些微小的物事,喜欢探找寻常视角之外的发现。我经常到湖边,留意这些每天都变化的叶。有时干脆就站在树下,等风吹,等叶落,等一片叶子凋落的全过程。
这些黄黄绿绿的叶,就像那些树经历过的日子,闪着亮光,带着露珠,悬挂在枝头上,展示不一样的姿态和颜色。时不时风过,它们摇摆一下,欲落还留。或许对一片叶来说,一年即是一世,一世只有一年。经历了冬的孕育、春的抽芽、夏的绚烂,此时已是告别的季节。对于秋叶来说,这一世之爱,一生的华彩,当然是值得留恋的吧。
风还是来了,从湖水上飘来,从季节的深处走来。风是一种自然法则,是物竞天择,冷漠中带点儿残酷。风力逐渐加大,终于,摇摆了很久的叶,那些曾闪亮的日子,凋落了。
叶落的姿态,是最美的舞蹈。一片一片,在风中画出翩翩的曲线,旋转着,飘落着,向着大地的方向;一起一落,旋转跳跃,宛如盛大的舞剧正在眼前。这边像睡美人在冰雪上的奔跑,急促而跌宕;那边像天鹅在湖上的起舞,优雅而舒展;还有的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拥抱,深情而凄美。最后在风声逐渐减弱的节奏中,在季节的巨大舞台上,它们落到地面。谢幕。
我看着这些叶纷纷落下,目睹这些美好生命的告别,也还是有感慨的。生老病死,都是生命必经的阶段。每个生命都值得珍惜,叶如此,人亦然。只是在繁华之后,遗憾之中,临终之际,我们能否如叶一般,如此从容和优美呢?
把掉落的叶捡拾起来,罗列在一起,看这些生命的痕,看每张记录的印记,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经常停下来拍一些叶,或是把不同的叶放在不同的场景中,用最适合的光影衬托它们的美。我总觉得既然它们选择了用最美的姿态告别,那么欣赏这种美,记录这些美,感怀这些美,就是对它们最大的尊重吧。
有一种心形的叶,每一片都是一颗爱心的形状,长得就很讨喜。只是这些叶大部分时间都青葱地生长在高高的树上,和人的距离有点儿远,自然比较生分。到了秋季,一部分叶就褪了颜色,风干了水分,随风落下来,变成落叶。落到地上的叶,开始和人们亲近。生长这种叶的树,叫爱心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榕树。南湖公园钟爱榕树,汇集了国内大部分的榕树品种,是榕树的天堂。这些高高矮矮、或大或小的榕树,有的覆盖如伞,有的盘根错节,有的弯曲如云,都很耐观赏。爱心榕的树干很平常,叶却别具一格。每一片叶子打开来,都像是一颗铺展开的爱心。也因这形状,人们给这榕树起了这个温暖的名字。
爱心叶是很让人喜欢的,就像好看的男女,本身就自带光环。飘落下来的爱心叶,有带着青绿的,也有枯黄的,斑驳参差,残缺不一,但都保持了心的形状。因为这个好看的形,我常常把一大一小两片叶子拼在一起,想象着这就是两心相依,不离不弃。拼在一起的爱心叶,无论怎么摆,都很有意境。
干枯了的爱心,褪去了翠绿,变成金黄色。在自然界的色谱里,金黄是亮色,无论放在哪里,都仿佛有一层光芒,熠熠闪光,遮盖不住。我把它们放在草丛中,绿色的底衬托着金色的叶,就像两只蝴蝶在嬉戏,不仅没有感觉到生命逝去,反而有了相伴双飞的浪漫;我把它们放到湖水里,和蓝天白云融在一起,微风拂来,云彩飘动,心儿也在动,宛如相爱的人儿在湖水里畅游;我把它们放在黑色的地面上,它们流光溢彩,成为路面上最亮的风景,吸引了所有的目光。所有最寻常的物事,有了这颗爱心的加入,就多了光芒和色彩,多了思想的指引和延伸,多了一份对人心痒痒的撩动。这份神奇,宛如自然界的鬼斧神工,或是人心里的梦想和渴望。此时,在这些感受的加持下,小小的一片叶,万般风采,一叶成景。
老廖和阿沁,一个湖南人和一个山西人,是我在南湖跑步时认识的。他们都已过中年,很多年前,他们在南湖那头的大学里相遇、相恋,后来劳燕分飞。不久前,他们相约回来,在这个城市里重新相爱,承诺彼此相知相守,共度余生。
能不能共度余生还不知道,但这对中年恋人确实是南湖公园里的一道风景。他们几乎每天都牵手散步,在湖边,在草地上,在榕树下,经常能看到他们牵手和相依的身影。有一次,夕阳西下时,他们刚好在湖边石凳上,男的在看书,女的枕在他的肩上打瞌睡。阳光从他们依偎的缝隙间穿透过来,万道霞光,勾勒着这对恋人的身影,宛如天堂里的爱情,光彩熠熠,光芒万丈,很是好看。这就是闪闪发光的爱情吗,还是秋天里的童话?这一幅爱情里的画面,如此激越和撩拨人心,如此浪漫而美丽。即便老廖和阿沁都已出走半生,即便他们心已沧桑,但相爱的光芒,依然楚楚动人。
老廖和阿沁,就这样成为我身边的风景,成为这个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他们每天到南湖去散步,沿着湖边,可以一直走到他们的母校。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去母校后边的巷子,去看那些燃烧了几十年的烟火,去吃当年他们最喜欢的牛杂。吃着吃着,我突然想,老廖和阿沁不就是飘落的爱心树叶吗?他们在不同的树干上成长,在各自的风中飘落,偶然碰到一起,却还是被风吹散。幸运的是,他们落地时挨在了一起,有了重逢的喜悦和更多的期许。人生那么多的沉浮,那么多悲喜,能够因为相爱而在一起,能够彼此承诺,能够不离不弃,该多么幸福。
有一种青绿相间的落叶,也让我很喜欢。它和那些在树上风干了水分、自然干枯落下来的叶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枯黄,而是带着很多绿叶的部分。这些叶一般都很完整,甚少残缺。可能落下来的时间不长,叶的一部分还有着生命的原色;而一些比较薄的叶面,则已经被风或者泥土带走了水分,慢慢变黄。在青绿的叶中,能看到颜色的渐变过程。可能是厚薄不一样的缘故,水分流失、生命流逝的时间不一样,在同一片叶上,从翠绿到枯黄之间,色彩像渲染一样,有层次地递进。而在黄绿之中的过渡色,便是我喜欢的青绿了。
我把这种青黄更迭的叶,叫作青绿,纯属个人喜好,并不是专业名称。小时候去看画展,对于单纯的水墨画并没有太多感觉。反而是那些或青或绿的山水画,让我觉得很有意境。青绿是画家眼中的、艺术化的山水。古代的艺术家们,把石青、石绿磨成粉,提纯出适合绘画的颜料,并把颜料的浓淡,作为艺术创作的发挥空间,从而创造出“青绿”这种山水构架和色彩概念。一千多年过去了,青绿的艺术形象,也在我们心中固定下来,成为对世界的一种认知、一份记号。
而对于落叶而言,青绿也不是天生的,是生命迈向死亡的交接点,是生命渐变的产物。生死之间最后呈现的华彩,让生命更美丽,让世界多一份颜色,作为落叶,或许这是最后的使命吧。
叶落以后,大部分枯黄,少部分青绿。追寻青绿的由来,应该是那些原本青葱年少的树叶,因为外力或者意外零落了。落到大地的这些绿叶,没了持续的养分输送,没了树干和树枝的依托,就成了孤魂野鬼,无奈地被风吹,被雨打,被虫子叮咬。慢慢地,翠绿变成了淡绿,淡绿变成了淡黄,淡黄变成了枯黄,最后风干成纸,零落成泥,一切归回自然。这生命的流转,有时候是灿烂,有时候是无奈。
我想,如果叶子也有感知,变成青绿的时候,它的心中一定装满了遗憾吧。少年时鲜衣怒马,豪情满怀却最终壮志未酬,又何尝不是人生的常态?满腔热血上路,满载遗憾归来,又是多少人的历练?如果遗憾可以摆放,我的屋子需要多大才能装下这半生的遗憾?
一九九二年,我从父母家里搬出来,开始人生的历练。十年的记者生涯,漂泊多归家少,是一个遗憾。二〇〇六年,我离开家乡前往南宁,开始创业生涯,也是与家人聚少离多。二〇一〇年,我在南宁装修好房子,想着把父母接过来,好好陪伴,好生伺候,让他们颐养天年。然而就是在这一年,父亲被查出胃癌,几个月后撒手人寰。那一天,我对着空荡荡的房子,痛彻心扉,欲哭无泪。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而更多时候,我们只顾着行走,却忘了告白。等到只此青绿,却也有心无力。这种遗憾和无奈的折磨,即便走得漂亮,即便一路风光,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久前,我把这些青绿的叶,带到父亲的坟头。那一天,我在墓碑前洒满落叶,我对父亲说:“爸,我想你了。”
南湖公园的落叶,更多的一种是伤痕累累的叶。没有爱心树叶讨喜的形,也没有青绿树叶好看的色,大部分落下的叶,都十分普通,简单不起眼。它们落在草丛里,路面上密密麻麻。我捡落叶时常常会忽视它们的存在。我的目光,会被有趣的形状吸引,会被不一样的颜色吸引,甚至会被残损和破败吸引,却很少在它们身上停留。直到有一天,我捡起一片端详,突然发现,如果把这些叶单独来欣赏,其实每一片都各有精彩,都独具风景。
我面对的这片叶子,落在一丛翠绿的灌木上。碧绿的底色衬托着叶片的枯黄,仿佛生命的两端。叶子是平常的榕树叶,叶片很厚,虽然枯黄却没有任何破损。能想象得出,这曾经是一片很骄傲的叶子,它身躯挺拔,体态标准。豆蔻年华的时候,它一定高高挺立在枝丫上,冷傲地面对周遭的一切。即便风过雨来,它也只是摇晃一下,依然昂扬,稳稳地立在枝头。
所有的青春都如此美丽。在季节的变迁中,这片叶子慢慢风干,变轻了变黄了。再后来,它开始摇摆,开始经受不住风和雨的侵袭。终于在一次大风或大雨中,它脱离了树枝,摇晃落下,等待着生命和颜色的慢慢流逝。这张完整的榕树叶,叶骨很干净,都挺直而舒展,让人想起仪仗兵挺立的身躯,威武好看。叶面却是斑驳满布,伤痕累累,给人另一种感受。受过侵袭的叶面部分,比其他部分干枯得快,水分也过早流失,已经是萧瑟的模样。同是落叶,有的金黄,有的淡黄,有的枯黄,一如老人沧桑的脸孔。是的,我们见过很多老人的脸,或皱纹遍布,或阡陌纵横,没了年轻时的新鲜和帅气。人老了脸色也暗淡下来,就像落叶。但即使是落叶,换一个角度欣赏,那种时光沉淀的岁月之美,不也迷人如斯吗?老人脸上的斑驳,又何尝不是他伤痕累累的勋章呢?人老了,胶原蛋白没了,但是那纹理之间、眉目之中、沟壑深处,却装满了岁月重量和生活历练,有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这份美是生命的累积、人生的财富,是弥足珍贵的。
此时,满是伤痕的叶子,静静地躺在灌木上。那些被风吹黄、被雨侵蚀过的疤痕,记录着它曾经经受的苦难。是的,从抽芽成为叶子的第一分钟起,它的命运就被决定了。它是一片叶子,只有站立在枝头上,只有和树成为一体,它才能生机盎然。因此,它避无可避,无可退却。它要面对烈日寒霜的洗礼,承受雷电风雨的打击,接受鸟儿的啄食和虫子的啃咬。日复一日,被伤害的叶面变得斑驳,变薄了的躯体开始风干,留下斑斑点点的伤痕。或许对于叶子来说,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斑驳的叶子,是这里最寻常的风景,随便拿起一片都能看见叶子上的痕。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经历。叶子也好,人也好,只要成长就都有代价。我愿意向这些普通的叶子致敬,向这些伤痕累累的勋章致敬,向生命致敬。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忧国忧民的大情怀,“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则是人生际遇的生动描绘。悲秋,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象。我想之所以会这样,大抵是因为季节到秋,则四季过半、人生半百。融汇了春的萌动、夏之灿烂,秋开始回复沉静,开始内敛和厚积。四季轮回,年年秋风到,岁岁皆不同。“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秋风起,秋叶黄,游客思家,游子思乡,是秋的赋予,是人生历练和人生阶段的必然,也是叶落归根的天道与福报。
于我而言,闲暇时到南湖边走走,看一湖水光天色,看半城繁华入卷,常常心怀感慨和感恩。此时此刻,秋风微凉,落英缤纷,这一湖的枯荣、半世的荣辱,若能彼此交融,相拥入梦,即便夜凉如水,或是雨雪雷电,又有何妨呢?
【作者简介】区晓菲,二十世纪七〇年代生人,文化策划人、导演、词作家,现居南宁。其创作的散文《残》《灵塔之上》《死的船》等散见于国内报刊,执导的影视作品《女人河》《瑶山葬》《谁动了我的土地》等多次获国内大奖,歌曲作品《广西等你来》《幸福嘹嘹啰》《姆洛甲》《蛙舞》等在业内颇具影响。
责任编辑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