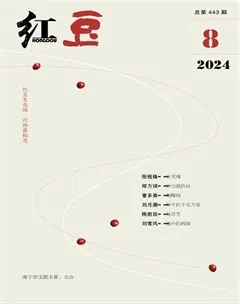种子的千言万语
2024-09-18刘月潮
一
每一朵花都藏着新的生命,有的花朵在半路走散了,在世间寂静地消逝,有的花朵却安稳地度过从开花到果实成熟的生长过程。而花朵的内部也时时在进行着一场生命的运动,花粉和花药就像一对热恋的男女,完成肉体与灵魂的碰撞与融合,实现生命的蜕变,种子渐渐成熟,成为生命新的起源。
种子一生的探求之路,其实是从一朵花开始的。我书房的窗户正对着一棵高大的枇杷树,我熟悉它每一季的生长,十几年来,我看着它一年年开花结果。枇杷在漫长的冬季里打开自己,打开生命通道。空闲时我就坐在窗前看书,累了便抬头望一眼窗外。有蜜蜂嗡嗡飞来,一头扎进枇杷花堆里,开始它们甜蜜的事业。
冬季开花的草木少,蜜蜂给枇杷花带来了希望,也把枇杷花带去远方。有了一朵朵蜜蜂授过粉的花朵,世间就多了一只只枇杷果,也多了一粒粒枇杷的种子。
初冬时节,正值枇杷花开。南方的冬天虽说暖和,但也有短暂的寒风凛冽的时候。天一冷刮起北风,蜜蜂就不来了,我顿时觉得枇杷树上少了什么。
寒风中窗外的风景总是单调得很,但这棵枇杷树却绽放出一树的花朵。漫长的花季,蜜蜂来了又走了,来来回回,这棵枇杷树跟蜜蜂有了深厚情谊,也跟我有了交集。穿过漫长的时光长廊,枇杷夏初成熟,色黄味酸,种子也就成熟了。
枇杷由青转黄时,不时有鸟儿飞来落在树上。枇杷是春夏之交较早成熟的果子,又格外柔软多汁,酸甜可口,鸟儿也跟人一样贪恋人间美食。
枇杷熟了一茬儿,鸟儿飞走一拨,又来了一拨。鸟儿就像枇杷花期的蜜蜂一般来来往往,鸟儿比人更懂得哪些枇杷酸甜可口,哪些味道欠佳,总找味道爽口的枇杷下手。那些被鸟儿啄烂了的枇杷在树上待不住,一口气掉落到地上,摔得到处都是枇杷核。
鸟儿啄食也是植物繁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们让枇杷的种子从树上跌落下来,回归大地的怀抱,种子又生出新的枇杷,如此不断繁衍生息,大自然中生命循环往复,严丝合缝得像是造物主早就设定好了似的。
跌落在地上的枇杷种子,春天来了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小枇杷树。有的被人挖走栽到别的地方;有的被小区清洁工连根拔起,扔在绿化带上干枯死了,树秧子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就失去了生命。
二
植物的生命,大多是由一粒种子开启的。
友人雪霏告诉我,她家族的迁徙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于种子的历史。她是客家人,家谱清楚地记录着这个庞大的家族每一代人的足迹、所经之地、居住之地,以及不断往南迁徙之路。她的祖先在迁徙的途中曾遭到官兵追杀,眼见就要被追上,只好藏进郁郁葱葱的粟地,躲过了一场杀戮。为感激粟的救命之恩,他们从此易姓为粟。山坡上的粟收获后被留作种子,粟的根须扎进易姓为粟的一代代人的生命土壤里,成就了他们一颗颗报恩之心。粟的根须也是他们一生的根须,他们迁到哪儿粟的根须就扎根在哪儿。逢年过节祭祖时,他们祭拜粟也和祭拜祖宗一样虔诚。
在雪霏家的一栋老宅子里,我见到了一千多年前的粟。
雪霏沐浴更衣,净手焚香,然后从柜子里抱出黑色的陶罐,从罐子里掏出一只沾满草木灰的麻布袋子,打开扎好的袋口,在一块绸布上小心地倒出一小把粟。绸布上粟的种子,像一道道闪电,惊醒了千年沉睡的时光,也惊呆了我。这些来自千年前的粟,依旧透着新鲜的光泽,携带着生命蓬勃而又丰盈的气息。
这些千年前的粟,我看不见它们内心深处的褶皱与沧桑,更看不见它们脸颊上一丝一毫苍老的痕迹。作为一粒粒种子,它们身体内依然积蓄着生命的力量,恰似风暴初起的大海,如同花朵含苞待放的一刹那,等待着播进泥土,期盼着一场春雨,催生它们一代又一代繁衍。雪霏说,祖先把从藏身的地里采收的种子晒干后,用麻袋装好放进填满草木灰的陶瓷罐子里,这些种子历经千年而不腐。粟庇护了她逃难的祖先,粟的种子被他们世代保存下来。千百年过去了,粟成为雪霏家族一代代人心中深深埋藏的种子。
这些种子穿越千年的时光,迎来送往了多少代人。在战乱频繁的烽火中,在流离失所的迁徙中,在背井离乡的颠沛中,这些种子被竭尽全力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一个家族的记忆,成为一代代人内心报恩的种子,也成为一代代人活下来的希望与信念。
我眼前粟的种子,它们仿佛是一粒粒生命,还安然地活在人世间。相信有一天,这些种子会走出漆黑的陶罐,被后人播种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让人看到千年前粟的种子繁衍出来的生命力量。
不只粟的种子,雪霏的祖先在迁徙的途中,常用草木灰裹住各种干燥的种子,用布袋或麻袋包裹好混合着草木灰的种子,再放入陶瓷罐子或竹筒里藏起来。一旦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些种子就随时随地派上用场,顺应天道及四时之气,种子虽播在还很贫瘠的土地上,但收获了五谷杂粮、蔬菜瓜果,能勉强糊口。
土地需要一代代耕作的人用时光和血汗来熬,熬够了几代人,土地才会肥沃,播下的种子才会有好的收成。一个地方实在难以糊口,就待不住了,只得又迁往他方。迁徙到哪儿就在哪儿扎根,只要身上带着繁衍生息的种子,到一个地方就有活下来的希望。有了种子就会有家园,有了种子就会有收成,有了种子也就会有未来。
客家人在迁徙的途中用心呵护并珍藏着这些孕育生命的种子,像呵护珍惜自己及族人的生命一般。
雪霏的祖先为了保护陶罐里的种子,怀抱着陶罐,用身体挡住土匪和山贼的棍棒、刀枪,有的甚至为保护种子丢掉了性命。
每一茬儿流传下来的种子都藏着一个悲怆的故事。种子是繁衍生息的种子,也是客家人生命的根。在客家人迁徙的途中,种子与人互相依存,进行一场长途旅行,穿越漫长的时光,经历风吹雨打,历尽世事磨砺,共同繁衍生息。
种子像人一样落脚在不同的地方,适应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一粒粒不同的种子在异乡的土地上播种,被从头至尾地呵护,它们一茬茬艰难地生长,人们一季季地收获。种子满足了人的一日三餐,也滋养着人的身心,抚慰着人的灵魂与精神。
三
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痴迷于种子的生命,很难相信那一粒粒的种子打开生命的方式竟如此简单朴素,又如此神秘莫测。
小时候,二月柳树早早地就发芽,三月开花结果,四月种子熟了果实就裂开来。每一粒种子都生着白色的绒毛,像携带着一个个小降落伞从柳絮上脱落下来,随着风飘散到远处。
一颗小小的种子,一经落到地上,经过一场雨水的浸泡,种子吸收水分后开始涨大、萌发,生出胚根、胚芽,长成了柳树秧子,完成了生命的新生旅程。
每年的六七月,我见惯了柳树种子的这些肢体动作,也见过一粒粒种子生长的千言万语。
每一粒种子的生根发芽都有着自己基本的动作,也有着自己特有的生长语言,以及生命的冲动。大自然的种子大多秉持着这些生命特质,每一粒种子的倔强,每一粒种子的执着,每一粒种子生命的冲动,每一粒种子迸发出的力量,都让我时时惊奇,也让我叹为观止。
事实上,在生活中我对种子的了解并不比别人多,甚至是个种子盲,虽然小时候在乡村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但这些菜园子里的事都是母亲一人在操持着。
春天来了。经过一个寒冬,日渐清闲下来的菜园子空出了大块地方,母亲便早早备了各种蔬菜的种子。一到播种的节令,母亲先用温水浸泡种子,再用纱布包着,晚上放在灶台上暖种。经过一两天,待到湿漉漉的种子涨大后,母亲就把它们埋在菜园子里,让蔬菜依着各自的节令生长,积蓄着生命的力量。
四月八,吃黄瓜。夏至,茄子、辣椒挤破脑袋。
瓜类豆类上了架,茄子、辣椒扦插后,母亲便开始着手给菜园子里的菜选种留种,选种留种贯穿着每种瓜蔬的一生。像黄瓜,母亲选头茬黄瓜中长得粗壮又好看的做上记号,直到种瓜彻底熟透了母亲再把种瓜摘回家,在阴凉处放上几天后再取出种子清除水分,用炉灶里的草木灰拌种子糊到墙上晒干。那时家里还是土砖房,墙壁白得像雪,种子上墙虽有些煞风景,但人间烟火的气息都安放在墙上。墙上依次按节令蹲着黄瓜、菜瓜、番茄之类的种子,凡是能上墙的种子母亲都让它们上墙,让种子安心地待在墙上。
母亲一直小心谨慎地对待选种留种,从来都当作一件大事,留的每一粒种子都经过挑选。每粒种子都是天地自然孕育的,每粒种子的世界都藏着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也贮存着二十四节气和阳光,每粒种子身上都隐藏着众多节令的开关,只要回归泥土的怀抱,每到一个节令都遵循着生长的规律,生命的过程中该做的它就去做,一样也不少。
附近的人家都知道,母亲留的种子好,年年开春后,总有人上门讨种子,回家种到菜园子里,收获了也要留出自己的好种子。母亲对上门讨种子的人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毫不吝啬。母亲留的种子在村里被人到处播种,那些瓜豆蔬菜样样长得生机勃勃,母亲路过时看到一畦畦菜地里都是自己送出去的种子长成的旺盛的生命,特别开心。乡村的种子就是这么在各家各户,年年互相串着门溜达着,你来我往。
那个年代,乡村各家的种子仿佛成了全村人共有的,那些发芽的瓜秧子、豆秧子也都是共有的。赵家地里的茄秧子多,却少了豆秧子,就拿茄秧子跟人换豆秧子。互换种子及菜秧子似乎成了乡村的一种礼尚往来,也成了乡村的人情世故。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自留的种子在乡村却再也不受欢迎了,一夜之间再也没人留种。就像我离开乡村二三十年后,早已在乡村失掉了自己的位置,而那些自留的种子也跟我一样丢失了在菜园子里的身份与位置。
有一年回乡,得知各家都是到种子店买种子,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怎么好好的大家都不留种了?母亲看出我的疑惑,忙说:“现在都嫌留种子麻烦,到种子店买方便得很。”我竟然没好气地说:“买的种子不好。”母亲望着我愣了一下,告诉我选种留种麻烦事太多,自留的种子产量也比不上种子店买的种子,人们索性图个省事,都习惯去店里买种子。
村里一代代传下来的留种的习惯,就这么被村人抛弃了,就这么无声地消失了,就这么悲壮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来这世间许多美好的东西就是这么与我们走散的,湮没在岁月的烟尘里。世事变迁,失去了自留种子的乡村,到处都是那些买来的种子种出的瓜豆蔬菜。它们还容易招惹各种虫害,村人只好一遍遍地喷洒着各种农药。菜园子里的菜吃在嘴里,再也没了先前自留种子种出的菜的味道,人顿时觉得生活的一切都变味了……
四
万物起源于种子。每一粒种子长出的植物都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每一株植物身上都藏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密码。我从小对种子有种特殊的感情,或许在城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也像一粒种子,长成了一株植物应有的样子。一粒种子经历的风雨我都一一经历过,一粒种子成长为植物的路,我也一路走过来了,身上有着一粒种子太多的生长印记。
进城后,离家五百多公里,我一度很瘦弱,像竹竿子般熬着,水土不服。医生说我脾胃虚弱,瘦弱的人大多脾胃不好。脾胃就像大地一样,土贫瘠,提供不了营养,人就犹如一棵怎么也长不好的树。在城里我不知我这棵树该怎么生长,怎么样一天天活下去。中医没给我开药,只告诉我要多吃自留种子种出来的食物,要多吃那些能做种子的东西。
为了治好自己的脾胃虚弱,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城里寻找着那些自留种子种出来的食物,很多时候都一无所获。那些菜贩子对自己卖的菜的来源一无所知,但他们笃定这些菜都是买来的种子种出来的,自留种子一般产量低,没有人再干这样的傻事。但也有有收获的时候,我从城市近郊一个菜农那里寻到了用自家留的种子种出来的瓜豆蔬菜,自然如获至宝地买回来,并约好了下回再去的时间。这世上还有人没有抛弃种子,他们自留种子,用原始而又朴素的耕种方式,种出人间食物应有的味道。
我对那些用农家自留种子种出来的食物迷恋到近乎痴迷的程度。我是从小吃那些自留种种出来的食物长大的,它们也在我身体内留下了一个个关于生命的开关,一个个关于节令的寓言。后来我远离了它们,它们也离我而去了,我却懂得了节令对于生命与万物的重要性。没有季节的枯荣盛衰,没有一年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没有生命的来来回回。现在种子又真实地回到了我的体内,我感受到它们生命的力量。天地万物,种子是最有力量的,那些能成为种子的各种食物,它们浑身充满生命的力量,只要按节令种进地里,它们就能生根、萌芽,长成植物,繁衍生息。
那些自留的种子,或那些种子种出的东西在我的体内转化着,种能生根,根中蓄精,精转为气,气化为神。一粒小小的种子繁衍出更多的种子,生发出更多生命的力量。我仿佛又回到了少时的村庄,仿佛有万千的种子在我的体内一起生发,一粒粒种子迸发着生命的力量,一粒粒种子在大自然中成为一株株植物所走的生机蓬勃的路,种子生发的力量充盈着我身体的每个器官,让我获得更多生命的力量。我脾胃的功能一天天好起来,身子也结实起来,我就像一粒饱满结实的种子,体内蓄满了力量。种子支撑起我身体的未来与远方。
中医朋友还告诉我,古今素有种子第一方——五子衍宗丸,就是著名的补肾良方,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配方中有枸杞、覆盆子、菟丝子、五味子、车前子等五味中药,就是利用这些植物的种子能繁衍生息的功效,来专门治疗男性不育的。除了结籽多的食物有利于人的肾脏,那些形似于人体肾器官的豆类,一般也有补肾益精的功效。它们既是繁衍生息的种子,也是助人繁衍生命疗人疾病的食物和药物。人和大自然的草木一样,一粒种子的生长发育,照见一粒种子生命的精神。
我时常伫立于开花的草木跟前,充满感激地看那些远道而来的蜜蜂蝴蝶,它们的忙碌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大自然中的万物。
站在开花的草木跟前,我跟蜜蜂蝴蝶一样愉悦。有了这些蜜蜂蝴蝶,那些草木的果实如约而至。种子熟了,落地生根,大自然才会繁茂。
在开花结果的大自然面前,种子背负着更多的重任。我一次次聆听种子的声音,种子从远古走来的脚步声,种子生根发芽的声音,种子破土而出的声音……
五
一代代传下来的种子忽然消失了,被用现代科技手段培育出的各种种子取而代之。
在寻找用自留种的种子种植瓜豆蔬菜的途中,我遇见一个年轻人。在他自建的种子库里,他用一种古老的仪式收藏着种子——用草木灰拌着干燥的种子,用陶罐、竹筒之类的器具贮藏着种子。他像从前村庄的老人那样培育着种子,让每一粒种子都散发着古老的生命气息,让一粒粒种子饱含着生命伊始的意义。
他种的菜不喷农药,也不施化肥。他用最原始的耕作方式耕种着菜园子。他请我吃过他种的瓜果蔬菜。我吃到了最自然朴素的味道,尝到了生命原始的味道。
在我眼里,他耕耘着一个童话。他懂得种子的许多知识,以及这些种子有趣的成熟及传播的方式。
在史前大洪水的传说里,诺亚方舟就是种子的家园。对当今种子来说,这个年轻人也是种子的家园。
在他耕种的这片土地上,藏着一粒粒种子的千言万语。每一种植物的种子都有自己在时光里的旅行方式,经历所有的风雨和磨难,并以独特的存在方式,去唤醒人类。
【作者简介】刘月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清明》《四川文学》《长江文艺》《延河》《散文》《散文百家》《红豆》等杂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选刊转载及入选多种选本。出版微篇小说集《五月桑葚熟了》《罗桑到底说了什么》等三部。
责任编辑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