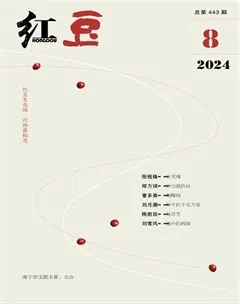这么近,那么远
2024-09-18张清华
“她起床从来阵容浩大/寂静无声/从孩童至今/你看着她/她看着你/人世间最纯洁的家人/不言不语”。在这组称得上浩大的诗作中,首先吸睛的应是《朝霞研究》这一首。读到它,我就放心了,因为我担心力斌就像担心我自己一样,把诗歌写得过于繁复和过载,希望能够透点儿风,让人读了以后不只能够感到有意义,还觉得有意思,不是用观念和思想来压人,而是用直觉与轻逸的东西来触动人,甚至愉悦人。
这首看起来十足简约的诗中,其实容下了很多,但作者却刻意用了最朴素和轻逸的语句,将这朝霞以及朝霞中的人,渲染得无比丰富和深邃,形象和生动。就像莫奈的绘画《日出印象》一样盛大而委婉,斑驳又迷离。
为什么我会首先提及这一首?因为他开篇就让朝霞人格化了,她的升起也变成了“起床”的过程,而且“阵容浩大”,壮丽雍容,充满了仪式感。这个神奇的开头,立刻让“朝霞”获得了双重身份,她可能纯粹是“朝霞”,也可能是家庭的一个成员,是妻子或者女儿——甚至其名字也叫“朝霞”(这我不得而知)。这样所有描写朝霞的文字,立刻复调化了,既是说人,又是说物;且诗中颇为简单的语言,也立刻变得双关化了。一首如此短小的诗,生发出了难以言传的深义。
显然,这才是一首诗真正的妙处所在:言近而意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首教科书式的作品,也不为过。
我知晓力斌写诗,应该很有年头了。但他大概也总希望给人一个“专心致志做编辑”的印象,这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自己写作的心态。不过看周围,很多批评家和编辑不都在写吗?怎么别人可以大大方方大摇大摆,自己就有点儿羞答答呢?
其实没必要,可以放松点儿,只要不那么“抒情”就好。
这个话题如稍严肃些,可以转换为“身份与写作的关系”。教师也好,编辑也罢,写作身份是不太一样的,藏不住,比较担心别人挑剔,容不得任性,也没有单纯的诗人那么神秘。总之,力斌写成这样的风格,我认为是很自然的。
那是什么风格呢?我自问,又有点儿哑然,也还没有完全想得明白。
但能够说出个一二。比如他的写作灵感或者素材的来源是生活化的,非常生活化。显然力斌最高明的一点也正在于此,从身边的日常中,找到不经意间发生的事,又总能够从中找出言近意远的道理——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浅至深,由谐到庄。
这就有了味道。细细琢磨,虽然下笔轻,但内涵却绝不潦草,这也证实了我原先的一个看法,即力斌是真正迷恋“知识分子精神”的诗人。
其实这已涉及我想说的第二点,也就是写作的“知性追求”。只是力斌没有端着“知识分子写作”的架子,拉高调门去处理,而是尽量以庸常甚或卑微的角色,去体味如今“智识者”的精神状况与生存处境;以“冷自嘲”的方式,以满身的烟火气,去面对日益裂变的大环境,以此来标立某些值得持守的东西。像《啃玉米棒,读〈管锥编〉》《爱才记》《拜望谢冕先生》《唯诗歌解忧》诸篇,都是如此。
一边“啃玉米棒”,一边读《管锥编》,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设定,有点像当年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中的主人公章永璘。他身为劳改犯,也能够一边啃着石头般的“稗子面馍馍”,一边读《资本论》,只要有一口饭,就在思考属于全人类的问题。在力斌这里,这显然是一个刻意的降解版,其实已经全然蜕化成了学术问题,没有了解放全人类的雄心,但毕竟也还算是个读书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现场:“而现在,你已彻底败在/琐事的战场上/意思不大,但必须完成/总算完事了,坐在晚霞秋风/包裹的转椅上诵读,方明白/通往神灵的高速路全在佳句里”。(《啃玉米棒,读〈管锥编〉》)
沉湎读书本身,其实已算是一件奢侈之事。细思之,难道没有百感交集吗?
最后,在有限的篇幅中我还要再说一下语言。力斌的语言是值得品咂玩味的,虽然刻意朴素,在比喻、隐喻、修辞方面几乎是“零添加”,但我注意到他的自我压制背后,其实是在寻找一种融叙事与分析为一体的调性,更注重叙述境况,典型的事件,可能生发意义但又刻意压低了敏感性的话题。然后在一种冷静的叙述和故意减载的意义分析中,完成意义的呈现。
这是十足睿智的写法。或许我可以称之为口语化的知识分子写作?如果是,那么便意味着力斌以他自己的方式,实现了“盘峰论争”以来一个有意思的弥合——历史性的弥合,即知识分子写作也可以使用完全意义上的口语。如果这样看,力斌写作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便具备了某种文化意义。
还有一点,是俗语、网络用语、以及卮言的大量引入。做到这点非常不易,需要敏感而强大的同化和嵌入能力。像在《生活的底部》一首中,他就密集地嵌入了“电话”“手机”“线上”“T台”“智能机器”“资本”等这些完全属于技术时代的、祛魅化的词语。如果缺少相应的语义场,它们就会像一个个硬块一样,使这首诗变得粗陋和奇怪,但奇怪的是,它们被牢牢地、合适地安放和溶解在了语言中。不要小看这种能力,语言的不断生长和改造,其当代性属性与标志的获得,相信都与此有关。
这样说来,师力斌不正是一直试图讲“当地话”“当代话”的诗人,也正行走在找寻“穿透精确的声响”的路上吗?
“这么近,那么远”,一首歌似乎有这样一个名字。读他的诗,不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如此平易,靠近尘世,靠近当下,靠近时代的话题,但又那么难以穷尽,那样言近意远,远得像天上的星星。
【作者简介】张清华,一九六三年生。文学博士,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有《猜测上帝的诗学》等著作十余部。一九八四年始发表诗作,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诗刊》《人民文学》《十月》《作家》《钟山》等刊,曾获《十月》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一〇年度批评家奖等。
责任编辑梁乐欣
特邀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