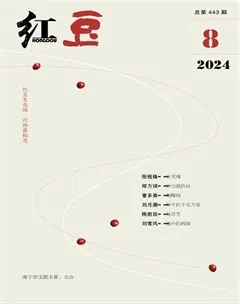晋国历史的诗意书写
2024-09-18高海平
张锐锋先生潜心十年创作的二百多万字的散文巨著《古灵魂》,终于杀青,应该说,这是一件盛事。阅读如此皇皇巨著,第一感觉是震撼,第二感觉依然是震撼。能把六百五十多年的晋国史,以散文的形式予以再现,显示了作家的气魄和胆识。这也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就像在刀锋上的舞蹈,惊险、刺激而又惊喜不断。
阅读中,感觉就像当年乘坐绿皮火车去完成一次长途旅行一样,舒缓,放松,坦然。窗外的风景因时而变,物换景移,无数琳琅满目的景色万花筒一般在眼前忽隐忽现、忽近忽远、若即若离,使得漫长的旅行始终不感觉累,相反充满了无穷的期待。读张锐锋的《古灵魂》,我想起了当初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的著作没有想象中的好读,总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无奈只好读一读,放一放,实在太长了,而且绵密而又细致的描写有时候会让人恹恹欲睡。
读张锐锋的《古灵魂》却不同,他把二百多万字的篇幅分成五百九十七卷,每一卷都有一个核心人物像导游一样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述其观点、感受和认知。这些人物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比如国君、使臣、农夫,他们像一个个智者,对你谈天说地,纵论天下。当然,国君有国君的胸怀和格局,使臣有使臣的认识和见解,农夫有农夫对生存的倾诉。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世事有着不同的评价。由于身份的不同,我们能从他们的观点中窥见每个人对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判断。
还有另一类人物,比如历史学家、盗墓者,这些人的身份很明确,但是生存的年代是模糊的,不是晋国时代的人这一点是明确的。也许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和追溯晋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林林总总。
历史学家的眼光兼具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而盗墓者追求的是利益,即从地下盗出的泛着幽光的金银玉器等价值连城的文物。作品从不同的视角以分镜头的阐释方式进行书写,读起来并不显得压抑和疲惫,相反因为结构的巧妙设置,有一种坐疯狂过山车的感觉,不断地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隧道来回穿越。忽而一头扎进历史的深处,呼吸古人的气息,洞见晋国的人间烟火、世事风云;忽而又被盗墓者和历史学家所引领,站在他者的角度审视出土的瓦当或者陶器,从神秘莫测的纹饰推测远去时空的人文价值。
作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只是来自故事本身,因为散文并不注重故事性,而是来自作者对事物的分析和说理,这种分析和说理能帮你把思维和想象无限扩大。这种思辨性极强的文字自始至终贯穿作品其中,读者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对晋国历史、政治、地理、天文、自然,甚至堪舆等知识的丰厚储备量,以及那种丰沛的、源源不断的元气在蓬勃奔涌。
晋国史一直是历代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因为其丰富复杂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激起了作家们的创作激情。有些作家从晋国的某个片段、某些人物切入,采用小说或者影视的形式进行再现和塑造,比如对介子推这位人物的状写、对赵氏孤儿故事中程婴的塑造、对晋文公的刻画等都有不少佳作问世。但是敢于全景式、多角度,而且用散文的形式进行创作的,张锐锋当属第一人。
张锐锋一向以创作长篇散文独步当今文坛。想当年,他创作的《马车的影子》《皱纹》《祖先的深度》等作品,以其巨大的体量和独特的思维,以及别出心裁的表现形式引起文坛的高度关注,他也成为当代新散文的代表人物之一。
近年来,张锐锋甘于寂寞,一头扎入历史深处进行钩沉,遍览《史记》和各种史料,在晋国六百五十多年漫漫的长河里打捞属于自己的文学元素。如今终于完成夙愿,奉献出如此浩瀚之作,这是一个优秀作家应该有的样子。张锐锋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断创造奇迹的作家。十年沉寂是为了今朝更猛烈的爆发,《古灵魂》就是实证。
如果把六百五十多年的晋国历史比喻为一片茫茫高原和山川,那么《古灵魂》就像一条穿越这片莽原的大河。不管山有多高,林有多深,大地有多么辽阔,这条河总是沿着自己的路径流动着。遇到峡谷它会湍急奔流,形成飞瀑,发出轰鸣;遇到弯道它会迂回缠绕;遇到平坦地域,自然静水流深,不疾不徐。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拥有巨大的辐射能力,就像一台尖端的扫描仪,洞穿整个流经之地的各个领域,并发现其中的奥秘,从而给予独到的精彩的解密和分析。
《古灵魂》以人物自述的方式进行文本架构。天子、国君、大臣、史官、仆人、孩子、农夫、妃子、掘墓人、历史学家、研究者、商人……各色人等交替登场。
作品开篇第一卷先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切入。孩子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陶片,由这块陶片徐徐打开了晋国历史之门。其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孩子的眼光是干净的、纯粹的,不带任何杂质,孩子一般具有第六感觉,预示着这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开始。第二卷以一个农夫的视角演进,农夫在默默耕耘土地的过程中,犁铧翻出了埋在土里的陶片。陶片这个特殊的意象第二次进入读者的视野。第三卷写了一个老人,他每天坐在大树下与树木聊天谈心,孩子发现陶片的事他知道,农夫耕耘时犁铧翻出陶片的事他也知道。孩子和农夫发现陶片的事对他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现象。老人在陶片面前能够坦然面对和平常待之,因为他知道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而且注定是有故事的土地。第四卷写了盗墓者,这已经不是孩子、农夫和老人那样的旁观者了,而是直接对脚下土地开始介入。盗墓者掌握了这片土地的非凡价值,觊觎之心已经肆无忌惮地对亡灵和文物实施非法攫取和破坏。第五卷国君出现了,他不是长袖善舞地出现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而是以亡灵的身份躺在墓地狂想时,被一把洛阳铲给铲了出来。第六卷写的是历史学家,至此,强大的文化信息量已经充斥着读者的心灵。孩子、农夫、老人、盗墓者、国君和历史学家六个不同类型的人物的次第登场,他们像画外音一样出现,为整部作品的陈述进行足够的铺排和渲染。第七卷写邑姜,一场与周武王惊心动魄的肉体狂欢,孕育了一个国君唐叔虞,以及一个划时代的古唐国的来临。
作者写到了晋国的起源,讲了周天子剪桐封弟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史书上有不同的阐释。《史记》中所写的叔虞封唐完全是一场游戏的结果,其他史书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作者借历史学家之口,说历史不应该是平凡的,它应该是一场具有传奇性的戏剧,也应瞬息万变、悬念重重,然后有突然峰回路转的童话般的奇迹。否则,一部毫无趣味的历史,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作者又借研究者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桐”和“唐”在早期的文字中可能是同一个字。至少它们十分相似,相似的字经常互换使用,也不会影响同时代人的识别。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留下了一个个谜团,因为失去了昔日的语境,而且今天的思维方式也和从前有了巨大的差异。如果猜想成立,那就可以将这一美好的封国故事重新讲述,转化为另一个一般的、平庸的历史叙事:这四个字应该为——剪唐封弟。也就是说,周王室剪除了唐国的叛乱者,然后将这一古国封给了唐叔虞。可能这一推论更为符合逻辑,却减少了神奇感和童话感,它的趣味也失去了。作家同时又引申到,如果“唐”和“桐”是同一个字,是否说明当时的唐国到处都有高大的桐树呢?如果把一个古国和桐树联系在一起,岂不是重新还原了它神奇的一面?一个谜如果永远不能猜透,又岂不是更为神奇?神奇乃是我们灵魂中所自有的,因而它才在世界上处处闪烁。
从作者对剪桐封弟故事的反复解读能够看出,作家写作古晋国并不是简单地复述故事,而是有着独到的思考。历史终究是个谜,怎样破解这个谜,需要站在更高更大的平台,利用自己丰赡的知识、卓越的智慧和超强的想象力,合理而又颇有意趣地洞穿历史的重重迷雾直抵事实的本真。《古灵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来进行创作的。
《古灵魂》五百九十七卷,每一卷围绕着一个人来写。这些人物有具象的也有抽象的,即使有重复的,也意味着有上百个人物被作者着力描写和刻画。这些人物从锦衣玉食的天子、国君、大臣,到底层引车卖浆者那样的普通百姓,各色人等,在作家笔下粉墨登场,而且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场,都能游刃有余地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这就对作家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好在张锐锋是个写鸿篇巨制的高手,他有驾驭大体量、大题材作品的超强能力,就像古人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魄力。这种魄力或者能力,来自对相关知识的结构性运用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他的语言天赋赋予他天使一般的翅膀,任其在文学的天空里自由翱翔。正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能力,他笔下不管是哪一类人物出场,这些人物除了有和职业有关的识见,还更多地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对事物的认知。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为每一个人物镀上了一层文学的光环,使他们能够闪闪发光,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了神性的东西。比如,写到御戎,御戎欣赏自己战车的马匹时,便出现这样的句子:
在繁华的宫殿,它们沦为了囚徒。局促的马厩难以放下它们的自由,饲马者即使不断给槽中添加青草,它们的胃口也是有限的。浑身的力量不能释放,它们需要在路上找到丢失了的天性,在汗水和劳累中获得快乐,以及不断欣赏山林、花草、石头和自己的蹄声。它们从来不属于憋屈的马厩,而是属于天神给它们的草地和原野,否则,它们的力气、速度、飞扬的气息又有什么用呢?它们的长鬃如果不在风中飘荡,又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写到车匠,车匠自然喜欢木头:
我看着这些木头,有着说不出的欣喜,因为我的心早已经从它们的形状中看出了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与其说车子在我头脑中,不如说它们早已存在于生长着的树木中,我只是动手去掉它们多余的东西,让它们一点点在我的汗水中现形。
类似这样逸兴遄飞的句子俯首可拾,随处可见。
《古灵魂》还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所描写的每个人物不仅仅代表着自己,还代表着某一领域或者学科。周天子眼里不仅仅有晋国,还有别的国家,要胸怀天下,平衡与制衡是一门政治艺术。国君也要具备战略眼光,治内的同时,还要统领三军对邻国的虎视眈眈严防死守,如有时机还要竭力扩张地盘。使臣也不甘寂寞,讨好国君争取上位,还不忘挤对别人,这是为官者应有之义。堪舆大师,在每次征战前的神机妙算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农夫看到的是农事,而农事又牵涉到种子的生长、维护、收获。车匠眼里的这门技艺不可小觑,关涉到车子的舒适和速度。铸铜师的工艺产品,比如鼎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屋匠代表建筑行业,女娲是此领域的鼻祖,为后来的建筑业树立了一个标杆……总之,作品在政治、经济、农业、工业、手工业、科技、文学、天文、地理、自然等领域多有涉猎,就像一幅《清明上河图》。
《古灵魂》对嘉禾的烘托和渲染有其深刻的寓意,是对晋国未来无限的期许和展望,六百五十多年的晋国生存史,其中有一百五十多年的称霸史正是明证。
这部皇皇巨著,彰显了作家丰厚的文化底蕴。文学、历史、天文、地理、玄学等领域的深厚学养,在作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加了作品的厚度。
《古灵魂》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观点,强调天道、仁德思想,无论国君还是人臣都应该谨守规范,恪尽职守,并且要时时刻刻从自身做起,从自身找原因。这些思想也契合了当时的文化思潮。春秋战国时期正值诸子百家思想活跃时期,作者立足这一客观事实,展开自己的思维大胆地进行逻辑推演和哲学思考,符合历史的定位。
《古灵魂》是一部散文巨著,始终坚持散文的艺术风格,就像游走在骨骼中的一把刀,总能恰如其分地避开小说的诱惑而从容不迫地表现出散文的肌理,这必须具备超强的能力。因为晋国历史上太多精彩绝伦的史实用小说艺术手法表现更为恰如其分、美轮美奂。散文家自有与众不同之处,他有时也经不住故事的诱惑,以小说的笔意小试牛刀。比如写晋国和楚国在敖山与鄗山之间的交战,郑国在晋楚之间的撺掇,楚国使者向晋国使出的障眼法,双方几进几出交战,完全具有小说的魅力,让人读后回味无穷。读者完全可以把这些篇章当作小说来读,体现了作者写作手段的多样性、艺术呈现的丰富性。但是,散文必须依着散文的河道流动,就像前行时看到岸边有独特的风景,迂回了一次,歇了一下脚,继续上路。
《古灵魂》中,有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作者并没有涉猎。比如有关介子推因为重耳忘记封赏他,一气之下,背着老母亲躲进绵山,重耳放火烧山的故事。张锐锋认为,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史书上没有记载,所以《古灵魂》中没有涉猎。可见这是一部非常严谨的文化散文巨作,作者借助哲学和想象思维的翅膀在晋国历史的天空飞翔,但是所有的想象和描写均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之上。
晋国前后六百五十多年,不可谓不长,但历史再长,也难以逃脱改朝换代的命运。晋国后期各大臣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军队,最后韩、赵、魏三家分晋。从此晋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晋国故事成为历朝历代作家、史学家争相钩沉和艺术再现的题材。
《古灵魂》在艺术表现上还采用了魔幻主义表现手法。比如鉏麑刺杀赵盾一节。鉏麑已被撞死,灵魂已经出窍。为了能够活灵活现地表现这个人物的内心感受,呈现在场感,作者大胆地采用了魔幻主义的手法,让出窍的灵魂在空中看到自己肉体在现实中存在的样子。这种写法在书中出现多次,无疑为传统艺术表现提供了巨大的张力。
《古灵魂》是一部描写晋国史的长篇散文巨制。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创作,挑战作家的胆识,挑战作家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的能力,挑战作家面对史料如何艺术地使用,挑战作家面对巨大的虚空如何谨慎地弥合,使其成为完整的文学架构。
这让我想到散文的三“虚”问题,主要包括内容、结构和语言三个方面。
第一,内容上的虚,也就是实与实之间的连接,这个连接是必须的,无法回避的。就像一件出土的陶器,破损是难免的,也许还有残缺。考古工作者必须运用自己娴熟的修补技术进行精心的修补。修补过程中需要使用黏合剂,还有别的材料,如此才能把一件陶器完整地呈现出来。那么,残片与残片之间的黏合就是一种虚,这种虚是不能省略的。像《古灵魂》这样二百多万字的巨制,又是描写距今很久以前的事,史料又是如此阙如,如何再现那段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以及生活生存状态,合理使用“虚”的手法是必然的。
第二,结构上的虚,体现在留白,也就是要“空”。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中写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讲的就是“空”的重要性。他举了三个例子,比如车轮的辐条、泥做的陶罐、房屋的门窗。车轮上的辐条,不是图美观而存在,而是要解决车轮中间风的穿越问题。如果没有辐条之间的空隙,车轮行驶中就会受到风的阻力,从而影响车子的前行。泥土做的陶罐,造型固然重要,但是做陶罐的目的是要有能使用的空间。如果忘记了目的,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有门窗,盖房子必须留门窗,门可以进出,窗户能透气和采光。老子用现实当中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空”的重要性,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散文创作同样如此,结构上不能太满太实,要留气口,能够自由地呼吸,文章也要呼吸,同时也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这里的“空”,也是一种“虚”。
第三,语言上的虚,体现在“闲笔”。所谓闲笔肯定不是主题话语,它是紧紧围绕主题起到烘托作用的。比如农夫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躬耕于陇亩之上,腰酸背痛是难免的。此时,直起腰来,向周围环视,会看到地垄上的大树、树上有栖息的鸟,还有旁边潺潺流淌的小河、河边摇曳生姿的小草等,以此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把这些与躬耕的场面联系起来写,看似闲笔,其实闲而不闲,对主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溢出价值。张锐锋正是既大胆又合理地在内容、结构和语言上运用了“虚”的功能,为读者呈现了如此花团锦簇、文采斐然、妙趣横生的散文力作。
这是一部不仅考验作者,同时也考验读者耐心和毅力的作品。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值得的。这不仅仅是作者和读者的幸运,更是当代文学的幸运。
【作者简介】高海平,山西乡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散文集《带女儿回家》《一抹烟绿染春柳》《我的高原我的山》《太阳很红,小草很青》等。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梁乐欣
特邀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