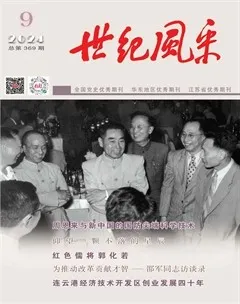为推动改革贡献才智
2024-0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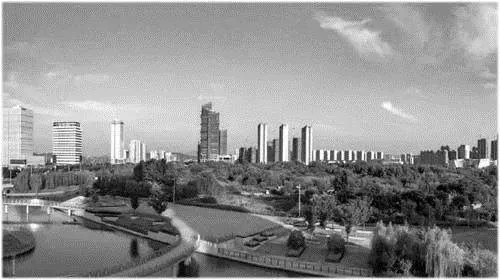
我们小时候读毛主席的诗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觉得38年是多么漫长,现在研究室成立45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江苏省委研究室开始叫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而发展的。
我1979年9月从灌云县委宣传部调到省委研究室工作,1983年离开研究室给韩培信书记做秘书,真正在研究室工作的时间4年左右,不算长。但是这4年正是江苏改革开放启动的关键时期,省委研究室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省委研究室早期和省委办公厅分得不是太细,有两块牌子,但是人事、财务没有独立,人事关系都在省委办公厅。两家在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领导下打统仗,不论是调查研究还是起草文稿,很多事情都是办公厅和研究室一起做的,一直到顾介康当研究室主任的时候,才分得比较清,有了独立的机构,人事才分出去。这个时段,有的成果是省委办公厅和研究室一起做的。
我来的时候,研究室在省委大楼里面,一进门右转东边的一间大办公室,现在是101会议室,会议室用两个很大的书橱隔开来,十来个人就一大间办公室,主任以下包括吴镕同志都和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我在研究室工作时间不长,回忆起来有这么几件事印象比较深:
第一件事是无锡大调查。记得当初到研究室报到,那时候办公条件差,我在南京中山北路81号招待所,就是现在的议事园住了一个晚上,最后没地方住,领导说:“你到无锡去参加大调查吧。”那时候省委主要领导在无锡做改革开放的调查,办公厅和研究室的写作班子全部出动。我记得1979年的下半年,在无锡做了长达两三个月的调查。调查由省委主要领导领队,调研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情况,为研究江苏大的改革总盘子作准备。那是研究室参与的一件大事。当时还抽调了省级机关很多厅局领导,分农业、工业、商贸等各个条线,主要是经济类。我主要配合曹顺霖同志,帮着写一写、记一记。我们两个人负责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调研。那时候调查没有现在这样庞大的队伍,商业体制改革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就两个人在做,要了解现状,还要提出建议。当时我们国家的商业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国所有商品在三级批发体系流通。什么是三级批发体系?以茶杯为例,一级批发站在省一级,茶杯全部在一级批发站汇总;二级批发站在市一级,一级批发站把茶杯分配给二级批发站;三级批发站在县一级,再往下就是零售了,乡镇的供销社要卖茶杯就到三级站去进货,就是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小时候都深有体会:为什么物资匮乏?为什么买不到东西?全部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控制。我对此是有体会的,也曾具体研究过这个事,这个体制的问题在于产销严重脱节,商品严重匮乏,严重脱离实际。
我参与这个调研,也是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第一个针对性调研。我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是,适当推进直销,允许工厂直销。那时候还没有市场这个概念。江苏有大量的生产企业,比如电风扇不少乡镇企业、中小企业都已经做起来了。直销开始也是不行的,比如生产了100台电风扇,必须进入商业体制的计划内,国家的批发站先收购,然后再分配。我们都领过电视机票、电风扇票、电冰箱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两个部门能发这个票,一个是商业厅,一个是轻工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改革,经济是没法发展的。除了商业体制改革以外,乡镇企业改革也是一个重点。当时无锡县号称中国乡镇企业的第一重镇,曹鸿鸣任县委书记。调查无锡县的乡镇工业,我跑了很多次,到过无锡县的一半乡镇。
第二件事是农村改革。江苏的农村改革跟全国不完全一样,当时首先引起轰动的是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在全国形成了很正面的冲击性影响。江苏泗洪的“春到上塘”也引发了关注。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风气,大家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个不同意见可以是很尖锐的、很明确的。农村改革在江苏争议比较大,当时农工部负责农村工作,农工部有3位同志坚决支持改革,都是处级干部,但一些层次比较高的干部对此有不同看法。
当时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提出“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中央的政策有灵活性,实际上是对不同情况的分类指导。但为了“可以、可以、也可以”,江苏争论了很长时间,我们开过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县委书记都参加,天天讨论,有的人就明确讲不赞成“大包干”。
江苏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苏南和苏中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不靠种田生活,在当时“以粮为纲”的背景下,种田是贴钱的,叫“以工补农”。所以,种田已经不挣钱了,把田分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当时的问题是乡镇工业、社队工业怎么发展的问题,是农民怎么致富的问题。把田分给农民种,农民已经靠“以工补农”才能不亏钱,已经不愿意种了。上塘没有工业,农民全靠种地生活,“大包干”可以提高产量,改善收入,也是不错的。调研显示,中央提出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做法,在江苏是适用的。
全省大部分地区采取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者是联产到组责任制,或者叫专业承包责任制。什么叫专业承包?就是一个生产队的田由几户专业户承包。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根据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情况,留给下面一定的自主创新和选择的余地。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的农村改革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在中央“可以、可以、也可以”大方针的指导下,各地的选择都是有利于促进当地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当时我在省委党校学习,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忽如一夜春风来”,觉得耳目一新,不再是唯上、唯书而是唯实,不是天天背语录,写文章不是靠引用来发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多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可以研究了。
第三件事情是乡镇企业“一包三改”。当时江苏的农村已经呈现农副工全面发展的态势,工业已经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大包干”之后,江苏农村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乡镇企业的改革。
现在回头看,江苏农村改革真正吸收了“大包干”经验的精华。“大包干”的内核是责任落实和绩效挂钩,本质上是解决产权认同问题,包括支配权、自主权、获得报酬权。
无锡县堰桥乡“一包三改”的调研是韩培信书记牵头的,我那时是韩培信书记的秘书。江苏的“一包三改”实际上是把“大包干”的内核移植到乡镇企业问题的解决上。
乡镇企业从社队企业起步,发展到80年代中期,已经有一定规模了,有些比较大的乡镇企业出现了向国有和大集体方向靠拢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是靖江。靖江把一些好的乡镇企业收归县里的大集体,当时企业领导愿意,员工也觉得更光荣、更有保障。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样搞下去变成“二国营”,改革还怎么推进?改革的正确方向应是产权越明晰越好,责任越明晰越好。
江苏的农村改革贯彻了中央“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指示精神,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及时把“大包干”的精髓移植到乡镇企业改革上。“一包三改”以后江苏的乡镇企业迎来了一个大发展。当年,靖江和对面的江阴是差不多的。江阴现在成为工业强市,很多上市公司当年都是乡镇企业。靖江也有很多很强的乡镇企业,但是都收归集体了,现在两地经济发展有了差距,我认为这与90年代前后两个地方不同选择相关。
韩培信书记认为,无锡的“一包三改”符合发展的方向,不能是集体化、“二国营”,而是要向更加明晰责任的方向发展。“一包”就是领导班子总承包,跟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本质是一样的;“三改”是指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省里对“一包三改”肯定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大飞跃,为江苏后来整个工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江苏的民营经济主要有两块来源,一块是原生型的从个体户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还有一块是已经成规模的乡镇企业通过改制发展成为大型民营企业,最典型的有红豆集团、沙钢集团。
第四件事是乡镇企业改制。“一包三改”再后来就是乡镇企业改制,那时候我已经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了,主持了乡镇企业改制这项工作。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一包三改”已经解决不了发展的动力问题,需要变成产权非常明晰的民营企业。江苏的民营企业不可能都从个体户开始做。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营企业,经历过一些探讨,也有一定的阻力。
当时浙江走了另外一条路,个体私营经济比较发达,全省都是个体厂。那时候江浙“蚕茧大战”,争蚕茧、争资源、争丝厂,我们的吴江县紧挨着浙江,却竞争不过人家。我们去调研,吴江的乡镇企业反映,浙江的私营企业体制比我们灵活,我们很多事情乡镇还管着,还要向领导请示汇报。所以要改制,我们研究怎么样把一部分资产量化给管理团队,一部分给政府。当时要找一个理论依据,解释为什么可以把集体企业的资产量化一部分给经营团队。后来我们研究发现,从马列经典到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都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管理也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包含着体力劳动。我们认为,既然承认管理者花了几十年的劳动把企业做成这么大的规模,那么给这个经营班子一定的产权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于是就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上搞了这么一个量化的方法。如果不改革,还是走过去的老路,就没有陈建华、没有红豆,还会变成大集体、变成“二国营”。
第五件事是小城镇调研。小城镇调研是研究室牵头的.那是我们的一个大成果。那时朱通华任研究室副主任,我还在研究室工作。小城镇研究主要是朱通华负责,他对小城镇调研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费孝通到江苏调研,把苏南作为小城镇调研的重点,当时连续几届省委主要领导都非常支持,我也参与比较多。在小城镇调研期间,我差不多跑遍了苏南的小城镇。我们当时也把小城镇发展纳入农村发展总体盘子,把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发展空间布局的一个方面来考虑。利用费孝通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乡镇工业集中区这个概念,解决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问题。村办企业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明晰产权的发展方向,后来发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空间布局是不合理的。虽然是村办企业,但是不一定只在村里,可以办到乡镇工业集中区去。后来逐步调整思路,鼓励搞乡镇工业集中区,再进一步就是开发区,这与小城镇研究成果有关,解决的是工业太分散的问题。
关于文稿起草方面,我们研究室参与撰写了很多重要文稿,比如时任省委主要领导的文稿主要是牛钊主任负责起草,江苏农村工作的文稿主要是叶绪昌副主任起草,牛钊、叶绪昌带着我们写大文章,朱通华也独立承担了不少重要文件起草。后来我在办公厅当副主任主持文件起草的时候,王雪非和项兆伦都是主力,每个大报告都少不了他们。可以说,研究室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稿起草。
最后,我再谈一些关于调查研究的体会。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决策参考,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智库或咨询,用我们党的传统来讲,我认为就是调查研究。我在研究室工作期间最大的收获和进步,就是跟着老一辈的领导学习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路线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的体现,研究室就是干这个事。当时信息不太畅通,打个电话比较费事,传真机也很少,所以省委不可能很迅速直观地了解基层的情况。比如要了解今年是不是丰收、经济任务是不是能完成,就得派几个调查组下去转一圈。我们直接到乡村田头,去看庄稼到底长得好不好,到乡镇企业问今年的销售额到底是多少,然后回来一个一个向领导汇报。像这样大的调研,省委都会召开常委会会议听汇报。那时候的调查研究尤为重要,真实的情况都靠调查研究来提供。
后来情况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传真也容易,统计容易多了。我当办公厅副主任主持调查研究工作时,就在思考一个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不是不重要了。我认为,调查研究并不能因为信息化的进步和完善而降低它的地位,信息化、数字化代替不了面对面的调查研究。后来我有一个观点,在信息化不完备的时候,要下去摸情况,回来研究问题;在信息化逐步完备的情况下,要在家搜集情况,下去研究问题。我很反对只依赖大数据,大数据有失真的一面,不能代替面对面调查。抽样调查存在误差,调查对象在填表的时候一定是经过思考的,在思考怎样填写对自己的企业有利或对个人有利。任何时候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都不能完全代替调查研究。比如,韩培信书记喜欢亲自调研,当时就带着我一个秘书,跟乡镇干部当面了解情况,一样一样地去问。我的任务就是把该记的记下来。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年轻,认识水平有限。在调研的时候韩培信书记会讲出一些很重要的观点,我就认真记下来。群众说什么,领导说了什么,把群众和领导说的加起来,那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调查报告。比如苏北调研,从方法上来讲,那就是群众讲的和领导讲的碰撞出来的火花,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对后来整个苏北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杜润生调研了解情况时有一个特点,我们的行话叫“勾住”——认真听农民讲完,听到有启发有用的关节点时,就勾住这个关键点,一步一步深入问下去。费孝通的调研也是这个风格。我无论是在研究室还是办公厅工作,凡是遇到大的宏观经济调整,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就去调研一圈,一个月回来,信心也有了,办法也有了。再举个小例子,有一次我去调研“三角债”问题,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是坐火车去苏南的。车上全是人,有两个采购员,都是去要账的,一个要到了,一个没要到。我回来在调查报告写道,“在火车上遇到了很多要账的供销员,一个要到了很高兴,一个没要到很沮丧。”这样形象的语言写在调查报告里,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
我始终认为,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深入一线调研是不可取代的,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思想路线的体现。大数据不能完全反映群众满意不满意,面对面才能更加真切地看出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
再讲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当日寸研究室的氛围非常好,十来个人大体上有两个倾向,一部分同志倾向更激进一点,在农村改革、乡镇企业改制主张更快一点,还有一部分同志主张更稳一点。我们经常争论一些问题,在办公室争、走路时候争、吃饭时候争,碰撞思想火花。现在我们研究室还是要继续倡导内部讨论的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