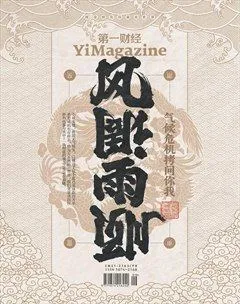潮起潮落,慢水黄岩行
2024-09-14朱英豪
送大暑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7月22日,大暑日,海门民众在东山岭五圣庙举行“送大暑船”祭祀活动。那天气温高达40摄氏度,我背着相机跟着送船的迎圣队伍,从五圣庙一直走到海边的集装箱码头,浑身都湿透了。
嘟哝了两句,突然瞥见路边一片绿油油的叶子丛中开得灿烂之极的木槿花,顿觉自己的可笑。
蒋柯均,一位从杭州赶回来的海门籍版画家、在地社群项目策划人,早已经在微信群里向大家实况分享道士在庙里做法的情景。他的另一位朋友老四,同时给我们做另一场实况分享——当天一共有两个版本的“送大暑船”仪式,不远处的葭沚老街还有一场。

我们观摩的东山岭这场,规模要小得多。船体也是按旧式下海的三桅帆船原样设计制作的,但只有真船的1/4大。一群老年人哼哧哼哧地抬着,伴随着不紧不慢的锣鼓声,一路逶迤巡行,走起路来有点慢。但它历史更悠久,基本上是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且在我看来,它的组织更接近过去封建社会淫祠的祭祀活动。葭沚那边就不一样了,阵仗大,更热闹,有领导剪彩,还有演奏革命歌曲的现代化军乐队和消防车加持。抬大暑船的人都是壮劳力,前后有抬阁花车表演,国字头媒体和网红博主也在现场直播。
“送大暑船”是浙闽沿海渔村常有的民间传统习俗,简单来说,就是把“五圣”送出海,送走酷热大暑,保平安民。送船祈福,从宋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到清代的《吴友如画宝》《清稗类钞》都有详细记载,其目的不外乎保佑人船平安、驱逐瘴疠、穰灾送厄。仪式的最后一个流程,都是算好潮汐时间,在开始退潮的时辰焚烧船只,并让潮水带入大海。



几乎与大暑时辰同步(申正三刻),在码头高耸的海塘边,东山岭的大暑船被起重机放在海边沙滩上,燃起熊熊烈火。没过多久,被拖向台州湾的葭沚大暑船会驶经此地。彼时,涌来的海潮裹挟着眼前这艘大暑船焚烧后的余烬,簇拥着船上的神像人偶、金箔度牒、酒食米面、猪羊鸡鸭甚至刀矛枪炮,消失在海平面上。
也有夹带私货的。在东山岭的船上,我似乎看到一个举着车牌的小人偶。清代著名文人俞樾曾来黄岩看送船仪式,他在《右台仙馆笔记》里记录了自己在船尾,看到一个打着雨伞的卖布商人的人偶。
另一位在现场的朋友、本次工作坊组织者、“方志小说”发起人芬雷穿了一件印有奥特曼的T恤衫。后来我从照片上得知,去年的五圣庙大暑日祭祀,有人在大暑船的两侧放了奥特曼人偶护卫,保佑活动顺利平安。
“一夜潮回葭沚船,花蚶白蟹不论钱。”这首清代椒江竹枝词道出了古代海潮对台州这个城市的影响。在观摩送船的时候,我们胃里还残留着前一天摄入的海葵肉。据说,海葵是海里的向日葵,它望的,不是太阳,而是海潮。
在台州吃饭,总能看到听到“家烧”。有意思的是,俞樾带领下的台州学派的授学方式也是传统“家烧”,即所谓家学传承,大师亲炙。
“送大暑船”祭祀最让我着迷的地方,是海潮把船带走这一部分。它不是一个僵死的愿望,而是流动的,正如大海的脾性。大海再无情无常,人类也能参透其中一些规律并加以利用。
Y先生的慢船
观摩“大暑船”是我们一行最后一个活动。过去10天,“方志小说”黄岩工作坊一行历经黄岩老城、沈宝山国医馆、朱砂堆洞窟、凯华模具、第一罐头厂、九峰山、委羽山、长潭水库、沙滩老街橘园等地。芬雷和龙奕瑭(“方志小说”的另一位合作者)还邀请到了戎怡——一位黄岩当地考察古代水利的民间学者,请她带领大家考察了永宁江及几大官河上遗留下来的老水闸如西江闸、蛟龙闸等。
在参观完长潭水库、蛟龙闸等几个水利设施之后,我才知早在1960年,长潭水库大坝合龙,溪流被阻断,永宁江悠久的航运历史就画上句号。而上世纪末,永宁江下游江口船闸建成后,彻底隔断了海潮。从那时候起,永宁江上不再有潮起潮落,变成了平静但不一定全是清澈的江水。当我们站在三江口大闸——江水进入椒江流往台州湾的地方,水面上隐约传来阵阵难闻的化工味道。在过去潮水可以涌进涌出、吐故纳新的时候,这种现象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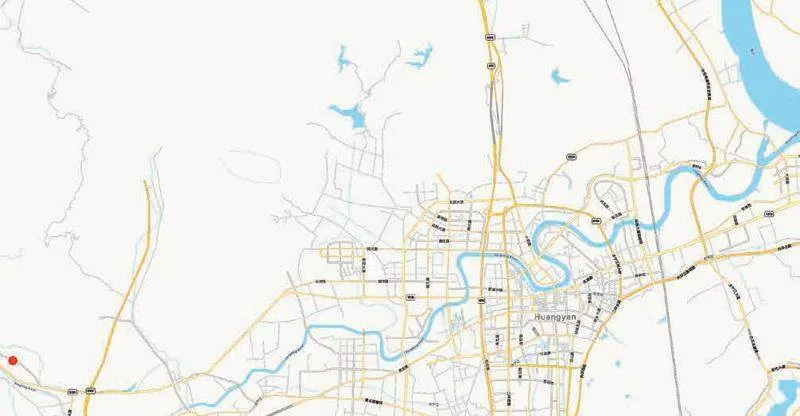
来黄岩之前,工作坊中很多人对台州的印象都停留在黄岩蜜橘。虽然不是橘子成熟的季节,城市里依然能看到很多带有它的印记的地方:桔源路、柑橘研究所……有成员搜集到了很多橙色标记。聊到蜜橘,不止一个当地人告诉我,黄岩蜜橘的秘诀在于海水和淡水的交汇带来磷钾镁钙等多种微量元素,是它们让橘子变得可口。这种说法被政府认可,它其实早在古代就已经成为农民的种植知识。明时徐霞客游雁荡经黄岩,题句“未解新禾何早发,始知名橘须高培”,告诉世人滨海斥卤之地筑墩栽橘这项今天可以拿来申请非遗的栽培技术。
宋元时期,橘林沿着永宁江延伸,直至方山下,呈现了“九曲澄江如练,两岸橘林似锦”的景象。它与当时的占城稻平分秋色,成为温黄平原上的主要种植作物。今天,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模具车间。而且,当潮水不能涌入平原,蜜橘还能维持之前的口味吗?在台州,好几个当地人都说现在反而是涌泉蜜橘比较出名。我妄自揣测,是否因为那里的柑橘园还能接受海潮的洗礼?
黄岩博物馆展出了一位出生于193 0年代名叫尤伯翔的老人的口述史。这位家住草行巷的老人和几位同龄老友一起,为大家拼凑出一幅解放前后黄岩县城的繁荣市镇生活图景。也是在他的讲述中,我才发现古时候台州湾的潮水竟然可以涨到今天的潮济古街。所谓潮济,其实是潮水边际的意思。






和芬雷乘车前往宁溪瑞岩寺,路边闪过冷清的潮济古街。我们没有看到水的痕迹,若是普通游客,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怪异的名字。潮济的风头已被附近的沙滩街抢了去。夏日黄昏,屿头永宁河边的汀步水坝上,不时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据老人回忆,民国时期永宁江上有永升轮、江大轮、黄济轮等共3艘小火轮,每天它们都按照海潮涨落的规律,定时行驶于临海、海门(今椒江)、潮济三地。
据光绪三年《黄岩县志》记载,永宁江上曾有22个渡口。黄岩溪上游咆哮的山水,流至今宁溪镇镇区方才“安静”下来,故此地被称作“宁溪”。自潮济起河段始称“永宁江”,也是由“宁溪”派生而来。
今天的黄岩文物古迹留存不多,但之前老城隍三十六街七十二坊的格局保留了下来。拿现在的地图和嘉庆年间的县城坊巷图相比较,会发现过去的壕沟和城墙被今天的环城路所取代,但连曲线都几乎一样,甚至过去的老县衙现在依然是黄岩区政府所在地。
据学者顾希佳的调查,举行送大暑船仪式的在黄岩一共有3个庙,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还有一个在黄岩古城西门的灵济庙,也供奉有五圣(另奉一保界神为晋代领士族南迁者),而且历史最为悠久。如果从古城的河道上把大暑船随着海潮送出台州湾,这条线路显然是最长的,也和客船的线路基本重合。
假设俞樾和尤伯翔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事实上差了一代人),那么,结合他当年走水路探亲经黄岩去乐清的记录,以及尤先生的口述,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下:1930年代,一个临海小盐商Y先生选择在重阳节前一晚前往潮济古街做生意,之后去县城购物,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乙夜潮至始行”,Y先生应该会和俞樾一样,选择在晚上10点从台州府(临海)上船,第二天早上抵达潮济码头。潮济集市热闹非凡,这位盐商找到自己的老客户——一群专走苍岭古道然后转水路到婺州处州去的私盐小贩(我是婺州人,也许祖上吃过Y先生的海盐呢)。最近行情不错,他卖了个好价钱。
潮济老街就在划岩山脚下,附近有两座庙宇——瑞岩寺和灵石寺。瑞岩寺是日本曹洞宗的祖庭,智者大师曾经驻寺。灵石寺被吴越王的国师德韶大师选中,在此造阿育王塔。Y先生是个虔诚的信徒,去灵石寺烧了香。
之后他继续走水路前往黄岩城。航行中路过一个叫断江的村子,这里是黄岩蜜橘生长得最好的地方(如今这里建了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正是橘子飘香的季节,永宁河两岸一片橘红色。
再往前,快进入县城时,在河的右岸,Y先生看到了刚刚兴建的西江闸,立在西江和永宁江的交汇处,边上还有一个亭子。那时候的船马邮件都慢,可以想很多事。
今天的西江闸和边上的孤魂碑亭是永宁公园的一部分。尤老先生在文章里特别提及西江闸的修建者——民国著名水利专家胡步川。据戎怡老师介绍,碑的背面还有八卦图案。当时建闸,屡建屡败,城中多议论,说触犯了此地边上的乱葬冤魂,于是胡步川为乱葬尸骨建公墓、立碑,上书“魂兮归来”。
更早在黄岩修闸的善人,是时任浙东常平使朱熹。他到工地勘察,由于天色已晚,索性在下闸村百姓家住下,夜晚却被潮水吵醒——有诗为证:客怀今夜不成寐,风细月明江自潮。“利于温黄援新嵊,造福人民万古芳。”戎怡指给我们看村口的一颗古樟树,原来是村民把朱熹当年给皇上的奏疏都给刻成铭牌挂在树上了。落款时间是1999年,正是海潮被拦住的那年。
Y先生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赶赴大井头的沈宝山大药房举办的两年一度悬宰仙鹿仪式,并在现场买几盒全鹿丸,作为送给父亲八十大寿的礼物。沈宝山有一味秘方药很传奇,用著名的天下十二洞天之一的委羽山方石熬制而成。来的都是客,这副药Y先生竟然也抓到了。
从药房出来,他先去就近的鱼鲜摊上买了几条大陈岛的大黄鱼。一日两潮,大井头的街面上,从葭沚、海门来的鱼贩络绎不绝。买完鱼,他直奔东禅巷的羊市,用剩下来的钱换了两头绵羊。东禅桥头的快船埠头(县志老地图上还能看到内城干河水道)一直很繁忙,Y先生赶着羊上了船,在北门头换上开往临海的府船,踏上了回程的路。


正在船上歇息时,他发现货栈上堆了几大篓天台山蜜橘。Y先生暗忖,应是小南门刘家发去上海的货。天台山蜜橘在1920年代前后闻名上海滩,皆因黄岩人氏、民初沪上三大书法家之一刘文玠的大力推广。这位出身行伍的“山农”在小南门自辟橘园,“接以嘉种,蓄以蜜蜂”,几年后结出的蜜橘“细嫩鲜甜,得未曾有”。他在自任编辑的《大世界》日报上推介“本地早”(一种早熟品种),并用非常漂亮的毛笔字在包装上手写“天台山蜜橘”几个字,辨识度极高。海上名流如吴昌硕、袁克文等人题词唱和,黄岩蜜橘因此满城皆知。
慢水
戎怡老师带领大家走了不少古代闸口,最后一站是玉林渡。从地图上查看这个地段时,会发现永宁河在这里拐了一个Ω字形的弯。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水量很小,河道还在。
在现代水利工程上,很多类似的地方可能就会被截弯取直,用来加快河流的速度,减少泥沙的淤积,从而达到所谓的河流治理。但在古代社会,正是这样蜿蜒密布的水道、沼泽和河潭,涵养了一大部分水源,是天然的水库。
据媒体报道,2004年治理永宁江时有一段河流原本也要裁弯取直,但最终得以保留。原本打算用水泥衬砌的公园堤岸,最终改以鹅卵石泥土衬砌,青蛙也可以自由上岸。这些现在看起来还很超前的理念,出自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俞孔坚教授,它们塑造了今天的永宁公园。
与洪水为友,倡导海绵型城市,俞教授有关水治理的一些言论,每逢哪个大城市被水淹,就会被网友扒出来。的确,当发现小区里不断翻新的地下管道越来越粗,当又有城市居住者在自己家门口被洪水卷走,我们是该想想,人类是否过于傲慢?
龙奕瑭最近几年一直践行对河流问题的关注。在他推荐给工作坊的参与者的《慢水,灾异时代我们如何与水共处》里,美国科学作者埃丽卡·吉斯(Erica Gies)向大家解释了巨型大坝给人类带来的“副作用”。在“当淡水遇上盐”这一章,她告诉我们抵御海潮的最佳武器不是筑坝,而是潮汐沼泽,因为它会长高……“波士顿放弃了最新的筑坝计划……荷兰著名的三角洲拦潮闸是浮动的,大部分时间海水可以自由进出……吉斯号召大家开展一场“慢水运动”,以水合作,复建水生态。
九峰公园边上的青春咖啡馆里,坐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工作者。工作坊经常在田野考察结束后随机讨论,成员里既有艺术家、艺术机构策划人、建筑师,也有国内外大学不少成员都对水文相关的话题产生兴趣,希望从古闸兴废、水井文化甚至女性主义的纬度进行观察,有人想借公园或者植物作为抓手,也有人迷恋这里的水下声音、被行政之手涂抹的色彩或者散发出来的特别气味。有外地艺术家体验模具城里廉价的客厅帐篷,也有本地艺术家穿过晃眼的林木找回了自己的童年。有人从模具里看到永恒的纪念碑性,也有人从自己的田野方式里反思何谓客观。
不同的话题,在不同地域身份的罅隙里流动、交织。点滴观察正在流动汇聚,模具自身尚未塑形,大家还处在一个呈现吸收的状态——艺术讨论的潮间带。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工作坊里还招募到不少来自本地的资深从业者,包括前面提到的蒋柯均,以及从事公共空间和社群组织的emma。近几年,很多大城市的文化创作者选择回到家乡,对外来者而言,这些洄游者的出现,意味着可靠的地方知识和成熟的外部视角。近几年,很多大城市的文化创作者选择回到家乡,对外来者而言,这些洄游者的出现,意味着可靠的地方知识和成熟的外部视角。
海潮的涌入和江河的排出,犹如呼吸吐纳,带来鱼类的洄游与流动,同时也为海河潮间地带的大片土地带来独特多元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动植物、岩石、土壤和各种微生物。
这也适用于两种文明的交汇。
“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写下这段今天看起来多少有些贬低台州人先祖的文字时可能不会想到,1200年后,代表中原文明的赵氏皇族一位嫡系子孙(赵伯澐)会在瓯越之地入葬。他身上穿的一件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竟然在80 0年后成为全中国考古视野内的宋服之冠。
还是以本土为例,海潮内外,台州最知名的两张名片,一为天台宗,二为蜜橘,也都是在被日本人学习,传到自己国内发扬光大之后,再度传回中国。
前者发生在吴越国时期,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武宗灭佛,佛教各类经典散失殆尽。后者发生在民国时期(1937年),中国留学生从九州带回了国内尚无的无核改良品种。
我之所以记得此事,是因为期间去黄岩第一罐头厂参观,发现正在装货的罐头就是要运往日本。临走道别,厂方代表一直在门口,用久违的目送礼送我们车队离开后才折返。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去日本参观时,也是如此礼遇。当我问起缘由,京都朋友哈哈大笑,承认这本来就是中国人的礼仪。要怪,得怪自己“相见不相识”了。
从东门岭回到茶室纳凉,我们边吃台州青草腐边听手机里的外放—有人在抖音直播,葭沚老街的大暑船正被轮船拖向海域。“就让大暑船把各种厄运,带到××国那里去吧!”播主突然间一句激情的喊叫,让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凝固了。
无论水文还是人文,不妨大度一点,随波逐流也不是坏事,而非谁要去控制谁啊。
注:方志小说是一个联合驻地计划,倡导从地方出发的写作实践与艺术行动。感谢工作坊的每一位参与者,因为那些流动着的交谈,才会有这篇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