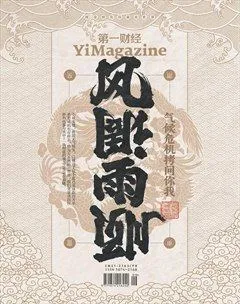一个老师为“游戏”正名
2024-09-14邓依云
走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楼地下一层,穿过一片似乎闲置已久、略显陈旧的空间,拐五六个弯,会进入一个别有洞天的游戏世界——两面墙边的五层铁架上摆满了各种实体游戏和游戏机,从小霸王电视游戏机到任天堂的新款Nintendo Switch游戏机,从1990年发行的单机游戏《轩辕剑》到2022年发行的独立游戏《沙石镇时光》,每个游戏玩家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游戏记忆。
这个游戏乌托邦的主理人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讲师刘梦霏。从2018年在杭州建馆开始,经历了一系列辗转,2021年,刘梦霏入职北师大两年后,“游戏的人”档案馆主馆(Homo Ludens Archive)最终在北师大校园内落地。这个只有39平方米的空间原是院系的储藏室,刘梦霏带着装满自己收藏品和他人捐赠物品的二十多个箱子,把这个并不宽裕的闲置角落搭建成了一个游戏的世外桃源。



档案馆的天花板是蓝色的,房顶上交错的管道被刷成了绿色,就像游戏《超级马力欧兄弟》里的场景。档案馆的象征物是蘑菇,这是馆内唯一能养活的植物。档案馆的吉祥物“角落君SMISKI”是一种夜光小精灵,它符合刘梦霏对档案馆的期待,一个“角落里的小东西”——静静地隐藏在城市一角,等待发现它的人。
在档案馆的留言本上,有许多游戏创作者参访时留下的痕迹。独立游戏《光·遇》的主美用他的风格画下了刘梦霏和档案馆,后来又有其他创作者画了“进化版”。有游戏人在本子上留言:“有一个这样的档案馆,如小石子一样存于此世,真是太好了。希望这里能够长存,在水中留下独特而真诚的涟漪。”
从4岁在父亲的带领下玩《坦克大战》开始,刘梦霏已有三十多年的游戏龄。在成为游戏研究者和档案馆馆长之前,刘梦霏学习和研究的方向是历史学。2007年前后,上大学的刘梦霏目睹了一场关于网络成瘾的论战,许多所谓的专家声称游戏罪大恶极,还有人提出应该把游戏玩家送去电击治疗。作为一名从小玩游戏长大的玩家,刘梦霏感到愤愤不平,在她看来,这些专家学者没有玩过游戏,也根本不懂游戏。
刘梦霏想要为游戏“发声”,她的研究方向自此转向了游戏,并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为游戏“正名”。
刘梦霏认同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提出的观点:人类天生就是游戏的人。档案馆名字中的“Homo Luden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游戏的人”,正来自于赫伊津哈的游戏研究著作《Homo Ludens :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在刘梦霏看来,档案馆保护的不仅是游戏,更是玩游戏的人,是社会中每一个普通人通过游戏来表达、成长,并打开更大的世界的权利。
以下为刘梦霏的自述。
为什么我们需要游戏?
在中国,许多人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游戏。每当社会讨论到游戏话题时,舆论的重点常常是错的,几乎每一次讨论都会回到“游戏是不是好东西”的问题上。
许多人不理解游戏,将游戏看作儿戏和一个小产业,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和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且不说游戏产业的产值有多高,实际上,游戏也不仅仅是作为产业的游戏,而是弥散到整个社会组织结构里的游戏,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游戏的状态。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即使不玩游戏,也处于游戏化系统的控制之中,它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所使用的互联网服务中。像美团、滴滴这类支撑人们愉悦生活的平台,它们的管理体系就是游戏化的系统,而外卖小哥和司机就是游戏化系统里被控制的玩家。这样的游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剥削工具,而游戏素养越低的人越容易被系统玩弄和操纵,成为被游戏玩的人。
另一方面,游戏也不是单纯的消遣和发泄,它其实是一种解放机制。人类天生就是游戏的人,我们在现代社会玩游戏是因为我们需要做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只能做工具人,但在游戏里我们可以做真正的人。我曾经对比过《魔兽世界》里玩家做的事情和狩猎采集时代我们祖先做的事情,发现它们能够完全对应,也就是说,玩家在玩《魔兽世界》时复现了一种狩猎采集时代的生活。
游戏是这个时代的自然乌托邦,对于普通人来说,游戏的世界反而可能是最好的世界,因为他可以在其中自主决策、自由行动。开放世界游戏《塞尔达传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做人”的游戏,玩家可以选择救公主,也可以选择不救公主而是去探索世界、欣赏风景。救公主只是一个借口,玩家是自由的。




由于大多数中国人看待游戏的态度是不正常、非中性的,以至于游戏在中国有很多环节缺位,比如我们习惯了在游戏问题上讨论亲子关系,小孩玩游戏似乎要么是游戏公司的错,要么是家长的错,可为什么游戏从未进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呢?
没有任何一种媒介是不通过学校教育,仅靠家长和厂商就能让孩子们学会的。我们是怎么学会欣赏鲁迅的“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怎么学会欣赏毕加索那些看起来像是幼儿园学生作品的立体派的画,怎么学会欣赏《公民凯恩》这样看起来有些沉闷的电影,怎么知道《红楼梦》比《小时代》更有艺术价值?这一切都是通过学校教育,让我们认识到它们比表面看起来更有价值。那为什么游戏素养教育不应该进入学校呢?
中国曾有长达13年的游戏机禁令,2014年才解除,这导致中国的青少年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游戏史。我在学校上课时会调查学生的游戏史,让他们拉一个时间轴列出自己玩过的游戏。今年我在本科生班级的调查里发现,约有一半的学生是上大学后才知道有主机游戏,他们小时候只玩过4399网站上的网页游戏。我很震惊,艺术生的家境通常相对不错,数字媒体系的学生又是艺术生里文化课较好的,这意味着他们的游戏经历应当是比较丰富的,可事实证明,他们的游戏素养也非常缺失。
以前有很多人说,随着玩过游戏的80后、90后成为中流砥柱,社会对游戏的态度,以及人们的游戏素养都会提高,但现在情况变好了吗?我发现这件事不会自然变好,必须要做游戏素养教育,让游戏渗透到教育体系中,否则一代会比一代更差。
从产业上看,忽略游戏这个在当今时代最新且最具统合性的数字媒介也是愚蠢的,这相当于放弃了一个文化阵地,而我们放弃的阵地总会有人站上去——我们没做出好的三国游戏,日本则做出了《三国志》。游戏不是想消灭就能消灭的东西,最后消灭的可能反而是最该保护的创作者。
在课堂上我可以明显感觉到,没有玩过好游戏的学生在做游戏化系统设计时做得比较差,因为他对游戏没有深刻的理解,不知道游戏能表现和表达什么。就像面对没看过《红楼梦》、只看过《小时代》的人,你能指望他写出什么好东西呢?他只能写出二流的《小时代》,写不出二流的《红楼梦》。
游戏不是教育的敌人
中国游戏最大的敌人是教育。在我看来,游戏和教育是同源的,二者不应该是敌对关系。
剥夺青少年游戏的时间,事实上是在剥夺他成为一个勇于探索的、独立的人的时间,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可持续,很可能还会在其他方面产生更严重的潜在后果。因为从来没有在游戏里体验过不同的人生,他可能会更加没有勇气走出框架以外的世界,他会变得越来越不宽容,无法拥抱多元的价值观。
游戏可以分为作品游戏和消费游戏,作品游戏是可以一次性购买的,它遵循做作品的逻辑,如果一款游戏卖得好,开发者会有更多动力做下一部。消费游戏则是免费游玩、道具付费的游戏,这类游戏是一套服务型系统,也是中国游戏产业的主流。消费游戏会在游戏中给玩家创造一些快乐,同时制造一些痛苦和不便,引导玩家付费购买道具消除不便。消费游戏也不完全是邪恶的,它遵循正常的商品消费逻辑,真正应该受到管理和抵制的是消费游戏中的赌博游戏,也就是以抽卡、氪金为核心的游戏,这才是很多青少年沉迷的游戏。
作品游戏是一种文化创作,如果青少年在人生比较早的阶段就玩过一些优秀的作品游戏,他不会再被赌博游戏所吸引。而这类游戏也可以成为教师的另一个教学工具,配合已有的学科教育内容。
与书籍、电影等媒介不同,游戏需要玩家自己参与其中并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观看别人的故事。玩家要在游戏里下判断、做选择,通过一系列行动改变世界,践行某种价值观,而他所做的一切都会内化为自身价值观的一部分。游戏是价值观渗透的重要媒介,非常适合作为育人的载体和工具。
在我小时候,很多大人会告诉我世界很大,父母也带我去过一些地方旅游,但孩子的世界是很小的,我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睡觉和吃饭的时间,对于世界到底有多大更没有概念。我第一次感知到世界很大是在游戏《大航海》里,“我”在海上冒险的时候死了,我这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海洋大到不能轻易看到海岸,如果船上的粮食和水不够,人是会死的。
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学生,但在《大航海》里,我可以不受任何桎梏地向前航行,想去哪就去哪。我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画着航线图,记录哪个港口会产出什么特产。《大航海》开启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和冒险的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游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像任意门一样的东西,不断为我打开新的世界。
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开关,但更多的孩子没有机会体验到自由探索的乐趣,而是一直被教育系统规训,直到后来通过一些离经叛道的经历才被打开。但我在人生比较早的时候就打开了这个开关,因为游戏。
我在上历史课之前玩《文明》,上地理课之前玩《大航海》,虽然学习的时间比一些同学要少,我还是能考得比他们好,因为我的知识是活的,其他同学可能只是背下来里斯本在哪里,但我真的在游戏里去过里斯本成百上千次。
游戏的影响力远远不局限于屏幕之内,因为人是活的、连续的,会把游戏中的经验、技能和判断带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在《魔兽世界》中,玩家管理一个数十人或上百人的公会,与在现实中管理一家公司是极其相似的。有很多原来《魔兽世界》的公会会长后来真的自己创业或者做了公司管理者,他在游戏里学到的东西,甚至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对现实生活都是有帮助的,游戏中的“魔圈”和现实生活并不是迥然两分的世界。

剥夺青少年游戏的时间,事实上是在剥夺他成为一个勇于探索的、独立的人的时间。
不过,档案馆的游戏素养教育项目并不针对青少年,在我看来,更需要被教育的是决定孩子教育路径的成年人,他们因为一层障壁不能正确认识游戏。游戏素养教育是为了移除教师对游戏的有色眼镜,教他们如何利用游戏教育学生。我们会给教师提供一些游戏案例、方法论和工具包,教他们在课堂上用游戏教学,帮助学生建立起批判性的游戏素养和游戏审美,让他们知道怎样选择好的游戏。
档案馆开设的第一期游戏育人工作坊的目标是招募30名中小学教师,帮助各学科教师打磨教案,没想到第一期有372个人报名,是计划的十多倍,这说明许多人对于游戏进入教育系统是有需求的。
游戏育人工作坊为期6周,参与的教师们做出了不同学科方向的共18组教案。有政治教师借助战争游戏《这是我的战争》帮助孩子理解“和平与发展”,从而形成正确的政治观;有地理教师用《仙剑奇侠传4》教授地理知识,因为游戏地图与中国地图对应,游戏中还有地貌和生物的设计;还有英语教师利用互动电影游戏《底特律:化身为人》教英语口语,让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并对话……
我们期待未来公开这些教案之后,会有更多的教师愿意将它们运用于自己的课堂中。如果教师能在课堂上用游戏育人,他就不会再一味反对游戏,而学生也会知道,游戏可以打开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更有建设意义的事情。
游戏可以改变世界
“游戏的人”档案馆是一个公益项目,馆里80%的藏品来自于捐赠,目前由乐予慈善基金会支持。我们收藏所有实体游戏和档案、游戏主机、设定集等,拥有中国现有所有游戏杂志的创刊号,可以说是一个金矿。档案馆并不追求许多收藏家关注的稀有物品,更看重普通玩家能接触到的东西。曾有人想捐赠雅达利2600(美国公司雅达利于1977年推出的一款家用电子游戏机)之类的稀有贵重物品,我们并没有收,因为那不是中国的普通玩家能接触到的。比起少数精英玩家的历史,我们更关注中国普通玩家的记忆。
档案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层面推广游戏素养教育,并给大众提供游戏解困的工具,运营的底层逻辑是我所坚信的游戏能够改变世界。我们办展览、进校园、输出一些游戏化设计,希望用游戏影响人,帮助更多遇到困境的人。除了主馆之外,档案馆目前在成都、上海、广州和珠海还有四个分馆,其中成都分馆在一个职业学校里,重点关注游戏素养教育。
我们并不希望档案馆成为网红,教育本来就需要站在一个相对更高的地方去影响下面的人,而成为网红意味着需要服务公众,我们不可能一边教育公众,一边服务公众,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中国的游戏产业还很年轻,刚到“而立之年”。国内首个本土单机游戏是1994年发行的《神鹰突击队》,首个游戏工作室是金山集团旗下成立于1995年的西山居,到现在都只有30年左右。它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有手有脚,但缺了点脑子,这种情况下档案馆就暂时充当了脑子的角色,补足了很多缺失的位置。《魔兽世界》中有一个职业叫德鲁伊,它是自然的守护者,并不维护某一个物种的权益,而是会平衡和维护整个自然界的秩序。档案馆就像游戏产业的德鲁伊,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并维持它的平衡。
我们做了一个线上游戏库,家长和老师可以按照涉及学科、游玩时间、游玩场景等维度搜索现有的游戏作品,这其实类似于海外的游戏分级机构的工作;我们会做游戏创作者的口述史访谈,帮他整理创作思路和历程;我们还会作为专家为产业决策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档案馆做的最酷的事情就是游戏杂志的档案化和数字化,我们把这些从未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数字化后放在网站上,让它能够被搜索引擎收录和检索。
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有一个妈妈农场,用集体养育的方式抚养一些虽有父母但父母无法尽抚养之责的事实孤儿。他们的社工老师在我们的游戏育人工作坊上做了一个农场游戏化的计划,用游戏化的方式带领孩子种植自己的小菜地。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像学生一样完成作业,但我上个月再去妈妈农场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农场游戏化计划进展迅速,孩子们在农场里种的葵花已经长得比我还高了,我们在当地吃的西红柿也是他们种出来的。
档案馆正在协助妈妈农场设计一套贯穿于农场衣食住行的游戏化养育系统,我们做了一些像分院帽一样的视觉标识,给每个孩子做了一个太阳盘,他可以通过一些行动得到奖励,在其中积攒各种属性的珠子,这些珠子还可以作为农场的货币在内部流通,帮助他们养成一些经济意识—有点像现实版的《牧场物语》。
我们还计划再为他们做一套关于生命教育的桌游,叫“蘑菇人生大冒险”。妈妈农场就像在将一些受伤受困的小狗收留并养育成健康的小狗,但这还不够,因为小狗是会长大的。这些困境儿童对人生道路的认知非常狭窄,他们的个性也相对偏执,很容易走上歪路。因此,仅仅在生理和心理上养育他们还不够,还需要协助他们规划未来的人生。
游戏是很好的解困媒介,因为它允许你在安全的情境下探索,可以为这些困境儿童打开更大的世界。这套游戏将贯穿从小学到毕业工作的人生,我打算将常规的人生游戏中单向圆环的棋盘改成一个八字形互相连通的无限棋盘,就像立交桥一样,有很多层和不同的可能性。如今大家都活在一条笔直的、狭窄的高速公路上,好像一旦从这条路上掉下去就没有再爬上来的渠道了。可这是谁规定的呢?我们偏要做很多弯曲的路。
不仅是困境儿童,许多北师大的学生也存在人生失焦的问题。他们在一个更加保守的、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成长,面临的压力更大,也需要一些精神的疗愈和慰藉。我希望通过游戏场景让孩子们知道,人生是可以后退几步的,就算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找到最理想的工作,往回退几步,还能走上新的路。
比起带来大规模的改变,我们更希望改变每一个具体的游戏人。档案馆是一个非常小的生态环境,但我已经看到它在具体的人身上产生了影响。就像小学课文里在海边救小鱼的人,有人说花这么大力气去救那一条小鱼,又有谁会在乎呢?那条小鱼在乎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