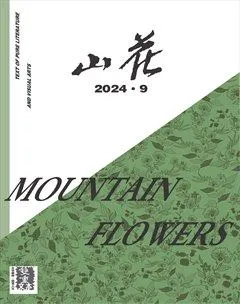花签
2024-09-14宋红星
酒柜上摆满各种酒。纳菲站在吧台后,身着米色的针织毛衣,正画着细密的圆圈擦拭酒柜。结婚三周年的时候,我给红英买过一件这样的毛衣。红英什么时候把毛衣送给纳菲了?也许,是纳菲自己的?
酒吧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来杯加冰的。”我坐到吧台前,抹抹额头上的汗说。也许是天气很热,也许是被困在家里,很久没出门,随便走走我就全身冒汗。
纳菲转过身,好像在确定是我,接着才将毛巾扔在酒柜上,然后拿出两只水晶杯往吧台上一放,其中一只暗暗用力,杯子便“沙——”一声向我滑来。我向门口瞟了一眼,门外阳光白炽刺眼,栅格窗户投下的阴影就像一张网将我罩了起来。我晃了晃身子,试图从网上挣开。
然后,是冰块扔进水晶杯的“咣当”声。
我回头看着纳菲。纳菲把开瓶器扣在瓶盖上,手腕稍一用力,啤酒瓶便“啪”一声打开了。为了防止泡沫溢出,她将瓶子紧贴在杯口上,倒得很慢。
“谁送的?”我看着吧台上的玫瑰问。
“你就不能送一次,哄我开心开心?”纳菲把酒瓶放在吧台上,不等我端起酒杯,就与我的杯子碰了一下,接着说,“难道没有男人,我们女人连一束花都买不起?”
我端起酒杯“嗞”了一口,杯口的泡沫就像一层细腻的雪,喝在嘴里蓬松而冰凉。我又盯着浅蓝色的心形花签发起愣:“祝菲子开心!夏。”清秀的字迹,熟悉的句式,我仿佛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
纳菲并不看我,心不在焉地自个儿喝着酒。
“再这样下去,生意只会越来越差。”我坐到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酒吧说。
纳菲没说话,突然两眼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心虚地收回了目光。我假装整理鞋带。她继续盯着我。我感觉她已经看透了我的心绪,便没有再遮遮掩掩。
“我真想把她的脑袋砸开,好好看看她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她在想什么?比如她对我的感觉如何?我们对彼此都做了什么?”我拍着沙发说。若不是纳菲久未打扫,沙发扬起的灰尘令我打了一个喷嚏,我还要继续向她倾诉。我还有许多话想说,但我知道,即使我没有说,纳菲也已经知道。
“你最好别犯傻。”纳菲劝道。
“难道当初,你从来没想过掐死他?”
“掐死他?我爱他还来不及。”纳菲端起酒杯,想喝,又突然止住,冷笑一声说,“也许每个人结婚之后,都有过一两次想杀死对方的冲动吧。”
我从来没听纳菲说过这种丧气话,从小到大,几乎任何事,她都抱有耐心。所以我有些吃惊,但似乎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个刚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心情能好到哪里?但我和红英之间的事,除了她,我还能和谁说一说?我打算和红英离婚。现在,我开始犹豫要不要告诉她,她只会送给我一顿臭骂,我恐怕连一句安慰都讨不到。但离婚,也许是我和红英最好的选择。
已经有人给红英送玫瑰了!
我真想掐死红英。每次和她吵架,掐死她的想法有没有冒出来,完全取决于那天我的忍受力。二月十四日,红英精心化了妆,但脸色却比往日更难看,我知道,因为一直被困在家里,她只是希望这个特殊的日子能有一点别样的情趣,但能有什么乐趣呢?半个月来,迫于病毒的淫威,我们提心吊胆窝在家里,把防疫阿姨送的洋芋和白菜进行煎、炸、蒸、炒,早就倒腾腻了!我和她说话,她爱理不理,我把做饭包了,洗碗包了,把所有家务都包了,她还想怎样?总不能出去吃饭吧,据说所有馆子都关着门,真想出去放松,也没有可以庆祝的地方。想到花店的老板可以漫天要价,而我的公司却大门紧闭,我就更加生气了。晚上,我把红英搂在怀里,试着吻她,但她一把将我推开,然后翻个身,背对着我,一声不吭玩起手机。我心里隐隐作痛,甚至感到屈辱,我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她,怎么就和她结了婚?现在我感觉我对她并不了解,陌生得就像一个陌生人。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断断续续暂停营业,我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曾经我们对生活充满激情,但现在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在人群中挣扎。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医院,有时在海边,我在人群中寻找红英,满心慌乱,但根本找不到。我发现我对她根本不了解,似乎一只口罩就掩盖了我对她所有的了解。
“她根本不爱我。”我说。
“妈妈活着的时候,你也这么说。”纳菲倚着吧台,端着酒杯说,“也许你根本不懂爱,也许,你们男人都是绝情的动物。”
我斜靠在沙发上,看着酒柜上母亲模糊的照片。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永远被妻子或丈夫蒙在鼓里。只不过公司不能正常营业,只不过欠了银行一笔钱,贷款快到期,钱还没有着落,但红英就可以整天对我板着一张臭脸吗?况且当初开公司,借钱,我都征得了她的同意。
“你还坐着干吗?”几乎每天,红英都会像这样冷不丁冒出一句。
“除了坐着,还能干吗?”我说。
纳菲却说,我们闹成这样,原因不在红英,而是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包容红英。
难怪红英把米色的针织毛衣送给了她,两个女人已经好得可以穿同一件衣服了。因为贷款快到期了,每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加上对疫情的恐惧和焦虑,我早已对亲热失去兴趣。而红英总是扬起她白瓷一样的脸,用冷飕飕的眼神质问我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一直被困在家里,我整天活动在她眼皮底下。她真会恶人先告状啊!
刚结婚那几年,我们过得还算幸福。应该说开公司之前,或者说疫情爆发以前,我们都很幸福,幸福得我把纳菲忘到了九霄云外。那时,我和红英的生活四处充满了欢笑。我们手挽手一起购物,有时我会冲进厨房,和正在做饭的红英卿卿我我,有时我们也会躲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搂搂抱抱。每个星期一早上,当我起床准备上班,她都会把修长而白皙的小腿从被子下面伸出来,用脚背勾住我的小腿,说要我别走。
“可是,现在已经八点了……”
“给你十分钟……”
“我会迟到的。”
“五分钟,行不行?就五分钟……”
在那段幸福的日子里,这经常成为我和红英相互调侃的笑话。我们爱的电流完全可以为整座城市供电。我们生活无忧,也许这得益于结婚之前我买了一套房,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房价几乎翻了三倍。相对于那些刚结婚就在房贷的苦海中挣扎的夫妻,红英对我超前的投资眼光总是赞不绝口。那时候,我从未担心我和她的爱会从某一天突然开始衰竭。一切似乎已经好得不可能更好了,却偏偏忽然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就像急驰的汽车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然后我被甩出车外。
先是下班回家,饭没有做。刚开始,我以为这只不过是百年一遇的偶发事件。后来,我从红英的话中听出了微妙的变化。比如每天回家,我已经坐在沙发上,她总会无话找话地说:“回来了,老公?”语气中带着疲惫和失望,好像我不应该活着出现一样。为此,我不得不用类似的口吻反击:“回来了,媳妇?”
糖吃多了也会酸,现在我深有体会。不过幸好,不管是不是病,早发现早治疗,长痛不如短痛,一切总比由内而外慢慢糜烂来得痛快。早上,我和红英又吵了一架。
“一个准备逃走的人,她口袋里总装着一万个和你吵架的理由。”我说。
纳菲不搭话。
口很渴,我让纳菲再来一杯,没想到她突然冲我凶道:“想酗酒,你最好滚去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当然,我知道她这么说只是不想让我成为那个男人一样的人,那个男人经常酗酒,她没少挨拳头,有时候,她还得忍着疼痛帮他处理那些臭气熏天的呕吐物,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个男人是突然走掉的,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所以她对这段感情心有不甘。她曾经在电话里向我哭诉,说她不明白,她这么容忍和包容,那个男人为什么还要走?她开酒吧,就是希望那个男人某天回来,男人不是爱喝酒吗?她每天坚守在酒吧里,等待那个男人出现。
其实不用说,纳菲也知道我和红英又吵架了。纳菲在吧台后走来走去,说都怪我们一直没要孩子,如果有个孩子,我和红英就会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而不是整天盯着对方的缺点。
“幸好没有孩子。”我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但腿有点酸,腰也用不上力,然后我笑着说,“你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滚!”纳菲指着门外说,“你是故意来气我的吧!”
门外依然阳光白炽刺眼。斗争无处不在,人与病毒的斗争,人与人的斗争,正变得越来越剧烈。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往洗手间走,尿有点急,好像刚才那杯酒不是进了肚子,而是直接灌进膀胱。洗手间就在酒吧北角,先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再拐一个弯就到了,但门紧锁着。纳菲站在吧台后看着我笑,好像我上不了洗手间她非常解气。她说洗手间坏了,手依然指着门外。
可恶的女人!
我恹恹地往家里走。不回家,还能去哪儿?去朋友家?说起朋友,我就想到马春风和蒋小兵,想到当初开公司时向他们借了钱,当初说短借一年,谁知疫情突然爆发,钱迟迟还不上,现在已经快四年,其间他们没少催我。有一天,我甚至看见马春风和蒋小兵来到小区门口,气冲冲的样子,若不是进不来,他们肯定会冲上来给我点颜色看看。所以只能回家,但家里就像一只火药桶,只要我回去,随时可能爆炸。一想到红英无辜的样子和她脸上挂着的鳄鱼一样的眼泪,我就生气。现在,红英喜欢吵架已经胜过喜欢我了,新买的牙膏不是云南白药牙膏,要和我吵一架;洗衣粉不是立白薰衣草,要和我吵一架;盐巴不是海藻食用盐,也要和我吵一架……
曾经她是多么善解人意啊。就算我在股市亏得一塌糊涂,她也没有责骂一句,只是提醒我以后谨慎一点。
街道空空荡荡,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红灯,绿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忘了戴口罩。幸好路边的药店开着门,我歪进去买了一包。
戴好口罩,转进一条巷子,见一家文具店开着门,我便鬼使神差走了进去。老板怀里抱个相框,正窝在椅子里打盹。我干咳一声,男人仿佛从梦中惊醒,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对突然冒出来一个客人非常吃惊。也许他和我一样,只是跟老婆吵了一架,然后从家里逃出来,躲在冷清清的铺子里只求两耳清静?
“我想买把刀。”我比了比。
“这么长属于管制刀具。”
“是不是除削笔刀,你这里什么都没有?”
老板抱着相框,把我带到摆满各种美工刀的柜台前,然后将口罩拉到下巴上,露出满脸的胡茬和疲惫。我以为他会急着问我想要哪一款,没想到他竟然把相框放到柜台上,给我递了一支烟。这样我就注意到了相框里的女人,女人眉心落了一颗芝麻大的痣,双耳戴一对漂亮的珍珠耳环,站在一片金色的油菜花里。
“你老婆?”我随口问。
“走了。”
“蛮漂亮的。”
“我连她最后一眼都没见到。”
看来,老板也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我想马上回家,纳菲都护着红英,我为什么还要跟一个陌生人絮絮叨叨,说不定只会成为他眼中的笑话。我指指柜台里一把刀柄有木质桃纹的小刀,让他拿出来看看。
回到家,我小心翼翼观察家里的情况。我非常好奇红英在干吗,但我把大卧室和小卧室寻了一遍,都没发现红英的踪影。我打开衣柜,米色的针织毛衣好端端挂在衣柜里。摸了摸,似乎还有一丝余温。我躺到沙发上,将美工刀往茶几上一扔,心想这下好了,省得我和红英吵起来,然后用美工刀切开她的脑袋,看看她的脑袋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什么想法。想到这里,我露出一丝冷笑。
客厅一片狼藉。电视遥控器落在卧室门口,当时,红英就是用遥控器砸在我的额头上,现在我的额头还肿得像被马蜂蜇过;还有那只她经常抱在怀里的玩具熊,也被扔在地上;沾满眼泪和鼻涕的纸巾散落在垃圾桶周围;而那些被摔碎的玫瑰花,溅得满地都是。
“滚吧滚吧,最好永远别回来!”我和衣躺在沙发上,暗骂着闭起眼睛,想睡,却又睡不着。翻个身,脑子还是迷迷糊糊。红英去哪儿了?
为什么我睡着了,还听到窗外垃圾清运车的音乐声?为什么我没有睡着,嘴角却挂着口水?难道我刚才真的睡着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客厅的窗户没有关。
红英会不会从窗口跳下去?六楼,虽然不至于把她摔得粉身碎骨,但要她的命还是轻而易举,曾经我就想这么跳下去。我想起红英仰着头和我怒目相对的样子。“打啊,有种你就打下来!”她说。我掐着她的脖子,把她摁在沙发里。在此之前,我们先是听到一阵敲门声。红英跑去开门。谈话声很小,嘤嘤嗡嗡,我想看看门外的人究竟是谁,然而客厅的隔断挡住了我的视线。等红英回到客厅,她的手里已经抱着一束玫瑰。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收到花了,但我从来没有给她订过花!最近,她隔三差五就会收到一束满天星、百合或者向日葵,现在是玫瑰。
“谁……谁送的?”我感觉牙齿有些打颤。
洋溢在她脸上的幸福没有任何收敛。
我夺过花,心形的花签和以前的一模一样,字迹清秀:“祝英子开心!夏。”送花的人应该叫夏吧?应该是个男人吧?他们的关系绝不一般!
“他到底是谁?”我将花摔在地上。
我并没有得到红英的回答,而是额头上得到了一个遥控器。我扑上去,掐着她的脖子,把她摁进沙发里,然后我肚子挨了一脚。
我趴在窗户边,楼下一个人都没有,更别说红英的尸体了。几片被风扯落的银杏叶就像几只绿蝴蝶,在空中翻飞……
天蓝得透彻,云白而丰满。关上窗,风叫得更欢了,呜呜扑打着窗户。小区门外像突然落了一朵乌云,哦,不是,是一群人挤在药店门口,大约二十多个,好像正在吵架。
我感觉有人在向我招手。会是谁?我瞪大眼睛,想看个究竟,就真的看见纳菲在向我招手。纳菲不是在酒吧吗?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而且身着黑色的紧身外套。
我并不喜欢凑热闹,但我还是站到了人群外。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站到人群外的。反正我远远躲在人群后,不敢上前。马春风和红英正在吵架,蒋小兵站在一旁,用耗子一样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好像正在寻找我的身影。我觉得马春风和蒋小兵不好好待在家,冒着风险跑出来,不止要账这么简单。纳菲推了我一把,我知道,她想让我上去保护红英,但我死死拽着旁边的行道树。马春风把红英骂得越凶,我就越高兴。特别是想到平时红英和我吵架,总摆出一副吃人的样子,我就有种报仇的快感。
最好再扇她几耳光!
马春风还真扇了红英两耳光。
红英不甘示弱,反手抽回去,没抽到。马春风真的像一阵风,身子轻轻一晃,就闪到一边,然后又朝红英脸上送了几拳。
见血从红英嘴里流出来,我突然感觉胸口有点隐隐作痛,心想这么多年,自从我们在一起,就算最近闹得水火不容,我都没有真的打过她。但又想,她平时那么霸道,现在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对付马春风。
她却突然蹲在地上,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
“钱什么时候还?”马春风朝红英背上踹了一脚。黄色的脚印就像一条脏兮兮的舌头,落在红英的白T恤上。
红英晃了晃,差点摔在地上。
“依我看,那混蛋是不敢来了。”说着,蒋小兵也朝红英身上送了一脚。
见红英鼻子一直流血,我掏一包纸递给纳菲,但纳菲生气地走开了。我站在人群后,希望红英能顽强地站起来,然后用平时对付我的泼辣对付马春风和蒋小兵。骂不赢,打不过,总可以跑啊。快跑啊,笨蛋!但她一直蹲在地上,就像一只不倒翁,任由马春风和蒋小兵踢来踹去。
想到我从来没像这样打过红英,她现在却被马春风和蒋小兵打得满脸是血,我就有些生气。
应该住手了。
但马春风和蒋小兵并没有住手的意思。他们骂骂咧咧,时不时朝红英身上送出一脚,就算红英被打得蜷缩在地上,也没人站出来替红英说句话,更别说拉她一把了。
还不住手!我气得咬牙切齿。再这样下去,红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像这样打过自己老婆,自己老婆可能就这样被人打死,我突然无比愤怒。
我握起拳头,瞅准时机,趁马春风和蒋小兵不注意的时候冲进了人群。在人们的惊叫声中,马春风和蒋小兵各挨了几拳。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这么能打,这么壮实有力,竟然随便几下就把马春风和蒋小兵撂倒在地。然后,我拉起红英就往人群外跑。没人阻拦我们,只有马春风和蒋小兵追在后面,骂骂咧咧。
我牵着红英,先穿过一片栎树林,然后是下坡。长长的下坡。也许是下坡,我们才跑得那么快,快得步伐差点跟不上脑袋,有几次差点摔了跟头。我想起第一次牵着红英的手疯跑是在抚仙湖边,那时我们已经交往了半年,第一次出去旅游,一切都很美,夕阳西下,海风卷起的浪花亲吻着我的短裤和她的裙摆。我瞟了红英一眼,红英脸上竟然没有一丝血,我有些诧异,但并没有问,马春风和蒋小兵紧追在后面,累得我气喘吁吁,根本无法开口。
前面就是桥了。很远我就看见了那座桥,就听到了哗哗的河水声。红英以前的家就住在桥对面,山那面,我想起刚谈恋爱那会儿,无数个夜晚,我们甜蜜地从桥上走过,有时是我把红英接过来,有时是我把红英送过去。若不是我突然回头,我几乎忘了当初为什么会喜欢红英。那天阳光明媚,我记得她穿一件蓝色的牛仔连衣裙,扎一束高高的马尾,站在她奶奶家门前,我刚好从门前路过,所以刚好看见她迷人的微笑,就和现在一样,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两排洁白晶亮的贝齿。如果说她的微笑格外迷人,那么她整齐的贝齿就是能摄人魂魄的神器。我以为,她会一直把我们的爱情像珍珠一样含在她的贝齿之中。后来当我告诉她,令我第一眼就着迷的并不是她高挑的身材,而是牙齿,她根本不信。
“现在怎么办?”我拉着她的手,站在桥上问。
“钱呢?”她说。
“哪有什么钱。”
“那就只有跳下去了。”
我瞟了一眼后面,马春风和蒋小兵已经追上来了。但是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只有一座大山挡在前面。前面的路呢?我非常疑惑。以前我可是经常沿着山上弯弯曲曲的水泥路把红英送到山那面。但又能怎么样?这就是现实,许多路走着走着,突然就没有了。而我们却经常陷入“曾经”的陷阱,以为曾经有路,现在就应该有路。
“曾经我就想从这里跳下去。”她说。
“为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吵架吗?就在这里。”
那次我们站在桥上,很久,久得好像彼此都舍不得分开,手拉着手,就像现在,扶着白色的护栏,望着波光粼粼的水,听着哗哗的流水声。清白的月光洒在河面。而那样的夜晚,不知有过多少次。似乎总是等到那只躲在树林里的猫头鹰发出咕咕的怪叫,直到红英突然抓紧我的手说害怕,我才送她回家。在这座桥上,有着我们的许多回忆,有我第一次说我爱她,有我和她的第一个吻,也有我和她的第一次争吵,她的第一滴悲伤的眼泪。那晚,当我和她来到桥上,当她告诉我她有了我的孩子,我竟然充满恐惧。
“真的?”我希望她说的只不过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骗人的小把戏。
“你什么意思?”红英很生气。
我还没有做好做爸爸的准备,就连结婚,我都没有准备好。红英扶着白色的护栏,哭得很伤心,眼泪雨一样落进河里。如今,河水已经把她的眼泪带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悲伤留了下来。
“你怕不怕?”我问。
“不怕。”红英说。
“我先跳。”
“我们一起跳。”
一个愿意陪你跳河的人,会有多爱你!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涌出来。
“我先跳,然后你再跳,我在下面接你。”不等说完,我就跳了下去,因为马春风和蒋小兵已经追上来了。但落下去的时间太长,长得我以为不等我落到水里,马春风就会捉住红英。我感觉从桥面到河面只不过七八米高,但为什么我半天落不到河里?就像坠入了一个无底的噩梦的深渊。我甚至有一种失重的感觉,好像下坠中扑面而来的风把我托住了。我绷直身体,尽量让自己不会一头栽进水里。
看着奔腾的河水,我非常害怕。我突然想起来,我并不会游泳。
我掉进河里,砸碎了沉在河底的月亮,呛了好几口水,才从水里挣扎出来。马春风已经把红英按在白色的护栏上,恶狠狠看着我。我拍打着水,奋力抵抗着水的冲击,我试图飞到岸上,把红英从马春风手里救出来,但我却开始下沉,快速向水底沉去……
我感觉我就要死了。强烈的窒息感就像一座山压在我胸口,令我四肢不能动弹。我在挣扎中惊醒。我感觉自己就像真的掉进了河里,明明很冷,却又很热,全身大汗淋漓。我支起脚,待汗水收了一些,才彻底蹬掉被子,但脊背还是像被火燎到一样难受,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灼痛感了。我翻了翻身,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继续躺着。
天早已黑定。客厅的窗帘没有拉,窗外银月如钩,月光投进来,洒在沙发和茶几上,像一层水,白汪汪一片。地上散落着许多东西,但看不清是什么,肯定都是我和红英吵架的牺牲品。我坐在沙发上,点一支烟抽了起来。
我环顾一圈涌满月光的客厅,还是不见红英的身影c491a7ee36c04361292d6d873bfce367。然后,我盯着茶几上的美工刀发起愣来,哪儿来的刀?我将刀扔进抽屉。红英会在哪儿?我打算去卧室看看。
我站起来,又坐下。
我突然想起纳菲的话:难道没有男人,我们这些女人连一束花都买不起?我心里一亮,就像突然明白了什么,然后我点燃打火机,开始趴在地上寻找。玫瑰已经被我摔得七零八落,几乎只剩花枝,幸好浅蓝色的心形花签还在。借着打火机的微光,我看了又看,字迹非常清秀。
我拿着花签,踩着满地的花瓣向卧室走去。
门关着,我轻轻推开,酒味扑鼻而来。红英好像正遭受胃痛的折磨,蜷缩在床上,但已经睡着了。也许她已经睡着了。我蹲在床边,入神地端详着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一丝泪水,但长长的睫毛上还留着泪水曾经来过的痕迹——所有睫毛粘在一起。我把花签放在床头柜上,放在一个她睁开眼睛就可以看见的位置。现在,这枚花签就像是我亲自送给她的。我捡起倒在地上的酒瓶,大口喝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喝酒。我喝着剩下的酒,来到床的另一边,这边有着属于我的位置和枕头。
我拉起被子,悄悄钻进被窝,然后慢慢向红英靠去,直到我的身体与她的身体微微贴在一起。
红英一动不动。
我从后面轻轻搂住她,她还是一动不动。
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刚开始,我感觉床有一点冷,但慢慢就变得暖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