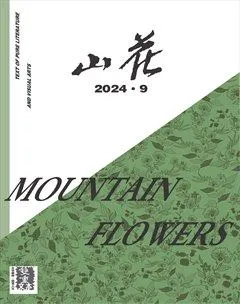赤水少年游
2024-09-14陈先发
上高中时,一年夏天,跟父母赌气,碰巧又刚读到法国诗人兰波,受了“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的蛊惑,发狠心去贵州浪荡了一大圈。
今天去追溯,再难想象那二十多天是怎么度过的。只背了个有破洞的旧黄挎包,揣着平时攒的不足百元的盘缠,和一张脏兮兮的省际地图。连洗换的衣服,也没带上一件,就怒冲冲地出了家门。记得真切的是,直到将手伸进小镇长途车站的售票窗口,才横下心,暗里咬定了目的地。一个全然陌生之处:贵州。
一种少年人特有的盲目而激越的胆气,充溢全身。没有一丁点对各种危险的预判。仓促间选定贵州,其实是受了些父亲的影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小镇上,父亲是一个非常醒目的漂泊者,跟足不出县的绝大多数当地人不同,他是一个推销员,每年有八九个月,他操着鼻音浑浊、拗口难懂的桐城腔,到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推销毛笔。我估摸这些以兔毛、猪鬃、黄鼠狼尾毛制作的毛笔,质量未必多么精良,所以父亲跑得越是僻远,毛笔的销路,似乎就越好……我心底一直刻着幅黑白画:好几个除夕,年夜饭前,我带着弟弟妹妹站在寒风中的老桥头,等着父亲归来。我们流着鼻涕,缩着脖子,跺着脚,仿佛闻到他从异乡带回的炼乳罐头、苹果、奶糖这些珍稀玩意儿的奇特香气。晚上,他讲的那些离奇故事,在我们眼前展开过一个神秘的世界,我第一次听到彝族、溶洞、天葬这些词儿,还有那些令人吃惊的风习……当他在饭桌上不停拍大腿讲着,他呼出的空气、打的喷嚏、每一次停顿,都让全家人紧张。而他讲得最多的一个地名,就是贵州。
这几日,好一顿颠簸!自合肥飞贵阳,换车至遵义汇川,再到珍酒的赵家沟基地。隔了这么漫长时光,终又来了赤水河流域。这真是很奇妙的一种感受——不管是途中昏昏欲睡时偶尔睁眼看向窗外的一刹,还是在下榻宾馆落地玻璃前静立的片刻;不管看见的是山林、村寨、隧洞,还是嘈杂的集市、清冽的溪水、排队过闸的货车长列——每一眼,仿佛都不是第一次看见,而是一种唤醒和重逢。黑白旧胶片中的记忆影像,似是幽闭在体内细胞壁深处,就等着这一瞬的按钮按下,恍惚中被释放出来,重播了一遍……只是这重播,另加了一层鲜亮的油彩。
当年楞头楞脑的少年游,真个是漫无目的,又全无顾忌。四下里游荡啊,每一天,仿佛总有挥霍不尽的蛮力,要快快地卸掉;要挖开体内的一道坝,让里面堵着的水,痛痛快快地泄出来。全不在乎走到的,是哪个县、哪个镇,也没有记下任何一笔当地风土人情。当时就从不上心,后来更是淡泊得全记不起353f1f1c548a718fa02c60043220b7fbad459b4e40b5d872bd03a74111379970,以至于想写下点什么,路线、地名、情节总是乱作一团,前后矛盾。不过,这么多年,让我感念最深的始终是,不管浪迹到哪一块,贵州从无一人欺我少年穷。扒运煤车也好,搭卖菜的轻卡、蹭乡间拖拉机也罢,有时对话叽里咕噜,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这少年心里,似乎从没为什么事儿慌张过。
而记得最牢的,有两处细节:一是在山间废桥洞里,睡了两个晚上。拱形老桥洞,离卵石密布的谷底有三四米,即便这是夏末,谷中也没什么流水,更没见到传说中赭红咆哮的河水。只是星空真的像是伸手可触,仿佛有亿万颗星星铺织的璀璨天幕,就盖在这老桥上。我在夜色中昏沉沉睡去,又不断地醒来。实在是太累了,躺下就像一摊淤泥。后来反复回味这段画面,倒真有点奇怪了,这样脏的山中废桥洞,怎么竟没有一点虫蚊叮咬,更没啥野兽侵扰,让两个少年睡得这么安生。
另一件,是某个晌午。从抛锚熄火的货车上下来,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山道上。蒸腾的暑气一层层晃动着,能看得见。贵州的夏天,比安徽凉爽,偏这一小块热得让人招架不住。山道像襁褓一般寂静。糙得皮开肉绽的路面,有几块残存的劣质柏油晒化了,走上去,脚底像踩在幽暗又强劲的拉力中,仿佛要将人定在蒸笼般的路面上。我的硬塑凉鞋原本就裂了大口子,没走几步,后半截竟生生拽断了,只好一瘸一拐往前走,又疲又饿。转过一处山脚,忽地眼前一亮,大喜过望。山坳处,竟有一家竖着招牌的小饭馆子。小跑过去,堂屋无人,喊了几嗓子,仍没人应答,就坐在小板凳上等。从后门吹来的穿堂风,沁凉入骨,满身臭汗一下子干爽了。过了好久,一个精瘦的矮个中年男人从门外抱着捆柴火进来。问,想吃啥?我指了指土墙上粉笔写的菜单第一行,就它了,猪油炒饭。便宜。
没一会儿,一股我没法描述的香味儿猛地钻入鼻孔。猪油炒饭,来了。接下来,应当先是狼吞虎咽,吃到一半时,忽然就放慢了。是不忍心一下子吃完的怜惜感?多年后,看周星驰一部影片,见到一个菜名“黯然销魂饭”,仿佛才从记忆中这份味道上,恍然回过神来。吃罢,抹抹嘴,愣了一会,忽地猛拍了一下桌子。
“店老板,再来一碗!”
是不是喊的店老板,记不清了。老板是哪一年才有的称呼?但猛捶桌子那一下,力道确有点失控了。插筷子的老竹筒,吓了一跳,从桌面咕噜噜就滚了下来。
这次来贵州的前一晚,正碰上几个诗人在合肥夜聚。我又讲起少年远行中,结交王迁的事。王迁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又黑又矮,眼窝深凹,性子特闷的一个人,可以两天不说一句囫囵话,但写起信来,又是个让人害怕的超级话痨。那些年,他给我写的信,很少有十页以下的。王迁是土城一带的人,除了添油加醋转述他爷爷讲的盐帮、船帮、马帮、茶帮、酒帮、戏帮、栈房帮、袍哥会等旧时“土城十八帮”的逸事,就是每封信要问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答王迁之问,一度是最让我头皮发麻的事儿。但毫无疑问,我对他信中描绘的川盐入黔、风云际会的水陆大码头土城相当着迷。我还专门买了一本分省地图,辨别土城、习水、赤水河等一箩筐的地名。只可惜,这次来,没去成土城,更是完全没有线索找到我和他曾住过的废桥洞。九十年代后的几次搬家,让两个萍水相逢的少年间大撂的书信,早就没了踪迹。
大概在1995年前后,王迁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后,突然地跟我断了音信。后来我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企图捕捉他的踪影,多年了,依然一无所获。也不知我最后寄他的一幅字,他收到没有。王迁一家人都嗜酒,他经常跟外婆、父母四人围桌而饮,每次都要喝到桌倾椅倒。那段时间,我迷上草书大家林散之的字,就顺手抄了林散之的一副联给他:“乘月归田庐,千载论交唯纪叟;大江流日夜,一生低首是宣城”。
怕他看不懂,我又附了封信讲讲谁是纪叟。李白寄居敬亭山下的宣城时,跟城中酿酒的纪老头交好,常常深夜在小巷中的这家小作坊买醉。纪老头孤老无依,死时也很是冷清。李白为他写了这首短诗:“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这是不是李白唯一为真正底层人写下的诗?不敢确定。一直偏爱这首小诗,情真意切,我觉得比《静夜思》好。
王迁给我寄过好几个小陶罐封装的赤水河酱酒。那些年,安徽人的舌尖只对古井贡一类的浓香酒敏感,这可是曹操举杯高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老牌子呀,印象中,没几个人愿意为酱酒一醉。近几年,大家忽然都对酱酒趋之若鹜了。想想王迁当年寄来的,是真正地道的土酱琼浆,翻箱倒柜再去找时,也早没了踪迹。
这次由皖入黔,在两边朋友小聚的餐桌上,我又讲起多年挂在嘴边的一个说法。要讲中国物产,真算得上苍厚爱的,其实只有两样:安徽泾县产的宣纸和赤水河边产的酱酒。这两样,是极特殊小气候下的产物,在世上任何别处,都不能复制。要做出上好的宣纸,必须集齐四件东西:韧性最佳的皖南青檀树皮、泾县小田块的砂田稻草、两条小河汇聚时酸碱度适中的河水、黏性奇特的皖南野猕猴藤汁。普天之下,能集全这四样的,也就泾县那一块地儿。而酿造这世上最美酱酒,需要赤水河畔特殊微生物菌群、从紫砂岩层穿行而生的矿化水、支链淀粉成分特别的红缨子糯高粱、秘而不宣的酱酿工艺等等,别处又哪能凑得齐?没有了宣纸,古来的书画艺术将寡淡几许;没有了赤水河畔的酱酒,今天国人的生活,似乎也少了份神采。造化之功,奇妙不可尽述,用爱因斯坦的话讲,老天设定的造物密码,谁也篡改不了。
在糟香扑鼻的珍酒车间,我目击了“走糟”“踩曲”工艺。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切近地踏入名酒的核心工序。车间的柱础上、砖缝和墙角,斑驳的薄苔中,处处散发着时间与发酵后粮食混成的独特气味。好酒中,自然地蕴藏着时光的秘义。据说珍酒酿造的用水,是赤水河流域的地下水。碰巧前两年我受诗人梅尔邀请,到访过邻近绥阳县的十二背后溶洞群。梅尔曾指着约一人高的石笋说,滴水凝成这根笋子,需要七亿年时间。这赤水河的地下水,点点滴滴,穿缝过隙,层层提纯、酿制,最后成了一杯琼浆。好酒中,当然也包含了对人的生命的相逢、相认。精壮汉子走糟,精巧女工踩曲,也仿佛是人的蓬勃生命以这种渗透的方式,进入到酒的酿制之中。人世间,无论是“浊酒一杯喜相逢”“西出阳关无故人”,还是“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哪一场酒,不是生命与天地万物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深刻对话?我应向那个在旧光影中埋头吃着猪油炒饭的少年,敬一杯酒吗?
另外,从资料中我得知,因珍酒快速扩产的催动,附近山民们种植的“懒汉高粱”价格,比别处高出了三到四倍。这个数字最让人开心,因为我熟悉一粒种子从入土到入仓的艰难过程。每一粒,每一人,每一杯中,其实都有着关于利益、情感与生命发现的动人故事,此处且按下不提。
古往今来的酒之好,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它包含了人之寄托。在我抽屉深处的日记本中,我曾为赤水河边的少年游,写了一句诗:“今夜,河水不会高于我发烫的嘴唇。”
嘴唇滚烫,可能因为与好酒相逢,也可能因为一些更为内在的东西。人在少年时,酒是眼界、豪情、游历与憧憬,是朝向来日的催化剂。中年之后呢?正如此刻微酣中走到堤上吹风的我——酒是体内无碍无顾、时而陷于记忆与执念的一场少年游。一场无边无际,也无始无终的少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