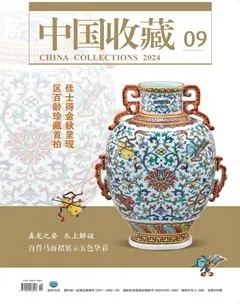真龙之姿 爪上解谜(下)
2024-09-14奚文骏
在上一期《中国收藏》杂志中,本文作者带领我们透过传世明代瓷器,窥见了明末龙纹使用日趋失控、王朝走向衰落的一段历史。那么,与一度严格管控龙纹瓷器的明代相比,清廷对龙纹的使用权限、对民间烧造龙纹瓷器的态度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明代朝廷对龙纹的使用管控在总体上采取了严格的态度,直至明末社会动荡、朝局危难,才终于无暇于这些形式细节。进入17世纪以后,龙纹瓷器在民间的使用权限一下变得松弛,大量五爪龙纹瓷器在民窑生产出来,百姓一时以拥有五爪龙纹瓷器为荣,以书有施主姓名的供器尤为多见。这一现象一直持续至明朝结束。1644年,随着满清入主中原,新王朝对龙纹瓷器的控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谓清承明制,满清入主中原之初,在国家典章、驭民政策等诸多方面都沿袭了明代的制度。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证明,但顺治帝入关之后应是对龙纹的使用有所管控的,因此似乎一夜之间,五爪龙纹瓷器便在民间消失了。一件顺治十一年(1654年)款的青花四爪龙纹三足朝冠耳炉表明,不论是出于朝廷的要求还是民间的自觉,延续明末产自民窑的用于供奉的瓷器上,龙纹的五爪已经悄然改为四爪(图1)。

清初秉持宽容态度
目前的史学观点认为,入主中原的满清朝廷在统治中尽量表现出了宽松的政策,以稳固自身的执政地位。传世实物表明,自顺治朝以来民间用瓷虽基本不见五爪龙纹,但四爪龙纹的使用未见中断。这说明在清初的政策中,龙纹的使用不再等级森严,皇家仅掌握了五爪龙纹的支配权,并未限制民间使用其他形式的龙纹。
据官修的《皇朝文献通考》,顺治八年(1651年)“时江西进额造龙碗,奉旨: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此时江西甫定,地方为讨好新朝,自主烧造了龙碗并进献给皇家,而皇帝则表现出与民休息的姿态。一派臣恭帝贤之下,表明了朝廷对民间自主烧造龙纹瓷器的宽容。此后,从顺治十一年起,清廷在景德镇多次烧造龙缸,均未成功,最后也只得作罢。上述龙碗和龙缸目前均未见传世遗物,但从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几件顺治款娇黄和茄皮紫釉龙纹盘来看(图2),顺治时期宫廷使用的龙纹瓷器当为五爪,并且很可能是委托民窑烧造的。
康熙初年,清廷一方面陷入与郑成功的战争,一方面又经受了三藩之乱,官民之间的关系相对严峻,因此当康熙二十年(1681年)朝廷启用御窑厂大规模烧造宫廷用瓷时——此时的御窑被称为“臧窑”,在体现皇家威严的五爪龙纹的使用上也就比较谨慎。从目前传世实物来看,“臧窑”产品主要以宫廷实用器和赏赐器为主,其中就有大量的五爪龙纹碗、盘,显然主要用于内廷餐饮。当中有一类“臧窑”青花地绿彩和青花地五彩龙纹碗,最初以青花绘制了五爪龙纹,但施彩时被小心地用深色颜料涂去一爪,改绘为四爪(图3、图4),颇有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五爪龙纹降级使用的味道,说明这两种龙纹瓷器在当时的使用中存在某种限制。而同样品种的碗、盘,当康熙末期“安窑”再行烧造时(当前研究已经支持通过款识判断康熙官窑的烧造时段),便已光明正大地使用了五爪(图5、图6)。由此可以看出,清廷对于五爪龙纹的管制在康熙二十年前后是尤为严格的,但时至康熙末期,随着满清执政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使用规制也就没有早前严格了,至少可以说五爪龙纹瓷器的使用范围放宽了。





龙纹特权彻底放开
乾隆初年,一次重要的君臣谈话代表了清代皇帝在龙纹使用上的重要态度变化。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皇帝传旨给时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的唐英:“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表示以后御窑厂的瓷器淘汰品在景德镇折价变卖即可,不用运往北京。唐英于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二十日上奏皇帝建议道:“国家分别等威,服物采章俱有定制,故厂造供御之瓷,则有黄器及锥拱彩绘五爪龙等件,此等器皿非奉赏赐凡在臣下不敢珍藏擅用……请将此选落之黄器、五爪龙等件照旧酌估价值以备查核,仍附运进京,或备内廷添补副余,或供赏赐之用,似可以尊体制而防亵越。”乾隆皇帝则朱批回复:“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
这段对话揭露了清早期至中期朝廷在龙纹瓷器管控上的变迁:其一,清初朝廷沿袭了明代的做法,将五爪龙纹瓷器视作皇家专享,但经由皇帝赏赐,臣民是可以拥有和使用的;其二,时至乾隆初期,朝廷对龙纹的管理已经比较松弛,民间私用五爪龙纹瓷器的情况已然存在,以至皇帝都知道“外边常有”;其三,乾隆八年,经由皇帝授命,以变卖御窑厂次色瓷器的方式对民间直接开放了流通、使用和仿制五爪龙纹瓷器的权限。
这代表着乾隆皇帝对五爪龙纹特权的放弃,自此以后民间均可使用,五爪龙纹不再作为特权阶层的一种图像化的表征。虽说如此,由于古代政令落地实施的延后性以及民众的观望态度,直至嘉庆朝以后民间五爪龙纹瓷器才多起来。总体来看,康雍乾三朝民窑瓷器绘制五爪龙纹的情况不甚常见(图7)。

色彩昭示位份高低
虽然清代没有像明代一样赋予龙纹森严的社会等级含义,但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仍需要某种形式化的表征。以清廷后宫妃嫔为例,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8个等级,不同位份的妃嫔享有不同的衣、食、住、行标准,在瓷器的使用上也有着相应的规定。
根据乾隆七年始修的《国朝宫史》卷十七《经费》篇,各等级妃嫔的专用位份瓷器包括:皇后用黄色瓷器6 6 0件,皇贵妃用白里黄色瓷器14件,贵妃用黄地绿龙瓷器14件,妃用黄地绿龙瓷器12件,嫔用蓝地黄龙瓷器12件,贵人用绿地紫龙瓷器10件,常在用五彩红龙瓷器10件。
这些不同颜色的位份瓷器更多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主要用于重大典礼和宫廷筵宴,以表身份之别,妃嫔在日常餐饮中可能更多使用宫中按规配发的其他普通瓷器。因此除身为一国之母的皇后所用黄色瓷器的品种和数量较多外(图8),其他等级妃嫔的专用位份瓷器仅盘、碟、碗、盅各几件而已,从颁制《国朝宫史》同时期的乾隆传世御瓷推测,可能但不限于九寸盘、六寸盘、中碗、茶盅等形制。
其中白里黄色瓷器即内白釉外黄釉瓷器,可能是素黄或暗刻龙纹的(图9);黄地绿龙瓷器是娇黄地暗刻龙纹填绿彩的装饰(图10);蓝地黄龙瓷器是青花地留白龙纹二次加绘黄彩的装饰(图11);绿地紫龙瓷器是娇绿地暗刻龙纹填紫彩的装饰(图12)。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朝宫史》规定的皇贵妃以下的专用位份瓷器数量实在太少了,因此并非所有御窑生产的上述品种的瓷器均属位份瓷器,多数可能只是皇家的日常用瓷而已,未必包含特殊的含义。





传世实物印证文献
《国朝宫史》记载常在所用的五彩红龙瓷器,传统研究一般认为是指五彩龙凤碗(图13),但从形制和纹饰来看,可能并非如此。一方面,五彩龙凤碗所见主要为大碗、中碗、汤碗3种,历朝传世数量巨大,但未见《国朝宫史》规定的盘类制品;另一方面,五彩龙凤碗纹饰由龙凤组成,与记载不符,也与其他认定的妃嫔位份瓷器不同。穷举乾隆朝传世御瓷实物,可能常在所用的位份瓷器应是此类青花地五彩龙纹瓷器(图14)。
若如此,上节所提“ 臧窑”青花地五彩龙纹瓷器改绘为四爪的原因便可以推测为,在彼时的后宫,常在这样的低位份妃嫔可能并不允许使用五爪龙纹瓷器(见图4),但在康熙末期情况即发生了变化。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遗留问题,康熙时期的青花地绿彩龙纹瓷器(见图3)又是什么性质?从传世实物来看,这类青花地绿龙瓷器仅见康熙一朝生产,并且见有足尺盘、九寸盘、中碗等多种形制,且都存在“臧窑”时制品抹去一爪的现象,因此可以认定为这是当时的规制所在,而非偶然现象。但时至乾隆时期,这类青花地绿彩龙纹瓷器便不再生产。
如果参考康熙“臧窑”时期青花地五彩龙纹瓷器抹去一爪而绿地紫龙瓷器保持五爪的现象,此时的青花地绿龙瓷器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位份瓷器品种,当然也有可能青花地绿龙瓷器排在青花地五彩龙纹瓷器之后。也就是说,在“ 臧窑”生产的时候,宫廷所定妃嫔位份瓷器可能是:贵妃用黄地绿龙瓷器,妃用蓝地黄龙瓷器,嫔用绿地紫龙瓷器,贵人用蓝地绿龙瓷器,常在用五彩红龙瓷器。由于贵人、常在在妃嫔中位份较低,不受册封,因此按当时的规定这两种位份瓷器使用了四爪龙,但康熙末期就取消了这样的规定。之后的雍乾时期不知何故减除了其中的蓝地绿龙瓷器,而使贵妃、妃共用黄地绿龙瓷器,嫔使用蓝地黄龙瓷器,贵人使用绿地紫龙瓷器,常在仍使用五彩红龙瓷器,从而形成了《国朝宫史》中规定的妃嫔专用位份瓷器惯例。



结语
龙纹在明清时期曾被视为皇权的象征,其使用规制是极其复杂的,瓷器只是其中一种载体而已,当时朝廷的规定是一方面,具体到实施和执行程度是另一方面,留存到今天仍为我们所见所知的史料、实物留存又是一方面。我们今天试图通过这些留存资料的蛛丝马迹去拼凑和还原明清两朝龙纹瓷器的使用规制和实际存在的历史现象,其多样性和随机性肯定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所能涵盖的。本文试图通过传世实物观察,对史料的记载做注释、对文献的缺失做补充,从而归纳龙纹瓷器使用中可能明确规定或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制,揭示龙纹瓷器在明清两代使用中存在的一些特殊现象。希望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收藏工作提供更多的线索和参考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