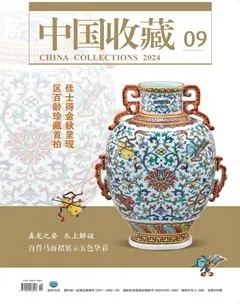动静相生 见书生意
2024-09-14慧鉴堂主人
今天我们来欣赏两件篆书作品,它们均涵义深邃,直指奥妙——有动有静,动时波涛汹涌,静时可照万物。因果转化,动静相生,即洞察一切却不被矛盾束缚,不被欲望捆绑,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见书而意生,两位名家篆书展现的正是此意。
婉约中有劲健
唐孙过庭《书谱》曾说“ 篆尚婉而通”,清刘熙载补充道:“余谓此须婉而愈劲,通而愈节,乃可。不然,恐涉于描字。”今天我们要说的金城书法对联正合“婉而通”,不露锋芒,“婉”中有劲健,“通”中有节制。其中锋用笔,线条饱满、圆转、通畅。
金城(18 7 8年至19 2 6年),近代画论家,书画篆刻家。原名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浙江吴兴人。出身文化艺术世家,幼即嗜画,兼工书法、篆刻及古文辞。1918年与周肇祥、陈师曾等在北京筹建中国画学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创“湖社”形成画派。筹设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隔年举行一次。偕同陈师曾诸画家赴日与会,将中国画和中国画家推向海外。有《金拱北印谱》《藕湖诗草》《画学讲义》《北楼论画》等传世。
其美学画论主要体现在19 2 2 年所作的《画学讲义》中,该书分上下卷,涉及面极广,论点深入浅出,我们不妨选几段看看:“画之可传,全在气韵,无气韵之画,工匠而已。盖气之来源在乎笔力,而韵之流露,在乎修养。”
“画,美术也,应从美字着想。曰古茂,曰苍润,曰秀逸,曰荒寒,虽粗豪工致,画法不同,而各有美之观念存乎其中。古茂者,气味醇厚,色泽浑朴,是美之发于静穆者也。苍润者,草木华滋,峰峦峻厚,是美之发于雄伟者也。秀逸者,沙明水净,林木萧疏,是美之发于清幽者也。荒寒者,枯树断云,长空岑寂,是美之发于淡远者也,总之观画者各各有好,作画者应就性之所近而专工之。古茂一派,须令观者生静穆之想。苍润一派,须令观者生雄伟之想。秀逸一派,须令观者生清幽之想。荒寒一派,须令观者生淡远之想。质言之,凡制一幅图画,能引人入胜,斯为美矣”。
画“无旧无新,新即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作画者欲求新者,只可新其意,意新固不在笔墨之间,而在于境则艺术自然臻高超矣”。“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者流,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腆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无愧乎?”
不难看出,金城的画学经验与审美思想通古达今、比对中外,非常可贵,对当前文化艺术仍具有指导意义。他无疑是一位被历史低估了的艺术大家。2023年5月5日,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防止近现代珍贵文物流失,国家文物局列有“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金城代表作名列其中。

金城此作释文为:“笔浚宗工,激赏每垂青,庭雍亲睦;学耽沉思,朗月在川波,笃孝友家。”钤阳文“金城印信”,阴文“巩伯”。上款题识:“伯宛先生方家属书金石文字为联,即希大雅鉴之。”落款“丁巳(1917年)二月既望 吴兴金城篆于墨荼阁”。 钤“金城印信”阳文印(见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名家印款录》上卷第855页),“巩伯”阴文印(见前述书籍第854页)。其字的行体优美、沉厚、挺拔,金石味道十足。这正是“篆之笔法当圆,过圆则弱而无骨;结体当方,过方则刚而无韵”。其字势上也有变化,秩序感极强,既整齐划一又点画挪让,既有篆书的立体感,又有篆书的弹性感,审美效果极佳。其上款人“伯宛先生”或为吴昌绶。吴昌绶(1867年至?),字伯宛,一字印臣、印丞,号甘遯,晚号松邻,藏书处名曰双照楼,浙江仁和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入民国后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以藏书、刻书著称,并精目录金石之学,诗词笺奏,涉笔皆工。
轻盈中显刚柔
我们再看一件篆书作品,该作题识:“观菁女士正琢。乙酉(1945年)九月集石鼓字,弟吴敬恒时年八十有一。”钤阴文“敬恒金石长寿”,阳文“稚晖八十以后书”(两印均见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名家印款录》下卷第2174页)。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其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718字。唐宋以下学篆者,无不推崇,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文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特点是字体线条化,线条均匀柔和,十分简练生动,空间分割均衡与对称是其特点。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四体皆擅的书法大家邓石如就从石鼓文中获益,著名书画家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其书写者为吴敬恒(1865年至1953年),字稚晖,江苏武进人。25岁入江阴南菁书院,1891年辛卯科举人。1901年春留学日本,1902年5月任上海爱国学社教员。1903年利用《苏报》鼓吹革命,同年“苏报案”发生,被迫去英国。1905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唐山大学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与蔡元培赴欧,待袁世凯逝后回国,与钮永建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任主编。1920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成立,任校长。1923年回国,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代主席。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故宫博物院参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10月30日因病去世。

68.5厘米×25.5厘米
吴敬恒一生官衔数不清,是知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在清末民初四大书家中,以善写篆书为代表。他自幼习大篆,得益于《石鼓文》《散氏盘》等一些钟鼎金文。其用笔看似轻盈疏淡,实则刚劲内敛、柔中寓刚,静中有动,虽笔势整齐,但整齐中有参差。其晚年的篆书可称得上炉火纯青,人书俱老。
此两位近代大家之作虽都是篆书,但风格不同,长联短句,形式各异。它们都是中锋用笔,但又各有所重。从内容上看,两作又都极为罕见,寓意深刻。明代著名大学者、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1526年至1590年)认为:书画重具象之体,诗文重意义之用。他将书画归为一类,诗文归为一类。书画相比诗文来说,更为重体,学习时可以从临摹入手,摹写其象进而领略其意。诗文则不然,相比书画的具象而言,诗文之象是抽象的,不能直接临摹,而更重其意。他曾说:“书画有体文无体,书画无用文有用,体故易见,用故无穷。”书法绘画本身都是技,都是形;诗文的内容才是意,才是神。“画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绝矣;书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绝矣;唯于文章更万古而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