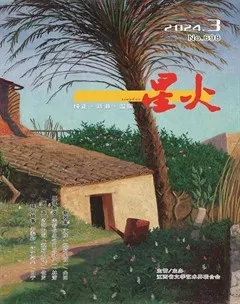旋转木马(短篇)
2024-09-11陈修歌

一
花铃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有了新家。她光着脚站在窗边,伸手触摸绛红色油漆剥落后在窗棂上留下的瘢痕。风一吹,两扇窗户“吱呀吱呀”地响,扑到纱窗上的,不只有蔷薇花香,还有雪白杨絮和不知名的小飞虫。一张小巧而饱满的蛛网搭在窗户与屋檐形成的折角之间,日光在上面跳来跳去。
这个梦过去没多久,花铃跟着妈妈来到黄山栾街22号。一个暂时只需要花铃开口叫叔叔的男人摸出一长串钥匙,挑中了其中一把。
花铃面前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
“就是这儿,收拾一下。”叔叔看向花铃的妈妈。他左边那只义眼,呈现黯淡的蓝色,异质而神秘,竟比那只瞳孔直径不够大的正常右眼好看。
花铃抱着巧克力色的小熊,跟在妈妈身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间房子一如她的梦。后来她也糊涂了,那究竟是梦,还是幻觉的无数触角错乱地交叠进现实里,让她的记忆出了错?
她推开窗户,观察起掉落进窗户缝里的绛红色漆皮,粘在绿纱窗上的杨絮和飞虫,还有檐下的蛛网……她看到窗外是一个小花园,但疏于打理,花砖墙上爬满了张牙舞爪的蔷薇藤,像垂挂着一条条绿色瀑布。
花铃两颊发烫,郑重其事地将巧克力色的小熊摆在了铁架床中央。
“不会再搬走了吧?”叔叔离开后,她小心翼翼地问妈妈。这两年,母女俩经常搬家。花铃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俩人搬进一幢高层里,房间宽阔而明亮,花铃可以在落地窗下搭积木、拼拼图。没过多久,争吵的声音像一条条闪烁而细密的电流,频繁地刺痛她的神经。花铃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喘不上气。很快,她们搬走了。接纳母女俩的,是一座位于某条旧胡同深处的低矮平房。在这里,水泥地面凹凸不平,卫生间的墙壁上蔓延着雨水淌过的灰黄色渍痕,空气中来回飘荡着厨余垃圾霉变的味道。她们到的第一天晚上,突然停水停电。花铃抱着巧克力色的小熊坐在一片混沌中,听妈妈用一只塑料桶屋里屋外来来回回地拎水。狭小的窗户外没有星星,漆黑一片。
妈妈终于忙完了,能空出手抱一抱花铃。她反复道歉,向女儿解释只能找到这样的房子,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花铃抬头看妈妈。月光下,妈妈的眼白微微发蓝,像覆着一层海水。很快,里面浪花涌动。一滴泪落在花铃手背上,迅速向低处隐匿。感受着手背上那条洇湿的路,花铃知道,妈妈一定还有办法。
那个梦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幻生的。然后,花铃美梦成真。
黄山栾街22号同样老旧,但是老旧得有腔调。房子坐落在大学校园深处,有个窄窄的门厅,外墙被粉刷成天蓝色,窗框和前门是白色的。这样漂亮的房子站成两排,组成一道美丽的景观。偶尔有学生绕到附近拍照片。花铃从窗户探出半边身子张望,立刻被妈妈喝止。
校园里的林荫道宽阔畅达,径直通向气派敞亮的校门口,但妈妈非得带花铃拐向一条弯弯绕绕的窄巷子,从一个旋转小铁门进出校园。这个小铁门是学校为了方便家属区居民外出采买而开设的,一推开就是一条街市。拉着小推车从小铁门进进出出的,多是职工家属或保姆。母女俩低着头,行色匆匆。被熟食、水果、冷鲜……各种味道熏过一遍后,花铃终于站到了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切豁然开朗:高高的公交站牌,“嘀”一声的学生卡,天蓝色的塑料座椅,抱在怀里的双肩包,有时勒脖子的红领巾……她在课堂上大声朗读着课文,那些句子在阳光下大胆地发着光。
一个百无聊赖的傍晚,花铃在衣柜底层的一叠报纸中发现了一本薄薄的日记。扉页上写着“四年级一班,桑元”。花铃翻看日记上的时间,只写了月和日,没有年份。日记本的主人应该比自己大,花铃想,因为日记本封面已经泛黄了。前几篇日记带着红笔留下的“阅”的印记,像随意应付的家庭作业。每篇日记的前两个字永远是“今天”,然后流水账一样记着一些男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比如足球、奥特曼、桃园三结义和麦当劳。
后来,红笔印记消失了。一些秘密在日记本最后几页被潦草记录。花铃囫囵吞枣地看完了,她感觉喉咙里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上气。她要缓一缓,才能得到勇气再看一遍。哪怕后来她看了无数遍,甚至准确捕捉到了笔画间的一些情绪。透进窗户的一束束白光逐渐减弱,最后残留下一团雾蒙蒙的棕色颗粒,附着在空气中,缓缓下降。很快,天完全黑了。花铃打开了电灯。
3月7日,星期一,晴。开学满一周了,我们要搬家。搬去新家后,爸爸妈妈就不吵了。一定,一定,一定。
3月12号,星期六,阴天。小金刚死了,我把它埋在了梧桐树底下。我知道它是怎么死的。该死的不是它,是那个长头发的女妖怪。
3月13号,星期日,晴。今天在游泳馆又碰到班上那个该死的家伙了,他说爸爸是独眼龙,我想冲上去揍他。但我忍住了。妈妈骂爸爸会更难听,嗯,奸夫yin妇。我恨。
…………
无数个念头从脑海中升起,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迟迟不肯落地。花铃想起有天吃早饭时,她往厨房里瞥了一眼。妈妈正在盛汤。叔叔从背后揽住她,将一个钱夹轻轻塞进了妈妈腰间的围裙口袋里。那一瞬间,妈妈脸上流露出一种花铃从未见过的表情—亲昵而讨好。总之,妈妈的目的达到了。
花铃迅速收回目光,装作什么也没看见。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她应该试着习惯。起码现在的境遇胜过从前—她们有舒服的房子住,不再饿肚子。更重要的是,妈妈又重新端起了颜料盘。她穿着宽大的米色罩衫,用一条波光粼粼的绸带将长发挽在肩前,脸上挂着的,不再是一张画也卖不出去的忧虑,而是享受其中的随意和满足。花铃喜欢这个模样的妈妈,她会联想到曾在圣米埃尔教堂里见到的圣母玛利亚画像。很久远了,那时她学着画里人物的样子,眼睛微微眯着,双唇弯出温柔的弧度。有时她偷偷睁眼,觑着端坐画中的玛利亚。玛利亚朝她抿嘴微笑,头发边缘处镶着一层斑驳的金边,丰腴的手臂自然地垂落腿间,寂静而圣洁。哦,那就是妈妈。花铃想象自己变成赤足的小天使,扇动着翅膀飞进画里。
二
自从花铃看见日记后,一根不安的链子就开始形成。后来的一件件事像一颗颗珠子不断连缀,将这根链子越编越长。母女俩中的一个必须给出信号。瞬间的憎恨,莫名的敌对……如同刀刃上的闪光,暗示着争吵的发生。
“走开,”花铃在过小区旋转门的时候,书包带被铁栏杆上凸出来的一颗螺丝钉挂住了。她下蛮力去扯,“走开!”她看见妈妈面无表情,又大声说了一遍。书包带断了,花铃推开妈妈,头也不回地跑了。
早在起床时,她就开始找茬。原本只需要五分钟就能结束的刷牙和洗脸,她磨蹭了很久。妈妈敲卫生间的门,问她怎么了。她想说快了,但糊了一嘴的牙膏沫让她突感气愤。牙刷在嘴里粗鲁而用力,她很快尝出一丝牙龈出血的腥甜。紫色的塑料水杯在地板上“嗒嗒嗒”跳着滚了一圈,最后被一根水管挡住去路……花铃终于坐到了餐桌前,她因为要努力抑制住泪水而憋得双颊通红。
“是不是生病了?”妈妈伸手摸她的额头。
花铃没躲开,也没说话。昨晚风有点大,而窗户全部敞开着—她想闻到蔷薇花的味道。她的确有些发烧,妈妈准备带她去医院。
“是用我们自己的钱吗?”花铃极力装作漫不经心,将餐盘里的煎蛋一块块拨碎。叔叔当然不在,他坐在这张餐桌前吃饭的次数并不多。他会在哪儿?那个家吗?他和妈妈什么时候见面?很多疑问,花铃只能凭空揣测。
花铃刻意低着头。她听见妈妈抽泣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弹拨着她的神经。花铃将拨碎的煎蛋拢在一起,全部填进嘴里。
“不去医院,去上学。”花铃说。她仍不肯抬头。
走出旋转门,穿过卖菜的小巷子,花铃站在了宽阔的街道上。她抬头看见远去的飞机在空中拉出一条白线,刺眼的阳光照亮了高楼上的一块块蓝色玻璃。马路上,一辆辆小轿车匆匆驶过,坐在里面的男人都是神情自若的样子。他们的太太大概不必在冬天戴着橡胶手套一遍遍浆洗厚重的衣服,更用不着买隔夜削价的面包。妈妈现在不再推说自己不习惯吃新鲜面包了,她报复性地买来很多面包,整齐地码在冰箱里,直到过期都吃不完。她像个正牌太太,一部分时间用来烫头发做指甲,另一部分时间则熨烫衬衫、研究食谱—打理漂亮房子里的一切家务事。除了不能抛头露面,其他没什么不同。
事实上,这次的情形跟之前的确不同。说不上是更过分,还是获得了幸运。
花铃最终见到了日记的主人—那个叫桑元的男孩。桑元比她大一岁,个头则比她矮一点,圆脸颊旁围绕着微微发黄的鬈发,两只眼睛明亮而有神,浓密的眉毛和上翘的嘴角与叔叔如出一辙。
桑元和花铃成了兄妹。两人从各自的视角目睹了这个故事。桑元的妈妈作为无辜的一方,声称自己厌恶这场婚姻带来的一切,包括孩子。她只需要钱,越多越好,去治疗该死的抑郁症。花铃的妈妈则遭受了很多谩骂,甚至殴打—正常生活一度难以为继,总会有人堵上门来。没有人同情她,毕竟最后的好处都是她的,不是吗?她在另外两个人办完离婚手续后的当天下午,洗了澡,喷了香水,找出一条系腰带的白色长裙,踩着一双浅口高跟鞋出现在了她之前不敢露面的地方,比如邻居家的花园门口。花铃曾在这里给妈妈拍照片,那时,花园里的几株牡丹热烈得一览无余。镜头里的妈妈多美啊,她面颊饱满,身材匀称,蓬松的长发披在肩上—像牡丹花一样国色天香。梦幻的氛围并未持续多久。邻居家胖太太从花园里走出来,毫不理会母女俩脸上示好的笑意。她打量商品似的打量着妈妈,冷不丁地嘲笑了一句:“怎么敢招摇过市的。”
眼下,牡丹花期已过,占据花园大部分空间的,是五颜六色的百日菊,憋着一口气似的,开放得密密麻麻,展现出异常茂盛的气象。
太久了,花铃被妈妈护在堡垒之中。妈妈接送花铃上下学的时候,从不肯拉她的手,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并有意与她隔开一段距离。花铃很明白,必要时,她甚至不能承认这是妈妈。这种做法会让妈妈感到某种层面上的欣慰。不经意间,花铃感觉自己性格中的有些方面消失了,有些则顽固地保留了下来,还有一些,是新滋生出来的,比如察言观色的本事。
在一个周五下午,两个孩子被安排面对面地坐在一家儿童餐厅里。扎蓝色领带的男服务员麻利地把两只餐盘摆放到他们面前,然后分发亮晶晶的刀叉。甜点、牛排和披萨依次被端上来。两个孩子默不作声,低头自顾自地吃着。形势尚不明朗,他们能做的只有服从。
吃完之后,他们会前往同一个家。他们会用周末的两天时间,熟悉彼此,接受现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都会安定下来的。”在车里的时候,两个大人盯着车头与前车车尾之间的一片虚空自我安慰。两个孩子继续默不作声,除非有人要他们做出回答。花铃坐在后排座椅上,紧贴着一侧车门—尽量离桑元远一些。
车子驶过沿海公路,波光粼粼的海面映照得天地一片明亮。夏天的时候,花铃曾越过质感粗糙的沙砾沙滩,一路往大海里走。越往里走,沙滩越柔软,好像大海在引诱着你往里走。花铃忍不住脱掉鞋子,让细腻的沙子在脚趾间流动。终于,浅浅的海水漫过脚背,花铃却感觉害怕了。一个浪头涌上来,雪白的浪花张开无数触角奔袭而来,花铃“啊呀啊呀”地跳脚跑开了。
卧室做了重新分配。花铃抱着巧克力色的小熊去了顶层阁楼改造出的一个单间里,这并非妥协—她只是把桑元的东西还给桑元罢了。她希望借此减轻桑元的痛苦,她怕那些痛苦变成仇恨,蛰伏在心思幽微处,等待一击致命的时机。
三
一切看似安定下来了。桑元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透明鱼缸,里面有几块干燥的赭红色鹅卵石,外面则顺着玻璃壁积满了层次不一的灰。“该买几条鱼装进去,”妈妈站在一边,“爸爸说你喜欢鱼,会给它们起名字。”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讪讪地退出门口。
暑假里,两个孩子趴在窗台上看鱼,花铃想都没想就给一条遍体金黄的小金鱼起名叫“小金刚”,她当然不会提起那本日记。
“我爸告诉你的?”桑元有些恼怒。
“嗯?”花铃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她在想那本被藏于书架背后的日记,是否找个机会转移,或者干脆销毁。傍晚时分,金鱼们因缺氧而时不时上浮,鱼尾在水面搅动起无数条颤动的涟漪。该给鱼换水了。
“不,我有过一条小金鱼,就叫‘小金刚’,可惜它死了,”花铃漫不经心地补充道,“我把它埋在一棵树底下了。”两个孩子从捞鱼到换水,直到把鱼重新放入—配合得天衣无缝。
为了洗脱一部分嫌疑,花铃特意篡改了弹珠匣子做棺椁的事实,改成手帕裹尸,这更符合女孩子的偏好。而那棵树,仍然是梧桐树—为了制造更多巧合。
桑元从来不接受妈妈的示好,但也没有说过“是你们把一切都搞砸了”诸如此类的话。他很懂事。但花铃如履薄冰,她被自己无休止的恐惧给毁了一半。她有时觉得正因如此,一切便能扯平。
他们渐渐熟络起来,甚至互相生出了怜悯—苦难把他们拉近了。大人不在的时候,他们会躺在地板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就在这间有漂亮窗户的卧室里。他们无可避免地聊到过去的中心事件—花铃妈妈是如何介入并大获全胜的。于是,他们互相拼凑着各自知道的那一部分,循着天花板上一道道平行的蓝色线条,像练习弹吉他,一点点把谱子补全。
花铃动情演绎着她们住在小胡同里发生的故事。有天晚上,妈妈一直没回家,她实在要饿疯了。后来妈妈晃醒了她,然后她开始像疯子一样大口咀嚼着妈妈带回来的食物。在下咽的间歇,她听见妈妈崩溃了。“对不起,对不起。”好像妈妈唯一能做的只有道歉。后来妈妈不哭了,轻轻拍打着花铃,哄她入睡。此时花铃拍打着桑元,手掌触到海魂衫是绵软的感觉,还带着若有若无的体温。
桑元用一个暴力事件作为交换。那天他正在看动画片,电视机里的奥特曼与怪兽在群山之巅进行决斗,一束束光线刺得桑元睁不开眼。怪兽发出一阵阵怒吼,但算不得壮烈,因为一切被隔壁房间里的吼声覆盖了—是桑元妈妈发出来的。桑元将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大。没过多久,他关掉电视,跑出家门。为了表演的真实性,桑元翻出橡胶制成的奥特曼小人和怪兽,模拟了那场电光四射的巅峰对决。
“妈妈会想办法的。”花铃想伸出手去拭妈妈眼角的泪,但她被妈妈搂抱得很紧,根本动弹不得。妈妈喃喃着睡着了,花铃则瞪着眼睛熬了很久。
“想想孩子,就当是为了孩子。”桑元妈妈的声音很怪,像干噎着了,后来她从房间里冲出来,在电视柜最底下抽屉里倒出一把安眠药,不管不顾地往嘴里吞。还好,爸爸及时阻止了。“一起死!”他突然甩了自己一个耳光。冷静后,他把桑元妈妈扶到沙发上,倒了一杯水。
…………
这些场景,被两个并排躺在地板上的孩子滑稽地重复出来。“一起死!”桑元沉低嗓音恶狠狠地喊道,花铃则是一副因抽泣而肩膀大幅度颤抖的可怜相。
“你要是敢离开我们,我就带着他一起死。”桑元在模仿中展示出一派心有余悸的样子。桑元妈妈完全发了疯,甚至掐住桑元的脖子,一路将其逼到墙角。好在最后时刻手松开了,她浑身颤抖着瘫软在地,痛哭不止。后来,她去看了精神科。“真是有罪啊。”花铃觉得自己再听下去就要崩溃了。出于私心,她所模仿的妈妈是弱小的、可怜的,甚至假装出宝贵的真心。“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愿意为了你而死。”花铃蹙着眉头,语气矫揉造作,这是跟着偶像剧桥段学到的。
“她变了一个人。不能交流,处处管束,偷看手机,谁能喘得动气。”这话是花铃真真切切从桑元爸爸那里偷听到的,她将其原封不动地表演出来,只不过换上了绝望的口吻。而原版的语气,带一点威胁的意味。当时,花铃妈妈问桑元爸爸昨晚去哪了,为什么不接电话。桑元爸爸没有直接回答,反而说出这些批判前妻的话,后来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妈妈立刻闭嘴。
夜幕逐渐降临,花铃擦干脸上的泪水,立刻起身—她得回阁楼那间卧室了。她向桑元道了晚安。
这场小型婚礼还是顺利举行了。地点在近郊的一块草坪上,周围摆满了白色百合花和香槟色玫瑰,音响循环播放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流水线歌曲。一家四口并排站着,强烈的阳光让花铃睁不开眼,她悄悄抬头去瞥新“爸爸”。和她料想的一样,那只蓝色义眼不受光线的影响,睁得大大的,而另外一只好眼睛微微眯着,这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古怪。桑元则站在新“妈妈”身边,他的皮鞋踩在了新娘的曳地白色裙尾上。摄影师提醒他,但他明显心不在焉。
他脑海里全是关于前一天傍晚的回忆。他和花铃演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戏份。他非要知道真相,一向妥协的花铃只能胡编乱造,脸上淌满了泪水。她设法动了真情,她一直都擅长假戏真做,只要能让桑元满意。
“我看见他俩在楼下一条路上散步。路灯很暗,我看不真切,但我肯定他俩接吻了,”花铃说,“真的很恩爱。”她转过头,看见桑元闭着眼,痛苦地皱着眉头。她翻了个身,两条细胳膊努力撑起上半身,这样她就能看见桑元完整的一张脸了。
“让我们为他们开心吧。”花铃伸出一只手,去抚摸桑元两眉间的疙瘩,但抚不开。然后,她的嘴唇慢慢凑近,直到吻上另一张嘴唇。柔软,潮湿,仿佛沾着一层雾。桑元一下子睁开眼睛,眉间的疙瘩瞬间消失了。
“就是这样。”花铃重又躺下,泪水继续在她的眼眶里积聚。
四
每个周六早上,桑元会被送到他妈妈那里,周日傍晚再接回来。花铃就在那间卧室里等他。
后来,探望时间完全颠倒过来了。桑元只会在周末两天出现在花铃身边。
“她想要回我。”
桑元继续说,他觉得相较于爸爸,妈妈更需要他。妈妈现在还是干着老本行—给人处理官司。更兢兢业业了,也更爱美了,妈妈会根据不同场合来选择口红的颜色,对着镜子一遍遍擦上又抹掉,不厌其烦。
“挺漂亮的,很多人喜欢她,”说这话的时候,桑元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她还换了房子。新房子在市中心,楼下什么都有。要是晚上拉开窗帘,啧啧,那种景色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到的。”
一阵闪烁、细密的痛闪过花铃的额头,就像一道闪电在瞬间割破夜空,烫出一条大树根系模样的伤口,随后扎进大地深处。花铃觉得有什么要被改变了。但她表现得异常安静。
“她把之前那些衣服都扔了,剪了短发,完全换了个风格。她现在的样子准会教我爸大吃一惊。”
“他们肯定见过了……不一定大吃一惊。”花铃撇了撇嘴。
“她不比你妈妈差呢。”
“那又如何?”差点脱口而出,花铃及时住了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桑元一直看向别处。
“你想住在这儿吗?就说你还要教我做数学题。你去跟她说。”
“我不能那么说。”
“我知道,你就是想离开了。”
“她是我妈妈。”桑元说。
“好!”
花铃开始哭,像桑元妈妈曾经那样,俩孩子表演过很多遍—“求你,看在……的面子上。”本来应该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花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替换,嗫嚅着一带而过。桑元想安慰她,像爸爸安慰妈妈那样子,尽管一点也不奏效。游戏里的“爸爸”始终没有妥协,他们的游戏也发展不出花铃想要的结果。
第二天一早,桑元被送走了。
“你不必为他担心。他妈妈完全好了,马上还会有一个孩子。”花铃妈妈说。
“还会有一个孩子?”一定是他们拼凑片段时漏了什么信息。花铃独自待在那间卧室里,仔细回忆每一个细节,并不断补充新的情节。眼下,这间卧室完全属于花铃了。铁艺床上铺着女孩喜欢的粉红色被褥,床头灯做成了月亮和星星的形状,枕头边坐着巧克力色的小熊,黑眼睛亮晶晶的。本来,桑元爸爸想拆掉那年份久远的木制窗棂,花铃不让,她说她喜欢。
“是个女孩。”这是桑元又一次到来时带来的消息。那时他们俩正在游乐园里一遍又一遍地排队玩大摆锤。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有时候会互相拉着手,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叫里被抛到高点—短暂的停留—再任凭重力使他们下落。安全带将他们牢牢捆缚在座椅上。俩孩子一点也动弹不得,但足够安全。没人再提起那些黄昏时刻—在那间漂亮卧室里,他们的低语声,泪水,紧咬的牙关……他们曾互相试探着、妥协着。在他唇上轻轻一点的,是她的双唇。谁也不会忘记。
花铃妈妈和桑元爸爸坐在不远处的水上咖啡厅里,一人喝着一杯饮料,朝这边张望。偶尔,他们也会吵架,但不是桑元日记里的那种吵法。
桑元会陪花铃去坐旋转木马,那是他们在大摆锤游戏后使剧烈喘息得以平复的间歇。两个孩子骑着旋转木马,一前一后,在片片光影里闪进闪出。桑元说起那个小女孩,“头发毛茸茸的,喝奶的样子像个小兔子。我喂她,她全喝光了,嘿,一点不剩,真给哥哥面子。”桑元边说边回头笑着。迎着灯光,花铃看见桑元唇角飘荡着几根纤长的绒毛—他已经比自己高出了半个头。花铃和那个女孩一样,也是桑元的妹妹。这个云彩一样缥缈的意识终于落地了,尽管她从没喊过哥哥。
花铃松开紧握木杆的右手,向前抓去,好像只要她足够用力,就能触碰到前方桑元的肩膀—她曾依偎过那儿。《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一直飘荡着: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我的马儿你快快地跑……”花铃对这首英文歌一窍不通,一边随心所欲地音译着,一边奔赴旋转木马新一圈的循环。
陈修歌,1995年生。小说作品见于《青春》《青年文学》《大家》《西部》《山东文学》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