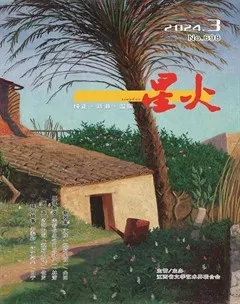四楼住了个郑法官(短篇)
2024-09-11李敬宇

刚开完庭,庭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庭长说:“小李,我知道你开了一天的庭,辛苦,但没办法,给家里打个电话,晚上迟一点回去。”我问庭长是要加班吗,庭长说:“加什么班,我们去小郑家。”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上午来了一对夫妻,来告郑法官的状,庭长要亲自出马,去解决问题。
庭长开着私家车,带上我,先去快餐店叫了两份快餐。饭毕,我们驱车过去。
“我跟他们约好七点钟的,你看现在几点?”庭长说。
“还不到六点半。”
“时间还早,他们可能正在吃晚饭。我开慢一点,提前几分钟到就行。”
“早点到比较好,”我说,“她家那边不好停车子。”
幸亏我提醒,庭长早一点停好了车,不然的话,肯定要迟到。
小郑家在一个不像小区的小区里,巷子深得仿佛不见底,汽车根本开不进去。我告诉庭长,这里的楼房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放在当年还算高档,现在早就落伍了。庭长说,小郑父母是外地人,她是随父母做生意过来的?我说,也是也不是,那边生意不好做,她考到我们法院,她父母就跟着过来了。庭长问,他们做的是什么生意?我说,听讲是卖水果,但小郑说现在水果生意不好做,街上卖水果的人太多了,赚不到钱。
说着话,我们已经走到了小郑家的楼下。
庭长说:“我们先去老金家,这样比较好,人家不会怀疑我们偏袒一方。”
然后,我们上楼,敲响了三楼老金家的房门。
上午,一个自称姓金的人和他老婆来到北门区法院,进了办公楼,说要找民事审判庭的庭长。那时候我刚开完庭,从审判法庭那边过来,见到来人,问他们找庭长有什么事。男人脸皮白净,气汹汹地,说,我是来告状的,先找你们庭长,庭长要是不接手,我就去找院长!
话才出口就那么咄咄逼人。我把他们领进了欧阳庭长的办公室。
等这对夫妇离开庭长办公室,庭长把小郑叫了去。那时候小郑也刚刚开完庭,连胳膊上搭着的法袍都没放下呢。庭长与她单独谈话,谈了一阵,小郑回了办公室。我未及与小郑搭话,庭长又过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
庭长拿起桌上一叠三四页纸的告状信,抖一抖,对我说:“告小郑的。你知道告她什么吗?他们是小郑楼下的邻居,告小郑骂人,还动手打人。你可相信?”
我笑了。我笑的是不相信。
“这封信是写给院长的,他们不找院长,来找我。你帮我分析一下,他们是什么心理。”庭长给我出题目。
我拿过信来,一目十行大致看一遍。这白脸汉子名叫金又强,住在小郑家楼下,小郑家房子漏水,他找上门去,两下谈不通,小郑不仅骂人,还跟他动手,今天来,他要求郑家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
“他们底气不足,知道找院长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找直接管事的。”我如此分析,“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多捞一些便宜。”
“嗯,跟我想的基本一致。”庭长点点头,“那么你说,我们把信收下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既然抬头是写给院长的,我们不如就交给院长,看他怎么处理。”
“不行,绝对不行。”庭长摆手。
我问为什么不行,庭长说:“那样动静太大了。一个小姑娘,闹得全院上下都知道,没必要。在我们庭,除了你,我还要指望她呢。你们都是办案主力啊—不就是想捞点便宜吗,我的意思,想捞便宜,就让他捞一点。”
这么一说,我懂了。我苦着脸,会心一笑。
庭长又说:“我跟分管领导汇报一下,汇报以后再说吧。”
汇报的结果,就是庭长主动揽下这个活,带上我去小郑家,做调解工作。
庭长刚才的话不免叫人发笑,“一个小姑娘”,人家小郑已经不年轻了,只不过到现在还没结婚,甚至还没谈恋爱而已。小郑大学毕业,跟着读研,之后去公司干了几年,终于通过司法考试来北门区法院,工作也已经三四年,这么一来二去,三十二岁了。不过小郑长相好,一张娃娃脸,温和,看上去倒像是二十刚出头。这样的长相,也好也不好,从工作角度讲,肯定不占优势。在法院搞审判,长得老成一点,受人尊重。
下午一上班,庭长就给金又强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晚上过去,七点钟。
我们首先敲了老金家的门。
开门的,是老金的老婆,紧绷着一张胖脸,像是故意绷着,和身上紧绷的衣服相呼应,很难看。“来了。”欧阳庭长说,说得煞有介事。女人并不应答,我们便径直往里走。穿过如过道一般的客厅,进得房间。老金背对我们坐着,红背心,黄裤衩,这会儿侧过头来,朝我们象征性地点点头。“来了。”庭长又说,是自我解嘲的口吻。
房间不算少,但都不大,东西堆得很乱。正不知如何落座,老金忽然站起来,说:“来来来,你们跟我去看看,看看我讲的是不是实话,看看我骗没骗你们!”几乎没有一点儿过渡。我们只好跟着他去旁边的房间。
抬头看,靠天花板的墙面果然斑驳,一块一块,仿如深暗的山体,有连绵之意。“还有这边,这边!”老金说着,又把我们领进隔着厕所的另一个小房间。这边的图案有点变化,不像群山,倒像是脏兮兮的河塘了。
“关键是这边!”老金不容我们讲话,又把我们带到厕所门口,指着厕所里面说,“上边!上边漏水,漏得哗哗的!”
我和庭长钻进窄小的厕所,仰头望。一条细长的湿痕沿外露的水管而下,老实说,不至于“哗哗的”。
“嗯,是有问题,是有问题。”庭长节制地说。
回到房间,我和庭长在旧沙发上坐下。老金也在旁边坐下,开始控诉。
“看到了吧?我是不是说假话?这一家,太不上路子了!前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漏了几次水,我住楼下,成天就跟下雨似的!她还在法院,还当法官,我上去评理,她还跟我凶!”
庭长笑着,拍拍他的胳膊,“老金,有话慢慢讲,慢慢讲。我听说,派出所这次也出面了,处理的结果你不满意?”
老金又激动起来,“我提出少说也要赔给我两千,你知道怎么调?调成七百,说多一百都不能给。 我当然不干!你们这次要是处理不好,我要跟她打官司,告她跟我动手!”
“她一个女孩子,弱不禁风的,还跟你动手?”庭长不笑了,已经笑不出来了,“这样吧,我们长话短说,我先拿个初步想法,你看行不行?”
“你说。”女人站在旁边,显得迫不及待。
“责任是明确的,这个不用说,楼上小郑家漏水,是楼上的责任。作为单位领导,我拿两点意见,你们看能不能接受?”庭长看看老金,再仰脸看看女人,“第一,我叫小郑这两天就找人施工,把漏水的地方补上,这是最关键的,这个要是解决不了,一切都等于零;第二,补好了上面,就来修补你们家的墙,该铲的铲,该粉刷的粉刷,这个你们放心,起码,要搞得比你们家现在这个墙面漂亮。”
“第二点不行!他们来搞,用什么烂料我也不知道,我不放心。”老金说。
“那你说,采取什么办法?”庭长问。
“她家给我们钱,我们自己修。”女人再次迫不及待。
“这也是个办法。”庭长说,“要多少钱,你们商量过吗?”
“商量了,她家不同意。”女人说。
庭长问是多少,女人不言。老金翻眼看看庭长,说:“你问四楼去,你一问就知道。”然后胡乱地摆一摆手,似乎有了些许不耐烦的、逐客的意思。
楼上楼下的房间格局完全一致,连各个房间装修的简易程度也基本一致。
小郑一家人早就在家里坐等了。我们进门,小郑的父亲却坐不住了,简单招呼一声,突然显出激动的样子,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小郑及时伸手,拉他坐下,可他刚坐下,忍不住又站起来。小郑和母亲坐在床沿上,她母亲说:“小她,来领导了,你去倒水。”想一想,又说:“小她,你去倒水。”自己却始终坐着。
小郑扭脸对半截橱边一个正在摆弄手机的大小伙子说:“你去,帮我们领导泡茶。”
“你支派你弟弟干吗?”小郑母亲说,“你去,小她,你自己去。”
开始我没听清她是如何称呼自己女儿的,不明白“小”字后面跟的是个什么字;几遍听下来,突然大悟,原来是“小她”。
这个称呼,令我感觉奇异。小郑不是有名字吗?虽然名字太过普通,可能会被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同名者淹没,但三十多年下来,作为母亲,也不至于连个“桂花”都喊不顺口,偏偏要叫她“小她”!
庭长似乎司空见惯,就像小郑对之全然不在乎一样。虽是初次登门,初次与小郑父母见面,但庭长一句客套话都没有,坐下来便直奔主题:“大哥,你坐,坐下来,我们靠近一点,商量商量。”
这话是富有感染力的,距离顿时拉近了,像一家人。老郑个头不高,紫黑着一张瘦削的脸,既粗犷又苍老,受宠若惊道:“我坐,我坐。”
小郑挨着她母亲,平静地坐在床沿上,一直没动。她弟弟去为我们沏了茶。小郑的母亲,四方的脸,如同小郑父亲一样的黑,嘴里一直絮絮叨叨,只是听不清在说什么。
小郑父亲沙哑着嗓子,向我们介绍情况。
说三年前,他们一家从河南搬过来,买了这套二手房。这房子质量太差了,老是漏水,几次维修都修不好。一漏水,老金就上门来,已经赔过三次钱了,这是第四次。“我说要帮他修,他也不愿意,就是伸手,死要钱!第一次赔两千;第二次找派出所,赔了九百;第三次也找派出所,赔了八百。”老郑说。这次又找派出所,派出所的老吴上门几次,说这次比上几回的损失都小,赔六到七百就差不多了。老金虽然不很愿意,但也找不出推翻的理由。老郑眼睛一闪,说:“可不知咋的,他知道我女儿是法院的法官了,起先一直是跟我打交道的,现在不干了,一下就把我甩到一边,专找我女儿的茬!”
“怎么找的茬?”庭长问。
“上楼来,也不找我,专找桂花,开口就要八千,不给,就要去单位,告状!”
“就这么大点事,责任也明确,他告什么?”庭长说。
“他那天上楼,桂花在洗澡,他也不管,一劲地捶门,桂花洗了一半就穿衣服出来,头发还滴水,就问他讲不讲理,把他往门外推。本来这事过去了,他也没啥可说的,一听说桂花是法官,就又提起这事,说桂花推了他,打了他。”老郑说着又站起来。
“是个无赖啊!”我不由得开口。
“别瞎讲小李!邻里纠纷,哪有无赖!”庭长不看我,只看着老郑,“他说赔偿的数额都跟你们商量了,怎么商量的?”
“哪商量了?开口就要八千,不行就要告状。就是这样!”
“八千是不可能的,损失就这么大。大哥,我只和你说说利害关系。”庭长语重心长,拽一拽老郑的袖口,“郑桂花虽然年轻,可在我们法院,她是办案主力,一年要办两三百件案子呢。她承办的案子,债务的,房产的,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你说你们家这个小纠纷对她来说算什么?我是考虑吧,她这两年都是市先进,又在入党考察期,这个时候闹一场官司对她有什么好?不管怎么说,错在我们,是吧?人家住楼下,没有错。真要闹起来,为了一点邻里纠纷,对郑桂花造成影响,你说值得吗?我看是不值!常言说,三人成虎。本来没有的事,大家一传,倒传得跟真的一样了。”
“可他也不能狮子大开口,要这么多呀!”老郑像是有所领悟。
“大哥,大嫂,你们给一个心理底价,你们看能给多少,我和小李下去谈。”
“六百五!”女人看上去像是全无主见,却抢先发话,“屁股大的一块地方,修一修,能花几个钱?派出所老吴说了,六百就够了……我们多给五十!”
“大嫂,你这就叫没诚意了,相差太大,谈不拢啊!大哥,你是明白人,你说呢?”
老郑磨着牙,下巴颏左右动得很夸张,良久才说:“我看七百只多不少。”
“七百肯定不行!”庭长态度坚决,“真要是打官司,还要找人做鉴定,光是鉴定费,起码也要上千了。”
“上千,那也不能就我一家付呀!”老郑戆戆地说,似乎清醒了一下,又道,“那就……那就八百……还是九百?”
“你败家呀,败家呀……”女人痛苦地发感叹。
“大哥大嫂,你们听着—”庭长站起身,伸出两个手指头,作出决断,“我和小李现在就下楼,我们按这个数字谈,两千。”
我们和小郑交换一下眼神,及时抽身。这个眼神交换了等于没交换,小郑是没有态度的,一如她那张娃娃脸,竟是懵懂无措的样子。而她母亲,这时却转换了攻击目标,一迭声地哀叹:“都是因为你呀,当什么法官呀,遭罪……”
回到三楼,谈话继续。作为事后的复述,我现在已经没有欲望再去叙写与这对夫妇交谈的经过了。这一轮的谈话,只有一件事情或可留下一笔。
何事呢?老金居然拿出一份起诉状,以表明他打官司的决心。而这份三页纸的起诉状,即刻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不为别的,只为其中的字迹。
这份手写的起诉状,抬头“民事起诉状”几个字较大,是宋体,横细竖粗,写得十分规整,不细看,以为是印刷品;接下来“原告被告”以及“诉讼请求”,则是仿宋体,一笔一划,很见功力;然后“事实和理由”的长文,则是漂亮的行书字体,自由放松,但每一笔每一划都仿佛有其出处;到末了,“具状人”一栏以及时间,又回到了仿宋体。如果说上午在庭长那儿看到的告状信,单一的行书字体尚会引起人的误解,以为是别人的代笔之作,那么看到这一份仿佛是在练习硬笔书法、差不多就是卖弄钢笔字的起诉状,就不能不叫人惊叹,这书写者真是水平够高,也实在是闲得无聊了。
“这是你写的字?”我忍不住问。
“我写的。”老金说。
“这字写得真漂亮!”我由衷地夸奖。
“那时候我在里面,时间多,没事干,成天练字,就练出来了。”老金显出十二分得意的神情,彻底放松了警惕。他说的“里面”是指坐牢。
讲这些的时候,我以为他老婆会显出羞愧之色。没有。不仅没有,站在他身边,一脸自得,似乎为有这样一个丈夫,颇显自豪呢。
除了这一节值得记录,还有一点,也可以顺带一笔。老金说,上回房子漏水,他没找老郑,直接上四楼,揪住施工队那个小头头,一下就把对方镇住了。“我叫他停工,他小子还不愿意停,说签了合同,不能停。我说,是老子说了算,还是你他妈的合同说了算?!他长得比我横,光凭我,肯定搞不过他;我是带着两个朋友上楼的。我让他有个数,看我们谁能搞过谁!”
庭长默而不言,我则目瞪口呆。
再上楼,到小郑家,小郑的母亲正在哭,一抽一抽的,两行泪还留在黑脸膛上,在灯下闪亮。我突然想到一个叫东施效颦的成语。这个念头出现得很突兀,有点冒失。
“大嫂,我们就事论事,就是一点小纠纷,不算大,别哭,别哭。”庭长劝道。
“小她是法官,小她是法官又咋啦,就该受人气呀……”她反复叨唠着,哭腔里的这句话如同挽歌,听起来竟有点瘆瘆的。
老郑站在屋子中央,似已等候多时,说:“我就知道你们谈不成,他家那样,谈不成!谈不成就算!他不是要打官司吗?他打好了,我等着!”
“这不行啊,大哥,你要冷静!”庭长一口否定,“要不是为了郑桂花,我们就不会上门。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她年轻,不能因为这个小纠纷,耽误了她的前程。”
“前程!可他家……他家欺人太甚,现在都欺到这一步了!”
“屁股大的一块地方,死要钱。唉,我命苦啊—”女人又不合时宜地抽泣起来。
“大嫂你别这样说,这样说会引起更大矛盾。”庭长正色道,“两个房间都有,都是一大片,厕所也有,都不小呢。”
“不小什么呀,他拿了钱也不会修的。这种人,我知道!墙上的印子,还说不定是上几回的呢!”老郑说着,扭脸去劝哭哭啼啼的女人,没有效果,有点难堪。老郑说:“两位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可这一家,你讲多少也没用,他们就是为了钱……这样吧,作为一家之主,我做主,就定一千,他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败家呀,你败家呀……”女人又重复先前的话。
庭长说:“大哥,你还是绕不过这个弯子。他提八千,那是扯淡;可他提两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想往下拉,也拉不下来……这样吧,我就在一千五到两千之间去做工作,就按我说的定了。”
“不行啊—不行啊—”女人及时哭道。
“我把利害关系都跟你们讲透了,大哥,你是开明人,我讲的意思,你应该懂。”庭长转脸向小郑,又说,“小郑,你拿个主意。你在单位办案子,果断得很呢,怎么在家,一句话也不讲了?”
小郑躲过庭长的眼神,低了头,依然一言不发。
这中间,庭长又谈了许多,正面的反面的,反复做工作,如同在老金家我们反复讲废话一样。很多废话是不能不讲的;同样,明知道有些工作做了等于白做,还是要做。
庭长再次喊我下楼。我们出门时,身后传来老郑沙哑的声音:“这种人家!干什么呀,抢钱啊?!”
按小郑的岁数,她应该是独生子女;我比她大十来岁,连我都是,她凭什么不是呢?可她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弟弟不算新鲜事,这样的家庭绝然不少;但有一回,我无意中看到小郑的一份履历表,在“家庭成员”一栏中,除了填写父母和弟弟,她居然还填写了一个姐姐,在“工作单位”一栏里,填写的是“失踪”。
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同在一间办公室,聊天方便,所以我刻意与她闲聊,方才知晓早前她还不止有一个姐姐,而是两个。大的没养成,几岁就死了;第二个长到十来岁,跟着父母外出做生意,失踪了,找了两年也没找到。父母一心想要男孩,生小郑的时候,一看是个丫头,就动了心思,想把她丢弃掉。丢了两次,没丢成,都被派出所民警抱着找上门,送回来了,还批评得不轻。父母不甘心,继续生。又生了两个,果真都是男孩。大弟弟前几年拿了个驾驶证,开车给人运货,因为连夜驾驶,在路上犯困,结果车毁人亡。现在这个是小弟弟,才刚二十岁,成绩不好,没有工作。
也就是说,父母最不待见的就是郑桂花,可她在家里又最有出息。这很矛盾。虽然矛盾,但在父母眼里,她已经成了“小她”,是习惯成自然了。
听她平淡地叙述,我仿佛进入到另一个生活圈子里。虽然这另类生活并不陌生,但发生在小郑身上,我还是感到惊诧。
三楼四楼,我和庭长就这么反反复复,起码跑了四五个来回。时间在我们的脚底和嘴皮子上迅速流逝,不觉已将近十点半。但是,进展不大。
老金夫妻的回话甚是模糊,两千元仿佛也能接受,但仍在提八千,有得陇望蜀的试探之意。此间,老金的老婆反复强调,说既然她是法院的,还在乎这几千块钱吗?老金更是得寸进尺,索性问起小郑的工资,说她每月拿不到一万五,起码也能拿到一万吧,她还在乎这点钱?听此言,我几乎瞠目结舌。庭长只好说,哪能呀,我都拿不到,何况是她,刚参加工作,你把我们的收入估计得太高了!
至于老郑这边,经我们反复劝说,晓以利害,老郑终于咬了牙,说:“看在两位领导的份上,一千五,我答应一千五,多一分也没有!”而小郑的母亲,像是刚刚学到了一个新词,哭诉的内容也变了:“抢钱啊,抢钱……”
几个小时,小郑始终坐着。这个晚上的小郑,在我眼里完全换了个人,无声无息,全无主张,像一截木雕。
庭长打算再下楼去做最后一次尝试。老郑决定跟我们一同下去。庭长想了想,说也行,争取一次把问题解决。又说,最好把钱带上,当场订协议,干干净净。小郑母亲立刻“不行啊不行”地喊,只是坐着不动。
老郑扭头瞪她一眼,匆匆忙忙地打开橱门,取了钱,跟我们下楼了。
却不料,刚进门,还没坐下,两个男人发生了冲突。
正走在金家厕所和房间的过道处,我和庭长走在前面,老郑跟在后面,老金也落在后面。就听得老郑说:“老金啊老金,你真是算一户!人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相反,你专吃窝边草!”老金说:“我吃你草,你那几根鸟毛还够我吃?!”老郑说:“不够你吃,你还吃得欢呢!”然后,两个人突然就动起手来。待我们听到动静回头看的时候,老金已经把老郑的手腕反剪住,像擒拿格斗的老手,眨眼之间就将对方制服了。
“你们俩干吗?”庭长返身过去,横在他们中间,拉架。
“他嘴里不干不净,还跟我动手!”老金并无松手的意思。
因为有庭长的帮忙,老郑狠甩几下胳膊,挣开了,说:“我就是拍你一下肩膀,跟你开个玩笑,你就跟我动真的!”
“谁跟你开玩笑!都要打官司了,还跟你开玩笑!”老金白着一张脸,转向庭长,“我说的吧,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动手动脚,你们还不相信!”
“你是小老弟,我凭什么不能……”
“算了算了,谁跟你扯!”不待老郑说完,老金不耐烦地说。
好歹把两个人拽进房间,安顿下来。庭长话入正题,说双方现在所谈的赔偿数目已经很接近,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快刀斩乱麻,早点把问题解决掉。
老郑硬生生地说,人家欧阳庭长亲自来调解了,我高姿态,一千五,多一分也没有。
老金说,我也不跟你谈七千八千了,凑个整数,就两千,少一个都不行!
老金的老婆站在老金身边,绷着一张胖脸,明显是故意绷着,像是声援。
双方都是犟脾气,拉紧了弓,就这么僵持着,都没有让步的意思。
庭长说,时间真的不早了,你们都要有点诚意,啊?
在我听来,庭长这话说得,一点劲道都没有。
老郑这时站起身,很主动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钱来,一小沓百元钞票,兀自点着,像是对庭长言谈的回应。大约是多出两张,他将那两张单独折起,随手放进了衬衣口袋。“一千五,我说了,多一分也没有。”他强调说。
老金看也不看,只冷哼了一声。
看着他点钱,我一点儿都不抱希望。几个小时下来,我们的“强弩”早已成了“之末”,看来,我们只能半途而废打道回府了。
眼看着山穷水尽,调解即将陷入绝境,关键时刻,老金的老婆亮出了奇招。
就见她猛一抬手,照着老金的脖子就是一巴掌,脆生生的。
这一巴掌来得太突然了,差不多把我们都打懵了。
“你别死犟了,人家法院领导都来了,你还死犟!你听我的!”女人居高临下,下命令似的看着老金。后者抬脸,表情异常麻木,是一副愿打愿挨、司空见惯的态度。女人接着道:“加一百,一千六,讨个吉利数字!”
“我说了,一分都不能加,一分都不能加!”老郑说。
庭长仿佛于黑暗中突然见到一线曙光,冲着老郑,严肃地说:“老郑,你听我的,加一百就加一百,凡事向前看,我们早点把问题给解决掉!”
老郑本能地握着手里的钱,似在抵抗,庭长又说:“刚才我不都跟你说啦,为了郑桂花的……嗯,前程。”
女人像是嗅出了某种气味,立刻接话:“老金都答应让四百了,你凭什么不答应让一百。人家庭长也辛苦,都来几个小时了。你听庭长的,为了你家小她的前程嘛!”
这么说着,女人竟伸出双手,抓住老郑握钱的那只手,将他的手指头一一掰开,把那一沓钱抽过去。紧跟着,她出人意料地又伸出一只手,几个手指头迅速探进老郑的衬衣口袋,老郑尚未反应过来,那折起的两张钞票已经到了她的手指间。她拽出一张,塞往另一只手里那一沓钞票,将剩下的孤零零的一张,递给老郑,但老郑尚处于惊愕之中,她用食指和中指夹住那张钞票,从容地伸向老郑的衬衣口袋,塞了进去。
“这不,简单得很!问题不就解决啦?”她说。
这一连串的动作,把我看傻了。
后续为双方订立协议、叫双方签字,都由我来操作。这中间,老郑和老金仍在杠嘴,庭长则在空谈“邻居好赛金宝”的家常道理,只是那女人,老在我旁边干扰我的书写:“写这玩意干吗,多费事,又不能当饭吃!付过钱不就行啦?”
这事发生在六年前。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离开小区的时候,我和庭长都有点发懵。我们讨论了几句女人甩向老金的那一巴掌,然后都噤口,像一对寒蝉。那巴掌脆生生的,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
六年后我旧话重提,是因为,这两天法院又有了新的任命,郑桂花当了庭长。
她进步的确是快,这与她的综合素质有关。相比之下,虽然三年前我和她同时提了副庭长,但这一回,她先上了个台阶。我自认绝非小肚鸡肠之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上台阶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天晚上小郑茫然无措的神情,在我眼里是那样的陌生,仿佛完全换了个人,与她在办案中干练、精准而又不失温和的作风、态度比较,简直判若云泥。一个人,怎么会因为某件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呢?我还想,如果那个晚上调解不成功,事情被我们搞砸了,老金和他女人接下来大闹一场甚至几场,搅得天翻地覆,那么小郑,还会在三年前和我一道提任副庭长,并在眼下升任庭长吗?
看来无论是谁,在他(她)的周围,都有一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场”。
李敬宇,法院工作者,中国作协会员。在《中国作家》《花城》《清明》《长城》《北京文学》《十月》《星火》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篇,共200余万字,部分被选刊选载。发表并出版长篇散文《老浦口》、长篇小说《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