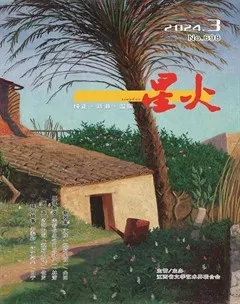鹅鸭成群(短篇)
2024-09-11戚佳佳

1
表舅妈第十次被捉了回来。之前我们已经麻木地闭口不谈这件事,她回来与否,似乎都不再那么重要,她就是去了亲戚家,什么时候回来,是她自己的事。倘若在村前的路上遇见她,顶多看看她穿了什么衣服,和她打个招呼,攀谈一两句。现在却不同,村子里被稀释的热议,又像她每次跑了被捉回来时一样,沸腾起来。我们想知道的问题太多,她是胖了还是瘦了?哪怕只是细微的变化,也逃不过大人们的眼睛,他们总会从她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眼睑上去判断表舅妈离开蒋庄的这段时间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境遇,是心惊胆战,还是风平浪静?是花天酒地,还是清汤寡水?大人们说得眉飞色舞,我们这些小孩听得如痴如醉。那一刻,什么霍元甲、陈真、霹雳舞,都成了山外之物。我们瞪着一双对这个世界好奇探寻的眼睛,盯着大人们,也盯着我表舅妈。我们能看出什么呢?我们看不出什么,她还是她,一张我妈说的肚肺脸,大得空洞的眼,一笑眯成一团,声音嘎嘎的,脸上的横肉跟着一颤一颤,两手乱扑腾。说实话,我真没看出什么,我妈偏说表舅妈像公鸭,而且是表舅家的公鸭,言下之意是她吃公鸭吃多了。表舅家的鸭子为什么都是公鸭?我妈说公鸭能长得大,又肥架子又大。每天两个表哥把鸭子赶进水塘,赶进稻稞里,鸭子窸窸窣窣,叽叽咕咕,像一群饿死鬼,奔跑着,将扁嘴塞进水草,在水田里吃得昏天黑地。两个表哥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像两个卫士,举着系了化肥袋塑料薄膜的长竹竿,以哗啦啦的响声,指挥鸭们。
表舅家的鸭和我家的鹅不同,表舅家的鸭从换掉绒毛起,会隔几天少一只。那些鸭肉的香味满村子飘,等到热燥燥的夏天过去,表哥们已经不用赶鸭子了,剩下不多的鸭子放门前的小塘里荡悠。而我家的鹅却被我爸挑到集市上卖掉。我的脑海总是被表舅家那些肥嘟嘟香喷喷的鸭肉灌满,我只能咂巴咂巴我寡淡无味的嘴。
我真是搞不懂,过这么好的日子,吃香的喝辣的,表舅妈为什么要跑?要是我,赶我都不走。表舅妈跑了就跑了,表舅总要去找,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跑了找,找了又跑。十几年时间,我从一个香喷喷的娃娃蛋,变成了人见人厌的臭狗屎。我的耳朵都被我妈唠出了几层老茧,我妈说话从不避开我,只要我姐不在,她就尽管说。
我妈说,这不要脸的女人,好吃懒做,找回来干吗?玉清就是窝囊蛋,没女人不能活了。
玉清是我表舅。每次我表舅妈出逃之后,表舅就像霜打的茄子,蔫巴的样子跟一只被主人踹了一脚的哈巴狗一样。我妈说,不屈,女人家女人家,女人不是过日子的人,都是男人惯的,你个大男人把她当祖宗一样供着,早晚没好果子吃。
我妈说的是十年前,那时候我表舅妈三十来岁,很有几分风姿。我们村子建在坝子上,屋后有一条河,村子是东西走向,一字长蛇般。我们家是东边的第一家,我表舅家是西边的第一家,中间隔着二十多户人家,但我常常能闻到表舅妈碗里油炒饭、煎鸡蛋和烧鸭子的香味。表舅妈不下地干活,天天偎在家里,表舅白天在田里忙活,临晚放笼,清早收笼,还得把收得的黄鳝背到街上去卖。
表舅自然是不会把钱揣进自己口袋里的,除了遵照表舅妈的叮嘱,采买她想要的抹脸的雪花膏,抹头的发乳,洗澡的香皂,穿的,吃的,只要表舅妈吩咐,表舅准会不折不扣地照办。每回回了家,剩下的钱得如数上交。
表舅家有两双儿女,前面两个是儿子,老大的腿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腿有点瘸,走起路来朝一边歪。两个女儿,一个比我大两岁,我叫表姐,另一个和我同龄,比我晚出来两天,她就得管我叫表哥。冲这,我也要感激我妈。每次表舅卖了黄鳝从集上回来,表姐表妹便占据着门的两边,等表舅到了跟前,用身体黏着表舅,眼巴巴地看一眼表舅,再看一眼表舅。表舅那个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口袋,在她们的眼里,大概像是一座藏着无数山珍的高不可攀的山,她们用力咂巴着嘴的声音,和咽涎水的声音交替响起。
无奈的表舅,脸都挣红了,不忍心甩开孩子们,脚也跨不开,只得放慢脚步,抠抠搜搜,好不容易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白色圆粒小糖,塞进她俩手里,抬手朝外指指说,出去玩。表妹乐颠颠地转身朝外跑。表姐却站在原地,手里攥着糖,视线依然停留在表舅的口袋上。表舅有点发慌,又用手指指门外。
外面是成片的槐树,花一样的叶子被风吹得窸窸窣窣地响,阳光透过叶子,砸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窟窿眼。表姐仍站在原地,眼神里漫溢着忧伤。表舅不知所措,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表舅妈出来了,手里捏着个麻雀头。那是我家乡的面食小点心,上面沾了芝麻,圆形,拇指大小。表舅妈把麻雀头递给她的大女儿。麻雀头拿在手里,表姐并不走,盯着麻雀头的缺口看。表舅妈瞪圆了眼说,怎么,你还不想要?表舅妈说着要去夺,表姐哧溜一下蹿出了屋。
2
我妈和所有的乡邻一样,把这一段翻来覆去说过之后,再加上一阵近乎癫狂的笑。我爸则始终保持沉默,低头抽他的烟袋锅,不时朝凳腿上磕两下。那明明灭灭的烟火在尘世中明明灭灭着。
表舅妈很喜欢吃油炒饭吗?我有意问我妈。我妈说,废话,谁不喜欢吃油炒饭?谁还能跟好东西有仇?可是妈妈你就不喜欢炒油炒饭给我们吃。我妈说,死孩子,死一边去,没脑子的货,就知道插嘴,也不想想,不年不节,又没来人,哪有恁多油,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也被吃空了。
关于油炒饭费油的程度,可以从我表舅在河里洗抹布时,漂在水上的那些油星子见一斑。
一般是在下午,家里空下来,两个表哥不是去放鸭,就是去捉鱼摸虾,房里不见人影。表姐和表妹跟着表舅去屋外头的荫凉下,看表舅往笼子里下蚯蚓。表舅必须要选一处离堂屋门远一点的地方,保证在屋里的人闻不到腥味,风也吹不来。表舅妈鱼也能吃,就是闻不得蚯蚓破了血的气味,一闻到,就作呕,上气接不上下气,脸也憋得真似一个肚肺。这样,表舅倒霉的时刻就到了。
表舅是个妻管严,比表舅妈高出一个头,麻秆一样细,走起路来,生怕踩死蚂蚁。表舅人白,细皮嫩肉的,太阳也没把他晒黑。庄里人说,表舅是男人生了个女人的身子。表舅妈却生得敦实,腿像藕段子般粗壮,来一阵龙卷风都刮不走。
为此,表舅妈没少骂表舅。表舅妈常是咬牙切齿地看着表舅,恨恨地说,你就是一个偷生鬼投胎来的,风能把你吹走,树叶能砸破你的头。你现什么世,来这世上,都怪我,当初眼瞎了,非要跟你。还是我妈说得对,嫁人不能看脸。表舅妈和表舅是自由恋爱,表舅是在放笼子时遇见的表舅妈,开始表舅妈家人不同意,拗不过表舅妈。表舅妈骂得嘴角都是白沫,肚肺脸也由红变白。表舅搁一边像是在听大书,脸上保持着之前的表情,眼皮耷拉,该做啥就做啥。偶尔表舅会说,你骂累了吧,累了就歇歇。表舅妈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半天把自己憋笑了。后来干脆不骂表舅,闲了,就吃,吃饱了就睡,睡够了就坐,拿着个巴掌大的小镜子照来照去。表舅妈的头发好像一直都没长过,齐耳,我们蒋庄的人叫耳朵毛子。表舅妈就顶着那一头抹得油光发亮的耳朵毛子,一日日坐在堂屋正中,看门外。
没别人时,她会摸几个麻雀头,或者一把多味瓜子,在那里慢慢嗑。到了黄昏,她会去炒饭。一边往灶洞里塞柴火,一边煎蛋,倒入一勺油,蛋煎得焦黄,盛碗里,再倒油炒饭,饭也炒得金黄,入碗,盖在蛋上。蛋吃完,碗底汪了一堆油,能照见人影子。表舅妈把碗搁在灶台上,喝一瓢水,就躺床上去了。人在吃饱喝足之后,一心只有床。不上床,表舅妈还能做什么?
碗要等到晚上表舅放完笼子回来,吃完表哥们烧的稀饭之后,再由表舅统一洗。盛过油炒饭的碗积着厚厚的油,先用抹布洗,油沾在抹布上,黏滋滋的,腻歪人。表舅拿了抹布到河里洗,河面上便漂了一层油。我妈说起这,口中总是喃喃地,身体禁不住抖,好像那些油,不是菜籽油,而是从她身体里剐出去的油。
3
与我表舅妈起纷争的第一个男人是秃头。
我妈每次说到秃头男人,就恨得牙根痒痒。我妈说,都怪你表舅,有了几个臭钱就烧包,搞不清自己姓什么。
我猜我妈想说,表舅是咎由自取,引狼入室,正好把表舅妈身体里潜藏的某种能量给激活了。
表舅卖黄鳝有了钱,喜欢上了喝酒,而且是找人一块喝。蒋庄的人是不会去的,男人们被女人们管束着。女人们说,手里有两臭角(家乡人读ge)子,就不知道东南西北,看他把女人惯成啥样?哪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在蒋庄找不到人,表舅就找庄子外的。表舅家住在最西头,往西是一段空圩堤和另一个庄子,汪波荡农场在庄子西边。
那时候,汪波荡农场像是个大地方,他们那种地的不叫农民,叫职工。他们收麦,不用人工,用收割机。这在我们庄里是会被另眼相看的。
那里本不应该有光棍。但秃头男人的确是农场的光棍。
秃头的头上无毛,光溜溜的。秃头的肤色黝黑,油光发亮,眼睛喜欢眨,一眨一眨,看上去很贼。庄人既反感他,又畏惧他。
秃头男人出现在表舅家,是在好多天之后传出来的。说那秃头男人可以随时进出表舅家,搁表舅家吃饭,喝酒,打麻将,有时晚上就在表舅家睡觉。
至于他是怎么和我表舅勾搭上的,庄里人认为不是表舅的功劳,是表舅腰包里的钱和表舅女人的功劳。庄里人谈起表舅,撇嘴说,瞧他那烂怂样,谁会把他当棵葱。倒是他女人嘎嘎的笑声和笑时两颗随着身体乱颤的大奶子,会勾魂。站几百里外的男人,都会麻酥酥的,像过电。
自从有了秃头男人这个朋友后,表舅在我们蒋庄似乎一下子变得高大伟岸了。腰直起来,歌哼出来了,脸上的笑容也灿烂了不少,走起路来,呼呼生风。那惨白灰暗的脸色竟然染了层红晕。
我妈说,秃子送镜子送雪花膏送发乳给表舅妈,秃子还带苹果梨子麻雀头麦芽糖白切糕给表舅妈,秃子带的总要比表舅买的大而且多。
我妈说,这个秃子自己头上没毛,心倒是细。
我爸说,有钱谁不会花。
我妈说,我就没见你给我买过一根纱。
我爸说,你想让我变成玉清还是秃子?
我妈没等我爸把话说完,一脚踹了过去,把原本蹲着抽烟袋锅的我爸踹得向前打了个趔趄,差点跌趴下。我爸转过身,推了我妈一把。
秃头男人出现后,表舅妈每天吃过饭就睡觉,睡到三四点钟,起来炒鸡蛋饭,吃完坐大门跟前,先是往头上抹油,再拿着一个比脸大的镜子,左照照,右照照,对自己的肚肺脸、洞穴眼和大嘴厚唇,越看越想看,越看越爱看。
我表舅和秃头男人的友谊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不到半年,秃头男人就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据庄里人说,秃头男人得罪了我表舅妈。我表舅妈原想让秃头男人带她跑,秃头男人说,我带你去哪?我表舅妈说,只要离开这个家,去哪都行。秃头男人说,我就认识这巴掌大的地方,我想不出能带你去哪。我表舅妈说,你去哪,我去哪。秃头男人害怕,搞死不肯。我表舅妈生气了,说没想到你也是一个怂包,既然是一个怂包,就别来我家,你喝的那些猫尿就当我们喂狗了,我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怂包。
秃头男人不来,我表舅蔫了,表舅的眼睛开始迷糊,路也走得窸窣。在凌晨和黄昏的原野上,远远望去,他越来越像那些在他笼子里盘踞的黄鳝。
我表舅妈不拿正眼看我表舅,表舅妈也不说话,只斜睨表舅。表舅妈的眼睛就是一个洞穴,阔大,幽深,像一眼深不可测的井,她即使不拿眼瞪谁,就那么干巴巴地睁着,也犹如冷冰冰的刀片。
某一个晚上在夜空下乘凉,我妈突然说,别说,这个秃头还算有点良心。
我爸说,到嘴的肉都怕吃,怂货一个。
我妈说,你是为他抱屈?
我爸不吱声,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我成了一团,四处黑漆漆的,只有我爸烟袋锅一时一时地蹦出的火花在闪。
能听到风摆柳以及蛐蛐和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宁静安逸,与青稞的香味混在一起。似乎有谁在说话?有谁在哼歌?更多的人沉默在夜色里。
4
十年了,表舅如丧考妣般往复在寻找表舅妈的路上。他这根树棍就要干瘪,可他还是执拗地不肯停止寻找。
表舅上茅厕,碰到的庄里人跟他说,你要么就别找了,找了也是白找,她还是会跑,她已经跑油掉了,像她肚子里的那些油,像你放的那些黄鳝,它们想给你抓你便能抓住,它们不想给你抓,你抓了也还是会滑掉。表舅蹲在茅坑不吱声,表舅那会子才进的茅厕,茅厕没有门,开放式的。表舅本来是感觉肚子有点疼,肚里有货要出来。跟着表舅那么一蹲,那些货果然迫不及待地到了门口。可是表舅不习惯上茅厕时旁边有人,像被盯梢,感觉浑身都是刺。没办法,表舅只能憋,全心全意地憋。
庄人又说,要么你就把她的腿打断了,让她跑也跑不了。表舅还是不吱声,茅坑里的臭气一阵一阵往他的鼻子里钻,他觉得那些到了门口的货又被他憋进肚子里了,肚里也是臭气,嘴里也是臭气,他哪里还能管得了庄人。
庄人见表舅不买他的账,就有点生气,说我是为你着想,你别好心当作驴肝肺,这你也不愿意,那你也不舍得,你找你活该找,你就等着找一辈子,找得倾家荡产,老子不像老子,儿女不像儿女,直到找见阎王爷。庄人拍屁股走了。
表舅终于撂出一句,这次再找回她,我要让她生不如死。表舅说时,牙咬得嘎嘣响,像刀锉在了钢板上。
表舅的豪气在庄里沸腾过几天,但很快就沉寂了。表舅为了找表舅妈,套黄鳝的笼子也不放了,他每天就像去上工,早出晚归,起早贪黑,不知道去了哪里。家里的小娃子们也不知道吃什么,怎么吃。反正十年之后,大表哥走路还是歪,却也没妨碍他朝上生长。大表哥二十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兄妹四人除了不怎么言语,眼光略显呆板,身体都还正常,跟小树一样,都蹿起来了。十六岁的表姐出落成大姑娘,亭亭玉立。有一回,我见表舅来我们家,悄悄跟我妈说到了大表哥和表姐的名字,说大表哥大了,脚又跛,家又穷,只能委屈大丫头了。
我看见表舅走后,我妈偷偷地拽衣角抹眼睛。我妈说,造孽啊!黄大傻就是个傻子。
那个坚持在十年内十次和我表舅妈私奔的男人也是个光棍,头上的毛比秃子多几撮,将就能盖住头顶,眼神看上去比秃头男人柔韧许多。他姓宋,表舅和表舅妈叫他老二,庄人叫他宋老二。皮肤黝黑,一嘴黄牙,不及表舅高,家在河对岸,听说家中有一个老母亲,母子俩守着两间茅草屋和几亩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也不知道他和表舅家怎么接上线的,距秃头离开几个月后,宋老二迅速成为表舅家的座上宾。表舅家每天晚上又过上了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好日子,一家人的脸上又有了久违的光,就连我的表妹看我时,眼光也不一样了,尾巴翘到了天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第一次到第十次,每年都要和表舅妈跑一次。
表舅妈第一次私奔时,表舅还不相信,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跑了?表舅不相信归不相信,在找了别处碰壁之后,他还是悄悄地潜伏在宋老二家的茅厕外。他想,表舅妈再怎么的,也要出来上茅厕拉屎吧,他不信她能天天屙马桶,表舅妈闻不得那个味。表舅那次的判断没错,两天后,他成功抓回了表舅妈。
这么多年,表舅捉表舅妈都捉出经验了,每次时间有长有短,但最终还是能把表舅妈捉回来。庄里人刚开始那几年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晚上匆匆扒一口饭,就赶紧往庄西头跑,大头贴小头地聚在表舅家给表舅出谋划策,指点迷津,说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巴望着能早一点把表舅妈找回来。表舅妈被捉回来,老老少少又往庄西头跑,他们撺掇表舅暴打一顿表舅妈,但往往这个主意在表舅的磨磨蹭蹭中只能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表舅不打时有不打的说辞,说是害怕把心打寒,怕把表舅妈打怕了,下次不敢回来。但表舅妈犯了众怒,民怨沸腾得要冲上房顶,表舅要是再不打,别人恐怕就要打他或者打她,这时候表舅也只得来一顿。但只是蜻蜓点水,手举起来,棍举起来,落在身上却像是棉花团。表舅的手放笼子抓黄鳝一抓一个准,割稻割麦插秧扶犁都是一把好手,就是打不来表舅妈。
所有人都认定了表舅是一个怂包,我们小孩子也表示十二万分的赞同。
这样来来去去,次数多了,表舅妈的出逃就不再是新闻,顶多是一般谈资。一人说,玉清家的又跑了。另一人说,那婊子啊,跑了就跑了,不稀奇。再一人说,人家玉清不急,我们急个屌?
5
表舅捉回表舅妈的消息我是在放鹅回来的那条大路上得知的。天擦黑,我们分好了各自家的鹅,一拨一拨,鹅在前,人随后,长蛇般向前蠕动。夕阳最后光束渐渐隐去,天上只落下单飞的鸟,孤单地扇着翅膀,路两旁的稻稞散发着清清的香气,偶尔能听到一声短促的蛙鸣。炊烟浮在村庄上空,时隐时现。
我们手中的竹竿树棍都成了摆设,鹅很自觉地向前走。我和我的鹅群在后面,走着走着,我感觉前面在提速,像是要赶时间。前面加快,我便也跟着加快,我把手中的树棍舞得啪啪的,原本迷瞪瞪的鹅群,惊得瞪大鹅眼,加快鹅掌。我急忙忙地问前面的出啥事了,前面的朝前面望了望,摇摇头。我向前面的法子喊,法子应该是得到了消息。他说,你表舅妈被你表舅捉回来了,今晚上有好戏看。法子说着怪异地笑,说时使劲抖着手中的竹竿,竹竿头上拴着的塑料布哗哗作响。他的鹅便纷纷向前跑,跌跌撞撞,慌不择路的,有几只还连滚带爬,被法子一脚踢起来。法子嘴里叫着,赶快赶快,再肉,看我不踢死你。
我说,回就回呗,哪年都一样,没有新戏。
法子头也没回,摇头晃脑地丢下一句,别说我没告诉你,晚上有好戏。
我喊道,法子,什么戏?
等我赶到家,慌慌忙忙把鹅归拢进鹅圈,发现家里大门紧闭,屋里早没了一个人,只见灶台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空了的碗筷。他们,竟然都不等我?
掀开锅盖,一碗发泡的米粒团在锅底,像一坨鸟屎。我没一点胃口,转身出了门。我已经和法子说好一起去。法子家在我家西边第五户,我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正站在他家灶屋门口,面朝锅灶,身子一抖一抖的,鼻子里直哼哼。我上去推了他一把,我说走。他没回头。我看他妈妈在灶膛烧火,他妈说,熊样,饭没烧好,等一会会死啊,我看你是又想挨揍,三天不打,皮作痒。法子哇哇地哭着看我说,谁家现在还不吃饭,我不吃了。他妈说,滚。
法子一听,得了圣旨般,拽起我撒腿就跑,生怕他妈变卦。
我们到了表舅家时,屋里已挤满了人,房里小娃子多,堂屋基本上都是大人。大人们围着蹲在地上的表舅,表舅提着个小锤子往地上砸,地上是盐。不透明的白,泛着阴翳的光。我来不及想这盐的用途,和法子赶紧往房里挤。只见表舅妈下身穿蓝色的确良裤子,上身穿着白底蓝花的布褂子,侧躺在床上,脸朝里,看不见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她根本不理会我们这些小娃子们。我好几次试图看看表舅妈的脸,都看不到。
看不到表舅妈的脸,心里蹿出的那团火渐渐小了,人却不愿意离开房间一步。我以为我可以一直占着那个地方的,可是一会工夫,表舅带着大人们进来,表舅左手拿着一把菜刀,右手攥着的,应该是盐,我看到表舅的食指上有透明的白。我爸我妈站在表舅身后,表舅说,小娃子们出去。一听说让我们出去,我们就龇脸了,好不容易占了个地方,想看好戏的,戏要开场了,怎么让我们出去?
可是胳膊拗不过大腿,爸妈们朝一溜小娃子们吹胡子瞪眼,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只能噘着嘴,垂头丧气出了屋。房门啪地在我们身后关上,表姐和表妹守在门口。法子说,去窗户。到了窗户前,傻眼了,窗户也被关上,大表哥和二表哥站在窗前。事实上,表舅家还是土墙瓦房,这与当时庄里多数人家盖的砖墙瓦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窗户是老式的,有一个中等锅盖大,窗框上贴着薄膜。要不是两个表哥挡在窗前,我们贴着薄膜,多少也能看到或者听到一点里面的动静。
我们坚决不走,站在窗户的两侧。
两个表哥对我们怒目而视,都把双手抱在胸前,随时准备着对我们可能的侵犯报以还击。每个小娃子都不吱声,脸上是少有的凝重。耳朵支棱起,心咚咚跳着,带着期望等待着。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感觉下眼皮快要撑不起上眼皮,空气中有一股臭屁味,接着是法子的肚子咕咕叫,我忍不住笑,用胳膊捣了下他,他不好意思地回捣了一下我,也憋不住笑。这样一笑,人立马清醒了。
6
大舅妈凄惨的叫声就是这时候冲进了我们的耳朵,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恐地冲向窗户,想从窗户的塑料薄膜上看见点什么,或者是听见点什么。两个表哥的手垂了下去,他们似乎已经无暇顾及我们。我们贴近窗户,耳朵里传来不同人的嘈杂声,其中当然有我爸我妈的声音,他们说的最清晰的字是血,血止不住怎么办?有人说,锅沿灰。
房门开了,里面有人出来,我们扑向房门,门口站着的表姐和表妹抱在一起,哭作一团。我听见表舅妈说,林玉清,你给我记住,除非你把我弄死了,要不然我还会跑。而且下次我要是再跑,死我也不会再回来,死我也要死在外面。
几个大人挡在了我们的面前,弄锅沿灰的我爸抓了一把灰过来,推开我们。我迅速看了一眼床上。表舅妈仰躺着,脸煞白,牙咬着嘴唇,眼睛睁着,恨恨地望着屋顶,白底蓝花褂子上散落着几滴血的印痕,仿佛是红色的花。蓝裤子没穿,花裤头露在了外面。裤头下的一条腿泛着白光,一条腿血红。表舅蜷曲着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脸死灰一样,手按着布,布盖在表舅妈那条血红的大腿上,布应该是白布,白布变成了红布。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感觉恐怖,身体里凉飕飕的。快九月了,我过几天就要去中学报到,我越来越盼着早点离开。这个暑假最好玩的还是放鹅,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我用胳膊肘捣了一下法子,我说,听你胡说,哪有好戏?法子一听,捂住肚子说,我要回家,我饿了。我的肚子也跟着咕咕叫起来。
我妈和我爸不久也回了家,我妈进了屋,意犹未尽,若有所思,进门时,差点绊在门槛上,我爸伸手拉住了她。
我爸说,别说,这个女人真够准的。我妈甩开我爸的手说,你们男人就是贱,一个比一个贱。我爸抬手猛推了我妈一下,恨恨地说,你哪还是女人。我本来觉得我妈不会倒,最多向前跨一小步,没想到我失算了,我妈竟然跌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我妈边哭边说,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你以为我想把那把盐塞进去?你看看玉清那个怂样,到跟前的事,当缩头乌龟。我爸说,那也不是你该掺和的事。我妈叫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啥,那女人,就是一个骚货,你是哪棵葱,自己也不掂量掂量。我可跟你说,你最好别惹急了我,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妈在地上腾挪着,既不想起来,又想撕扯我爸,处于两难境地。
我像是个呆头鹅,不知所措。幸好我姐我哥回来了,一边一个把我妈架了起来。我爸把着冒烟的烟袋锅出去了,我妈也就自动熄火,成了哑炮。
第二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家,听法子说,我表舅妈又跑了,还带走了我表姐。这下,彻底打乱了我表舅的如意算盘,我大表哥一气之下去了海南,说是不闯出一个人模狗样,绝不回家。
大表哥走了,表舅让二表哥去学木匠,二表哥把头一甩说我不去。表舅说你必须去。二表哥说,我要看着这个家,我要看着你,林玉清,我不会再让你去找马翠花,我哪也不去。表舅气得蹦到二表哥跟前,甩了二表哥一个嘴巴。二表哥没有后退,一脸愤恨地迎向表舅再次举起的巴掌。表舅愣住了。表妹在后面喊起来,够了,你们难道觉得这个家还不够丢人?马翠花走了,我们就当她死了,从今往后她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马翠花是马翠花,我们是我们,她不要我们,我们更不要她,她如果回来,我走。表妹又对二表哥说,林二子,如果你还是个男人,你就去学木匠,你是这个家的希望,你三年木工学回来,我正好也长大了,那时,如果你找不到女人,我拼死也要给你换一门亲,我要让我们这个家能够在这个庄里和别人家一样,过得像一个家,家有家样,人有人样。
林玉清,表妹直呼表舅的名字,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这一切,总该结束了吧?表妹说得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表舅惊呆了,他腿打软,一屁股坐在地上,什么话也不说,愣愣地,仿佛在梦中,又仿佛在梦外。
关于我表舅妈和表姐是如何离开庄子的,众说纷纭。
其中,最有鼻子有眼睛的说法是,那天下午,表舅照常放笼子,走时,让表姐看着表舅妈,结果表舅妈连表姐也给带走了。庄里人推测,庄里肯定有内鬼,要不然她们走不了,那个宋老二也不敢来。我表舅早说过,要砸断他的腿,打烂他的头。他那个样子,就是披着一层虎皮,庄里人也能认出来。
那么就是内鬼了,有人甚至说,看见有个男的骑着自行车,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轻悄悄地把她们带走了。
晚上吃晚饭时,我妈也不看我爸,又开始嘀咕,是谁呢?我爸吃得好好的,听我妈说话,像想起了什么,端着碗往外走。我妈看了眼我爸的背影,呸的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二表哥去学木工了,表舅没再去找表舅妈,他早晚照常准备蚯蚓,放笼子收笼子,卖黄鳝,他还用卖黄鳝的钱买了一百只小鸭。小鸭子毛茸茸、黄灿灿的。表舅不在家的时候,表妹没事就围着鸭子转。
有一天,表妹对我说,等它们长大些,她会和我一起去放鸭子。我说我放的是鹅,我们家没有鸭子。表妹说,那怕什么,鸭子和鹅又不打架,都要下水的。我说,你们家鸭子到我放假时,还不知道能剩几只?表妹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气冲冲地说,除非它们得瘟病死了,要不然一个都不会少。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鹅鸭成群的画面,好气派的样子。我说,那好吧。
戚佳佳,安徽省作协会员,自2019年起,小说作品散见于《清明》《山东文学》《当代人》《阳光》《四川文学》《延河》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