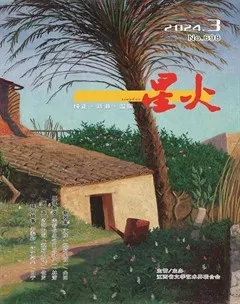今我往矣
2024-09-11燕茈

一
像一个走了很久很久的人,九十多岁的阿婆就要倒下了。
身上哪哪都疼,又说不上具体哪里疼。她经常双手抱紧自己,头一直往被窝缩,尽可能地把自己裹在温暖的棉絮里。她在大儿子家住几年又在小儿子家住几年,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她是一个负担,就商议决定将她送回花树下,家人轮流回来照顾。阿婆张了张口,把所有的话都嚼碎了,吞进肚子里。
有一天,阿妈打电话来同我商量:“你阿婆想住在我们家,住你的房间,由我们照顾她,她家人住城里来回不方便。”
我说:“阿婆五世同堂呢,末了就一个人都没有吗?”
我妈说:“我上午去看你阿婆了,她很高兴,很想和我们一起。她一个人太可怜了。”
我说:“好。”
阿妈最终没有接阿婆过来,她说觉得这样会对不起我阿嫲。
我们家住在一层低矮的平房,是旧房子拆了重建的,老屋后半截没拆,留下两间房,一间给阿嫲住,一间用来做厨房。老屋和新屋之间是相通的,同一个大门进。阿嫲不愿住新房,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不能把房子弄脏。她确实又很喜欢这敞亮的新房子,时常在平房里进进出出,坐在厅里和左邻右舍说话,将房前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阿嫲自己不舍得住的房子给别的老人住,她知道了是会很伤心的。
阿嫲和阿婆是妯娌,两人年纪相同。我阿公是兄,家贫,连住的几间瓦房都是借弟弟家的。阿嫲已经过世十几年了,活着时,处处矮阿婆一截,阿嫲心里暗暗较着劲。她羡慕阿婆家大大的房子,羡慕阿婆四代同堂笑得开怀,羡慕阿婆衣服布料的柔软……她每每看阿婆那派头,心里总酸楚得不行。
阿婆的曾孙都已经两个了,我才姗姗来迟。我出生时,家里一件旧衣裳都找不到,只能用粗粗的草纸裹上。阿婆来看过我,将曾孙的旧衣裳整理了两大箱,洗干净送到我家里给我换上,细细地抚摸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脚,一种怎么疼都疼不够的感觉,说:“唉哟,阿妹手长脚长呢,像爸爸。”听阿妈说,我还会对阿婆笑。阿嫲很高兴,也对阿婆笑。阿婆对我的疼爱自然是不必说的,我对阿婆的好也是不必说的。
阿婆怜惜我们家徒四壁,怜惜我父母一把年纪孩子这么小。她会把家里用来喂猫的猪皮带给阿嫲炒青菜,也会带来点零食给我,一块糖,一根芭蕉,一片红薯干……我记得这许多细节,记得这许多的好。
当我慢慢长大,阿婆的家人全都离开花树下到城里过好日子去了。阿婆说在城里像坐牢一样,终日一个人坐着等一日三餐,等时间到了就睡觉。她那时还能照顾自己,便让家人送了回来。我对阿婆也好,给她挑水,给她送去柴薪。她的厨房很大,里面一片漆黑,多少次,我走进去像走进了隧道里。没用的那几个火炉散发着陈旧的尘土味,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刺鼻气味,应该是一种快被人遗忘了的气味,陈腐的气味。看得我有些伤感,我将小木窗的门打开,有风进来,梁上的蜘蛛网在动。
她一有时间就来我们家,有空时我会拿来指甲钳给两位老人修剪指甲,阿婆的手指又长又白又细,在松弛多褶的皮肤包裹下依旧是好看的。阿嫲的手黑乎乎的,有一根手指头还因摸石螺被水蛇咬弯了一节。她的指甲很脏很黑,我总是给她剪掉指甲后再细细挑去夹在里面的污垢。阿嫲多忙啊,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她拿什么和阿婆比呢。我安静地给老人修剪指甲,听她们说话,讲那些遥远的故事。阿婆从不掩饰对阿嫲的羡慕,羡慕她身体强健还能帮家里操劳许多家务,羡慕她儿孙绕膝有人加餐饭有人添衣。她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乖的女孩,她说她的儿孙们只会给她钱,给她买吃的。她说钱有什么用嘛。我当时不理解她的孤独,觉得钱怎么会没用呢,我们家这么辛苦不就是因为缺钱吗?
阿嫲去世时已八十多岁。我们全家守在她身边,听她一声一声地呼唤我的名字,呼唤家里的每一个人。阿婆说阿嫲好福气,走得安详,不知道自己以后走时有没有人送。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我已开始工作。回去时会给阿婆买上面包,麦片。我常常遗憾阿嫲没有等到我成年就去世了。我常说:“阿婆,您比阿嫲多活了十几年呢,不亏。”阿婆说,活着有什么用,一个人在这老屋,白活。
阿婆有好几个孙女,都已成家,也常常回来看她。有一次我听见阿婆埋怨:“你们老是不回来。”几个堂姐解释,要上班,要带孩子,有时间都会回来的。“你们多点回来嘛,好不好?”我从阿婆的语气中听见了委屈,还有一点点的撒娇。她的声音柔弱,弥漫着忧伤。我的心小小地疼了一下。堂姐们走后,阿婆叫我过来,递给我两张红色的人民币,说你爸妈生活条件不好,这钱给阿妹上学用。我摇摇头没有接,她以为我还是那个上中学的女生。
阿婆一天到晚坐在凳子上,瞭望着山瞭望着水,瞭望着日出日落……怎么望也望不够。她看见许多光,她就在这美好的光里做梦,她的梦越来越美,越来越远。她梦到了春天百花开,梦到做女孩时的娇羞,梦到了与意中人白头偕老、儿孙满堂……她眼中浑浊的泪让梦变得又苦又涩。
二〇一二年腊月,阿婆与世长辞,如她所料一般孤单。阿爸阿妈去看她时,尸体已经僵硬,可能是夜里走的。她的孤寂照见了人间的许多无奈、冷漠。报丧后,孝子贤孙齐刷刷站了一屋,可谓壮观,我和他们一起,也披麻也戴孝。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难,无力去苛责什么。
我只能悄悄在阿婆的墓穴里抛一朵小白花。
二
“和你商量个事,我们订了两副长生(棺木),按照规矩这事得女儿办。”阿爸六十岁生日那天,阿妈的电话把我吓得不轻。
“干吗呢?”我问。
“我们都老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按照以前的风俗,早该准备了。到时候,你把钱付了,顺便把我们的寿衣也准备一下。”
村里老人一过六十岁就要提前买一副棺材放在家里摆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看淡生死,从容面对迎接死亡。这种对生的眷恋与对死的坦然,让我挺动容的。村里有个伯婆,迎接死亡迎了四十几年,依旧顽强地活着。她是和我阿嫲阿婆同一时代的老人,具体多大年纪了没人知道,大家都忘了她具体的生辰,按照推算肯定是有一百多岁了。
她的儿孙也已搬到城里,儿子开始也留在花树下和她一起生活。当她第三个曾孙出生后,儿子就再也腾不出空回来了,在城里帮着带三个孙子,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接送他们上学放学。
她一个人住在花树下,一晃好多年就过去了。
伯婆是稳婆,接生了几十年,我们的父辈是她从娘肚子里掏出来的,我们也是。她一生接生过多少孩子,没有人去计算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她还到卫生院培训学习过。一把剪刀、几卷纱布、一瓶红药水、一盆热水是她的全部工具。她懂女人,无论是阵痛还是撕裂般的剧痛,她都能感同身受。她会一边轻声安慰:“很快就见到宝宝了,加油,你已经很勇敢了。”
按照规矩,每接生一个孩子,主人都应该送她一篮子红鸡蛋、一壶客家娘酒。不管是闹饥荒还是生活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她都没有要过,“我一个闲人,吃了干啥?得给产妇补补身子,一人吃两人补。”几十年来,孩子们一茬一茬地出生,一茬一茬地长大。
长大后的年轻人都搬到别处了,此时整个花树下都是安静的。伯婆一个人住在两层半的小洋房里,房子里装了监控,每一层楼都有摄像头,儿孙们一有空就看监控。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难,全投影在监控里。伯婆的棺木就放在一楼的杂物间,红漆早已掉光。伯婆硬撑着就是不死。她身体挺好,一年到头无病无灾,生活完全能自理。她养了一群鸡,种了一园子青菜,迎着节气种花生、黄豆、玉米、红薯……从前河对岸种了好多柿子树,几十年后,就剩下一棵了。我觉得伯婆就是这最后一棵柿子树。
很久以前的清晨,阳光明晃晃地照耀着名叫花树下的村庄,河水悠悠地流淌。许多妇人卷起裤脚,站在清凌凌的河水里浣衣。河边一束束墨绿色的叶子,上面开着红色的花,红得有些耀眼,还有一些透明的碧色浆果。枝叶缠缠绕绕,和其他藤蔓缠在一起,散发出一种甜甜的气味。没有风,但是树叶在晃动,或许有什么小动物在里面走动,也或许什么都没有,是树叶自己在动。我坐在柿子树下看她们,也看花。前面是金黄的稻田,稻田被群山环绕。身后是石阶,一级一级,一会儿妇人们陆陆续续走在石阶上往家的方向走去……有时会被一片落叶打了头,抬眼看看,柿子熟了,红色的果子“吧嗒”一声砸落在地上,溅出红色的果酱,像是古时的马蹄,从河对岸传来。
伯婆即将死去了吧?她驼着背,一步一步走得缓慢。她的背很弯很弯,身体越来越靠近泥土。她总是在河对岸的菜园里忙忙碌碌。从前热闹时,河对岸整片地都被种满了青菜,一到傍晚都是妇人挑水淋菜的身影。现在整个菜园子都没人管了,她想种哪块就种哪块。以前划分界线,锄多一块土,就会有人不乐意,大动干戈地又吵又闹。现在没人争,没人吵没人闹,都清净了。
我们家有一只狸猫,养了很多年。我们搬离花树下时,没能带走那只狸猫,想着它会抓老鼠,也不至于饿死。阿爸经常回来,他会在猫碗里放上剩饭剩菜,离开时再撒上满满的鱼干。弟弟的小孩出生后,父亲照顾孙子都照顾不过来了,再没有精力大老远地去照顾一只猫。后来回去,父亲到处找,找遍房前屋后,猫不知所踪。再后来,阿爸很高兴地告诉我,猫去了伯婆家。有一次我和阿爸回去,看见伯婆抱着狸猫坐在门口晒太阳,她和它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她低头问猫:“饿了没有?”我被这一幕烫到了。
伯婆的样子和我阿嫲阿婆离开时很像。瘦骨嶙峋,双眼深陷,嘴巴凹进去,耳朵听不清了,眼睛也已经模糊,有个人站在她面前,她把花树下所有认识的、还能想起来的人的名字念一遍,都不一定能念到准确的名字。
我喊伯婆喊了很多遍,她才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我。看了好久,才问:“你是谁呀?”我告诉她,她看着我,一脸困惑,不可思议的样子,信号不通似的又问:“谁呀?”她的声音变得遥远而缥缈。我大声说:“五婆孙女。”五婆是大家对我阿嫲的称呼,她这会儿信号接上了,“五婆身体好么?归来么?几时归?”她以为那些老人都和我们一样只是搬了个地方,逢年过节还会回来。我哄她:“年晚就归,到时来家坐坐呀。”“哦,好,她归了你讲我听啊。”“好的,一定讲你听……”
许多年没有回去了,有一天在莲花山上遇见一只狸猫,蹲在树下,好奇地打量路过的新人。我打电话问阿爸:“我们家的猫还在吗?”“早不在了。”“那……伯婆还在吗?”阿爸说:“不在了,都走了很多年了。”
嗯,许多事,我都没办法一一讲给你听。
此时,烈日炎炎,白云滚滚,还有芒花一片。
三
空气有些潮湿,晚上,还下了细雨。我们疲惫地盯着屏幕上的监控回放,看见伯父走出来对正在忙碌的儿子说:“狗仔,早点给我洗澡。”狗仔哥说:“好,等一下。”
伯父等了等又说:“端午了,叫小妹她们回来。”
“今天晚上放假,明天早上她们就会回了。”
“嗯。”伯父徐徐走回房间,慢慢躺回床上,掖了掖被单,被单又滑落了一点,他轻轻地将被单拉了一下,闭上眼睛睡着了。半个小时后,狗仔哥进来喊爸。一连好几声,都没有回应。伯父无声地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端午节的前一天。
他是知道自己要走了吗?叫自己小女儿回来,叫儿子将自己洗干净好上路。之前无病无灾,谁也没有接收到他的信号。子孙们立马就放假三天,奔丧都不用请假。百日回来烧屋给他,刚好中秋也放假。如果这样,他在离开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
都说他很会死,不给孩子们增添一丝一毫的麻烦。这样的声音迅速落入我的耳中,我为他对人的体谅感到些许的疼。
伯父是我阿嫲早逝的前夫的侄子,名义上和我们沾亲带故,其实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伯父家人丁单薄,整个家族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这个世界,最后剩下他一个人,家里穷得无遮无拦,他捡了个疯子老婆,想着过过平常人家的小日子。我没有见过我的疯子伯母,她曾经生育过几个儿女,但那都没活下来。我那伶仃孤苦的伯父,饱尝了多少人间的苦。
疯子伯母再生孩子,我阿公毫不避讳就在门口等。伯母这一对儿女全是我阿公小心呵护着成长的,他们长大成家后各自生了两个儿子。每当有人对伯父说不要太操劳,太辛苦了。他总会淡淡说一句:“对于我来说,最苦的日子过去了。”在那个灰头土脸的村庄,他一定重生过。
有个疯子娘对于堂哥堂姐来说是崩溃的。她常常兜着脏兮兮的红薯到学校教室喊他们的乳名,要把红薯给他们吃。同学们的笑声如此刺耳,他们含着泪,心里又气又疼。他们常常看见疯子娘被嘲笑,被辱骂,被扔石头,看见疯子娘傻笑,一跳一跳笨拙地躲避,有时候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声与求饶声。一个人怎么可以悲哀到这个程度呢?堂哥二年级时,疯子伯母去世了。有人说她是病死的,有人说她是饿死的,也有人说她是被打死的。堂哥堂姐哭得不能自已,娘就是娘啊,疯子娘也是娘,她活着就有个人可以喊,就有个人可以操心,可以心疼,可以感受她笨拙的关心与疼爱。死了,就是再也没有了。
从三十多岁开始,伯父孤独地活了半个世纪。他对我们家极好,插秧时节会卷起裤腿加入我们,秋收时又带一把镰刀出现。我看着那个年迈的老人,颤颤巍巍走在金黄的稻田中。阳光一晃,洒落许多光。
彼时,阿公阿嫲早已去世,阿爸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他们的贫穷。伯父的儿女们已成家,伯父带大了孙子们。他一个人住在老屋,吃穿自然是不缺了。他闲不住,养了一塘鱼,他经常在河边割鱼草,鱼塘上漂着绿油油的青草。有时他会钓来几条鱼,剖肚洗净挂在我家的门环上;有时会择一把芥菜立在我家门边,有时则是几个削好皮的芋头……这是他的心意,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善我们的伙食。他是把对我阿公阿嫲的思念与感激化成关爱转移给我们了吧?他用自己的方式对我们好,朴素又真诚。
我们离开那个村落好些年了,有一次傍晚路过灯塔镇,想着回老屋看看,看见伯父坐在我们家门前的阶梯上,静得像雕像。我问伯父怎么不回家?天都黑了。他说他在等阳仔(我阿爸的乳名)。我有些难过,有些惊慌失措。老人都擅长等待吗?
老屋的屋梁上结满了蜘蛛网,房子空着,桌子空着,椅子空着,满眼满眼的尘灰盛开着寂寞。仿佛是一瞬间的事,我们就突然长大了。那些人和事还留在这里。那些温暖与感动还挂在老屋的门环上。
知道伯父走得安详,我没有哭。堂哥给伯父洗了脸,换了衣服,伯父就被挪到大厅去了。他全身冰凉地躺在冰凉的席子上,神态安详,皮肤上沟沟壑壑的皱纹一起苍白着。他穿着白色的棉布衬衣衬裤,蓝色的棉袄棉裤,藏蓝色的罩衣罩裤。堂哥怕他冷,又给他穿上一件厚厚的黑色呢子大衣……入殓时,入殓师说再看一眼吧,这是最后一眼了,以后想看也看不到了。我努力挤到前面跪下,看见他僵直地躺在那里。我的泪终于落了下来。每一个人的泪,都在那一瞬间落下。他一生清苦,终于解脱了。
他的床、被子、椅子、桌子……全都搬出来,一一焚烧,和他一起灰飞烟灭。那个他一直不舍得丢的烟盒子里有一千多块钱,是他留下来的。按照老家风俗,这是他留下来的福气,要留给自己的子孙。堂哥和堂嫂也分了一张给我。我分到他福气的那一刻又想哭,这张人民币是我上次回来给他的那一张,左下角有个用红笔画的小小的6字。女儿分不清6和9,当时拿着笔随意就在人民币上写了这个字,问我是不是6。
加上我们一家人,送葬的队伍依旧是冷清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家人丁依旧单薄。我们把他送上风流坳,看着他的棺木徐徐降落,最后被泥土覆盖。他那提起就让人觉得心酸不已的过往一并被掩埋在这小小的土坑里。伯父曾经是抬棺木上山的“八仙”之一,他旁边的老人大多都是他抬上来的。人们活着太辛苦了,总得找个合适的时候死一死,需要好好躺着,需要安息。
我们要回去了,按照风俗,每个人要带点青回家,辟邪。我折了一把山茶枝、一把山稔花。我手上缠着的白线垂落下来,垂到了青上。我用它串起琳琅的晨露,挂在老屋的檐下。替我,等他们。
燕茈,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散文》《美文》等刊;出版散文集《花树下的旧时光》《再见花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