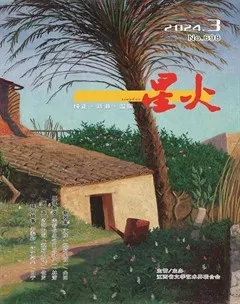走出深渊
2024-09-11逸云

1
那是一个深渊,至少在一个孩子眼里。
我躲在父亲身后,父亲身上弥漫着的异常的悲愤让我产生从未有过的害怕,在我眼里心地良善温和的父亲,于那一刻,像只凶狠的野兽。
他手里抓着一只小狗,用尽全部的力气把它砸下深渊,小狗微弱的挣扎声消失了。这个画面一直像梦魇般,不管我长得多大,都会不定期地清晰再现。
我一直弄不清这是梦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我不敢去问父亲,甚至不敢去问其他人。如果发生过应该是在我刚满两周岁不久,可那么久了我能确定它是真的吗?
后来,我从身边不同人欲言又止的话语中还原了当时情景。一九八一年农历十月初八,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母亲,因为一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狗。我们家在村子中央,旁边就是村小学。本来在上海纺织厂工作的母亲因为怀了我,回到江西老家,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店。那是全村唯一一家商店。母亲热情好客,我家院子里常常坐满了左邻右舍,无形中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村里人都喜欢养狗,母亲也不例外。母亲养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仔,小狗在母亲细心呵护下长得毛茸茸的招人欢喜,几只小狗习惯地在人群中蹿来蹿去装可爱,大家都爱逗逗它们,用手抚摸它们。
这天,其中一只小狗有点异常,莫名其妙见人就不停地吼,有些癫狂。母亲连忙上前制止它,半蹲下来试图用抚摸来安抚它。那只小畜生扭头咬了母亲的中指。母亲一惊,边生气边本能地把手指放嘴里吮了下,又连连吐了几口口水。谁也没有料到,阴险的病毒就此悄无声息地潜伏到母亲的身体里。四十天后,母亲病发,不到一个星期她短暂的人生就戛然而止,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那年代农村对狂犬病认识不深。奶奶曾遗憾地跟我说,当时劝过母亲去医院。上过初中的母亲,在那个时期也算是知识分子,可这个事她竟没当回事。她压根没有想到她眼里的小奶狗是病毒携带者。病毒毫不留情地入侵了漫不经心的母亲,把她带去了另一个世界,留下我和哥哥姐姐四个孩子,而我尚嗷嗷待哺。从此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被改写,原本简单幸福的家庭,坠入痛苦的深渊。
母亲有位闺蜜,她说她陪了母亲最后一程,每次看到我似乎都忍不住想和我说些什么。有一次跟我谈起母亲去世时被病魔折磨的样子,说母亲竟发出狗吠声。我皱着眉头缓缓抬头看着她,我揪心的样子让她不敢再说下去,却又不好马上停下来,只好把话题转移,说我父亲当时伤心欲绝,说我没有断奶,怕被病毒感染,连续给我打了好多针。
母亲的离去,让原本欢声笑语的家破碎了。父亲承受的伤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那个梦魇,极大可能是真的。这伤痛会滋生仇恨,作为罪魁祸首的小狗必然要受到严惩。但就算如此,依然不能减少它带给父亲,带给我们整个家庭的伤害。
我小的时候,亲人和邻居掩饰不住对我的同情和疼惜,让我显得和同龄人很不同,这份不同里夹拌着的小心是复杂的,极不自然的,似乎时时在提醒我没有妈妈。我过早地懂事,心里清楚这一切看似美好只因我是没有妈妈的可怜孩子。这就如从小长在我身体里的一个肿瘤。我与那夺走我母亲的畜生不共戴天,不管它以什么姿态出现,都让我感觉面目可憎,我深深地恨着它们,它们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控制不住,只要见到它们,就会想到自己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它们剥夺了本属于我的爱,最天然最真切的爱。虽然父亲重新为我找了新妈妈,但丝毫弥补不了因母亲过早离开带给我的残缺,让我对“母爱”这个词穷极想象也无法正确解读。
2
我把我生命中一段漫长的时光理解为复仇岁月。
十九岁时我嫁的那个人,大我七岁,那时候的他也算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较殷实的家底。十年婚姻,开始于所谓的爱情,却不过是无知的惩罚。他仿佛比陌生人还理直气壮地把那个物种带入我的生活,让我不得平静。一九九八年,他从省城带回一只混有藏獒血统的犬,在乡镇招摇过市。我们正在建房子,他说让它守着工地。那时候的我乖巧无比,只是对那个畜生尽量避而远之。房子造好了,屋后面扩了两个大院子,近两百多平,他又有了理由,说必须觅只狗来看家护院。两只罗威纳耀武扬威地进了家门。
三只大物,他给了它们乐此不疲的恩宠,每天为它们煮食、喂水,带它们溜达,和他人洋洋得意地谈论。他给它们起了洋气又响亮的名字,什么马菲,什么炮弹,什么扎西……罗威纳那短短的尾巴,硕大的身体,黝黑的皮毛引起了小镇上人们的好奇和热议,满足了他带狗出去的虚荣。只是很快他有了新的烦恼,因为养狗人好斗,总是喜欢起哄纵容它们打斗,赢的人就人仗狗势不可一世的样子。而他一直是个不服输的人,于是开始寻思着要弄只打架厉害的……
他开始跑省城的狗市,两千元一只买来两只不到两个月大的比特犬狗崽,可养不到一周狗就夭折了,埋在后院。他不肯作罢,再次去省城淘来两只,更加小心地饲养,还是没有撑过一周。第三次,他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终于把两只黄色的几乎没有毛发的比特犬养大了,期间那只野种藏獒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被他埋在后院里。
他本不是爱犬之人,是乡镇的生活让他无所事事的时光变长,狗只不过是他的玩物。在这个过程中他貌似用心,每天早上到家对面的菜市场猪肉摊前拿屠夫帮他留好的猪肺,两元一个,两个是最少,多的时候五个,在人均工资不到三百的年代,这些是他从来不放在心上的开支。他又特意买了超大的钢精锅,煮猪肺要加米或者面条,不能放盐,煮好后要等其冷却才能投喂。那些年他养了一波又一波狗,煞费苦心。他还学会了自己给狗打针,给它们喂药。狗链、狗笼、狗绳这些也让他挖空心思,普通的狗链是无法约束两只比特和两只罗威纳的。他从工厂弄来较粗的铁,绕成环,擦得锃亮,环环相扣,沉重之极,有点像人们攀岩时用的卡扣,然后将数十个环连接成链。这又再次招来了镇上人的赞叹。带它们出去战斗,处理狗身上的伤口,给狗清理身体,平常清理狗窝,不做家务的他干得毫无怨言。
两只比特犬疼痛神经迟钝,在外面被咬伤了也不“哼哼”,更不会感觉戴在它身上的链子如“镣铐”。咬斗中它们麻木又凶狠,不咬死对方不松口。这两只比特犬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带着它们打遍附近村庄,无往不胜。通常开战之前就约好,咬死的狗留给赢方处理,不管多舍不得。
那些土狗一只一只成了他的美食。他不需要自己动手收拾,都交给了陪着他壮声势的所谓朋友。他们中总有些能人,在弄吃的面前是能显神通的。那些惨死在斗狗下的土狗,他们细心地处理,手法和现在很多美食主播有得一比。狗被处理干净后放进自搭的柴火灶的大锅里,加上点生姜和八角煮到恰到好处。深夜,正是他们美餐的好时刻。没有多余的配料,通常是蘸着老干妈熬的汁吃,应该算是白切吧。他袖手旁观,又心安理得地等着香喷喷的狗肉端到面前。他和同伴们津津有味地吃狗肉,比起吃狗肉的兴致,他更喜欢听他们津津有味地回忆现场的惨烈,夸他的比特犬所向披靡。这中间得到的快感,让他觉得为此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经常会带弄好的狗肉回来。我会吃,每次吃的时候心情都难以言表,咬牙切齿地,想着本来要把它们碎尸万段,吃肉算是便宜它们了,嚼碎了吞下肚又让我很是膈应。
很多人家里都有一条叫“来福”的土狗,我们家也有一只。与那些有着特殊基因的狗同在一个屋檐下,它是那么楚楚可怜。它长得灰不溜秋的,个子也只有它们三分之一大。每次比特犬和罗威纳一吼,它就吓得无处躲藏,企图往我这边躲,可惜我不是疼惜它的人。能让它靠近已经是我最大的容忍。来福的友善在我这里没有得到一丝回应,它更加无所适从,后来来福被他送到他妈那里去了,它的去处我毫不关心。
比特犬长得很快,很快到了要配种的时候。他早就有打算,两只比特犬本来就是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何况还有罗威纳,还有他早就怂恿他朋友也买了一只公比特,为了保住好基因他早就埋了伏笔。他朋友的比特和母比特很快交配成功,母比特产下四只幼崽,只是两只很快夭折,还有一只挺过了一个月,也随前两只一起埋在后院。幸存的那只,他异常小心照顾,只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意外发生的那个夏天的上午,异常闷热。他是个生活没有规律的人,深夜清醒,第二天下午才起床。而我在自家房子开着超市。我隐隐约约听到小狗的叫声,只是一直没有去后院看看怎么回事。直到下午他醒来才在后院发现小狗被吊死。他一直知道我对狗的冷漠,只是说了下那狗跳到围墙上,从另一边跳下来时,它脖子上的绳索挂住了,小狗被活活勒死。我能想象到那景象,我脑补了下那死状,心里发怵,它呼救的声音和梦里父亲抓着的那只小狗的挣扎声是那么的相似。我清楚假如我稍微关心下,听到它的叫声时能去后院看看,就能救下它,是我的漠视让它没有了生的希望。它最终没有躲过埋在后院的命运。
半年悄然过去,那些消失的卑微的生命似乎没有了痕迹,比特犬这次产下八只小比特。冬日里暖暖的午后,他带着一双儿女在后院和八只小狗嬉戏。孩子异常欢喜,把企图逃离的小比特一只只抓回排好队面对着他的镜头,那一刻因有孩子的参与,也让我感受到片刻的美好。在儿女们灿烂笑颜的映衬下我注意到那几只小狗仔憨态可掬。只是好景不长,赶上过年超市生意十分繁忙,有次一整天没有喂食,等他晚上再去弄食物给它们吃的时候,它们被寒冷和饥饿带走。后院泥土再次被挖出一个个坑,它们被整齐地埋到泥土里。
我已经数不清后院埋了多少条狗,只是后院结的柑橘、脐橙、石榴又大又甜,每次摘给左邻右舍得到的都是赞许。乡镇上的人大部分有点地,都爱种点什么,很多时候人们热情送出些水果平常不过,只是好吃的不多。然而,吃过我们家后院水果的人总念念不忘,到了果子成熟的时候就嚷嚷着叫我摘点出来尝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时常站在三楼的窗台前俯视后院。想着这些畜生的死去,于我算不算一场轰轰烈烈的复仇?我沉睡很多很多年的母亲是不是能得到一点安慰?这分明是我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光,我却心事沉重,表情单一。我是该感谢他给了我这么多机会看着我的仇敌在我的视线里一个个离去,还是该愤恨他从不在乎我的伤痛多年来乐此不疲地养着这些畜生?我不得不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投喂它们,给它们煮投喂的食物。甚至我和孩子不可避免地被伤害,不得不去打狂犬疫苗,我独自面对我内心的痛苦和撕扯。我难过地一次次质问为什么母亲当初没有去打疫苗?一次次质疑自己没有感受过母爱拿什么去养育好我的孩子?用什么力量保护他们快乐平安?这样的恐惧没完没了。
我发现我已坠入另一个深渊,扭曲又迷失。我沉默隐忍,却常常失去善良和恻隐之心。两百平的后院埋葬的是一条条狗的身躯,五百平的房子埋葬着我的灵魂。我误入泥沼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3
我不知道姐姐对于母亲的离开会有怎样的疼痛。姐姐比我大十二岁,母亲走后姐姐就代替母亲照顾着我。因为要照顾我,她只上了两年学。从小她总是会把好的东西留给我,吃的、穿的。她身上的母性是天然的还是她和母亲生活过十几年潜移默化形成的?
七年前,上初一的外甥在垃圾堆里抱回了一只不足月的流浪狗。母亲出事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家再也没有养过狗,甚至谈都不谈。而这次外甥抱回来的狗,姐姐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了。姐姐有一双儿女,外甥是她三十六岁高龄在生死边缘抗争生下来的。我想也只有她的宝贝儿子才能把狗这个物种带进姐姐的家。
那段时间我寄住在姐姐家,姐姐总是会在我面前说这孩子抱这东西回来麻烦死了。我看着姐姐边抱怨边小心呵护着那只小狗,姐夫和外甥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米卡”。接下来的日子,姐姐家每个成员都参与照顾小米卡,喂它奶粉,网购宠物用品,给它舒服的狗窝、柔软的狗链……米卡长得很快,不久就胖乎乎,憨头憨脑的。当我们(是的,包括我)从外面回来,它雀跃欢呼地叫唤着,在我们面前打滚,做各种动作讨喜,吸引我们的注意,似乎在欢迎每个人。它是那么自然那么开心,成了这家的一员。
转眼五个月了,一天飞来横祸,米卡被汽车撞了,后腿伤势严重。外甥女心疼得不得了,她当时还没有参加工作,没有财务自由,姐姐家也并不富裕,平常体贴家人的外甥女,为了米卡一再地请求父母带它去省城看病。她一天不肯吃东西,那么悲伤。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哭着对我说:阿姨,米卡被撞了,你看它一定很疼,水都没喝。姐姐让我劝下她,说就在县城看下,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它的造化。送一只流浪狗去省城医院?大家都觉得未免太小题大做了。米卡坚强地挺了过来,只是后腿瘸了。它拖着后腿,依然在大家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奔到大家脚下,对着人撒娇打滚,一如既往地表达着它的爱意。
两年后,姐姐家拆迁,房子还没有弄好,就把米卡寄养在父亲身边。那年父亲将近八十岁了,由他朋友眼中的“街长”变成了一个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的沉默老头。父亲该放下了心里曾经的那份怨恨吧?总之他没有反对,并且每天为米卡准备食物。米卡只吃新鲜的粥拌“王中王”火腿肠,外甥女寄来的各种狗粮都不肯吃。父亲只好早上就准备好它的粥,分时段拌好火腿肠喂它。隔夜的粥饿死也不吃的。父亲每天早上还得去遛它,带它去方便,这成了父亲的日常。米卡跟着父亲却最怕父亲,总有那么几次父亲是真的会拿棍子敲它的,嘴里还骂两句“死狗”。我听到了,就想起父亲和别人聊起我亲妈时,会称我妈为“死鬼”。父亲带着米卡出去,偶尔绳子不小心离手了,米卡放肆地上蹿下跳,父亲已无可奈何。
那时候我和父亲一起住,为了生活我在一家咖啡店长期上晚班,下班到家通常已经到十一点半了。万籁俱静,我抬脚上门前的阶梯,米卡已闻风迎上来,仿佛知道是夜晚不能打扰他人,不叫唤只在我面前打转,那么多的夜晚似乎只有它一直在等候着我。我其实对它依然不够热情,对它的百般讨好视而不见。但那一个个相迎的深夜让我的心悄悄地柔软了几分。
我看着它小小的身躯,毛发混杂,眼周围是灰色的,两边的眼角延伸长长的白毛,眼睛总是充满渴望地看着我们,鼻子和嘴巴长长的,肚子下面是白色的,看不出有什么血统,又不像普通的土狗。
我多看它一会依然会本能地想到母亲,想到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的它的同类,特别是那只被吊死的比特犬……偶尔我出神地紧紧盯着它,似乎看到伤害母亲的那只狗,它眼里充满疑问、羡慕和祈求。似乎在说这世间多不公平,让它投胎做了一只狗;似乎在申诉它不是有意伤害母亲。它肯定希望自己像米卡一样被照顾被呵护;它似乎在恳请我不要再心怀仇恨,不要再因为它而仇恨它整个族类;它在申诉自己也是受害者,这世间有阴暗的诡异的病毒,会侵入弱小的身体,而它只是一个傀儡,一只替罪羊……
姐姐家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后,把米卡接了回去。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纷纷离开了家,姐姐清闲下来。姐夫上班奔波,更多的时间只有米卡陪伴着她。姐姐的母性延伸到米卡身上,整天为它操着心,它成了守在姐姐身边的孩子。冬天因为怕它冷,特意准备取暖器对着它,温度得调得恰恰好;自己不想做饭,也要为它准备吃食,每天带它下楼散步是必不可少的。米卡越发圆润了,毛发更加柔和有光泽。偶尔姐姐会带它去看老父亲,久了没去父亲还会念叨着,讲它的可爱和充满灵性。我也经常去姐姐家,当我敲门,米卡总是最敏锐地感应到,会“汪汪”地叫着家里其他人来开门。它翻滚着身体,朝我露出它肚子上的纯白,这世间又有多少这样子的在乎和欢喜呢?
有次我去姐姐家,米卡一如既往地热情迎接我。它使出浑身解数,各种翻滚表示对我到来的欢喜。四下无人我情不自禁地抚摸了它,它变得很是乖巧,我用手轻抚它的颈下,它抬眼深情地注视着我。我发现它的眼球黝黑,眼角线很长很长,那粗长的眼线仿佛延伸到它的心里。我似乎听到有个声音在问我:这些年你过得好吗?不知不觉泪水一颗一颗地滑落。曾经在北京的天桥上,南京的陵园中,成都的巷子里,甚至从小长大的县城,我也像只流浪狗。这种同病相怜的境遇,让我理解了米卡。从一只流浪狗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它在感恩在珍惜。我突然明白它不是四十年前的另一只狗。我不应该带着偏见对它,虽然在我生命中母亲的缺失总让我隐隐作痛,是永远无法填补的深渊,深不可测,深不见底。
曾被巨大的伤害碾压过的心,已失去了坚硬的保护核。仇恨只不过是我自己试图披上的盔甲,终究我发现这盔甲丑陋无比。父亲一生都坦然地面对着那颗受伤的心,那颗没有外壳的心在他身体里始终鲜活。他是尝过最痛的滋味的人,因此一生慈悲为怀。如今细数父亲做过最凶狠的事就是惩罚了那只狗吧。父亲的善良,曾因尺度过大,被某些人看成是软弱可欺。父亲不忍心伤害任何人,不抗争,不解释,时间终是给了他好名声。我从他身上得到的爱,足够让我有勇气面对人生各个阶段的黑暗,面对曾跌入的不同深渊。
逸云,本名杨国琴。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