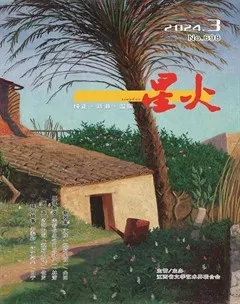缝合
2024-09-11石红许

一
别说我父亲,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半吊子文人。就像看着村前大湖上自由自在飞翔的高贵白鹤,那是丰满的理想,近村水塘里、草滩上土不拉叽骨感的灰鸭,才是父亲对未来的我最切实的想象。不过自从读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就不这么看自己了。
少不更事时,我就急着与门前湖面上游荡的水鸟比速度,结果是被大人从湖里捞起,就像捞起一条奄奄一息的鼻涕虫。那时的我做不到静如处子,不是一般的动如脱兔。下湖摸鱼,上山爬树,把褴褛的鞋袜、衣裤折腾得更污糟后回到家,时常招来父亲的一顿胖揍。可要不了多久,我没事人一样以自己的节奏接着皮。就这样无知无畏野蛮生长到十多岁。
小学一至三年级,我在家门口生产队复式教学点就读。学习成绩如今说起来,我仍有“好汉不提当年勇”般的害臊。每个学期还未过半,课本就一页一页撕过半了。除了折纸牌,已记不清小小年纪为什么和课本过不去。家里大人没时间管我,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去生产队“抢工分”,父亲在十几里外的公社中学教书。我经常一个人玩,爬高爬低是常态。独行侠般潜水横穿百米水塘,从歪脖子柳树上十几米高处跳水,稻草堆里睡一晚上,撕扯同学一撮头发,扔石头砸自认为欺负了我的人家中的房瓦。有一次玩火烧邻居家晾晒的棉被,所幸没有引发大灾祸。反正当时似乎就是没有我不敢干的事。想来我和一千多年前鄱阳郡太守周鲂之子周处有同一属性,只是无法预知会有谁来为民除害。
直到升入四年级在大队中小学读书。新的环境,我乖了几天也就无聊了几天。正式开学上课,一任课老师姓张,教语文兼班主任,是位女知青,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张老师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可她的脸却让我看了又想看,想看又不敢看。那张脸有现代人称之为娃娃脸的柔美轮廓。她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男孩子,皮肤白白净净的,穿着崭新、漂亮的衣服和鞋子。和小男孩相比,望着自己打了补丁,还经常沾满了油渍和污泥的衣服,我第一次尝到自卑的滋味。
更让我沮丧的是,每次只要我的眼睛碰上张老师的目光,我心里就像装着一只小兔子在“怦怦”跳。
一次我在课堂上和同桌的女生吵起来,张老师听到后走过来,没有责骂,微笑着耐心倾听缘由。我结结巴巴告诉张老师。那个女生多占位置,我不让,她就撕破我的新课本。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撕课本,可这一次不同,我已经不想再做从前邋遢的自己。那女生彻底惹恼了我后,我抓住她的头发就往地下拽。张老师的嘴唇在一张一合地翕动,她的秀发无意碰到了我的鼻尖,那一股香味是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突然我心里就安静了,变得特乖,闭着眼睛听凭处罚。等再睁开眼,发现张老师在安慰那位女生,我稍稍松了一口气。逃过一劫的我在读书期间再也没有吵过架。
那次吵架后,没有征兆地我的成绩一天天好起来。张老师上课的时候,我的眼睛紧盯着黑板,生怕错过了重点、要点、难点,生怕错过了她的微笑和赞许,生怕错过了那令人心安的肥皂香。期中考试评比,我得了奖,这是上学以来的第一次,学校让我们获奖学生带着大红花绕村庄游行,胸前那块糟心的补丁正好被大红花挡住。
暑假的时候,我忍不住去学校看望张老师。她给了我一本小说,微笑着嘱咐我要好好读书,做个有出息的人。我总记得张老师说话的样子,头发往侧边甩一甩,用手摸摸我的头,似乎母亲都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温存、呵护与慈爱。那本书的名字早忘记了,很多年来,每每想起,我都会努力回忆那本书的名字。或许就叫缝合,把一个泥坯般孩子的斑驳裂痕揉捏完整;或许就叫挽救,让一个顽劣的孩子真正明白什么是美好。
那个暑假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张老师了。那是一九七八年。听说张老师回城了,哪个城市不知道,有人说南昌,有人说上海,还有人说鄱阳。破小孩恢复了之前的孤独,常常悄悄地在张老师住过的那排教工房前徘徊,希望有一日那扇门突然打开,走出熟悉的身影。一次一次失望,张老师从此再没有出现过。长大后我曾经多次想要寻找她,由于没有地址,更不知道张老师籍贯,终究江湖遥远不复再见。
但遇见张老师宛若给我的人生照进一道光亮,那光亮冲破了我的懵懂无知,照耀我人生的小船驶向彼岸。她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刻在我心灵的版图上,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找到了打开通往成功之门的密钥。我常常独自跑到湖边,望着湖水发呆整整一个下午。我暗下决定,要好好读书,考到城里去,才能找到张老师,才能还书给张老师,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个最远大的目标,也是第一个最接地气的理想。
那本书在后来搬家时,不知弄哪里去了,怎么也找不到,这让我心情有点懊恼,甚至责怪父亲是他把我最重要的书弄丢了。掐指算算,而今的张老师怕是年逾古稀。
二
也就是张老师离开的那一年,我家恢复商品粮户口,一家人回迁到一个叫油墩街的小镇,寄居在外婆家。那时我才知晓一纸户口本隔着两个不一样的世界,折叠着两个不一样的人生。但我仍然觉得读书才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人生。翌年,我上初中。外公外婆是从庐陵来到赣北小镇经商谋生的,从事染布手工艺。外婆常常不经意向我们灌输经营小买卖的思想。春季贩卖桃子,夏季贩卖枣子、冰棒,秋天卖甘蔗,冬天卖葵花籽,一年四季都可卖米粑……听起来简单易学。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我,或许是书读得越多越清高,无法把自己和小贩重合在一起,况且还是个三毛一样的小贩子。这样将距离张老师那个散发肥皂馨香的世界越来越远,若是哪天遇到张老师叫我怎么还能抬得起头?在心里我始终迈不过放开声叫卖的坎,就像外婆手中扶不起的一个纸人。
油墩街小镇上生活的居民,无田无地,只能靠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开店成本大,不是家家都能开得起的,于是就有很多百姓摆路边摊,早出晚归。最热闹、纷扰的当属车站流动小贩,兜售土特产或自制食物。
当班车卷着飞扬的尘土缓缓停靠在车站门口,一群人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围了上去,吆喝兜售,卖甘蔗,卖米粑,卖冰棒,卖葵花籽……声音很快把弥漫过来的尘土压了下去,车内的人纷纷打开玻璃窗户问价钱,觉得适合掏出钱,与窗下那双被阳光晒黑指缝里还带着泥的手对接,交钱交货。看热闹的,挤在堆满货物和人的位子上,眼睛像庙里的佛居高临下,扫过小贩们的脸和手里拿着的货,不买也还是可以用神情挑剔的。也有吃“霸王餐”的,班车发动机响起时,有人似乎才想起要买东西,几经讨价还价后,接过货物,此时车已绝尘,经验不足的小贩追着烟尘跑,也没等到车上的人把钱扔下来。那一刻场面混乱,几家欢喜几家愁。嘈杂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过后,成交的喜形于色,没成交或是丢了货的垂头丧气。各怀心思折返原地,他们在积蓄力量期待下一趟班车驶入。
假期,在外婆的鼓动下,我终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景德镇、九江、湖口、都昌,本邑银宝湖、响水滩等地过往班车都要经过油墩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面上没有纯净水、矿泉水,也没有什么饮料,可小镇有汽水厂。汽水厂招聘了一批镇上居民做工人,大家无师自通就掌握了配制方法。一些人就在家仿制,价钱比厂里生产的便宜,颇受顾客青睐。每到暑假,外婆就吩咐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家制作高仿汽水。原材料是井水、白糖、食用色素,调配好后装进回收来的汽水瓶,然后拿到车站叫卖。那汽水在酷暑非常解渴、解馋,一瓶五分、一角不等,随行就市,灵活变通,反正成本不多。兼带卖冰棒、绿豆糕,运气好一上午能赚一元钱,一天下来,收入还是喜人的。
配制汽水我是愿意参与的,背着外婆可以偷偷喝几口,沁甜沁甜的,甜到心尖上,甜化了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生活。可要我拿着汽水到车站去兜售,还是感觉太难为情。一个爬树游泳有冠军气势的人,这时怂得迈不开步、开不了口,木头一样站在那守株待兔。车上几乎没有人主动下来买,其他大人或和我一样的孩子都是一窝蜂似的冲上去,一声高过一声喊“买我的、买我的”,嘴里不歇手脚也利索,一边做假动作撬开汽水瓶盖递上汽水,一边夺过人家伸出来的钱币。我第一次去车站,一瓶汽水也没有卖掉,还折了一瓶。当时还没近视,眼尖瞄到车上一人朝我挥手,示意买汽水,我心中暗喜。没料到刚递上汽水,那车子就开走了。踩着砂石路面我追了上去,一边喊“给钱、给钱”,车子毫不留情一溜烟远去,除了一阵阵尾烟和尘土落我满身满脸,还有小贩同行们看笑话的眼神打在我身上。
回到家外婆就开始教育数落我,眼神好像诸葛亮看着那个让他操碎了心的阿斗。我猜车上那个向我挥手买汽水的人,一定是看出我是个菜鸟,才作出了白吃的决定。
慢慢地,我也敢冲上去叫卖,但还是抢不过长期盘踞这里的人,他们泥鳅一样滑溜地穿梭于人群中,总是盖过我那从喉咙里犹犹豫豫打转后再冒出来的声音。总盼望着落雨,落雨了就不用去了,更盼望天凉,天凉降温了销路自然不好。可天放晴的日子还是居多,还是得去,怕惹得外婆不高兴,漫长的暑期于我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外婆不明白我的心思,还一本正经地说她老了跑不动,不然就亲自出马给我做个冲锋陷阵的榜样,说一个孩子,胆子一定要大点,要学会“抢”生意。站在马路边,迎着风,外婆大声动员,如同出征前的穆桂英,“卖东西不丢人,凭的是自己的劳动挣钱!”十来岁的我似懂非懂。
三
再后来自制汽水换了个升级版的名字,叫“果子露”,只是多掺了点香精而已。其时我已经到县城上师范了,有时也会像其他坐在车上的人一样睥睨小贩们争抢生意,只是有更多熟悉和庆幸的滋味夹杂其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小镇不远的垦殖场教书,两个读初中的妹妹时而还出现在小贩们当中。看外婆的样子,她们会是她重点培养的衣钵传人,我是辜负了外婆一片苦心。
一纸中等师范文凭,校长大会小会言外之意总会说师范生不好好教书,要“流放”到偏僻的乡村小学去,哪怕是考到了县教育局颁发的“初中学科教学资格证书”,我还是觉得自己矮人一截。那几年新分来的师专生,当年读初中时每个都是我手下败将,每每考试我都丢他们几座山,不承想几年后居然令人刮目相看,可以堂而皇之出入初中讲堂,我暗暗不服气,但顶着个师范生的帽子就得低声下气。
有天中午,两个师范生关起房门对着一碟花生干了一瓶白酒,放浪形骸,喘着酒气,对着天花板吼叫,很快昏沉沉头重脚轻,走路东倒西歪,后来就不省人事,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所幸没有被校长责骂,甚至连批评都没有。后来才隐隐约约知道,老校长原也是个可爱的饮君子,年近花甲的老校长原谅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师范生。这次酒后,我内心完成了转变,不得不向那一纸文凭低头,就像王小波文中那挨了第一锤的牛。我摩拳擦掌,不就一张纸嘛!思忖着要拿大专、本科文凭,函授是比较可行的途径,脱产进修找不到门路,也不会被批准。
我不再蔑视“世俗”,一边埋头教书,一边温习高中课程,参加成人高考。用了六年时间读大专、本科,一路走来喜怒、冷暖自知,最一言难尽的是寒暑假奔波省内各地参加面授,那时无暇顾及赣地风流,忽略了饶州物华。
那个寒冷的冬季,为了省钱,我住进上饶水南街一个简陋的旅馆。不提供热水的旅馆,早晨起来,水龙头愣是冻得拧不出来水,从大桶里取水洗脸,那水冰到骨头都痛。反复呵气,使劲地搓手取暖,迎着削脸的寒风去参加考试,一路念叨要考过,不然还要补考,这样想着心头就热血沸腾起来,以此抵御全方位包抄过来的严寒。
往往是年底的时候,函授面授指挥着我进入挤火车的队伍,感受那个年代绿皮火车的拥挤。在车上,一只脚站麻了,再换一只脚,确实困了,就不问地点,坐在过道上,席地而睡。头顶任凭旅客踩过,还要防备行李被人顺手牵羊。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在火车上喝矿泉水的感觉,实在是口渴,就咬咬牙花两块钱买了一瓶,拧开后一喝,还以为是什么好喝的东西,居然清淡无味,我第一感觉是买到了假货,心里直犯嘀咕,怎么不是甜的?怎么不似我小时候卖的汽水?又不敢询问同伴,幸亏没问,不然洋相出到大西洋。
在取得大学文凭后,却再也没有人问我是什么文凭了,以至于我想显摆都无法实现。和同一代师范生聊得火热时,反而能自带师范生的荣光,自我安慰我们那一代师范生相当于“985”。
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珍贵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那些尘封的往事,在时光的深处一点一点助长我的胆略,弥合我的羞涩和腼腆。
四
伴随大学本科文凭收入囊中,好事接踵而至,县报社、当地乡政府先后要调动我的工作关系。我深知那调动与文凭高低没有关系。发表了两三篇“豆腐块”的小鲜肉,在父亲眼里,还是村口水塘那只灰不溜秋的小土鸭,也会生蛋孵子,可怎么看就是不如其他同类那样光鲜亮丽。我在初中教的是代数几何,与舞文弄墨不挨边,但出于对文字的喜爱,权衡后我还是选择了报社。
行走在县城繁华的街道,卑微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人群里,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张老师。在我求学的过程中,还有不少老师对我也很好,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样想着,竟然又一次回忆起美好混沌初开的少年时的自己。
独自去县中学采访高一年级军训,我又像第一次和张老师对话那样手足无措,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完全不知道后来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交了一个短消息给编辑部,被告知没有细节,没有文采。不用掂量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一度茫然起来,回乡下教书是回不去了,只得硬着头皮上,翻阅各种报纸刊物向前行者学习。我懂得,一名好的记者要过社交、文字两个关,记者这一职业改变了我的不善言谈、腼腆内向,治好了我与生俱来的社恐,我穿行街头巷尾摄取热血为内心的怯懦补钙。
或许是骨子里流淌着湖边人不安分的血液,我小时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血性再一次复活,几年后我想跻身更高的平台。恰逢市报周刊部招考编辑、记者。市报所在地有徐霞客顺水而下的信江,有理学之光照耀的水南街,有陆羽种茶著书的茶山寺,有辛弃疾卜居的带湖,还有呼啸而过的绿皮火车,比老家更多的闪烁霓虹。如果能日日置身其中以此陪伴,我愿意风雨兼程。
招考分笔试、面试两个环节,笔试成绩我排名靠前,那时没有听说过面试,不知道还有问题要口头回答,天真地以为面试就是看看长相是否周正,至今想起来都暗自发笑。
面试地点设在报社二楼会议室,从全市各地来的考生一次一个进去。轮到我时,我雄赳赳气昂昂走进去,心想不就是看看长相嘛,虽然算不上器宇轩昂,至少浓眉大眼五官端正,鼻梁上架设的一副眼镜也许还能加分。
会议室显得昏暗,椭圆形长桌上围坐了许多人,只有靠窗户的一面空着,工作人员引领我坐在那里。来不及也不敢多看,只觉得阵仗不小,气势庄严,氛围压抑。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心跳加快,不敢正眼看对面的考官们。等我坐定,有个略显肥胖的男人开口了,你是谁谁谁吧?我笑着说是。他清了一下嗓门继续说,恭喜你笔试过关,现在进入面试环节,下面有三个问题请回答,请仔细听题,第一道题是你为什么选择我们报社,第二道题是……第三道是……别紧张,请回答,总时间是十五分钟。
我一听就懵圈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看着面试官鬓角的那缕白发,那缕白发一时丝缕分明,一时并成一团,最后我分不清那是白发,还是我脑子里的空白。似乎只简单回答了一句,我喜欢你们报社,所以报考了。后面就开始冷场,没有再憋出一句话来,像膀胱憋了满满一泡的尿临了却拉不出来。我像个嫌疑犯在接受审讯、裁决。这时有个中年女老师微笑着提醒我,别紧张,思考几分钟再回答。我还是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最后都不知道是怎么离开那个会议室的,只能说是落荒而逃。
幸亏笔试成绩优秀,两项统计还是勉强挤进了前六名。接到报社通知上班的那一瞬间,我愣了好久,硬是不相信自己被录取了,反应过来后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狂喜,我想我总算跌跌撞撞进入那个被辛词环绕的城市了。
在新单位上班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会绕弯避开那间面试我的会议室,似乎有个解不开的结在缠绕着我,击打我。那次面试的尴尬,削弱了我多年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自信和尊严。一切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只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成功和喜悦抚慰,需要鲜花和掌声来黏合、修复。
所幸时光能够缝合这一切,就像知青张老师以她的春风化雨,让一个粗陋鄙俗的少年懂得,一只白鹤飞翔的姿势,与一只灰鸭懵懂的样子相比,终究是有区别的。
石红许,著有散文集《河红万里》《风语西河》《山河新雨》等。获刘勰散文奖、首届中国红高粱文化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