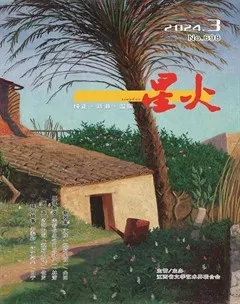盖着你生命的三分之一
2024-09-11林萧

捂着被子迷迷糊糊在床上躺了三天,烧终于退了。今天早上爱人给我换上了新的被罩,我独自躺在床上,头终于清醒了许多。身体再次被散发着薰衣草洗衣液香味儿的被子包裹着。每天晚上我都与被子相拥着进入另一个虚幻而又真实的世界。今晨梦中,我被送进医院隔离病房,躺在白色的病床上。父亲走进病房,我跟他说想回家拿一床被子。他摘下口罩一脸愁苦,说病房不是有被子吗。我说我嫌这儿的被子不习惯,我就是死了,也想盖着自己的被子。父亲说他回家给我拿去,就走了。父亲两年前就真“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梦见以前的旧棉被,也许是它给了我人世间最初的温暖,也许是它提供了最能让我自由驰骋的自我空间,虽然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但在年轻时代它曾像我的情人,我觉得它最懂我,它陪伴我的时间最长。如按照成年人每天睡眠七至八个小时标准,那人一生的睡眠占据了生命的近三分之一时间。
棉被,或薄或厚,它是覆盖我们三分之一生命的最初及最终的巢。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之后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有一块或薄或厚的被子,裹着或盖着我们的身体。但是在我们用过多年之后往往就把它给扔了,捐了,弃之如敝屣。
第一条被子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人生的最后一条被子在哪里等待着我们;而当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条被子盖在身上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第一条被子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不过我要说的并非是人生的这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被子,而是在生命历程中紧贴着我波折起伏的生命、盖着我天马行空之大梦的被子。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念中文系时接触到“衾”这个字,才了解其为大被之意。当时感觉到我们古人在用此字时,大多都是形容一种落寞凄苦的伤感。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亡国之君李煜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衾”字在此已经成为一种境遇和情感的载体,绸缎的被子虽抵不过五更之寒,但毕竟覆盖过李煜一段美梦。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写患失眠症的主人公马塞尔躺在床枕上,半梦半醒之间回忆童年的经历和梦境,洋洋洒洒不知多少篇幅,看起来冗长,但我很理解他,我想在他身上一定有一条温柔的大被子,这大被托着他的大梦。
作为一名60后,童年时盖的棉被早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大多是纯棉被。我曾看到过我周岁时父母给我拍的黑白照,身上就裹着一条小花棉被。三岁多的时候,父亲骗我说带我去首都北京,结果把我送到了上海大姑妈家。刚到大姑妈家时心中很想念父母,就会躺在被窝里哭。但渐渐感觉大姑妈给我盖的被子格外温暖,而且被面是丝绸,手感特别光滑,心情就好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当我重新出现在爸妈面前时,我不知怎么竟生出一种拘谨的陌生感,不过这陌生感很快被每晚跟妈盖着一床大棉被的睡眠淹没。
上学后很快我便独自一床睡觉了,母亲让我和姐姐九点半钟必须睡觉。可九岁后我便时常会在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玩手电,看小人书。后来还曾经把父亲买的袖珍收音机“偷来”,晚上贴在耳边“神游”。这一“恶习”一直保持到当兵岁月。
新兵连纪律非常严格。一个班的战士都睡在一个营房的大通铺上,晚上定时熄灯,大家躺下之后都不许说话。值班排长有时还会拿手电筒横扫铺面看看有无异常。我刚刚入伍时还不到十六岁,心中充满紧张和敬畏,所以钻进被窝除了胡思乱想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敢干。有时夜间紧急集合,迅速穿上衣服后,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军被叠好并打成三横两竖的背包背在肩上。当时我不理解夜间集合为什么非要这样,有两次我都打不好背包落在了后面。那时我曾经恨这个军被。
新兵连后我被招到部队文工团,那儿的气氛就宽松多了。晚上就寝后战友们经常聊天,我在被窝里默默听着,有时也悄悄听收音机或看书。一年后文工团解散,我被分到了山沟里的基层工程连。
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心情异常失落而孤独,每天只有当星斗满天,熄灯号吹响,钻进被窝后才似乎真正进入自己的自由天地。营房外冰天雪地,但营房内大通铺都烧炕,并不觉寒冷,搂着厚军被感觉被子是自己最贴心、最温暖的知己。晚间八个半小时的睡眠时间,我有一个小时可让自己的心灵驰骋。有两次营房熄灯后我把被子蒙上头,还盖着大衣,在被窝里打小手电看杂志,在逼仄的空间内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但有一次我被巡查的值班排长发现,黑暗中一束光钻进我被子的缝隙,“你干啥呢?”我立即紧张地关上小手电,预感到一场疾风将要袭来。第二天排长在全排的点名会上用鹰一般尖锐的目光注视我,严肃地点名批评了我。我的脸火辣辣的,我意识到我的自由没有了。当天晚上熄灯后,只有被子深深地抚慰我,盖着我的身体任我胡思乱想。早上,当我和其他战友一样把被子叠成像豆腐块一样的方形时,虽然床铺看起来整齐划一,可我总觉得我的被子有点委屈。
后来我们排换了一个排长,他知道我曾是文工团的演员,有时会在施工间隙跟我聊天。他还让我指挥全排唱歌,那时有许多新歌已经可以唱了。在全连开会的时候,我指挥着一排和二排进行拉歌。可以看出排长挺赏识我,我在连长和全连面前也露了脸,于是晚上熄灯之后我又渐渐开始在被窝里偷偷看《莱蒙托夫诗集》《唐诗选读》,我又回到了自我的世界。特别是袖珍收音机里的广播节目像不竭的甘泉通过一个小耳机滋养着我饥渴的心灵。北京人艺演出的郭沫若话剧《蔡文姬》中朱琳吟诵的《胡笳十八拍》那诗意盎然的悠长独白绽放在我的耳朵里;朱自清《荷塘月色》中“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好像说出了我的心声;而张家声朗读刘白羽《长江三日》时,那浩荡的江水从滚滚长江流淌到了我黑暗而温暖的被窝里,那连绵群山之间的雄浑江涛仿佛涌动在我的胸中,它和棉被一起伴我进入神游四方的大梦!
那段时间,白天在山上施工,回到营房里,看着床上的被子,我就像看到一个知己,仿佛每天都在等待着与它合二为一,而它似乎也在等着我。多年后,当我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时,丹麦王子的一句独白“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之中,我仍然自以为无限的宇宙之王”令我体会特别深刻。每晚狭小的被窝里不就藏着我精神上的宇宙吗?
此后我才理解部队行军打仗,为什么战士们都要用背带将军被打成背包背在身上。那是贴着生命的被子,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活着暖着你的生命伴你入梦,死了盖在你身上随你入土。那是每个战士移动的小家!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红军先后经过湘粤赣交界的汝城县时,有三位女红军借宿在一位老乡家里,看到床上只有一块烂棉絮和一件破蓑衣后,女红军便拿出被子和女主人徐解秀母子共盖一条被子挤在床上。第二天早上,一位红军姑娘找来剪刀,把她们仨唯一的一条被子从中间剪开,将一半交到徐解秀手里。这个半条被子的真实故事饱含了生命的温度。
退役的时候,一位四川老兵带走了两床自己盖过的被子。他说被子盖久了跟自己就有感情了。我听了之后深有感触。所以我复员时也将部队的纯棉军被带回了家。绿色的被套洗得发黄,上面渍迹斑斑。
回到家里,父亲要给我换被子,我不愿意,拆洗之后继续盖,总觉着这被子上有我的气息,有我岁月的痕迹。后来我赴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过关斩将,杀入三试和文化课考试,可回到家后却接到了未被录取的通知书。那天落日收尽余晖时,我觉得天穹也为我收尽了最后的一丝光芒。复员后父亲和姐姐都不同意我考戏剧学院,我是憋着一口气考的,最后还是功亏一篑。那晚我默默躺在床上两手夹着被,眼角涌出的泪水只能用被头擦抹,被子仿佛在抚拭着我的痛苦。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永远在漆黑的夜晚盖着你,暖着你,伴着你,你可以尽情地拥抱它,也被它拥抱,你把它怎么裹挟,怎么揉搓,它无怨无悔,从不会抛弃你。
后来我好赖读了一所普通大学的成人大专,之后又读了本科,于是棉被陪我又度过了许多苦读的夜晚。不过晚上所读小说居多,躺在被窝里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书,看到其中用诗意化的语言描摹男女两性赤裸淋漓的云雨之欢时,常会激动得心旌摇荡,体内涌起澎湃的联想,久久难眠。我只能把被子想象成自己的另一半,侧身搂着、夹着被子,寻找一丝安慰……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说:“人的理智只是海平面上随环境上下浮动的小部分,无意识则是海面下庞大的主体。”我觉得被子覆盖的世界就像人类真实的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
两年后搬家时,从部队带回的这床被子被关心我的二姐给换了。为了宽慰我,她对我说送给更需要的人了。那曾经盖抚我孤独灵魂多年的被子,如今早已不知葬身何地,降解为何物了。
我上学和工作后先后盖过其他的新被子,羽绒被、鸭绒被、真丝棉被,异地出差宾馆的白被,还有医院病房的被子。宾馆床上的被罩千篇一律地洁白,好像洗衣粉没有漂净,还不贴身,缺少人的温度;而医院病房的被罩总好像有一股84消毒液的味儿。盖着这样的被子时不用躲在被窝里看书听广播了,以前在被中那种躲进自我世界畅想的感觉也就弱了,但躺着看书,或盖着被子浮想联翩独与天地往来仍是我床上的主旋律。
步入新婚殿堂时,前妻青睐的婚被是品牌的漂亮的真丝膨胶棉被。虽然很轻柔,很蓬松,也很温暖,但我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感觉了。当然,生活已完全变了。人的情绪和状态也变了。人在爱情的海浪里翻滚,往往也躲不开被子。被子里激情的浪花涌动之后,退潮了,沙滩上一片宁静,被子开始默默聆听你们逐渐均匀的呼吸。任你思绪飘飞,梦语连连。
男女两人在一床被里共眠时常是要失去自我的。搂着你的伴侣和独自搂被子是不同的两码事。被子对你毫无要求,毫无怨言,它最能懂你,接受你的任何肢体行为,任何隐私的欲望,任何不合实际的幻想、幻梦、噩梦。它是你最逼仄的物质世界,但它又是你浩瀚的像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一样的精神世界。渐渐地我感到仍需要一个自我的空间和时间,所以结婚几年之后,我主张夫妻最好有合有分,年岁渐增,还是分房睡为好。我内心是希望每天近三分之一的休眠时间不仅有一个随意裹被的独立空间,更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空间,一段能真实地面对自我的时间,一段能自省、梳理和遐思的内心生活的时间。可看书,亦可梦中驰骋,梦中胡言,梦后留痕,而这一切不会影响到爱人。说到底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灵魂时空。对我这样一个神经衰弱时常失眠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多年后我这个目的达到了,然而爱却消散了。
我每天最自我又最真实的近三分之一生命归于被子的覆盖。白天,我的躯体在钢筋水泥的围墙中被包裹得衣冠楚楚,言不由衷,灵魂在碰壁;夜里,我卸去盔甲赤裸着钻进灵魂的庇护所,梦里偷渡灵漂泊,云上天马意奔突。那是一种多重的奇异的人生体验。于是,棉被成为梦的居所,梦成了棉被的伴侣。我有多次的创作灵感得益于这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时空。
一九九六年,我得胸膜炎住进总院二号楼的四楼,我发现这层楼正是当年母亲住院去世的楼层。晚上护士熄灯后,我躺在病床被窝里,病床上的被罩有一股来苏水的药味,很不习惯,我听着病友轻微的鼾声,辗转反侧睡不着。便回忆起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十一岁。那天抢救她时,父亲紧紧搂着我啜泣,我闭着泪眼不敢直视那巨大的恐惧。母亲没有被抢救过来,最终她的遗体被护士盖上了一层白布,后来忘了是谁给推走了,连被子也没盖。不知那个冬天母亲在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是否感到了寒冷。
眨眼间我这身皮囊已步入花甲,父母均已离我而去,每日陪伴我时间最长的除了手机电脑和书之外,就是盖在身上的被子了。有时我会在夜里想:应该给曾陪伴我生命最重要日子的被子颁发一个奖,奖励它的温暖、无私和贴心,陪我直到生命的终点。
人从出生时起就裹着一条小被子,是因为要给你一个出生前母亲子宫一般的温暖;而人终年时要盖一层寿被,是为了要送你回到出生前虚无的黑洞之空,那里再也没有温暖的被子,再也没有任何梦了。也不知能否投入下一个轮回生命的被中?
林萧,本名姬恒林,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兼职编剧。作品散见于《鸭绿江》《诗潮》《芒种》《读者》《星星》《辽宁日报》等报刊。广播作品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