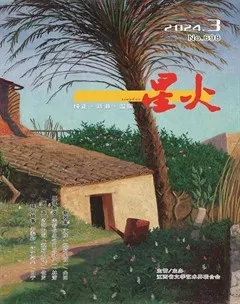王大妈的向塘时光
2024-09-11金艺

一
主卧桌上那台外壳斑驳的三五牌座钟,时针和分针在昼夜不息地奔波了半个多世纪后,依然保持始终如一的步伐,只是打鸣的钟声似乎迷了路,每半点能准确无误“当”一下,整点的时候,它就每次都要多“当”七下。这是睡在隔壁房间的我于夜深人静时算出来的,凌晨一点它“当当当”八下,凌晨两点它“当当当”九下。
王大妈是不深究这个规律的,她只知道钟鸣不准。不准的钟鸣既不影响她白天的活动,也不影响她晚上的睡眠,就像屋外不远处来来去去火车的轰鸣声和喘息声,随它们怎么响。
这台座钟有拱形的红褐色木质边框,正面四周原本金色的花边消融给了岁月,外层玻璃门上印着的长江大桥图案依然清晰,桥上白云朵朵,玻璃门里面圆形的钟盘下面吊着一个钟摆。
钟盘八点和四点的斜上方,各有一个发条孔,一个负责打鸣,一个负责走时。
这两天也没见王大妈用它来看过时间,没用还胡作非为,为啥还要留着?王大妈解释说钟鸣乱了没关系,三五牌钟上一次发条管走十五天,等这次走完了,记得不要上打鸣的发条就好了。它走时还是准的,扔了怪可惜。
王大妈那辈人不习惯表达没有实际用途的情感,尤其是在晚辈面前。我想,“走时准扔了怪可惜”这样的勤俭节约不过是借口,她真正不舍的,可能是这台座钟陪伴她在向塘走过的所有时光。
每一次钟声与钟声的间隔都是一扇门,从每一扇门都能走回从前。
二
一九六六年是王大妈的向塘元年,那年她十九岁,经人介绍从丰城白土山窝里嫁给了二十八岁的铁路工人朱德友。
新婚的家是铁路边八排房子的其中一间。里面放张一米二的床和一个书桌后就剩下一溜溜过道,书桌上放两个樟木箱子,三床被子,其中两床是新郎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床垫一床盖,另外凭结婚证又买了一床厚被子。婚礼收到的贺礼包括一个搪瓷脸盆、一个红色塑料外壳的热水瓶和一张贴在墙上的《祖国江山一片红》宣传画。脸盆和热水瓶上写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多人的名字,宣传画上大大的囍字下面的署名也让新娘记住了这是三位铁路工人的共同心意。
至于其他的年份,年复一年,王大妈很难记清楚。在向塘的早年时光,她通常以孩子的出生和年龄作为纪年方式。
王大妈挺着大肚子怀着我姐的那年,老朱同志在向塘西火车站调车组工作,三班倒,其中有一班是半夜上岗。没有钟表,老朱吃过晚饭后也DY3uv+kkjuX9VNYV5/loNsWEm+HKrTQMvKVtMv+uSsA=不敢好好休息,在床上睁着眼睛躺一会,估摸着差不多到点了就出发。虽然从来没有迟到过,但长期休息不好酿成的事故差点要了他的命。有一天,他在调车时不小心从两节车厢连接处掉了下来,几节车厢从他身体上方轰隆隆驶过后,他已是鲜血淋淋。幸好只是额头、胳膊和手受伤。出院后,老朱同志左手大拇指残废,王大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哥出生那年,他们终于攒下四十八元钱,相当于老朱一个多月工资,从南昌百货大楼抱回来那台三五牌座钟。有了钟,老朱上夜班前可以安心休息,王大妈也有更精准的计时方式。
我哥出生的第二年,王大妈有了城镇户口,这意味着她每个月有了二十多斤的粮票。这之前,全家四口全靠老朱每月四十多斤大米过活。不够吃日子也要过,老朱学会了种菜钓鱼补给家用。隔壁拐阿姨家更困难。拐阿姨四个孩子就靠付大伯一个人的口粮,大娃穿着麻布袋子缝成的衣服,二娃三娃趴在地上玩泥巴,拐阿姨手里抱着老四,中午做饭的米都不知道在哪里,照样在树下和王大妈有说有笑。
王大妈说她最小的孩子是三个孩子里唯一出生后就有城镇户口的,生下来就有六斤的口粮。如此说来,我虽说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也是含着六斤大米出生的。
王大妈肯定不知道,同年八月,袁隆平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这种水稻亩产千斤,将在此后大大缓解中国人多粮少的问题。
我出生那年,王大妈和老朱在单位登记了一块一百二十元的上海手表,每月从工资里扣十元钱,又从工会借了五十元寄给贵州生病的爷爷,通过“来会”的民间筹资方式两人分别买了一块呢子布料做冬衣。
我三岁那年,王大妈托在贵阳供销社上班的小叔子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通过火车货运到向塘行包房,王大妈和老朱半夜里把缝纫机抬回来,激动得一晚上没舍得睡,对着缝纫机左看看右摸摸。那一年还请人到家里打了一个杉木五斗柜,一个枕木的储物柜。五斗柜正好五个抽屉,家庭成员按年龄大小从上到下每人一个,装自己的衣服和私人物品。
什么时候从马路那边的八排房子搬到马路这边的二排房子,王大妈记不清了,只记得孩子们还小。后来我们有记忆了,也模仿王大妈用事件纪年。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她和老朱花两千元在后院盖起了一栋小楼,相当于在一众平房的向塘铁路地区给儿女们建了一座可以四面观景的城堡。我读大二的时候,二排房子拆迁,在原址附近建起了六层的楼房,王大妈抽签分到三楼,一直居住至今。
从马路那边搬到马路这边,从平房搬到楼房,王大妈的向塘时光里不变的是铁轨依然在同样的地方延伸,火车依然在不远处每天轰隆隆驶过。
三
作为铁路职工家属并有了城镇户口的王大妈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向塘火车站售货组当售货员。那会儿向塘是全国有名的中转站,南来北往的火车都要经过向塘或向塘西站,来来去去的绿皮火车将她在向塘的每天分割成不均等分的小格子,追着她日复一日地转圈圈。
画出清晨第一道格子线的是50次广州方向来车,接这趟车倒不是卖货,而是拾取车上倾倒下来的煤渣,那是家里一天生活所需燃料,为此王大妈凌晨四点多就要起床。一年多以后,她把第一道格子提前到了凌晨两点多,因为要去售货组发面做包子馒头迎接早班的列车。我时常在被窝里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吆喝“走罗,走啦”,然后是王大妈开门关门的声响。铁路地区的孩子对父母半夜起床去上班习以为常。王大妈从没叫过苦,那会她年轻,腿脚也利索,走路带风,星光月色下,酷暑严寒中,数不清走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每月二十六元工资是她不竭的动力。
下午两点半的指针是由80次上海方向来车拨动的。这趟车到达向塘西后,不往北进南昌而是向东拐去。一趟小运转负责从向塘站开往向塘西站,接上从这趟车下来中转去南昌的旅客。王大妈要坐上这趟小运转从向塘站到向塘西站,在它停车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在站台的食品亭售卖食品。她现在还记得卖得最火的是卤猪蹄,一只猪蹄对半剖开,一角五分钱一片;卤豆干一角钱一串;肉包子开始是五分钱一个,后来涨到一角钱一个;三花酒一元三角六分一瓶;黄金叶和欢腾的烟才卖两角多钱一包的时候,红塔山烟就以好几元钱一包的价格吓退了不少旅客。等到小运转要发车了,她便锁了食品亭迅速登上小运转回到向塘站,又忙着接其他班次的列车。
“北京快”列车夜晚十一点多驶来,为王大妈一天的工作画上休止符。大部分同事会放弃接这么晚的车,王大妈不会,自从卖的商品可以提成后,她能多卖一点是一点,为此没少心酸事。有一次为了卖掉最后两个盒饭,她登上“北京快”。车上灯光昏暗,收了钱就要赶紧下车,清点的时候才发现收到的是两角而不是两元。原本想赚两角钱,反倒亏了一元八角钱!
还有一次北风呼啸雨夹雪,王大妈推着商品车在“北京快”车厢边来回走动,列车上所有的窗户都紧闭。就在她觉得无望的时候,有一扇窗户被打开,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王大妈赶紧把车推过去,还没开口问他要什么,男子就满是同情地说:大嫂,别卖了,天太冷了,回去吃大哥的吧。说完把窗户重新关上。几十年后王大妈说起这事还会哈哈大笑:人是好人啊,就是听得眼泪都要掉下来。
回家的路上叮叮当当的冰凌从路边的屋檐掉落,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就这样王大妈也舍不得花三元钱买一个可以遮住脸的帽子,反正热不死的屁股冷不死的脸,冷就冷吧。她和老朱能把小家拾掇得越来越像样,孩子们穿得暖暖和和,吃得健健康康,全靠她对自己“将将就就”,对日子精打细算。
心酸里也有惊喜。
有一年元宵节,别人都在家过节,她吃过饭后,带了四个健力宝试着到车站去卖。接到的是23次西南方向来车,一个健力宝赚一块钱,总共赚到四块钱,可以买两斤猪肉。这样意外的收获让王大妈记了一辈子,像是军功章上最闪光的部分。
在这个车次与那个车次之间,王大妈还有很多事要做。
起初她要抽空每天走四趟回家给还在摇桶里的我喂奶,后来要给娘家的父母和兄弟做布鞋,要帮助没上过学的老朱给贵州的家人写信寄钱,要给孩子们织毛衣、包饺子。每年要在春节前做一大桶芝麻糖冻米糖,炒一大锅花生和瓜子,食品的香味和她的这种热乎劲,让孩子们很多年后都觉得这才是春节的标配。
王大妈个大,一米六四的身高,体重常年保持在一百五十斤左右,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心思敏锐手脚麻利。
有一次在站台上看见一个小女孩穿了件胭脂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连衣裙,多看几眼后,她就依葫芦画瓢给我姐做了一件,连外翻的口袋都一模一样,洋气又活泼。
她第一次做衣服是在我姐一岁半的时候。王大妈去工地给人搬砖,每天赚八毛钱,赚到五块六的时候,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摸索着给女儿做了一件小衣服,穿着很合身。别人说她好大胆,从没做过衣服还敢下剪刀,她呵呵一笑:不去做,永远都不会做。自此以后,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她手工量身定制。
王大妈不仅脑子灵光,手巧,嗓音也像百灵鸟一样清脆婉转,什么歌都会唱,《马儿啊,你慢些走》《红梅赞》和洪湖赤卫队演唱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是她的拿手曲目,做家务的时候时常哼唱。她学歌快,听一两遍就会唱,如果一时想不起来,睡一觉旋律就回来了。她爱唱歌却不爱看电影,什么电影都会让她打瞌困。她也许是这么想的: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去看别人的故事,不如养足精神多接几趟火车。
她也会和一起卖货的姐妹们在等车来的空隙里聊八卦,说笑话。今天是老李两口子打起来了,打得哭爹喊娘,明天是老黄家的孩子个个都乖,好有出息,后天是老陈家里的麻烦事真多等等。一个阿姨说她家老袁兄弟姐妹十几个,父母不想再生了又没有节育措施,做父亲的就每天晚上去亲戚家睡,结果有一天刚出门就下大雨,走不了,然后就有了老袁。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直到火车进站才急急忙忙各自推着小货车卖货去。
王大妈读过初中,且成绩优秀,她很多初中甚至高小毕业的同学都当上了赤脚老师,后来转为正式教师。如果不是我外公重男轻女固执地不让她读书,她可能会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可她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她在以火车为指针划分的向塘时光里,在推着小货车的叫卖声里,在孩子们路边热切盼望母亲下班的眼神里,留下一个个清晰坚定的剪影。
四
王大妈生我姐的时候大出血,她躺在床上都能听见自己的血滴滴答答滴在桶里。老朱找来医生打了止血针止住了血,但没输血,她和老朱也不知道要吃补血的东西比如阿胶,这让她很长一段时间日日夜夜头晕,整个头感觉是空的,一直要用毛巾扎紧。回娘家的时候,一张脸蜡黄蜡黄,村里人看见她都说好好的大姑娘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好草怕盖墙,好女怕嫁郎。
一个算命先生说她四十九岁是道坎。来自四川的邻居姜阿姨说,小王啊,活到四十九岁可以了噻,娃儿么都长大了。王大妈不甘心,四十九岁还没享到孩子们的福。
对算命先生的话王大妈不全信,可是偶尔想起来,也会不自觉地以四十九岁为终点重新规划她的向塘时光。
一九八〇年,她不明原因地双脚没有一点力气,走不了路,二弟的婚礼也没法参加,让老朱骑着自行车捎去四百个肉包子算一份贺礼。铁路医院就在家旁边,她独自挪了老半天去看医生,没有用,看了医生的双脚还是不听使唤软绵绵。
不会是被双脚拖累迈不过四十九岁这道坎吧?王大妈决定自救。她学着老人家用针扎放血,也不知道哪里是穴位,也不懂该扎哪里,她学到一个动作就是使劲拍脚,有青筋鼓起来的地方就用针扎,扎出血。最后也不知是扎针的原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段时间后她的双脚居然就好了,走起路来继续虎虎生风。
四十九岁是道坎的阴影,让王大妈变得敏感。我那会儿刚学会用纸折花,没有彩纸就用信纸,折出的白花一朵又一朵,全都摆在她房间的缝纫机上。偏偏又是个闷热得让人烦躁的黄昏,王大妈进屋惊见白花,瞬间脸上血色全无,苍白得就像那些纸花,随后,全身的血液加倍往上涌,好像要从眼睛里喷出来,她厉声呵斥:咒我死啊,丢掉去!吓得我扔花以后好久都不敢进屋吃晚饭。王大妈极少对我发脾气,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儿子的学习也让她着急,等到四十九岁别说享他的福,他能不能养活自己还是未知数。因为和数学老师赌气,我哥每天数学课都跑到操场去溜达或睡觉,一个多月后老师来家访王大妈才知道。她读过初中看得懂小学的数学,开始也想循循善诱,可是看着我哥每日每日鬼画符的作业,她还是没忍住举起了棍子,正好把我哥膝盖上因摔跤刚结的疤壳打落,鲜肉带着血露了出来。
这个细节我哥记了四十多年,首次披露却是在今年大年初二的饭桌上,当着一桌子晚辈的面,王大妈有点尴尬:不可能吧,我一点都不记得。嫂子笑着说,他是喝了酒才敢这么说的,平时都是顺着妈,妈说是怎样就是怎样。
大家都起哄让我哥再喝些酒看还有没有猛料。
饭后,王大妈坐在沙发上对我解释:我肯定是没看到有疤,要不然怎么会那么狠。
那个年代,哪个孩子闯祸不挨打?我就见过付大伯和香阿姨用石头砸拿脚踢儿女。王大妈情急之下打孩子一棍子,多大点事啊,我哥随口一说她这么介意,我想王大妈可能真的是老了。
顺利度过四十九岁的时候,王大妈已从向塘火车站售货组退休,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在享受孩子们带来的福气很多年后,王大妈的向塘时光又有了新的计时方式。
这次,是以老朱八十岁为终点。
她怎么也想不到,平时结实如牛的老朱会在七十六岁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恶性肿瘤,这样的晴天霹雳让她心沉大海。她总觉得以前生活苦,能活到八十岁很不容易,现在条件好了,人活到八十岁总是要的。老郑天天喘气都喘不上,活过了八十;老邓年年收到病危通知书,也活过了八十;老朱平时连感冒药都不用吃的人,怎么能活不过别人!
王大妈最初是在焦灼等待医生的宣判中度过的。我肩负着全家人的重望,带着老朱的CT片只身去上海,通过朋友找到两家顶级医院的权威医生,反复确认了通过做介入手术,有望活五年。王大妈紧绷着的心如吹进一缕春风,七十六加五等于八十一!老朱同志身体底子好,心胸开阔,过了八十再多活几年也是很有可能的。
全家紧急制定策略,先由大女儿和王大妈陪老朱去上海做手术,术后再由三个子女轮流照顾。活过四十九岁的王大妈如愿感受到孩子们回馈的温暖。
介入手术后最初的一段时间,王大妈对老朱每天发高烧出虚汗很是担心。她陪着他挺过了艰难期。半年后老朱复查状况良好,脸上“有红有色”,完全恢复了钓鱼、种菜、打气排球、打扑克牌的生活。王大妈松了口气,每天沉浸在老朱能健康活到八十岁的美好憧憬里。
第二年的正月初九,王大妈觉得老朱肯定是碰到了鬼。那天下午,他本来是去老年活动室打牌的,三缺一打不了,老朱就去向东菜地晒太阳,路过一段铁轨时,踩在石子上没站稳,从高高的铁路路基上摔了下来,回到家脸色煞白,胳膊也脱了臼。从那以后老朱的脸色就再也没有红润过。
儿子媳妇带着老朱和王大妈远赴泰国、新加坡游玩后,老朱还是没有逃过死神的追捕。
病情复发,在南昌做第二次介入手术后,老朱既没有发烧,也没有出汗,人瘦得皮包骨,腿却肿得厉害,吃东西难以下咽,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王大妈为他必须活过八十岁努力奋斗。早晨天溜溜光就泡好葛粉拿吸管给他吸;老朱有一天说想吃她包的芝麻糖包,她从发面到包子出笼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可是很小的一个芝麻糖包,老朱都吃不下去,他说包子原来很香的,怎么吃不出味道了呢?三伏天王大妈给他抹身子,以前很多汗,现在全身没有一点汗,干巴巴的,腿也不肿了。
古话说,一肿一消,准备锄头锹。王大妈知道,老朱活不过八十了。
老朱同志生于一九三八年,卒于二〇一六年。我在《铁路生活区的坚硬和柔软》一文中曾写道:常带我去卖菜给我买油条的父亲,七十八岁上,健硕的身体被癌细胞吞噬,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将体温散尽。
王大妈看到后很有意见:你爸是七十九岁不是七十八,老人都是算虚岁的。
好吧,我在原稿上把七十八岁改成了七十九岁,离王大妈的理想更近一岁了。
五
王大妈说她妈妈年纪大了以后做不动事,每天坐在屋前数屋檐下的麻雀,看着它们从这个洞里飞到那个洞里,等麻雀都回窝天空安静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王大妈楼前每天也有很多麻雀叽叽喳喳,但她的晚年可不需要靠鸟儿来计时,在我外婆数麻雀计时的年纪,她爱上了刷手机,一个视频一个视频地打发时间。
年轻时没空看别人的故事,现在她是时间的富婆,每天刷手机短视频,什么样的人生景观都能看到,刷刷刷,一上午就过去了,再刷刷刷,一下午又过去了。
二〇二四年的早春,刷视频的间隙,王大妈瞥见铁轨上走的绿皮火车多了些。曾追着她每日陀螺般转动的绿皮火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向塘西火车站也从客运站变成了货运编组站,怎么突然又来了这么些绿皮火车?王大妈感觉有点纳闷。
我笑话她:你天天刷手机视频,都没有看到对绿皮火车祖师爷铺天盖地的赞美吗?南方大面积的雨雪冰冻天气让高铁彻底趴了窝,春运刚开始火车站就滞留了大量旅客,关键时刻还是不受电力线路影响的绿皮内燃机重出江湖,拉着返乡的旅客一路风驰电掣。
王大妈自豪地大笑:原来是这样的,绿皮火车还是好!
似乎绿皮车是她的亲朋好友。
她错过绿皮火车的视频,是因为近期特别关注一个彝族女孩的爱情故事。她说女孩是真正山里的淳朴女孩,长得又好看,追求她的男子富裕又帅气,是博士还很有爱心,经常去山里帮助女孩和她的家人,王大妈说每期视频更新她都不会落下,要一直看到他们结婚。评论区好多阿姨也和她一样的想法。这是灰姑娘和白马王子式的爱情故事,遵循现实主义风格生活了一辈子的王大妈们,是否内心也深藏浪漫主义的理想?
除了情感故事,王大妈看得最多的是健康养生、求医问药的视频。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去年脑梗在深圳大女儿那住了会儿院,王大妈发现自己连说话唱歌的嗓音也没有原来清脆。最让她烦心的是那双曾经在向塘和向塘西火车站之间来来回回走多少趟都不觉得累的腿,现在走起路来像鸡崽划水,一摇一摆,走不了两步就累。
医生说她膝盖半月板磨损得厉害,要少走路。王大妈也很心疼自己的腿,这双腿带着她征服过那么多的路,现在还要继续承受她已八十公斤的身躯,太难了。
我姐去的地方多,不管到哪里都惦记着打听治疗王大妈膝盖的方法,外敷的膏药内服的营养液注射的干细胞都用了,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王大妈也百折不挠地在各种小视频里寻找良方。
今年春节,我去向塘陪她,吃过中饭后她就打开手机刷视频,听的却是姜子牙和妻子马氏的故事,估计有二十分钟。我奇怪她什么时候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了。她说看视频也能赚钱,听完这个故事答对两个问题,就可以得到三毛钱的微信红包,另外一个养生平台每天也可以赚两角钱。我说你要小心平台用这种方式牢牢地抓住你,然后给你推送药品广告,到时候你要付出更多。她斩钉截铁地说不会,推广告就不理,反正每天没有什么事,打开了听听就有钱,上次攒到十几块钱,买了两天的菜,不是挺好的吗。
年轻时王大妈忙赚钱忙持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她用时间来变现赚钱。
有一天上午我将近十一点给王大妈打电话,她说刚到菜场买了点牛肉,准备包点牛肉饺子。这么热的天,将近四十度高温,怎么这么晚去买菜呢?她说晚点便宜些,早上四十三元钱一斤,晚点去就四十,她买了一斤,便宜三元钱;就是这双腿太不利索,走到半路就要坐在路边椅子上歇一会,不过没事,反正有时间。
反正有时间,这句话已经成了她的口头禅。
这条去买菜的路,也是她年轻时去上班的路。如果用电影回放的方式观察,就会发现王大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往返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近六十个年头,一个甲子,从青年走成中年,从中年走成老年,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路没变,她的腿脚一天比一天不听调遣。
我们常说王大妈是最幸福的老太太,远有大女儿,经常带她去看外面的世界,前不久还开洋荤,参加外甥的婚礼在美国住了一个月;近有在向塘铁路工作的儿子,每天下班后来探望;不远不近有在南昌工作的小女儿,不仅每天和王大妈视频通话,周末还时不时回来陪住。
二〇二四年的立春,我姐在全家的微信群里发了一张图,说有民间习俗立春要躲春,从下午三点多躲到五点多,待在房间里不出门,可以避邪消灾。我晚饭后照例跟王大妈视频通话,她神秘兮兮地说:我本来在家里躲春的,结果拐阿姨五点左右死命在楼下喊我,我本来不想理,她不停地叫小王、小王,算了算了,反正时间也快到了,我就出来答应她。
拐阿姨今年八十多岁,也是自己独居,就住在王大妈的楼下。她们在铁路边做了一辈子的邻居,王大妈喜欢住在向塘而不是和儿女常住,也是因为舍不得拐阿姨这样的好邻居,平时大家一起晒晒太阳吹吹牛,互相也有个照应。拐阿姨在楼下死命叫她,就是看她半天没有动静,怕她有个闪失。
我想起王大妈说躲春时的那种神秘表情就想笑,一百六十斤那么大的个,四十几平米的房子,还能往哪躲啊?
年轻时搏命求生存,别说刮风下雨落雪结冰,就是下刀子她都不躲,现在她用几小时的时间,躲一个看不见的春。
六
王大妈今年七十七岁了,卧室还完整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家居摆设,仿佛时间又转回了从前,仿佛时间根本没有往前走。
房间的西南墙边放着和老朱一起睡过多年的床,冬天床上被子和毯子铺了七八层。王大妈怕冷,但不习惯用空调和电热毯,她这传统的保暖方式让我很为难,每次想钻进被窝陪她睡一晚,都不知该掀起哪一层被子。床角靠窗的那面墙并排放着摆了三五牌座钟的桌子和曾经堆放过小白花的缝纫机,东面的墙边放的是杉木做的五斗柜和枕木做的储物柜。
孩子们像小鸟长大出了窝,老朱也消失不见,再也回不了家,五斗柜的五个抽屉都还是满的,就好像当年一家五口齐全的样子。我每次回去用过的毛巾,王大妈晒干后都会帮我叠起来放进最下面那个抽屉,我下一次去的时候,她就告诉我:毛巾在你的抽屉里。口气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那台年迈的座钟还会“当当当”地打鸣,不打鸣的时候,时针分针滴滴答地走,让夜晚愈发显得宁静。王大妈在孤寂悠远的滴答声里回忆过去,也在依然清晰有力的打鸣声里畅想未来:如果还能再活几年,我一定要找一家好医院给双腿膝盖做个手术。
金艺,在《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啄木鸟》《星火》《草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若干,有散文入选多个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