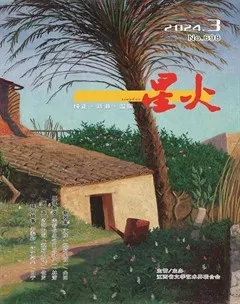文玩(短篇小说)
2024-09-11凸凹

1
这是京西的一个山间盆地,很小。背后的山峦分两半,西南叫笔架山,西北叫睡女峰,都是想象的产物。
笔架山,当然是笔架的形状;睡女,则是仰卧的样子,平坦的肚腹延伸处,有胸脯状的凸起,就有了性别。
盆地在两山的衔接处,因而叫夹户屯。屯里有三二十人家,散落分布,均是石墙立屋,石板盖顶,掩隐在绿树之中。如果没有鸡叫、狗吠、猪哼哼,真看不出这里还有人家。
屯西口,有个大土丘,上边长着棵大核桃树,结的果实当地叫麻核桃。核桃表皮多皱,坚硬,如果要吃里边的果肉,得施以斧头、锤子的重击。砸开之后,果肉破碎,需一点点捡起来,撮在手心,拿舌头去舔。味道真是香啊,咂咂嘴,有萦绕不去的回甘。
这样的果实虽然香,但获取艰难,便不宜吃,做文玩。一对麻核桃握于掌中,摩擦与揉,用于舒筋活血,防止中风。揉摩久了,核桃的麻面变得光滑黑亮,像眼眸,像卵蛋,也像神物,有神秘、贵重之相。
先是城里人来找寻,因为城里人大鱼大肉,血脂高,硬化重,便特别需要文玩,把血瘀、动脉斑块驱散于揉捏之间。后来本地人也依样学样,也握两颗麻核桃弄出稀里哗啦的声响,贫穷着也奢侈着。麻核桃的身价便大增,一对麻核桃,起初是三五块,之后是三五十,到了眼前,已是三五百了。
市值能改变人的观念。
刘记本是这棵大核桃树的主人,原来他一直不把它当回事儿,走过的人谁愿意摘两颗就摘两颗,还无须言谢。后来就不成了,他用铁丝网把树围了起来,按市价收钱。
高价核桃使夹户屯一举成名。
一天,来了三个人。
是两男一女。男的一个矮瘦,一个胖大;那个女的,身材高挑,白白净净,娉娉婷婷。
他们围着大核桃树指指划划、嘀嘀咕咕,面部表情均很庄肃。
刘记本见状,赶紧趋向前来,“怎么,你们也要弄几对文玩?”
他现在已经很雅致了,麻核桃这样的字眼他已经说不出口了。
胖大的那个男人呲了呲白牙,说:“没那个雅好。”
“那你们为什么而来?”
“为了这棵树。”
刘记本心中一惊,“怎么,要砍?”
“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砍?”
“见钱眼红,仇富呗。”女子吐了吐鲜红的舌头,嘻嘻地笑了起来。
这样的笑,让刘记本心惊肉跳,他连忙说:“这可是英雄树,我爷爷的血就洒在这棵大核桃树下。”
矮瘦的那个男人趋近了他,微笑着说道:“那么,你就是刘本正的长孙刘记本了?”
“你怎么知道我?”
那个女子抢先回答道:“这位是史志专家张文韬,那位是我们领导、区史志办主任谢民庆,我是史志办的干部于娜,嘻嘻,我们就是为你爷爷刘本正烈士而来。”
“来干什么?”
“来踏勘一下,想给他树碑立传,建一座小型纪念馆。”
刘记本不仅放心了,还立刻兴奋起来,“那我的麻核桃就更值钱了,嘻嘻。”
“可悲啊,可悲。”谢民庆倒背着手,大声地感叹。
张文韬围着大核桃树转了一遭。由于倒背双手,让人看到,他的背有点儿驼。
刘记本望着他傻笑。
张文韬知道他是在笑自己,正色道:“你表面上是在卖文玩,其实你是在卖英雄的血,你爷爷要是在地下有知,他会扇你俩二帖子(耳光)。”
刘记本说:“你这是胡说,明明是麻核桃,怎么会是英雄的血。”
“你爷爷是不是牺牲在这棵树下?”
“不假。”
“那么,他的血是不是也就流在这里?”
“那当然。”
“那岂不是在卖血?”
“我可不这样联想。”
刘记本的爷爷叫刘本正,当时是夹户屯的支部书记,日军扫荡到这里,在村里人的保护下,他逃出了包围圈。日军就把全村人集合在大核桃树下,架起了机枪,说,如果刘本正不回来就范,就屠村。天黑了,日军烧起了松明火把,燃烧的声音噼噼啪啪。村里人沉默,他们不惧怕,也不希望。
后半夜,正当日军失去耐心,准备动作的时候,从笔架山的山梁上走下来一个人,正是刘本正。他腰板挺直,步伐沉稳,踏在石凸石凹上,如履平地。
他径直走向日军,笑着说,我来了。
日军的头目也一笑,朝人群挥挥手,他滴来了,你们滴可以去了。
日军要把刘本正捆到大核桃树上。他说,既然我自己来了,何须再捆,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日军头目说,我捆的不是你滴身体,而是你滴灵魂,不能让你滴就这样轻松地来去。
日军头目知道,面对这样视死如归的人物,劝降、收买均无济于事,不必废话,便挥挥手,开枪滴干活。
一阵机枪扫射,把刘本正打得破碎。
鲜血迸射,落在土地上立刻渗入土里。
然而山环里有哭声,此起彼伏。日军朝哭声响起的地方放了一排空枪,怏怏而去。
刘记本的名字是他父亲给起的,用意是让他记住爷爷。起初刘记本还有“记”的意识,时间久了,就淡化了,以至于不再将麻核桃与爷爷的血联想在一起,麻核桃就是麻核桃嘛。
2
史志办的三个人经过一番踏勘,形成了一个认识:这棵麻核桃已成了革命文物,是英雄地标,便没有必要再行立碑,只需在大树上嵌一块标牌,上写“刘本正烈士殉难处”或“刘本正烈士就义处”就行了。活树毕竟比冷碑更有温度,更能进入人心。而且活化石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立一块石碑,不过是后人制造的记忆,让人顿感隔膜。需要做的,是精心建一座纪念馆。而麻核桃树的东侧,正好有一块平地,可作为纪念馆的地基。它背靠睡女峰,母性的象征,正好赋予它一种意义:缅怀先烈,孕育新生,代代相传,不忘初心。
三个人齐声说:“这很好。”
俗话说,白露的核桃,立冬的菜(白菜)。纪念馆如果现在施工,到大地封冻,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的工期。
张文韬认为,纪念馆是永久性建筑,是百年大计,要保证质量,需从容施工,放到明年开春施工也不迟。于娜也是这个意思,她说:“明年开春施工,到七月之前竣工,正好赶上正经的节庆活动,纪念馆的剪彩也就隆重了,岂不更有意义?”谢民庆阴着脸想了片刻,摇摇头,“你们俩是我的老下属,实不相瞒—我明年三月份退休,再后,就是别人的业绩了,所以,必须在我退休前完成这项工作,这样一来,我这个史志办主任,不,还有我个人的人生追求,就会画上一个最完美的句号,岂不快哉。”
张文韬和于娜已跟随谢民庆十余年,对他的为人处世了如指掌。史志办主任不过是个被边缘化的小官,但他有担当,有情怀,总是要求自己和下属可以不当大官,但是不能不干大事,而且要在寂寂无闻中多干实事。修了两千万字的革命史(党史)和地方志,谢民庆可以说是常年超负荷地工作了。组织部门的领导曾经试探过他,难道你还有别的什么想法?他回答道,无他,只是有瘾。这个回答,让区主要领导大为感动,指示区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和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只要他想干事,就大力支持,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么一个没有个人野心而只想干事的领导,他们真心敬佩,也无条件地服从,那么,也就别再说什么,配合他把这个“句号”画好吧。
谢民庆找到财政局局长,作了汇报。财政局局长说,这不过是个小型纪念馆,也花不了几个钱,我支持。他又找到了建委主任,“我们史志办负责展陈设计,你们建委负责纪念馆建筑施工,咱们合作一把,好不好?哦对了,财政我已经说好了,不用你犯难。”建委主任哈哈大笑,“横竖没几个钱,即便是我们建委白给你建也义不容辞,眼下,像你谢大主任这样的人不多了。”
接下来,谢民庆负责展陈的整体策划,展陈设计的文案工作则交给了张文韬。
张文韬是个生活的极简主义者,他的住房有宿舍性质,标准的蜗居。但卧室、客厅,甚至包括厨房、卫生间,都被他“塞”满了书,留给生活的空间便极其有限,几乎是仅够容膝。书架之外是书垛,层层叠叠,翻检不易。但是,只要你说出书名,他总能从被覆盖、被遮掩之处迅速找出,让人惊讶不已,觉得他真是个读书种子,一如劲草,地表之乱,乱不了他捕捉阳光的意志,总能向上生长,且钻隙而出,站在明处。
他肚里装的书的确多,几乎是无所不包。
中国的古典名著,只要你说出篇目,他都能给你叙述出概要;古典诗词的名篇佳构,只要你说出题目,他都能倒背如流;历史方志,只要你点出方向,他都能给你作一番清晰的勾勒;地理名胜,只要你有所问询,他都能给你作一番泾渭分明的描绘;文献典籍,如果你想借用,他都能给你提供有关的影印图像和考据、索引。
张文韬的渊博,源于他的家学根脉。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好读书,敬惜字纸。他的父亲,虽是工人,却喜钻研学问,遇到好的诗文,不仅研习,还恭恭敬敬地抄在本子上。他父亲留下的笔记,有数十本。本子上的字迹,差不多都是小楷,很见功底。张文韬参加工作后,也成了工人,他父亲就开导他,做工人不意味着就远离学问,要学会用书香修身养性,以便活得超逸脱俗。他听父言,勤于阅读。但父亲还嫌不足,告诉他,书要能真正读懂,并且装进肚里,就要勤于抄,不仅摘句,还要抄全文,且要用小楷,做到一丝不苟(后来张文韬成了书法家,入了北京书协,问他如何学书,他说,无他,抄书使然)。所以,张文韬与父亲一样,也有很多抄本。娶妻生子后,家里的这个气氛,也感染了妻子和儿子,他们也都手不释卷。他的儿子刚小学毕业,就把成人需要研修的古典文学必读书悉数读完。他的妻子,因饱读诗书,悟性突出,被从售货员的岗位,上调到公司党委宣传部,搞文案,做电视节目。他们家可谓是真正的书香门第。
张文韬写了大量的文史小品,除了在各大报刊发表之外,还在他所在的厂报上以专栏的形式经年连载,他的读者可谓多矣。这些文章应读者要求结集出版,每篇文章之后,他都自绘了一张插画,与文字一道相映成辉。读者惊叹,一个搞文字的,怎么画也画得这么好?
上世纪末,张文韬所在的企业进行改革,搞一刀切,四十五岁以上的职工都被分流。或买断工龄,提前退休;或自谋出路,实行转岗。恰此时,区史志办扩编,由于相知,谢民庆突破种种阻力,把他顺势调来。
到了史志办之后,张文韬如鱼得水。
首先是谢民庆把和他的关系定位在兄弟、同道、知己的层面,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让他享受到被尊重的美好。其二是给他充分的信任和自由施展的空间,放手让他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施展才华。张文韬很珍惜,十几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譬如因为有很强的文献意识、档案意识,参加工作以来,他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地资料,包括文本、图像、原件,加上他个人的研究成果、文章著述,这些本可以成为他获利的独特资本,但只要是别人想借鉴、想引用,不管告知与否,他都慨然应允,决不计较所谓的版权与稿酬。许多人说他傻,说他不会经营,他却说,私人收藏如果不被利用,会烂掉;个人智识如果不产生实际效应,会胎死腹中—只要是被运用了,就是实现了我的个人价值,我就感到欣慰和快乐。
他到史志办以后,主动做了不少的事:详细编制了全区历年的大事记,建立了活动图像电子文库,印制了《地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志》,使地区的发展历程有据可查,为今后正规志书的撰写提供了原汁原味的一手资料。他因此被推崇为区内首席文献专家、史志专家。
既然谢民庆主任想要画好他履职的最后一个“句号”,张文韬觉得自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玉成此事。这既是忠于事,也是报答知遇之恩。关键时刻不能尽显身手,他还是张文韬吗?
3
张文韬开始撰写文案。
他遍查县志、地方英烈档案,但所得刘本正的事迹资料和信息极其有限,最为遗憾的是,烈士生前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个人相片,形象展示就成了问题。
他只身再去夹户屯,跟刘记本住在一起。
近距离接触,他发现刘记本居然也是个驼背,而且比自己还要驼得厉害。本来是想用他做模板,还原他爷爷的形象,这样一来,还怎么还原?
张文韬有些失望,不停地咂舌。
“你对你的爷爷有没有印象?”他问。
“当然有印象,因为我是他的大孙子。”刘记本说。
“即便你是他的大孙子,但他牺牲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哪里会有印象?”
“我爹是他的大儿子,他对我爷爷有印象。”
“你爹有印象不代表你也有印象。”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刘记本解释道,“在我们夹户屯,有个风俗,就是家传老大,爷爷传给老大,就是我爹,我爹传给老大,就是我了。我爹总是在我耳边絮叨我爷爷长什么样,我爷爷的样子就活在我眼前了,嘻嘻。”
“那么,你爷爷到底长什么样?”
“嘻嘻,你看看我,就知道我爷爷长什么样子了。你要是不相信,就去问问村里的老人,他们准会对你说,我和我爷爷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就不符合逻辑了。”张文韬很困惑,“人们叙述你爷爷走向日军的时候,可是腰板挺直,步伐沉稳,踏在石凸石凹上如履平地。他要是个驼子,怎么会‘腰板挺直’?”
“那是他心情沉重,被压力压直的。我们这地界有句歇后语,叫作‘碾盘上躺着个驼子—滚子一过就直了’。嘻嘻,那是不得已的直。”
张文韬觉得这多少是一种道理,但嘴上却打趣道:“你这是谬论。”
刘记本也打趣道:“在我们山里,除了牛粪、羊粪、猪粪、鸡粪和大粪之外,遍地都是谬论,信不信由你。”
他们是站在刘记本的屋地上说这番话的,这时,刘记本的老婆从外边走进来,瞪了他一眼,愤愤地说了一句:“贵客进门,你也不让座,瞧你那点德性!”随着这一声呵斥,刘记本一个激灵,身子一挺,腰居然直了,“嘻嘻,张领导,你请坐。”
这倏忽间的变化,被张文韬捕捉到了。
落座之后,刘记本的老婆给客人沏茶。她从墙柜里翻出一罐自己不舍得喝的好茶,放在茶吊子里,用沸水冲泡。一系列动作,热情但有些笨拙。她也感受到这一点,羞得满脸通红。张文韬看到,她皮肤很好,容貌也很好,放在村里,算是个漂亮人儿。
沏过茶,女人对张文韬说:“领导慢慢喝,我去摘些丝瓜、豆角,顺便拧一只葫芦,凑几道菜。”
望着她的背影,张文韬情不自禁地说:“你夫人长得不错,看来你很有福气。”
刘记本得意得有些脸红,“嘻嘻,歪打正着。”
“怎么个歪打正着?”张文韬问。
刘记本叙述道—
是男人就喜欢好看的女人。张玉兰在村里数一数二地好看,我自然就动了心思,就去死打烂缠,最后居然就弄到手了,岂不是歪打正着?也赖这女子单纯,对我们家的长辈尊重。我爷爷是烈士,我爹根红苗正也当了支部书记,那天他带着村民扎沟垫地垒堰田,赶上山体塌方,他为了保护身边人,被砸死了,也就成了烈士。烈士加烈士,就让这女子的心酥了,她对我说,嫁你就嫁你吧,好女人不看面相,更重品行和家风。跟了我之后,起初她对我百依百顺,也贤惠体贴,到了后来就不成了,她嫌我不要求进步,也不积极争取加入组织,还好吃懒做,整天在麻核桃树下乱转悠,挣些黑心钱,毫无英烈之后的样子,便对我吆五喝六,指手画脚,不仅原来的柔顺跑得没了踪影,而且对我一点也不尊重。不尊重也就算了,到了晚上,还不让我近身,让我当活光棍。你看她都那么大岁数了,还风骚得跟个大姑娘似的,为什么?都是不尽妇道,闲的。
“闲的”一词,让张文韬感到有意思,不禁往深里回味了一下。这一回味,让他觉得特别可笑,就笑喷了。茶水喷出,口腔空荡,新鲜空气就乘虚而入,他闻到了一股馊味,“你的茶是不是变味了?”
刘记本咂了咂自己杯中的茶,“真是他妈的馊了,”他恨恨地说,“这老娘们儿,有好茶叶也舍不得让我喝,说是留到关键时候拿给客人们喝。你倒是留啊,留到最后,发霉变味,谁他妈的也甭喝了,呸,厌气!”
张文韬知道,所谓“厌气”,是当地土语,系献媚、下贱的意思。而且,刘记本所说的“厌气”,还有引申的意思,是指他的夫人,好像她的不让他近身,是预留给别的什么人。但是,到了最后,谁也不会对她动心思,因为“闲的”太久,搁馊了。
张文韬在刘记本家吃过中午饭,拽着刘记本来到大核桃树下。他让这个“模板”倚靠在树干上,自己则抻出速写纸坐着画。也许是膝盖上的那个小画板过于小,动作受限,他画得很慢。刘记本站得腰酸腿麻,不耐烦地说:“你能不能让我坐下来画?”张文韬反问道:“你爷爷牺牲的时候,是不是就站在树下?”刘记本点点头。“那么,你就必须站着,而且还必须站出视死如归的样子。”刘记本呲牙咧嘴地挠头,张文韬呵斥道:“你严肃点儿。”
刘记本打了一个激灵,下意识地往上挺了一下身子,居然就真的站直了。
张文韬吃了一惊,嘿嘿。
山里的太阳比平原的出来得晚些,所以,虽然是午后的时辰,但太阳正照在头顶,正经的高光时刻。强烈的阳光弄得刘记本睁不开眼。“把眼睛睁大。”张文韬命令道。刘记本努力睁眼,却还是弄得似睁似合。张文韬刚想纠正,立刻又想,他的这个样子,或许与当时的情状相近。因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刘本正,面对强敌,必心生蔑视,眼睛一定是觑着的,这样的目光才锋利,能刺穿敌人的魂魄。“也罢,就这么画。”
画了一下午,初稿终于完成。张文韬很满意,把画稿在手上抖了抖。
刘记本抢过画稿,“让我看看。”
画面上,高树,矮人,细眼,圆大的土丘,茂密的小草,怎么也看不出刘本正是其中的中心人物。刘记本忍不住说道:“我爷爷就这个样子?”
“依你看,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应该把树画矮了,人画高了,土丘画小了,小草画没了,我爷爷就显出来了。”
张文韬板着脸说:“那可就失真了,因为他毕竟是个驼子。”
刘记本急了,把画稿扔在地上,“驼子怎么了?驼子也能顶天立地。”
张文韬心中一震,看不出,身边这个人,居然也有舒展的气势,便笑着对他说:“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是一般的道理。我为什么把树画高?那是代表刘本正烈士心中的信仰,我为什么又把土丘画圆大、小草画茂密了?那是代表他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民。没有信仰,没有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民,他的高大又能有什么意义?我讲的,是道理之上的道理。这一点,你不懂。”
“我说不过你,也不想跟你多废话。”刘记本咽了咽唾沫,“拿回去让张玉兰看看,看她懂不懂。”
回到刘记本的家里,他老婆张玉兰正在案板上捏饺子。刘记本忙不迭地把画递上,“这是张领导画的爷爷,你给看看、判判,他画得怎么样。”
张玉兰用沾着面的一只手接过画来,双手捧在眼前,反复观摩。之后,她瞪了刘记本一眼,“你说怎么样我不管,依我看,这正是爷爷的样子。”
4
晚上,张文韬就住在刘记本家里。
他晚上跟刘记本喝了几杯“井里醉”。
所谓“井里醉”,是刘记本自己泡的酒。他家院子里有口水井,村里统一通上了自来水之后,就闲置了。但刘记本不让它闲,在井里放了一只坛子,装满了六十五度的散装二锅头,酒里泡着蜥蜴、蝎子、小蛇,还有人参、桂皮、枸杞子什么的。井底冷冽,弥漫着一团清气,正好“熟”酒。
这种药酒,滋阴壮阳,所以,刘记本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两杯。俗话说,人的器官都是用进废退,张玉兰不让他近身,他更要坚持不懈地喝,预备着一旦有用,即刻就能冲上阵去。不喝吧,担心“废”;喝吧,又深受折磨—躺在炕上,时不时亢奋,它自己就支棱起来,便腆着脸子乞求女人。女人说,你人不争气,它争气有什么用,恶心,你还是闲会儿吧。无奈之下,他只好冲黑暗的屋顶嘘酒气,骂道,厌气!
张文韬素日不饮酒,但架不住刘记本过度的热情。刘记本说:“领导你辛苦了,我爷爷跟你不沾亲不带故,你却顶着个大老爷儿(太阳)画个不停,既让我感动又让我不落忍(不忍心)。你是个什么人?对自家之外的事儿,还这么上心,我真是猜不透。不过,你这样上心,还真是好,如果你不来翻腾他的旧事、揣画他的样子,我爷爷就真的被人忘记了。所以说来说去,你对我们家有恩,你就必须端酒杯,好让我敬你。”
但这一敬就不可收束,第一杯代表他自己,第二杯代表他父亲,第三杯代表他爷爷,就把张文韬敬多了。
张文韬爬上刘记本家的土炕,昏睡过去。
不知睡到何时,一种特别的动静,让他在昏沉中竖起了耳朵。
炕那头,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别往我身边趋乎,满嘴酒气。”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今天不知怎么了,就想往你身边趋乎。”呜呜,呜呜,好像是嘴对嘴吹喇叭。女人说:“你注意点儿,那边还躺着个人。”男人说:“他早被我灌晕了,即便是敲锣打鼓,也不会动一动。”推拒了一番之后,女人说:“算了,算了,念你今天有功,就依你一次吧。”男人说:“你得说清楚,我今天有什么功?”女人说:“你顶着个毒日头,让他照着你画像,让祖上托身显灵,活在众人的眼目之下,让家族的荣耀传下去,也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儿,让我心软。”
男人也就不多说,赶紧趁着女人心软,但行好事就是了。
两个人裹着被子叠加在一起。动作激烈而沉重,出奇地有力。等完事儿了,不担心惊动旁人了,刘记本才摊开身子,一阵咬牙切齿。这是快活的声音。一如久旱了的土地,突然承接了雨露之后,一边欢快地渗透,一边发出嗞嗞的声音。
张文韬在暗夜里笑笑,因为他们既滋润了自己,也肯定了他的工作。他甚至觉得,他的画法是对的,刘本正的眼睛被画得似睁似合,恰恰符合人性的特点。他有妻眷,有儿女,面对死亡,自然有留恋,便不可能断然地割舍。但他又是组织上的人,不能因私情眷恋而迷失了公义,在两难选择中,他自然会有忧郁。
张文韬心中一热,对自己说,历史的现场,就应该这样被还原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他带着刘记本踏遍了笔架山、睡女峰和夹户屯的角角落落。他对刘记本说,你眼下就是刘本正而不是刘记本,你要带着你爷爷的语气说话,带着你爷爷的表情走路,带着你爷爷的动作坚壁清野,带着你爷爷的感情嘘寒问苦。
刘记本也真能入戏,他一旦这样做了,就好像他爷爷神魂附体,一招一式,均身不由己,都是他爷爷在身后推动。
几天下来,夹户屯的百姓,眼里也只有刘本正,而不知道谁是刘记本。
而张文韬的速写本上,已勾勒出连续的画像,且无不符合当时的情景。
他心中大悦,他的文案设计,也已成竹在胸。
5
张文韬回到史志办,谢民庆劈头就问:“你的文案设计搞得怎么样了?”
张文韬也不回答,只是笑着反问道:“你的建筑设计搞得怎么样了?”
谢民庆知道,这就是回答了,所以他不再追问,兀自回答道—
咱们京西,作为晋察冀的抗日模范根据地,像刘本正这样的英烈人物,上了册子的,就有两千多个,所以,建纪念馆时,不能大小划一,千人一面,而是要各具特色。再说,夹户屯屁大的一个地界,仅有三二十户人家,纪念馆不宜大,要依山依势而建,建得朴实、扎实、平实,不“跳出”水土。具体地说,刘本正纪念馆就是一个石头建筑,就是一座大石头房子。也就是说,它是当地民居的一个放大,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石头门楣和石头广场,以便于游人参观而已。
张文韬笑笑,打趣道:“英雄狗熊所见略同,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说的是真心话。夹户屯几无平地,村西口大核桃树下有个大土丘,大土丘往东,有个小小的空隙,是刘记本为了将来老房子翻盖,申请预留的宅基地。这就好办了,建纪念馆时,省却了拆迁征地的麻烦。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既然是为了他祖上而建,即便是痛,他也得忍着。
谢民庆把建馆的理念阐述给建委的领导听,建委的领导说,这好办,你就擎好吧。
选址的时候,谢民庆亲自到了现场,他怕平生波澜。
刘记本果然出来阻拦,“那宅基地是预留给我建房子用的,你们建了死人的场馆,我们活人住在哪里?”
谢民庆说:“正因为建了死人的场馆,你这个活人才真正活了。”
“你这是哪儿的道理?”刘记本问。
谢民庆在刘记本的后背上拍了一巴掌,那个驼的部分立刻就直了。他放声大笑,说道:“纪念馆建成了,大小也是个事业单位了,需要有人看管、打扫、经营,上边就要给两个人员编制。这个编制给谁,是有条件的。你既然把活人的地界让给了死人,那么,上边就要考虑活人怎么活,你岂不顺理成章地就住进馆里,理直气壮地成了管理人员?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谢民庆的话,让刘记本既明白又糊涂,他木在那里。这时,一旁的张玉兰狠狠地在他的驼背上踹了一脚,“你还犹豫什么?”
在山里,女人的踹,就是拿定主意的意思,男人即便是糊涂着,也作出了明白的回答,“听领导的。”
不过,刘记本还是怀疑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等到了一个机会,他把谢民庆拽到一边,偷偷地把一对麻核桃塞进后者的口袋里,“这是我把玩了多年的麻核桃,油亮油亮的,身上皴满了花纹,差不多就是文物了。”谢民庆嗯了一下,“是不是你爷爷留下来的那对儿?你要说实话。”刘记本说:“俗话说,先人的遗物,后人的想念,我又不真傻,怎么会把它送给外人?我把它放在衣柜最底下,藏着呢。”谢民庆便笑着拍拍自己的衣兜,“既然是这样,你的这一对儿,我就收下了。”刘记本憨憨地一笑,“这我就放心了。”
这也是谢民庆收下麻核桃的用心。人家既然不安心,就要给他一个安心的理由。
当他走到众人面前的时候(这个众人,包括他的下属张文韬、于娜和建委主管领导、专业设计人员),居然把暗藏在衣兜里的麻核桃托到手心之上,对大家说:“这就是夹户屯有名的文玩,你们看,它的品相有多好。”
在阳光下,麻核桃油彩熠熠地泛光,花纹暖暖地脉动,像灵物一样攫人眼目,大家齐声而叹,好物件儿!
谢民庆大声地对刘记本说:“你一个看(卖)麻核桃树的,手里有的是这种东西,还不每人送上一对儿,让大家都欢喜欢喜,大家一欢喜,这纪念馆也就建得快了。哈哈,本来是不值钱的货色,生让你给忽悠贵了,别舍不得。”
刘记本看了一眼张玉兰,像得了什么暗示,他苦笑了一下,在不舍得中舍得。大家笑成了一片。
一行人,既选址,又丈量测绘,还勘察民居,与百姓座谈,弄到天色很晚。
回去的路上,张文韬一直就合着眼。或者是在冥想,为他的展陈设计打底稿;或者干脆就是睡了,蓄养精神。谢民庆本来也很疲惫,只想睡去,但看到山路崎岖,车灯晦暗,开车的于娜又是个女的,他有些不放心,只好强打精神,大睁着眼。但毕竟快六十岁的人了,精神可嘉,皮囊趋瘪,在颠簸中,不由自主地就合Kgzrgcnj9krt3J/0v9nrAw==眼。这可不成,出门在外,做领导的,对一切都要负责,不能有一丝懈怠。为了对抗瞌睡,他拿出了那对麻核桃,不停地揉搓,哗啦哗啦。一路哗啦,以为车子会行得顺畅,没想到,在一个时刻,车子突然停了。谢民庆一愣,“怎么,有情况?”于娜回过头来,暧昧地一笑,“没情况。”“没情况就走,可别耽误在路上。”车子行走,他又开始揉搓麻核桃,哗啦哗啦。他一边揉搓,一边观察开车的于娜,他竟然发现,于娜腰身不停地萎缩,肩膀不停地颤抖。他忍不住地问:“你哪里不舒服?”于娜回答道:“没有不舒服。”既然无恙,走就是了,所以他继续鼓捣文玩。走到一处宽阔的路面,车子突然靠边又停下了。没等他发问,于娜颤抖着声音说道:“领导,我求你了。”
“求我什么?”他惊异地问。一个女下属在暗夜里突然求他,情况复杂。
于娜回过头来,似乎有难言的隐痛。
“你说,你说,求我什么?”他催促道。
“求您别再揉那东西了,您一揉,我心肝就发颤,脑皮子就发麻,大腿就发软,就把握不住方向盘,就蹬不牢刹车,只想把车开到山下去。”
“一路上哗啦哗啦的,烦不烦?我看你是闲的。”张文韬果然没睡,他毫不客气地插话道。
一个揉搓文玩的小小行为,居然在女下属那里引起这么大的生理反应,这是什么道理?而且,一贯驯顺的男下属,居然也为了一个文玩,不,为了女同事的奇怪反应而说出那么不客气的话,这又是什么道理?
他恨恨地说道:“张文韬,你他妈的也别再装睡了,你把眼睛睁大了,给她看路,从现在开始,该我睡了。”
6
纪念馆如期竣工。
那个大房子很和谐地融汇在山村的怀抱里,既看得见,又不刺眼,静穆地矗立着。但却成了百姓们的牵挂,他们自发地走进去,感受着从来就有却没有用心品味的光荣。
有关部门本来想搞一个隆重的开馆仪式,但是谢民庆主张,这个纪念馆,是个百姓自我教育的基地,既然百姓不请自来,就说明它已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再需要外在形式的加持。
其实是他心中有个隐秘—
他是从揉搓文玩引起于娜身体不适中得到启发,如果搞隆重的开馆仪式,那不啻是一种杂音,污染了纯粹,凸显了多余的用心,从而也就降低了品性。而他谢民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额外的野心的,即便是为自己政治生涯、人生追求画句号,也要用默默无声的方式,这样,才不会因张扬、炫耀而引起猜忌,从人格到作为便均无可挑剔。
他以一个普通参观者的身份走进纪念馆。
身旁,有刘记本和张玉兰殷勤的陪同。
他们如愿地做了管理人员。由于张玉兰是个形象很好的女人,还成了馆里的解说员(不仅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是经过了张文韬悉心的培训)。她那天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女式西服,由于贴身,曲线玲珑。且面上傅粉,白皙而有香气,秀美之姿,遮掩了村妇的底色。
谢民庆心里立刻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这个张文韬是怎么调教的,把她弄得这样脱胎换骨?他不好说破,只是朝她一笑,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不用她讲解,整个展线都是他和张文韬设计的,他已了然于胸。
此时用旁观者的视角看,他的心头荡漾起得意的暖流。张文韬与他真是天作之合,张文韬的画幅连缀起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使刘本正活着走进了人心。其中一幅,是主人公在大土丘上动员群众的一个画面,刘本正手里居然就把玩着一对文玩。他笑笑,心里说,这很符合人物的出身,村里既然出产麻核桃,他农民的本性,必然会让他把它揉搓于掌中。这代表着坚定与从容。张文韬虽然是个学人,但毕竟是在史志办里工作了多年的业内之人,他自然要从更高处考量。于是,他的展线布局,全遵循着客观的历史逻辑:全民族的抗战—晋察冀的抗战—京西地区的抗战—夹户屯的抗日斗争—刘本正的抗日风采—刘本正精神的历史影响—今日夹户屯发展风貌。这样一来,就有了大局和局部,就有了群体与个人,就有了历史与今朝。其中,在“刘本正精神的历史影响”这一版块中,刘记本的父亲也上了展板,成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证明。这就使纪念馆呈现出复调,既是浓缩的抗战史,又是一部村史和家族史。
谢民庆对自己说,看来,我的这个句号,画得还算完美。因为句号变成了破折号,为今后纪念馆—乡史馆、村史馆的建设,提供了样板,那么,我谢民庆的影响就是持续的、久远的了。
嘿嘿,他有些心花怒放。难以自持之下,他喊道:“刘记本,你过来。”
刘记本一直就尾随在张玉兰身后,一听到叫声,他擦着夫人的身子就蹿了过来,“我在。”
谢民庆指了指展墙,“这上边有你爷爷,有你父亲,什么时候也有你?”
刘记本只是傻笑,说不出答案。他求救般看了一眼身后的张玉兰。
张玉兰跨过来,说道:“谢领导,您不用着急,他也快了。”
“嗯?”
“您看,”张玉兰回答道,“我们家的那棵大麻核桃树,这些年一直被他独揽着,充作发财的家什,可现在他变了,对我说,那是烈士留下来的,应该随爷爷归属给纪念馆,成为馆里的文玩产品,卖出钱来,贴补馆用。嘻嘻,您看他是不是有出息了?”
“就是,就是,我虽然还没上墙,其实我已经在墙上了,嘿嘿。”刘记本得救了,延伸着豪迈了一下,夫人不踹,他也站直了。而且,他还顺势在女人的腰窝上摸了一把,“还是我媳妇懂我。”
他们走到一个玻璃展柜前,柜面上放着一个大号白晶托盘,托盘上有透明的罩子,里边罩着两颗大得惊人的麻核桃。麻核桃浑圆,油黑闪亮,其纹络像血液喷溅。谢民庆本能地问道:“这是不是刘本正烈士留下的那两颗?”
“正是。”张玉兰立刻答道。
一个村妇居然也会用简语,雅致了。
“这可是一件特殊的展品,它附着烈士的情感和体温,能吸引观众。”谢民庆说。
“正是。”张玉兰也觉得自己用这样的词说话有些可笑,便吐了吐舌头,把话说得家常起来。“人一来到这里,就赖着不走,且端详呢,他们老稀罕了,说,这两颗是夹户屯的灵物,咱不能动,但他们不是给预备着许多颗吗,一定要请几颗回去,一来是当作到此一游的纪念,二来带回去舒筋活血治病,得英雄的保佑。嘻嘻,我们坐地起价,卖出去不少。”
“坐地起价可不好,你们要明码标价。”
“嘁,不坐地起价还能当圣物使?再说,他们买的是心气儿,主贵不主贱。”
“那么,麻核桃总有卖完了的时候,你们卖完了又怎么着?”
“轻易是卖不完的,因为先人留下的两颗是母的,它衍着后边的子孙呼啦啦地长,年年是旺年,年年成群结队。”
母的?这个女人可真会比喻,好像一下子有了通灵的功力。
“哈哈,你可真不简单,快成精了。”谢民庆顺势夸了她一句,笑着说道,“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多栽几棵文玩树,让麻核桃有可靠的繁衍。”
“不栽。”
“为什么?”
“大核桃树就是刘本正,刘本正就是大核桃树,他已经牺牲了一次,不可能再牺牲第二次,更不可能牺牲第三第四次,那就不严肃了。”
“有意思,有意思,有见地,有见地。”谢民庆连连称叹。
见领导这么赏识自己的媳妇,刘记本忍不住在她脸上啵儿了一下。“瞧你。”女人的脸霎时就红了,是桃红的颜色。
再见到张文韬的时候,谢民庆说:“纪念馆的那对儿可真有意思,本乡本土的山里人,却也不忸怩,当着外人就秀恩爱。”
“你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以为山杏不知风月事,不懂土地。”
其实张文韬想说的是,你的句号画得着实完美,不仅建起了纪念馆,而且还拯救了一桩婚姻。
但是,他不便把这话说出口,因为有奉承、谄媚、拍马屁之嫌。
凸凹,本名史长义。1963年生,北京房山佛子庄人。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12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评论集1部,散文集30部,《凸凹文集》八卷,总计发表作品800余万字。
近60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30余项,其中,长篇小说《玄武》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散文获冰心散文奖、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老舍散文奖、全国青年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2013年被授予全国文联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