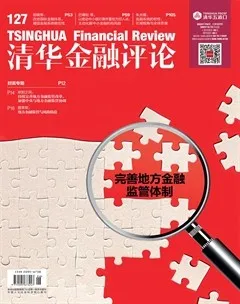激励共谋
2024-09-04马芳原

在产品市场中,“共谋”是指竞争者之间通过明确的协定或暗中的默契,共同实施限制竞争的策略,以期实现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当企业的股东为了增强利润回报而偏好共谋策略时,他们是否会设计精巧的薪酬激励机制,从而激励企业的管理者加入并推进共谋策略的实施?论文《激励共谋》(MotivatingCollusion)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实证检验。
在产品市场中,“共谋”指的是竞争者之间通过明确的协定或暗中的默契,共同实施限制竞争的策略,以期实现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共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价格操控(bid rigging)、市场分割(market allocation)、产量限制(outputre striction) 和排挤竞争对手(competito rexclusion)等。尽管这些策略可能为企业的所有者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它们往往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因此在世界各国,这类行为通常被视为非法的市场操纵。尽管法律禁止此类行为,并且对违法者处以严厉惩罚,但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市场上仍然频繁出现共谋案例。近年来,人们见证了多起共谋案例,例如针对美国四大铁路运输公司的民事诉讼,这些公司被指控参与价格固定;美国佛罗里达癌症专家研究所因同意避免与佛罗里达州西南部的另一家肿瘤学团体竞争,而被处以1亿美元罚款;Bumble BeeFoods LLC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因共谋控制罐装金枪鱼的价格而被判处三年监禁。
尽管一旦共谋行为被揭露并遭到法律制裁,所面临的惩罚可能极为严峻,但在监管力度有所放松的环境下,某些企业仍可能将共谋视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市场策略。对于股东而言,参与共谋或许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构成了最优选择,但管理层对此可能会持有保留态度,这主要是由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存在内在动机上的差异。高层管理者出于对自身职业发展和声誉的考虑,相较于匿名的股票投资者,更可能对参与共谋行为持犹豫态度。此外,参与共谋的决策者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如监禁等严厉的法律制裁,这进一步增加了公司决策者对于参与市场共谋策略的顾虑。因此,尽管股东可能视共谋为增加利润的最优策略,管理层的个人风险评估往往与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一致,从而在决策偏好上产生分歧。在管理层与股东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股东通常可以通过调整高管的薪酬和激励制度,来促使管理层执行符合股东利益的战略。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当股东为了增强利润回报而偏好共谋策略时,他们是否会设计精巧的薪酬激励机制,从而激励管理者加入并推进共谋策略的实施?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马芳原与合作者[哥本哈根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Sangeun Ha和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副教授阿尔米纳斯·扎尔多卡斯(Alminas Zaldokas)]共同撰写的2024年4月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上的论文《激励共谋》(MotivatingCollusion)(以下简称“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证检验。论文聚焦于近年来美国市场中反垄断法执行力度的减弱这一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股东可能会从偏好积极竞争转向更倾向于共谋策略,因为参与共谋的潜在利润可能已经超过预期的法律制裁成本。然而,即使在反垄断法执法力度减弱的环境中,管理层从个人角度出发,可能会因为共谋带来的声誉损害和刑事指控风险,继续倾向于避免共谋。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理论上可以通过调整薪酬机制,设计出抑制管理层执行竞争策略或鼓励其参与共谋的激励措施。论文针对这一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薪酬机制是否激励共谋策略,以及如何激励共谋策略的参与和实施。
激励理论阐明了管理者是否倾向于实施竞争或共谋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薪酬的结构,尤其是其报酬水平与竞争对手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如果高管的薪酬是基于超越这些竞争对手的业绩来确定的,那么其薪酬与竞争对手的业绩之间就会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即高管的报酬会随着竞争对手表现的下降而增加。然而,当抑制产品市场竞争对股东有益时,最佳的薪酬激励机制则会显示出与竞争对手业绩的正相关性,既高管会因竞争对手业绩的提升而获得奖励。在当前反垄断执法力度减弱的情况下,共谋策略开始受到股东的青睐。在这种市场环境中,股东可以通过将高管薪酬与竞争对手的业绩正向挂钩,从而鼓励管理者采取更为温和的竞争手段,或者直接参与到共谋策略中(以下简称“激励共谋”假设)。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论文基于美国市场近年发生的一个政策变动,设计了一个准自然实验。论文所关注的事件发生在2013年,当时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关闭了位于美国克利夫兰、达拉斯、亚特兰大和费城的四个地区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关键职责是搜集本地市场潜在的共谋行为的相关信息。由于2013年的政策调整目的是节约成本,并把重点转移到大公司上,美国司法部决定将这些地方办公室的案件处理工作迁移到华盛顿特区的总部和其他剩余的三个地区办公室。然而,这项监管上的调整无疑减少了对那些被关闭办公室附近企业的监察力度,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更易于形成合作共谋的环境,使得抑制竞争或进行共谋成为本地市场竞争者之间的最优策略。
论文选取了那些在本地市场中存在竞争对手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将那些总部设在四个被关闭的地区办公室的辖区企业定义为实验组,其余企业则构成对照组。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简称DiD)的实证研究框架,对“激励共谋”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揭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自2013年以后,实验组高管的薪酬与其本地竞争对手的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呈现出正向变化,而与自身业绩的正相关性则有所减弱,这与“激励共谋”的假设相吻合。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薪酬结构的这种调整主要是由现金薪酬部分的变化所驱动,而非股权薪酬调整的结果。这表明董事会在积极调整薪酬方案以适应监管环境的变化,并非仅仅是在被动地响应市场竞争模式的转变。
接下来,论文进一步探究了2013年政策变化对高管薪酬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个显著现象:在那些董事会治理较为出色的企业中,政策变化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一发现有助于排除一种潜在解释,即认为反垄断执法力度的减弱缓解了管理层对共谋行为的自然反感,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寻求共谋,并影响董事会调整薪酬结构,以向其他卡特尔成员提供保证并促进共谋的形成。如果这种解释成立,人们理应在那些董事会受到高管控制的企业中观察到更为强烈的效应。然而,实际发现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这表明所观察到的薪酬变动更可能是由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动机驱使,而非仅仅是管理层权力加强的结果。
论文还发现,在那些企业作为战略互补者相互竞争、因而更可能彼此勾结的行业中,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另外,对于那些处于集中行业的公司而言,这种影响也更为强烈,这是因为在竞争者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共谋行为更有可能发生,协调起来也更为可行。同样,对于那些本地业务更为集中的公司,估计效应更大,这些公司显然更容易受到该政策变化对本地市场监管的影响。此外,临近退休的高管往往持有短期视角,与长期股东或计划以对应长期内在价值的股价出售股份的股东相比,他们的偏好不同。论文发现,对于这些高管来说,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在高管面临流动性更好的劳动力市场的企业中,这种影响也更强,因为在这些市场上,高管大概会更关心自己的声誉。最后,在上市公司比例较大的行业中,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同行的业绩可以从股票回报中更好地推断出来。
此外,论文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在2013年政策变化之后,高管薪酬的调整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相关。具体来说,受政策变动影响的企业展现出了比未受影响企业更高的毛利率,而且这种毛利率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那些对高管薪酬激励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的企业中。进一步地,这些公司的股票回报与本地产品市场上同行企业的回报出现了更为紧密的联动,这一趋势表明了它们之间在经营业绩上的相关性有所增强。这些发现均表明,在政策变更之后,企业开始采取抑制竞争或共谋的策略。
最后,论文还研究了高管薪酬其他特征的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没有反垄断执法,共谋策略本质上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一个短视的盟友可能会随时偏离共谋安排,以通过激进的竞争来获得丰厚的短期利润。因此,在2013年政策改革之后,股东可能会发现延长管理层股权激励的锁定期可以帮助抑制这种短视行为,从而促进共谋的稳定性。实证结果与这一猜想一致。
综合分析论文的研究发现,股东可以通过设计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促使管理者与竞争者之间采取共谋策略,进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股东或其代表的董事会成员并没有明确指示共谋策略的执行;因此,他们可以合理地否认这些激励方案旨在反映实施共谋策略的意图。通过这种手段,他们避免了承担个人法律责任。这一发现揭示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难题:一方面,公司治理标准要求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激励机制必须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如果长期投资者的行为倾向于促成共谋,那么旨在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政策可能需要鼓励管理者的短期主义行为,这虽然会加剧委托代理问题,却可能带来促进市场竞争的效果。
(马芳原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论文《激励共谋》(Motivating Collusion)由哥本哈根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SangeunHa与马芳原和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学副教授阿尔米纳斯·扎尔多卡斯(Alminas Zaldokas)共同撰写,2024年4月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特约编辑/孙世选,责任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