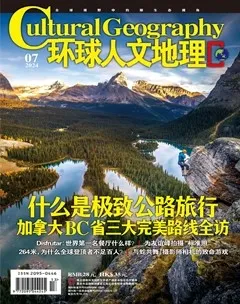麋鹿传奇
2024-08-18丸子

在中国,大众对麋鹿的认知度应该仅次于梅花鹿。早在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曾用“麋沸蚁动”来形容战争导致的骚乱,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麋鹿活动曾经非常繁盛。
很多年后的今天,麋鹿成为了江苏省的闪亮名片。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故事是,麋鹿在江苏的灭绝、回归和复兴,恰好是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从失衡转向平衡的一个缩影。
皇权之下“神兽”绝迹中原
麋鹿是一种喜水的湿地动物,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距今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动物分类学家将它归类为鹿科,麋鹿属,达氏种。
角似鹿,面似马,蹄似牛,尾似驴,俗称“四不像”,这是对麋鹿外形精准的概括。因长相奇特,在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中,麋鹿总是充满神话色彩,比如在《封神演义》中,麋鹿就是姜太公坐骑的原型。除此之外,它还被视为祥瑞之兆,备受古代君王的喜爱,长久以来都象征着皇权。
麋鹿常常以群体形式出现,性格比较温顺。但见过麋鹿的人应该清楚,它们体型庞大,十分具有压迫感,让人无法将其和温顺产生关联。成年雄性麋鹿的体长可达2米,体重甚至可以接近600斤,它们拥有粗壮的四肢与多肉的主蹄,双蹄间有宽宽的腱膜相连,增加着四肢末端着地的面积,能够减小压强,帮助它们在沼泽松软的泥地上运动。当麋鹿行走时,双蹄还会发出响亮的磕碰声。而它们的尾巴,主要是为了驱赶潮湿地区飞扰的蚊虫。

就毛色而言,麋鹿有夏毛与冬毛两种。夏季,麋鹿的体毛多为赤锈色,颈背上有一条黑色的纵纹,腹部和臀部为棕白色。9月以后,麋鹿的体毛被较长而厚的灰色冬毛取代。长相上,麋鹿头大、眼小,独有的眶下腺较为明显,与马有几分神似。值得注意的是,长有角的都是雄性麋鹿,雌性不仅没有角,体型也相对较小。麋鹿角的生长周期很长,两岁左右,雄性小鹿开始长角分叉,到六岁时叉角才能发育完全。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古人对麋鹿的记述不绝于书。它不仅是先人狩猎的对象,也是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祭物。然而,从书中走到现实,独特的外表却成了麋鹿持续了千百年的噩梦。

正是由于麋鹿身上加持了诸如祥瑞、神兽的色彩,使得历代帝王们都执着于搜寻它们的踪迹,活要见鹿、死要见尸。帝王们更是希望通过食其肉获得长生不老之力,以求统治千秋万代。麋鹿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孟子》中,“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这证明,至少在周朝,皇家的园囿中已有了驯养的麋鹿。汉朝以后,野生麋鹿数量日益减少。元朝建立以后,善骑射的皇族把野生麋鹿从黄海滩涂捕运到大都(北京) ,供皇族子孙们骑马射杀。野生麋鹿逐渐走向灭绝。
绝对皇权下,麋鹿一直被肆意捕杀,加上湿地开垦不断扩大,致使麋鹿生存范围日渐缩小。最初只是绝迹于北方野外,在南方沼泽地中还留有一些生机,但随着湿地开垦的延伸,南方种群也逐渐消亡。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王朝统治的尾声,大部分地方的野生麋鹿已被赶尽杀绝,唯一存活的种群只出没于皇家狩猎场。
那时候,国际动物学界甚至还不知道麋鹿的存在。

有人推测,野生麋鹿可能灭绝于晚清时期,也有人认为,野生麋鹿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灭绝。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烧圆明园,南掠皇家猎苑。中国本土最后一批麋鹿终于在风雨飘摇的夜晚,被押往国外的船,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流浪生涯。至此,麋鹿在本土彻底灭绝。
水土不服回归的十年适应期
然而,生活在异国他乡的麋鹿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繁衍生息。
当初被掠走的麋鹿,大部分因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死去,幸存者无几。幸运的是,从1898年起,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花费重金,陆续买下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等地动物园的18头麋鹿,饲养在自家的乌邦寺庄园。麋鹿绝处逢生。乌邦寺庄园良好的湿地条件使麋鹿开始繁衍。据统计,到1983年底,全世界的麋鹿已达1320头,都是乌邦寺庄园麋鹿的后代,乌邦寺庄园的麋鹿也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种群。它们尽管遍及亚、欧、非、美、大洋洲,但唯独没有回到世代生息的故里——中国。
在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协调下,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决定无偿向中国提供麋鹿种群,使它们回归家乡。1985年提供了22头,放养到原皇家猎苑,即北京大兴区南海子。1986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支持下,39头麋鹿乘坐专机抵达上海,再运送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这一举动拥有重大的使命,那就是让麋鹿在原生地恢复能实现自我维持的野外物种。

其实,在麋鹿重引入计划之前,各方都进行了漫长的选址调研,江苏大丰之所以能成为重引入的首选,是因为这里是19世纪末国内麋鹿在野外灭绝前最后的栖息地之一。现如今,大丰仍然保留了大面积适合麋鹿生存的原生环境,在麋鹿回归后,大丰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成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麋鹿自然保护区。
可谁也没想到,故土竟会让麋鹿水土不服。
为了使麋鹿快速适应水土环境,抵达大丰后,每一头麋鹿都被单独圈养在各自的棚舍中,但却因此忽略了麋鹿群居动物的属性。它们产生抵触情绪,不吃不喝。并且,当时正值夏季,炎热的天气导致麋鹿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而后,又出现了消化不良、皮下血肿,甚至是母鹿流产的情况……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与麋鹿自身的共同努力下,很快,这些麋鹿就熬过了初期的病害,适应了当地环境。随后,大丰保护区圈出了足够大的林地和沼泽,让麋鹿从棚舍中跨出来,走向面积更加广阔的围栏,同时,以半野外化的环境作为过渡,让麋鹿学习如何适应人为活动的干扰,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

就这样,两年时间,保护区实现了麋鹿种群数量的复壮,又花费了十年时间,让麋鹿完全适应当地环境,掌握野外生存技能。1988年,大丰保护区内的麋鹿被正式放归自然,恢复野生种群的时机基本成熟。
百年野化回归复兴之路挑战不断
1998年11月5日,对麋鹿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这一天,保护区挑选了体质最强壮的8头(2公、4母、2幼)麋鹿,在保护区核心内进行野放实验,这是100多年来,麋鹿第一次走出人工围栏,回归真正的野外环境。
转眼间,麋鹿奔跑进黄海之滨一望无垠的草丛中。而后,其中一头麋鹿佩戴的无线电颈圈源源不断发回信号,中断数百年的野生麋鹿生命链条在那一刻被重新连接。这只是开始,无线电跟踪之外,还需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野外观察,确保麋鹿的安全,如果连续三天无法在外围见到麋鹿的踪影,他们就要徒步进入芦苇荡寻找。

野化,每一步都让人们提着胆。
好消息来得很快,1999年春天,一头野外放归的母鹿诞下了第一头小崽。2003年3月,野外出生的第一批雌鹿又产下小崽,此后连续三年,鹿群之中都有个体孕有后代,并且全部存活。这意味着野化的麋鹿具备了种群繁衍能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野化放归。截至目前,大丰保护区的野生麋鹿种群已经扩大至3300多头,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麋鹿种群最多的麋鹿基因库自然保护区。不仅如此,大丰的麋鹿沿着海岸线向北逐渐扩散到大丰港,向南扩散到了长江入海口。它们甚至会跨出滩涂,靠近人类的村镇。


问题也随之而来,麋鹿种群扩张带来了新的烦恼。健康的生态系统就像一座金字塔,物种之间相互制约才能保持生态平衡。麋鹿这样的食草动物一旦得到过度保护,必会疯狂生长。随着保护区内的麋鹿越来越多,当地的农业受到很大冲击,也给同域生活的其他物种造成影响,就连放归野外的丹顶鹤也没逃过麋鹿活动的干扰。严峻的是,有限的栖息地已经无法承载庞大的麋鹿群体,大丰保护区内的防风林寸草不生,麋鹿的粪便到处都是。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麋鹿成群结队前往周边农田,与农民发生冲突……
为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当地相关人员制定了人兽冲突补偿机制,补贴受损的农户,同时加大人工补饲的力度。

实际上,人兽冲突与局部栖息地过载等问题,算得上是保护动物之下的一种“甜蜜”烦恼,但只要给予先行者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加之接力者的努力与诚意,用持久的眼光看待问题,荒野上奏响的生命之歌必定会持久地传唱下去。
(编辑 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