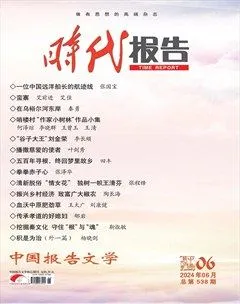五百年寻根,终回梦里故乡
2024-08-15田丰
在2024年龙年的春节期间,我经历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一个家族寻找到他们500年前的根。
所谓的叶落归根并非只是一句空泛的成语,直到现在我才能稍感这四个字的分量。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启了一个家族的寻根之旅,我想他们不是第一个,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叶落归根,不一定非得等到叶落之时再去寻根,毕竟叶落无声。早早地找到那棵属于你自己的大树,成为大树的一片叶子,枝繁叶茂才是每一片叶子归去时的最终愿望……
守望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2月15日,大年初六的早上7点左右,由于假期没事,起床都很晚。突然,一阵电话声音传来,看号码是河南的,他说是看到了我写的文章,想让我帮助他们寻找他们的宗亲。我没有马上答应他们,因为现在的骗子太多了,不知道又是啥新型的骗局呢。
这事儿我也就没有往心里放。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的电话响起两三声就挂了。我拿起来一看,又是早上的来电。我纳闷,他是怎么知道我号码的呢?
于是,我回拨了这个号码。他说是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的一个刘姓家族,他叫刘锁,因为老宗亲在明朝的时候从东明县搬迁出去了,现在想寻找“根”。
刘锁、刘新向给我讲了寻找宗亲几百年的故事,并要求加我微信。放下电话,我加了他们的微信,知道了根源。
原来,他们是根据自己家里的族谱来这里寻根的,已经寻找了几百年,始终也找不到。前不久,刘新向在网上看到我写的《东明地名文化》,知道我是一名作家,对地方文化有一些了解。于是查找到我的工作单位,天一亮5点多就赶到我上班的单位等候,7点左右,刘锁、刘新向向同事要我的电话号码,并讲解了很久,才算打动我的同事,给了他们号码。我本是一名爱心人士,热心肠,能帮助别人就帮助一下,家人们也都极力说服我去给他们帮忙,我也很乐意去干这件事。
刘新向发过来的寻根依据是族谱上的一句话,“时若武庠一世:武庠生讳时若明故生卒未详,旧籍河北大名府东明县城西刘枣园,明嘉靖年间迁居河南归德府夏邑县城西北十里……”
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都在苦苦寻求“刘枣园”这个地方,始终没有寻找到。我问了刘新向他们的寻找方向,他们是以目前县城以西为中心,一个个带刘字的村庄,基本上挨个都去过了。在以前,每年春节期间都要过来寻找一次,或是步行,或是赶着毛驴车,或是搭车,或是开车,来来回回几百年的寻求,每次来了,住上个三五天,再无功而返。三年疫情,稍稍停歇了一段时间,过后又开始寻找,基本上认为没有了希望。当看到我写的那些文章后,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激情。
我说:“你们先稍等片刻,我查查资料然后回复。”我旋即开始在地图上查找县城以西的带有“刘姓”的村庄,然后回电。刘新向说,这些村庄基本上都去过,与他们所要寻找的不是一个。
我问:“你们现在在哪里?”刘新向说正在回去的路上,已经到河南地界了。我说我就慢慢查查吧。
寻根
明嘉靖年间(1522年—1544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查东明县志载:公元1218年(金朝兴定二年),徙县治于河北冤句(县城在今东明集镇),原县城降为通安堡。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为避水患,县城迁至云台集(今县城西南西堡城)。1377年废东明县,县辖地分属开州、长垣。1491年(弘治四年)重置东明县于大单集(今东明县城)改隶大名府属河北省。
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没有找到,就说明有问题、有原因,就要拓展思维,寻求其他方法。我认为:一是他们寻找的方位是否错误;二是寻找的名称是否正确。
于是,我开始针对这两点来做文章。方位,现在的县城是否就是评判的标准和依据。名称,是否有错误之处,可否依据“刘枣园”来引申外延一下。
关于方位,这里,县城以西的概念很模糊。1522年与1490年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刘氏一世祖是明嘉靖年间离开这里的,他们应该在一个地方居住了很长时间,这很有可能是县城搬迁至大单集以前的地方,也就可以在东明集村至今东明县城划一道直线,这以西的地方都属于需要寻找的地方。远比他们寻找现在县城以西的范围要大很多。加之1855年黄河改道至今走向,县城以西的滩区里面的村庄,落河新迁也是变来变去,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村民投亲靠友,搬来搬去,亲人之间难以居住在一起,加之黄河发洪水时房倒屋塌,族谱也是丢来丢去,甚至遗失,很难寻找到一个宗族的“根”。
我开始翻阅《康熙版东明县志》《乾隆版东明县志》《宣统版东明县志》《东明县新志(1933年)》《东明县志(1985年版)》《东明县志(1986—2006年版)》《东明县地名志(1985年版)》《东明县村庄志(1—13卷)(2010年版)》《黄河的记忆之东明村庄(1—4卷)(2010年版)》等相关资料,一点点地寻查。
关于名称,我又与他们沟通,他们所说的“刘枣园”是否因为流传久远,名称有错误。刘新向说很有可能是错的,但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在“刘园”“枣园”之间寻找谐音的村庄。前些日子,我编撰写作了一部20万字的《东明地名文化》,把全县的村庄查询了好几遍,基本上对于村庄都有一定的印象。
东明县带“刘”的村庄有小井镇刘楼、洼刘等2个,三春集镇刘庄、刘小川等2个,刘楼镇刘楼、刘官营、大刘庄、刘庄、刘店等5个,长兴集乡刘乡、老刘乡、刘小台、刘庄、大刘寨、西刘庄等6个,沙窝镇刘沙窝、朱刘口、刘寨等3个,大屯镇火刘庄、大刘寨、刘堽等3个,陆圈镇刘堂、刘孝庄、刘东侯、刘香庄、刘士宽、刘庄等6个,武胜桥镇前刘河口、后刘河口、刘北城、刘庄等4个,城关街道北关社区刘庄、刘庄、刘墙、刘街、刘坟等5个,东明集镇刘庄、菜园集镇刘店、渔沃街道刘满城各1个,共计39个村庄。
与“刘园”谐音的有马头镇柳园,东明集镇柳园屯、柳园店。
与“枣园”谐音的有长兴集乡找营村。找营村又有刘姓始迁户,而这个找营正是在东明集村正西,基本上符合他们寻找的方位。
于是我把长兴集乡找营、刘小台、刘乡这三个村庄确定为他们需要寻找的重点村庄。
消息反馈给他们后,刘锁、刘新向家族又在一起开了个会议,确定要再次来东明寻找。
乡愁
这中间,刘新向又提供新的信息给我,说他们的一世祖曾是武举人。我又查找了旧志中的东明县历史上,特别是明朝期间的武举人有没有这个人。我没有查到。我又找到好友袁长海,他是研究东明县举人、进士等的历史文化专家,询问东明县明朝期间有没有刘姓武举人,他回答明朝东明县只有一个刘姓武举,刘祚昌,曾任参将,年代不详。
2月19日,大年初十的上午10点多,我接到刘新向的电话说,他们到了东明县。我们开始见面聊。
目前他们这一支刘姓人,经过500多年的历史演变,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是一个大家族。对于寻根问祖之旅,他们是念念不忘的,在族谱上写有谁要是寻找到先祖的根,是要上族谱的。
聊天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们先祖并不是武举人,而是武庠生。武庠生指州县官办的习武学校的学生,人员相对较多,如取得功名,中了秀才的有载,一般县志不载,武举人都有记载。
给解释了这些,他们非常感激。聊天过程中,他们讲了一世祖的一个故事。我旋即翻阅村庄志,找到“找营”村的由来:找营村建于明洪武年间。据传刘氏兄弟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时,随身携带着父母遗骨,到达目的地先找新茔地,故所建村庄取名为“找茔”,后依其谐音演变成找营。
这个故事恰好与他们讲的故事相吻合。几个人相当激动,刘锁、刘新向他们几个恨不得立刻就去找营村核对信息。
我问刘锁、刘新向:“你们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刘新向回答:“寻得宗亲,是一种心灵的归宿,这是五百载寻根之旅的终结与家族荣光的重燃。”他说,本来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而能够与我交流沟通,就是他们认为最大的希望。
东明到夏邑,只有200公里的路程,在现代交通工具发达的今天,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但却让他们走了500年时光。
中午,刘锁、刘新向几个人简单吃点儿饭,就抓紧去了找营村。
曙光
我到傍晚的时候给刘新向发了个信息,询问他进展如何。
刘新向很快回复:“找到了,还要考证才认。”
我与他们微信聊着天,谈论着这件事。
刘新向:“等他们商量商量再说,天太晚了我们就先回来了。”
我:“好嘞。”
刘新向:“他们这里没有家谱了。”
我:“那这样有些难度。”
刘新向:“他们是两个家族,一个原驻的,一个是外迁来的。”
我:“需要我帮忙吗?”
刘新向:“给点时间吧,我们双方都商量一下,停一段时间再说吧。”
2月20日,正月十一,一场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覆盖了整个中原地区,让急于相见的刘锁、刘新向急得在家里走来走去。
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前进的人类永远无法避免要遇到的问题,未来难以捉摸,过去已成定局,但对于更远的过去却吸引了无数人的探索,这不仅仅是出于人类原始的好奇心,更是源于血脉的传承,源于姓氏的羁绊。
2月23日,正月十四,我问有何新进展?
刘新向说:“正在核对。”
我回复:“希望你们能够核对成功。”
刘新向说:“据我们考证,有尸骨传说故事的不是只有这一家,应该是黄河发大水迁入的这一家,我们己经约好等路好走了,由双方家族再对接,要是对接成功,我会把这好消息告诉你的。”
看到信息后,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他们能够成功对接,早日实现500年的一个夙愿,愿上苍保佑一切如愿。
2月28日,正月十九。我在微信上问刘新向有没有新的进展。
刘新向:“山东那边还在考对。前几天他们说走访老年人,这几天也没给回话,我正想让田老师给看一下他们那的家谱和血脉图。”
我:“家谱中的内容,我也看不太明白。”
刘新向:“前几天我和他们联系,他就是说查资料,让等几天再去东明,我也没好意思天天问,那我再等几天吧。”
我:“那就耐心等待吧。”
刘新向:“他们口口相传,祖上有一个因人命官司外逃的,和我们的传说一样,他说他们这几百年也一直在找,就是他们家谱中的‘二门’那一支。”
我:“你们所说的两点基本上都对上了,应该是对的,那不就对上号了吗?你问没问他们最早的村名叫啥?”
刘新向:“他们好像刚从山西迁来时住西竹林,后来在1855年黄河改道才迁到现在的找营村。”
我:“他们现在在干啥事儿?需要我帮忙吗?”
刘新向:“他们确实是修谱。初十那天跟你告别以后,我们就去了找营村,现在叫长兴集十号村台,他们正开会研究修家谱的事情,我们互相把对方家谱中的序给拍了照,一直谈到天黑我们才回来。”
我:“现在可以这样说,基本上算是找到了!”
刘新向:“现在我们认为应该是找对了。”
我:“祝贺你们!”
刘新向:“正好他们有一支失传,就是他们的家谱中的‘二门’那一支。”
我:“你们寻找宗亲有多少年了?”
刘新向:“不知道。最少也有两百年以上的时间,我爷爷说他爷爷的时候都在找。”
我:“你们河南那边,现在有多少世多少人?”
刘新向:“我们从东明县迁来一世祖算起,已经十九世了,有2000人左右。”
家谱
2月29日,正月二十上午9点多,我单位一同事来电说,他的朋友刘庆勇、刘胜创找我,是关于刘氏宗亲寻祖的事儿,想与我聊聊。我爽快地把电话给了他。
晚上9点多,刘胜创给我来电,我们打了快一个小时的电话,聊了他们寻找的结果:100%的确认夏邑这一支就是他们这一家人了。他给我讲述了近段时间以来,他们续修家谱的事儿。
他说:“年前,我们家族长们在一起提议,年后初五开始续修家谱。从年前开始,我就做着续修家谱的准备整理工作,把这么多年以来的没有续修上的,查老家谱,新增加的都准备增加上。”
2月14日,正月初五,刘庆勇、刘胜创他们开始续修家谱。
正月初六,联系河南省民权县低庄和邹庄的宗亲。
正月初七,刘庆勇、刘胜创一行8人去了河南省民权县,找以前来联系过的还没有续修上家谱的宗亲。
正月初八,河南省长垣市雷店宗亲过来8个人。
正月初九,刘庆勇、刘胜创一行6人去崔庄、王店、甘堂、李庙等地。
无巧不成书。正月初十那天下着雨,刘庆勇、刘胜创正在校对续修家谱,夏邑的刘锁、刘新向来人,在打听刘姓,刘庆勇接待了他们,一直聊到傍晚才结束。刘庆勇执意挽留他们住下,刘锁、刘新向说有事非要走。在聊天中得知,双方的家谱前言很相似,老坟的位置在刘乡北边、小园南边,双方都予以确认。但是,关于背遗骨这件事,刘锁、刘新向也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上一辈老年人并没有这个说法,口传下来的祖坟里面有石碑石谱,这一点倒是与刘庆勇族谱里的说法一致。后来大炼钢铁时期,石碑被拉去烧成石灰了。包括他们出走的原因,先祖出事后,一些亲人受到牵连,把土地变卖,都出走了,始终联系不上,这一点,基本上和老年人的说法一致。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出走的这一支人,有说在菏泽牡丹区这一带,具体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
夏邑刘锁、刘新向宗亲找过来以后,刘庆勇、刘胜创就开始查找老族谱上面是否有记载,又去联系各村。现在刘氏这个家族有3000多口人,分布在30多个村庄,老族谱被安徽省亳州的刘姓人拿走没有归还,现在的族谱是后来又修订的。刘庆勇、刘胜创去河南长垣、民权、濮阳等地方向老年人询问这件事,前后跑了几天,证据越来越对上号了,一一证实了这些事儿。刘锁、刘新向初十来的,正月十一,刘庆勇、刘胜创去了民权县,本来计划再去夏邑县的,因为一场大雪,随即赶回来了,也没有去成。
对接
刘庆勇的先祖最早落户的村庄,家谱上记载是刘砦,老人传的是大刘砦,刘砦在老竹林村西北,林场西边。前四世祖先都住在刘砦村,五世祖有一部分人从刘砦搬到竹林定居,现在这一支脉是1855年因黄河改道,从刘砦搬到找营村的,分散开了。据老人说,搬迁前,刘砦有刘、张两姓,共3000多口人的村庄。
正月十一,刘庆勇一行7人第二次去河南民权县,其中有一人参与了1980年、1987年、2013年的三次修家谱,夏邑县这支走的原因他们知道,一直在寻找,一直没找到,那天原打算从民权去商丘,因下雪未能成行,从民权直接回来了。
正月十二,在刚下过雪,路还不好走的情况下,有宗亲带队,刘庆勇几个人去了竹林、刘乡、崔庄,寻找夏邑这支的证据和传说。
正月十三,大家再一次在一起商讨这些事情,刘庆勇也一直在老族谱上找有效的线索,对照新家谱上有没有错的地方。这期间,一直和夏邑刘锁、刘新向在联系,这边有进展,都是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经多方查找走访家族老人,刘锁、刘新向提供的信息,刘庆勇、刘胜创这边一一证实,这期间整个宗族的人都在想办法联系失散的宗亲。
正月十五,刘庆勇、刘胜创再一次聚在一起商讨寻亲这些事。
2月26日,正月十七,长垣五个村庄的宗亲带本子,十几个人过来,一共40多人在一起商讨这个事情,后一至认为是这边走失的人,因老家谱被亳州的宗亲拿走,现无法确定是几世走的,现在打算双方见面一起商讨,刘庆勇、刘胜创这边也在规整统计这次家谱的名单。
现在可以说,基本上100%对上了,同意认领刘锁、刘新向回归。
刘庆勇知道,自己的宗亲还有一些没有联系上的,有在贵州的,南乡那一带还有很多没联系上的,还有菏泽的、开封的、杞县的,一直在努力寻找,也希望这些宗亲看到后,能够回归家园。
正月廿三下午1点43分,刘庆勇留言:“我们两边族人准备在5日见见面。他们过来,说今天晚上他们商量一下,确定什么时候来,现在还没给信息呢。等确定了时间,我也给我们这边的族人说一下,到时候都在一起聊聊。”
3月5日,正月廿五,河南夏邑、宁陵、虞城、淮阳四个县来了20多人,山东这边30多人,都是各个家族的领头人。双方见面谈了一天,基本上认可这是刘氏宗亲。只是在入谱后是几世人上有些分歧,双方没有谈妥,年代误差太大。最后,回去商议后再谈。
3月8日,刘锁、刘新向等人去虞城谈了一天,商议与山东接洽事宜。
3月11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下午,刘庆勇、刘胜创与我见面,聊到晚上12点。
3月15日,刘新向来电与我沟通后,我又与刘庆勇、刘胜创沟通,正式确认认亲,商谈见面。
我把写好的初稿分别发给他两个,让他们提提意见。
3月16日,刘锁、刘新向看后回话:“等文章发表后,情况稳定了,刘庆勇、刘胜创他们把家庙修好了,我们再正式举行归宗认祖仪式。”刘庆勇、刘胜创回话:“没意见。”
“我谨代表我和我的家族,向您表达深深的感谢和敬意。是您的无私奉献和热心帮助,让我们在500年的寻根之旅中找到了归宿,也圆了我们世世代代的家族梦想……”3月23日,刘新向等刘氏族人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
归来
刘新向说,他们终于找到了根,也圆了祖辈传下来的梦想。
500多年的离别与牵挂,5个多世纪的血脉相承,如今在这里交融交汇。
刘氏家族一直以来都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希望能够找到自家的宗亲,以告慰先人的在天之灵。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间的流逝,寻根之路异常艰难。直到最近,在我的帮助下,刘家成员才终于找到了宗亲的线索。在寻根的过程中,刘家成员们不仅找到了自家的宗亲,还结识了许多同宗同族的亲人。他们共同分享了家族的历史和传承,感受到了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这一过程中,我也始终陪伴在刘家成员们的身边,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感人的历程。
东明,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迎来了一场感人的寻根之旅。对于刘家来说,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圆了祖上遗愿,更是让他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刘锁、刘新向表示,将倍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家族情感,将家族的传统和文化传承下去,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刘氏家族的成员们,在历经500多年的漫长岁月后,终于找到了自家的宗亲,完成了祖上宗亲的遗愿。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寻根之旅或许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艰难。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族情感始终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珍惜这份情感,传承家族的文化和精神,共同为家族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
刘氏家族的寻根之旅,不仅是一段感人至深的家族传奇,更是一段传承家族文化和精神的历史见证。愿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去追寻自己的家族根源,传承家族的传统和文化,让家族的情感永远流传下去。
刘庆勇:“以后要常回来看看,不要忘了东明就是你们的家。”
刘新向:“肯定要回来的,你们也一样,到了夏邑就到家了。”
…………
相见便是熟稔。幸运的是,感谢时光对这场不期而遇的旅行给予的厚待,老一辈记忆中的故乡,并未因为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而改变太多,依稀还是记忆中的样子。
通过这次寻根之旅,我深感学力不足,提高学术水平,成为当务之急。感知自己不仅要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得善于运用文字去探寻人性的真谛。在得知刘家的寻根愿望后,我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最终帮助刘家找到了宗亲的所在地。对于这次寻根之旅的成功,离不开我的无私奉献和付出。我的帮助,不仅让刘家圆了寻根梦,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家族情感的力量。对此,我将继续关注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更多的家族寻根之旅提供支持和帮助。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家风正,民风淳,国风清,才能社会和谐,国富民强。“家家修家谱,人人学家训,个个传家风”,让“家国”文化深入人心,携手有识之士,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竭尽绵薄之力!
异乡、故乡,寻根、乡愁……一次普通的寻根问祖,就是一段寻找家族之梦的过程。故乡,是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
田丰,山东东明人。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写作学会会员,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建》《筑梦黄河滩》、报告文学集《慧眼妙笔写春秋》《乡村振兴路上的追梦人》、散文集《风花雪月的故事》《东明地名文化》、散文诗集《贝壳的思念》,主编《散文十二家·东明专辑》等著作。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