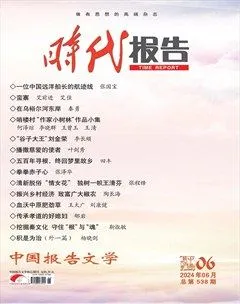终归田园
2024-08-15斯詠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问道,终归诗酒田园。这是南怀瑾先生对人生的参悟,道出了人生最美好的归宿。
回归诗酒田园,大概是所有中国人内心一直怀有的梦想。然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又是现代人“人往高处走”的现代化目标,几乎没有哪个村庄能够逃离城市化的洗礼。我们曾经以为城市的光鲜亮丽必定是乡村的未来,甚至“美丽乡村”也是由城里人的田园梦和乡愁所定义的。不知道是因为出身农家,还是长期从事“三农”工作,我虽然也享受着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成果,但对这种乡村的丢失,还是感到一种隐隐的担忧。
就这样,我沉溺在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中:现代社会如何回归“诗酒田园?”当我问道哨楼村后,心里有了答案。
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平坦直达的大路,但丁在《神曲》中设想的人生“三界”,其实就是关于生命的宿命提醒,预示着做任何事情,都可能经历多重考验。比如那天,2024年1月21日,我以“五新”而非“五星”的姿态——一名驾驶新手、写作新人,探求新知,行走在一条陌生的乡村“新路”,去完成一项富有巨大挑战的新的书写时,就有一种强烈的“炼狱”感受。但还是要出发,不是身不由己,而是心甘情愿,世间的许多事,都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去判断。我第一次独自驾车翻过丘山、穿越风雨、绕行小道,到了仁寿县方家镇,参加我向往的哨楼村“作家小树林”热身活动。
诗酒田园的概念,是在我走进哨楼村,领略了这里的田园风光,参观了村史馆藏,聆听了村民故事,感受乡村振兴的希望,洞见古今后形成的,只是,我在“诗酒田园”的前面加了一个定语“现代”。是的,哨楼村就是我心目中的现代“诗酒田园”。
终归诗酒田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终”——终于。
是的,终于。它代表着历经岁月坎坷、阅尽世间铅华后的最终选择,在历史光影和现实境遇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
寻脉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诗酒田园本就是中国文人追求的理想生存目标和精神原乡。舜帝在历山精耕细作,并推广到普天之下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来源。《诗经》里劳动人民的吟哦倾诉,成为中国田园诗意流淌的发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韩愈“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苏东坡“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曾国藩“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
盛唐诗歌、锦绣宋词、大家散文、名臣家训,字里行间虽意象缤纷,内核本质却始终如一。简洁明朗的东方审美语境,先贤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与哲思,无不折射出中国人、特别是文人的理性世界和心灵家园。而这些,在彼时彼人,却只能梦想着“桃花源记”,吟唱“归去来兮”,有着难以言说的伤痛与无奈。
长久徘徊于这样的“终于”里,情绪难免受影响,对“彼时彼人”,总有着深深的遗憾与怜惜。“终归诗酒田园”,总是伤痛与无奈吗?会不会有一种更积极的向往与格局?
哨楼村告诉我,不仅有,而且是精神原乡的重要标志。
不信,先看哨楼村4个古村落的名字:菊塆、晓止、哨楼、长富,这地名里隐藏的地域历史文化密码,理想与现实、诗意与忧患,交织得那么紧,岂是一个“伤痛与无奈”所能解释的。看这里的区位,无论天府腹地,还是黑龙滩、天府机场、仁寿县城“金三角”黄金交汇处,都配得上“天府”的盛名。再看这里的历史人文,无论是两千载文明足迹和海量历史文存,还是清代文人为本村题写对联“廉泉让水地,文里武乡风”,都可窥见这里村官廉谦、民风淳朴,村人文武双全,乡邻和睦相处……
这样的“诗酒田园”,既有乡村的质朴,又有诗意的栖息,既有现实的生动,又有历史的纵深,求之而不得,好个终归。
现实的“桃花源”,就在哨楼村。在我开着车,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沿着一条不宽不窄、蜿蜒的水泥村道盘山而上,又翻山而下的时候,就乍然出现。感觉不是现实,是马致远的诗,“小桥,流水,人家”。只是没有了诗中的幽暗部分,没有“枯藤,老树,昏鸦”,也没有“古道,西风,瘦马”。一切都在现实当中,在眼前。道路井然,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油菜青青,农舍安静,良田层叠,桑竹摇曳,河流逶迤,山色入塘。不仅有江南的柔美,还多了沟通天地的从容与大气。农家小院书声琅琅,留存着深厚悠长的文脉,亦有着不一样的灵气与通透。狮子坳、哨楼山、敬恭里、菊药湾、月亮坝、凉水井、解放路、晓止山……一块块标牌掠过车窗,仿佛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从头说起。
狮子坳形似雄狮,蹲踞作势,是进村的必经隘口,怪不得当年的哨楼要设置在坳头。据说是在清文宗咸丰年间,匪患猖獗,村民募捐建哨楼于山上,练民团,保家园,哨楼村因此得名且沿用至今。哨楼村的真正长治久安,让哨楼遁入历史,还是在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走过这里之后。哨楼村人感恩记情,在此条石护坎、沥青铺设,修了解放路。行驶在解放路上,心中尽是满满的敬仰与感动。那曾经奋战的生命终会渐渐故去,而历史的印迹却难以磨灭,还将越来越深刻,因为红色基因已写进你的我的、满坡满地、遍山遍水的诗行。
一口口湖塘星罗棋布,那水如同神奇而深情的画笔,在大地上画下了生命与希望的脉络;一畦畦庄稼整齐列阵,积善之地、物产丰饶,是对哨楼村最长情的告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就是答案。
水塘之边的一黛瓦赤檐、白墙明窗建筑,以“哨楼村村史馆”的名义,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一一收藏。这是哨楼村人自己策划、设计、历时三年建成的村级历史纪念馆,馆内外总面积6000余平方米,序厅、哨楼春秋、红色哨楼、乡土哨楼、忠孝哨楼、展望哨楼,6个展区一一展开。实物呈现、史料展陈、文字描述、重要场景还原、重要人物访谈,深度还原哨楼村历史。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诗意的圣地,承载耕耘与生长的美好。哨楼人心里诗意的圣地,或许就是这矗立在大地上的村史馆。它如同哨楼人灵魂的皈依,收藏了太多川流不息。绵延千里的故事,涌动厚土之下沉默不语生命的气息,使无数跋山涉水不曾放弃的归心终于泊岸,使万般千回百转未曾消失的情意慢慢浮现。它与天空相映,印记星辰的轨迹,迎送迁徙的鸟群;它与大地相生,滋养一座村庄的万物生命,永远给予一方柔软与安宁。将诗意留住,回到生命的源地。在哨楼村村史馆,行走,聆听,凝视,触摸,对话,感悟,仿佛穿过诗意的时光隧道,向我们款款走来,我们以为是热情的主人迎接远方的客人,留神一看,才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在欣赏诗酒田园的时候,自己也成了风景……
跟随主人的讲解,仰望历史的天空,跨越时间的长河,星辰闪耀,星光如炬,随便一个注目,都令人动容。李春旺,号阳俶,太阳开始之意,明末任河南按察副使,虽身处乱世却正直敢谏,以身殉国。后人为纪念他,将家宅后山取名为“晓止山”,晓止,乃太阳停止之意。我想,又何尝不是“知止”之意呢?生逢乱世的辜学照常叹“文官不要钱,武官不要命,何以天下不太平”,身为昭武都尉将军的辜有闻异常清苦,卒于所任竟贫无以为丧。曾任成都市长的袁郎如内外兼修,善书画、工于诗、精于琴,教导百姓开凿堰渠,百姓拥称“袁公堰”。
哨楼村斯地,斯人,斯文,斯武,文化浸淫,生生不息。
最好的诗歌来自于心灵,最美的风景永远是人。这是一片承载历史与现实、平凡与神奇的土地;这是一方写满光荣与梦想的热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无不让你感受到强烈的振兴律动。
农村乡野有一种生命力,平时似乎销声匿迹,春风一吹,须臾间就会活跃了起来。对哨楼村来说,最有象征意义的是,离乡的人儿又渐渐回来了。他们中有青年也有老年,有党员干部也有寻常百姓,有退休高干也有商界名流。他们从城市回到乡村,进入山间田野,从春夏到秋冬,昼夜不止,以跨界之识,行振兴之举。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他们归乡时的心情,他们可能也说不出诗酒田园这样文绉绉的句子。但我相信,他们是带着田园一样的心境,诗酒一样的情愫回来的。这是植根于人性深处本我存在。曾经污浊干涸,而今清澈流淌的方曲河,如同闪亮的缎带,带来生命的给养,是献给归乡人最好的礼物。因为“清澈”,可以明鉴,而成暖流,这股热流汇合了家乡所有的爱与包容。
村党总支书记张国君,黝黑的面庞,壮实的身材,一副大度宽厚、朴实憨厚的模样,但大大的黑框眼镜,也挡不住他眼里的光芒。2016年,他作为大学生村官走马上任,村委的家底只有一间平房和2000元现金。村民纷纷背井离乡,不外乎想多挣几个养家的钱。留下的人七老八少,不知道谁起了个“386199”的绰号。哨楼村和各地许多村庄一样,成了“空心村”,人空,心也空了,弥漫着空洞的疼。
张国君从上任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这片土地。守土有责,他深知,实施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核心,人才振兴是支撑,文化振兴是灵魂。于是,他和村委班子及众多乡贤带领全村人,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筹集资金,又从仁寿农商银行贷款2000多万元,整合资源,精打细算,专款专用,培优种养产业,大兴水利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立村史纪念馆,引进生态燃料项目,吸引村民返乡创业。
张国君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空了的心找回来。守住田园,就守住了乡村的根本;有了根本,“终归”才有依托。
十年树木,也树村。拿哨楼村人的话说,这些年乡村从脱贫到振兴的变化,可以概括为“路上山,水上山,荒山变金山”。
不仅仅是用事实说话,还有数据。张国君说,他们村全村1901户5629人,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7万元;除了是天府粮仓外,村里还发展了蔬菜、藤椒、肉牛、养鱼等产业,培育新型农场主23家。燃气覆盖率48%,自来水安装覆盖率98%,网络覆盖100%,卫生厕所覆盖率95%。现代农业产业初具规模,农旅融合已然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进家入户,生态文明全面提升;诗书继世、耕读传家,既是村民家风,也是村约村风。
“四川省乡村振兴省级示范村”“眉山市村级集体经济增量收益十佳村”“四川省乡史村史和社区博物馆建设示范项目”……
仍是田园,或者说终归田园,但已不是那个田园。
村党总支副书记张凯,是一位80后年轻人。他既是被“终归”召唤回来的返乡农民工,也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他头脑精明,敢拼敢干,当年的外出是迫于无奈,选择了销售煤炭、经营超市,挖到第一桶金,是靠吃得苦中苦;而毅然决然选择返乡创业,则是乡村这个根的召唤与血脉里“终归”基因的苏醒。
返乡后再次创业,张凯再次受挫——生态养殖的15000只鸭,突然遭遇瘟疫的袭击,欠下高额债务。但是,有了那个骨子里的“终归”,他没有再选择出去。他抹干眼泪,在获得仁寿农商行贷款支持后,转而发展藤椒。有文化,肯钻研,技术过硬,适销对路,很快成为了当地的藤椒种植专家,走上了致富之路。2016年,张国君举荐张凯入职村班子,主要任务就是指导带动更多的村民种植藤椒。一个“终归”,带动了无数个“终归”。哨楼村所在的方家镇,目前种植藤椒2万余亩,亩产值6000多元,仅此一项为村民每亩增收2000多元。
仍是那个田园,但不在文人诗文里,归来在哨楼村。
“田园”到底有何意?万物生长、生生不息,安定富足、宁静祥和。《论语》中有一段孔子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个人抱负的精彩描述。孔子和其他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皙在旁边悠闲地鼓瑟。轮到曾皙时,他铿然拢瑟,坦然而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季羡林先生认为,孔子与曾皙所向往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国家自主、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有真善美的人生。近代学者辜鸿鸣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真正的中国人,有这样一种气质,从容、镇定、历经磨炼后成熟,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是灵性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何以如此?答案只能是来自中华文明和中国精神。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村庄亦成为新市民家庭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既为其完全融入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为其可能遭遇的进城失败提供退路。我想,正是日益振兴的“田园”,给了哨楼人温文尔雅的心境与宁静祥和的生活。
一场文事,一阙风雅;一程问道,一脉文化。
责任编辑/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