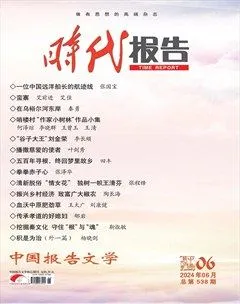在乌裕尔河东岸
2024-08-15秦勇
我的家乡小河东村因坐落在乌裕尔河东岸而得名。村子东侧有一片耕地,大约2700多亩,因在村子东侧,村民们都习惯地称之为“东大地”,又因为这片地是盐碱地,又叫它“碱巴拉地”。生产队时期,这片地是苗长草也长,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村民们一天天吃不饱。土地承包到户后,这片地只见苗长草不见了,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村民们再也不愁饿肚子了。又经过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这片地已由旱田变成了水田,粮食亩产超千斤,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回想起东大地的变化让我记忆犹新。
生产队时期“上纲要”望而兴叹
小河东村过去叫小河东大队,下边有4个生产小队,东大地被分成4块,每个生产小队耕种一块,每块地大约有700亩左右。我们家是在第一生产小队。
1975年我高中毕业,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到东大地种玉米。出发前,生产队长在队部给社员们开个小会,算是动员会。队部屋里北墙上也有一个红纸白字的标语,上面写着“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队长手指着那个标语说:“今天我们到东大地种玉米,一定打好这一仗,争取今年粮食产量‘上纲要’。”那个年代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粮食产量要“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上纲要”粮食亩产要达到400斤,“过黄河”粮食亩产要达到500斤,“跨长江”粮食亩产要达到800斤。这还是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根据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产量三个发展性指标。
东大地是盐碱地,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为了实现“上纲要”的目标,1954年冬天,队里安排20多名男劳力,到河套刨河泥土,还出动4台马车、4台牛车往地里运。两个多月时间把东大地铺上一层河泥土,有一扁指多厚。所以队长胸有成竹地说:“今年东大地‘上纲要’是有把握的。”
队长讲完要求后,让大家自己找组,一组4个人,有刨坑的,点籽的,滤粪的,埋坑的。刨坑和埋坑是最累的活,基本上都是男劳动力干,女劳力和体弱的老年人点籽、滤粪。因为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对农活也不太熟悉,队长让我点籽。
到了地里太阳已经很高了,队长选一伙打头的种第一条垄,大家依次跟着。队长边干边在后边检查质量。700米长的垄,种了两个来回就开始歇气了。歇气时大家有的围在一起唠嗑,有的坐在垄台上抽烟,有的找一块平地两个人下“五道”,还有的躺在路旁枕着锄杠睡着了。也就一袋烟工夫,就听队长在喊:“起来,起来,干活了,再干了两个来回就收工了。”出工时大家都围成一个团,仨一群,俩一伙,一边走一边说笑,远看像一条乌龟在通往东大地的路上慢慢地爬行着。回家可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年轻人连跑带颠、你追我赶往家奔,就像放飞的鸟。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出工慢慢腾腾,干活磨磨蹭蹭,到点就收工,回家快如风”。300多亩地种了10多天才种完。
十几天小苗就出土了,刚出土时嫩嫩的、绿绿的非常可爱。可恨的是小草围着小苗也都从土里钻了出来。小苗长出三四片叶时,队长领着男女劳力就开始铲地了。到了地里先给大家开个小会,总的要求是松土、除草、保苗。还重点强调一下,一定要斩草除根。和种地一样,先安排一个打头的,打头的铲第一条垄,其余人你一垄我一垄地跟着铲。几十把锄头在地里上上下下、起起落落,锄头板紧挨着小苗在土里走,发出沙沙啦啦的响声,把板结的土翻活,一棵棵小草都应声倒下。可有些人偷懒不使劲,锄头举起来轻轻地落到地上,锄头板在土地上边跑,只是把小草搂倒了却没有除根。队长就把他们都叫回来返工,有的人不但没把草除掉,还把苗给铲掉了。队长气得从兜里掏出小本子记上了,还大声地说:“如果再有铲掉苗的,每三棵苗扣一个工分。”其实队长是在吓唬大家,为了让大家好好铲地。有时草和苗挨得很近,铲草时极容易把苗给铲掉了。这块地铲了两遍趟了一遍,草依然满地都是,苗长草也长,草比苗长得快,把小苗欺负得瘦瘦的、黄黄的。那一年这块地粮食亩产不到300斤。
第二年,这块地种的还是玉米,由于地洼春雨又下得勤,整个地被水泡上了,只铲了一遍,满地长的都是水稗子草,基本上看不到苗了,到秋是颗粒无收。
多年来,东大地粮食亩产始终在300斤左右徘徊。
土地承包到户
“过黄河”轻而易举
1981年,我们村融入了全国农村的改革大潮,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东大地按人口分到各户。我们第一生产队一共三十多户人家,40多名劳动力,120多口人。分地时是先抓阄把每一户都排出顺序来,然后按着顺序号一口人一条垄往下分,分完了再把顺序号倒过来(原来是头号变成尾号)接着分,直到分完为止。因为一片地也是有好有孬,大家认为这样分合理,就是零散不利于耕种。完整的一片地,像生产队杀年猪似的割成一条一块分到了各户。分完的地,地头都立一块带有户主名字的标牌,牌子上还标明每户几条垄,无论什么时候到地里看到牌子就能找到自己家的地了。
生产队分田到户那年,我和二弟都成了家,我们姊妹7个,我是老大。那年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后来考上了依安师范,爱人和两个孩子都是农村户口,享受着村民的待遇。记得我们家三口人分了18亩,二弟家4口人分了20多亩,父亲家7口人分了40多亩。各户分的地都不在一起,每户都有五六块地。地分到户后,有些农户为了耕种方便,互相商量自己调换,把分散的地块变成了一块地。
生产队牲畜和农具也是按着每户人口和劳动力的多少采取抓阄的方式分到各家各户的。为了能分到好的大牲畜,我和二弟弟还有父亲三家合到一起抓的阄,我们很幸运,分到了生产队最好的灰骒马和一匹枣红马,还分到了一台车、一副犁杖、一副耧耙等农具。
分到每一户的牲畜和农具都是有限的,种地时只能互相借用或者合伙耕种。有的户不愿意和人家合伙,利用自家分到的农具和牲畜各自为战。种地时就出现了一头牛与一匹马拉一副犁杖的场面,也能看到一匹马与一头驴拉着一台车往地里送粪的情景。有的人家只分到一头牛,就用一头牛拉着一副犁杖种地。
我们三家合到一起分到的牲畜和农具够多的了。但种地也是不够用的,父亲就和后院邻居老李家商量一起合伙种地。
当年我们家养了两头猪,父亲家也养了两头猪和十几只鸡,再加上分的牲畜一年积攒了好多粪。父亲把所有的粪都拉到了地里,连扒炕的小灰也都用上了,父亲说这是天然的钾肥,种植蔬菜还不生虫子。
生产队种地不管土地墒情好不好,一般都是干子下地。我们家种玉米,是把玉米种子催出芽再坐水种,这样种能抗旱保苗,能提高粮食产量。记得那年种完地后,一春天没怎么下雨,还经常刮大风导致干旱加剧。父亲担心躺在地里的种子出不了土就会夭折了,每天都跑到地里刨开几埯玉米,看看芽子被掉死没有。没几天小苗像新生的笋尖,顽强地钻出地面。父亲回家很高兴地对我们说,小苗都出来了。
铲地时父亲领着弟弟和妹妹起早贪晚,两头不见太阳,中午有时还带着饭,一天天在地里忙活着。一般人家都是两铲两趟,我们家的地是三铲三趟。地侍弄得干干净净,到地里想找一根草都很费劲。由于铲趟及时,再加上那一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父亲是170cm的个头,走进玉米地都见不到影子,到了黄豆地,黄豆都遛腰高,来到谷子地,谷穗儿快要搭肩了。有一次,父亲来到地里,顺手抓一把谷穗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很兴奋地说:“这地里的庄稼都是孩子啊!虽然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也是有感情的,只要你懂得它的心思,给它浇水、施肥、松土、除草,它就会茁壮成长,就会奉献给你沉甸甸的果实啊!”
秋收时,父亲把房前的小园收拾得干干净净,小园东侧堆的是谷垛,快有房子高了,小园南侧堆的是黄豆,有一人多高,西侧堆的是玉米棒子,一堆挨着一堆,为了便于通风每个玉米堆上还插几棵玉米杆子,防止发霉。整个小园就是临时场院,里边摆得满满登登的。
一个月后,风把潮湿的玉米棒子吹干了,父亲用手揉下几粒,还放到嘴里咬了一咬,觉得可以脱粒了。就把房前院子平整平整,用石磙压了又压,院子就成了打谷场了。村里有4台玉米脱粒机,每个生产队一台,脱粒机当时没有分到户,还是放到队部的场院里,村民们可以把收获的玉米棒子拉到生产队场院去脱粒,也可以把脱粒机拉到家脱粒。父亲借一个脱粒机,先把玉米脱粒了。然后把黄豆平铺在院子里,两匹马拉着两个石头滚子不停地碾压。打完黄豆接着打谷子,打谷子是把谷子铺成圈,谷穗那头在圈的里边,马拉石头滚子一圈一圈地压,压了几圈就用木叉翻一翻,接着再压,直到穗上没有粒了为止。十几天时间,场就打完了。打出来的粮食先交公粮,再交村里的提留,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了。
父亲掐指算了算,玉米亩产达到700斤,黄豆亩产400多斤,谷子亩产超过了500斤。这个产量在生产队时期是从来没有过的。土地分到户后,凡是种高产作物的,粮食产量“过黄河”是很平常的事了。父亲说:“庄稼是枝花,全靠粪当家。来年再多积攒点儿粪肥,上到地里产量还能高。”
生产队时期,我们家分粮食是有数的,为了防止鼠盗,都用袋子装上再放到屋子里。现在是屋子放不下了,就放到没装过粮的仓房里,有一部分还放到了房顶上。第二年开春,父亲在自家的房西找一块空地,专门盖一个粮仓。为了防止老鼠盗洞,粮仓底部是用破砖头砌的。粮仓内又用土坯隔成4个小格,每个格里装一个品种,仓子盖完后,父亲又把粮食都搬运到新盖的仓房里。父亲还和我们说:“这就是咱们家的储备粮,以后再也不愁没粮食吃了。”
土地承包几年时间,我们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sGC0RsVJfDAPj+Qbpn9TrlOyPBoZvRG0dmLkZbIUB44=化,不愁吃不愁穿,手上也有了余钱。大妹风光地出嫁了,三弟也成家娶了媳妇,四弟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县城找了对象。又过几年,二妹嫁给本村的一个小伙,是我们家多年的老邻居。小妹在县城找了对象。我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全家都搬到了县城。
凡是在农村成家的,父亲都把承包地按生产队分的数额又分给了弟弟妹妹,地随人走。一家人各奔东西,最后,老屋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了,老两口谁家也不去,就自己单过。父亲又买了一头驴,拉着一台小车,父亲赶着,母亲坐在车上,天天到东大地里侍弄自己家那点儿承包田,老两口的生活过得很滋润。
不幸的是2001年父亲突然病故,扔下了母亲。母亲还是谁家也不去,坚持独挺这个老房子,幸亏二妹和三弟都在村里居住,平时能照看着母亲。父亲留下的承包地,母亲年岁大了不能耕种就交给了三弟。
土地统一耕种
“跨长江”势不可挡
土地承包后,地侍弄得再好,粮食产量再高,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大富大贵,因为每家每户分的地是有限的,遇见丰水年和枯水年,粮食产量就会直线下降,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兴修水利,实行土地流转统一耕种。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村里决定,把乌裕尔河的水引到东大地,让东大地旱田变成水田。修水渠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在开工前,村里召开了村民代表会,征求村民意见,大家都举手赞成。乌裕尔河离东大地有2000多米的距离,雇用挖掘机村里没有钱,只能靠人工干。村干部请水利专家到现场勘察,进行科学规划设计,制定了施工方案。村干部把需要修的工程一段一段地分到了每个农户,要求在半年内完成。村民们利用农闲季节,有时间就去挖渠,结果不到半年时间,乌裕尔河的水就从“半拉泡子”穿过一片茂密的草原乖乖地流进了东大地。一条笔直的渠,像一条细长的银带,把乌裕尔河和东大地连接起来,村民们再也不为枯水年和丰水年而发愁了。
土地分到各户时,一家都有几块地,零散不好耕种,再加上分的土地少,劳动力多的人家侍弄地的时间不到4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闲着。面对这个现实,村里鼓励村民们进行土地流转,采取互换、转让、租赁、委托等多种形式向种田能手集中。村里还成立水稻合作社,村民们可以把承包地转交给合作社耕种,自己出去打工。土地转出去有收入,到外面打工又能挣到一笔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村民们都积极响应,洗脚出田纷纷到城市工厂里去谋职。
大侄子秦文通是村里的种田能手,脑子里也盘算了,是出去打工还是守家种地呢?如果出去打工,自己家的地就得转包给别人耕种,如果选择种地,那就把东大地和自己家挨着的地转包过来实行规模经营。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把致富的定盘星定在土地上。拿定主意后,说干就干,他跑东家串西家和人家商量,把土地转租给他。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的努力,村里有14户村民把承包地转租给了他。最高的一亩地租金是460元,最少一亩地300元,共转租了130亩,再加上自己家的承包田一共144亩。
侄子筹资20万多元,先后购买了一台大马力轮式拖拉机、一台耕整机、一台插秧机、一台收割机、一台打浆机、一台旋耕机等机械设备。告别了过去种地使用弯钩犁、锄头、镰刀等农具的时代。侄子要用新技术、大机械在东大地这片土地上开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他和妻子说:“咱们俩一定好好经营这片土地,这就是咱们家的希望啊!”
承租这片土地后,小两口决定把旱田改成水田,计划种100亩水稻。先平整了土地,再修渠筑堤,根据土地的平整度规划水田池子的大小,随高就高,大小不一。由于是盐碱地,对土壤盐碱度进行处理,防止土壤盐碱化对水稻生长的不利影响。
在承包地里选择一块地势较高、平坦、含盐碱低、浸水适中的地块育苗。弄了几栋育苗大棚,又到乌裕尔河挖一些草炭土(河泥土)做苗床土。挑选适合东北生长的米质好的“稻花香”子种育苗。育苗期间采取施肥、灌溉、除草、防病虫害等管理措施。一个月后,小苗就长出了三个叶,可以往稻田地里移栽了。
侄媳妇开着三轮电动车往地里运秧苗,还雇用两个人帮着装卸。侄子开着水稻插秧机一个池子一个池子插秧。插秧机在前面跑,后面就留下一棵棵绿油油的秧苗,远看像一条条绿色的琴弦。插秧机如同一台乐器,在这绿色的田野上演奏着丰收序曲。十几天时间,100多亩水田就插完了秧。
插完秧后,开始田间管理。灌水以不淹没秧苗心叶为准,以水护苗,以水增温。进入到分蘖期,用浅水促蘖。水稻不同生长阶段所需要的养分不同,根据不同时期选择使用氮、磷、钾等元素含量高的化肥。还定期检测土壤的肥力和酸碱度,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针对性的施肥。地里有草就用稻田专用除草剂进行除草,有的杂草除不静,就动用人工薅。侄子侍弄水稻就像抚养自己家的孩子一样精心。由于按着水稻栽培技术进行管理,水稻长势喜人。
晚秋的一天上午,我回到家乡,侄子把我领到他的承包田里。看到一池子水稻,随着秋风翻滚着金色的稻浪,好似一幅幅徐徐展开的美丽画卷。我的两只眼睛被这丰收的景象给吸引住了,怎么看也看不够啊!侄子顺手掐一株稻穗放到手上,黄澄澄的,沉甸甸的,粒粒饱满。侄子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和我说:“今年的水稻亩产能突破1000斤,这片水稻至少能打15万斤啊!”他又扒开一粒放到嘴里咬了咬,听到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和我说:“能收割了!”
水稻丰收了,家里的小粮仓是装不下的,侄子家房前小园有篮球场地那么大,水稻收割前就把小园里种的各种蔬菜全部拔掉,用推土机把垄铲平,再用石磙压一压,上面铺一层塑料布,就成了一个露天的大粮仓。
侄子开着水稻收割机,起早贪黑地收割,仅用5天时间,就把水稻收到了家,一车车黄澄澄的稻子堆放在院子里,像一座座小金山似的。
没几天,有人就找上门来收购,满院稻子足足装了两大挂车,卖了14万多元。侄子一次还清了欠下的债务,剩下的钱又添置了一些新机械,准备来年再多租一些土地,要大干一场。
东大地实行规模经营后,由过去的上百人耕种变成了几十人耕种,最少的一户耕种110亩,最多的一户耕种了300多亩。统一耕种、规模经营解决了土地零碎化问题,发挥了大型农业机械的作用,农业机械能在耕地里尽情地“撒欢”了,农用无人机可以在耕地的上空自由自在地翱翔了。机械化耕种省时省工又省力,效益非常可观,每户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村民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都高兴得合不拢嘴,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东大地的蝶变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一天天在地里不辞辛苦地劳动着,正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幸福之花。
作者简介:
秦勇,笔名咏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会员。2014年以来在《北方文学》《山东文学》《海外文摘》《绿叶》《参花》《奔流》《诗林》《中国报告文学》《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百篇。著有诗集《绿野短笛》,散文集《留在心中的时光》《岁月细语》《遇见》。多篇作品被书刊选用,多次获得各种文学作品大赛奖。2023年被齐齐哈尔市文联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责任编辑/董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