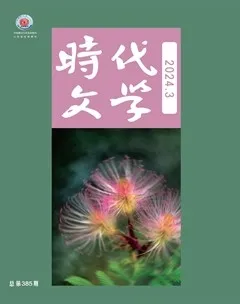如果故事有另一个结尾
2024-08-09张哲
小说写完,我拿给我爸看,他和我妈永远是我的第一读者,他看后说一切都很好,这个故事独特,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是编造不出来的。然而大概隔了两年的时间,他又问起来这篇小说,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有点接受不了后半部分,最好改了。
在做菜的间隙,他在抽油烟机的混杂噪音下,突然问起来,我说怎么了,他迟疑了半天,显然在做着最后的斟酌,然后关了抽油烟机,厨房瞬间安静,顿一顿,他问我:“能不能不杀那只羊?”
海马体是人大脑里神秘而古老的区域,海马在神话里是波塞冬的坐骑,鼻息能吹动大海,金黄色的双蹄能跨越黑暗之渊。《山顶上的雪》就是这样一个藏在海马体里的故事。
我没有见过我爷爷,每次提起他,我爸都加上这样一句:如果你爷爷还活着,他一定最疼你,因为你是他第一个孙女,是家里第一个女孩。因此,我自小就有一份额外的凭空虚设的爱,那是我假想出来的爷爷对我的宠爱,因为是假想出来的,是一种代偿之爱,所以不着边际也用之不竭。小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和老年男性对话,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见的不是或苍老或矍铄,而是一份我假象出的亲缘,故而不知道在他们面前我应有的姿态,在疏离中总有意无意带着一点讨要关爱的本能。
我明白事理之后,我爸才告诉我,爷爷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年轻时死于一场事故。他是乡村医生,给人看病也给动物看病,中年时调到外村上班,十天半个月才回趟家,平时都住在单位宿舍,有天夜里一氧化碳中毒去世。那天和他一起的还有另一个人,那人是县里的,去他们单位下通知,因为地方偏,人又少,和我爷爷又是旧识,便歇在他们单位,两个人都没了。肉体之死背后又多了许多其他的疑问:那家人住在哪儿?那家人后来有没有来过?两家人有没有见过面?如果那家的人找来,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找来,我们又会说些什么?都没有,没有下文,没有人找过。我对这个事实感到失望,因为二十多年来每次想到爷爷,那个我甚至不知道姓名的人也会隐隐浮现,于是便有了这篇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从卡拉拉山开采出一块大理石,请匠人雕琢一座大卫像作为城市的象征,后来请来了米开朗琪罗。在被问到要如何用这块大理石雕刻出大卫时,米开朗琪罗说出了那句打动人的话:大卫其实已经在里面,我只要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好了。这篇小说的写作不同于以往其他的写作,这篇小说的故事是现成的,它已经在那里了,我只要讲明白、讲好就行。也正因此,我格外珍视这篇小说。
小说里,昆宝娘俩来了,昆宝是第一次来,母亲打算炖一锅羊肉招待他们,也算是一种逞能,一种孤儿寡母应付生活游刃有余的示威,一种对于沉默拷问的孤胆对抗,甚或是一个血淋淋的逐客令,于是祭奠了一只羊出来。我觉得应该以死亡对抗死亡,羊被杀了,但肉难以下咽,几个人围坐着开始自然而然地谈论起两个父亲。对于这样的情节安排,我自认为是罗曼·罗兰所谓的英雄主义,不惮于与丑陋为伍,所以没有做大的改动,更没有听从爸爸的意思,因为我本能地抗拒温情的结尾,觉得那是一种美化,模糊且平庸,我甚至会认为那是一种高调的谎言,一种卑微的逃避。
然而人归根结底是趋善的,这是进化留下来的一种本能,“不忍”这个词可以被解读为“软弱”,也可以被解读为“慈悲”,我逐渐理解为什么爸爸要改掉结尾,因为他对于那样的结尾是不忍的。
虽然没有付诸行动,但我的大脑自动校正了这个家族故事,它或许还可以有另一个结局。显然爸爸想了很久,两年的时间,我怀疑他多次欲言又止,所以在说出口的时候,这个故事被接续了一个已然成熟的结尾,他语调缓慢,克制,忧伤,像是说起历史本来的面目:
我跟昆宝讲这只羊的来历,讲它小时候的孱弱与洁白;讲它甚至有个名字,叫白河;讲它爱吃咸味的草,钟爱山坡;讲它耳朵上的豁口,眼睛是淡红色……我如泄露天机一般吐露出关于这只羊的一切秘密,然后把它领到昆宝面前,把拴它的绳子塞到昆宝汗津津的手掌里,一个仪式结束了,一场回溯开始了。而回溯,远比一场杀戮更回肠荡气。
昆宝母子牵着羊走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
一只活着的羊比一只死去的羊更有人情味,它是歉意,是陪伴,是一种呈现退让姿态的拥抱,良善温和含蓄,不含咄咄逼人的杀气,它由爸爸手中到了我手中又到了昆宝母子手中,被带走,被好好圈养,何尝不是另一种代偿之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