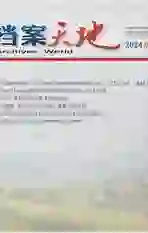一份卖母合同
2024-08-06衣抚生贡伟龙

《白毛女》的故事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旧中国河北穷苦人民悲惨生活的艺术再现。贡伟龙珍藏的一份卖母合同,与杨白劳卖女的情节颇有相似之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白毛女》叙事的真实性。
一、卖母合同的内容与解读
立合同人贾某某(一字因纸张破损看不清)、贾某成,为某成不在家中,欠人外债,屡讨不休。有他母身价陆拾元,零星家倨(具)几件,偿还外债,并无留余。恐后遗忘,立合同为证。(后面有十字画押)
民国十八年(1929)新正月二十二日立
同人:贾某仁、张某智、刘某杰、贾某科、杨某昌、张某桂(其后皆有十字画押)
通过这份合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贾某成欠人一笔钱,其数量至少比他母亲的所谓“身价”60元要高。当然,他为何会欠这笔钱,我们无从知晓。为了躲债,他常年“不在家中”,债主“屡讨”却毫无所获。贾某成家中只有一位母亲,还有“零星家倨(具)几件”,无偿还能力。这份合同书上没有写贾某成有没有房子,我们可以进行合理推断:既然破烂家具都会被拿来“偿还外债”,贾某成要是有房子的话,肯定也会被拿来“偿还外债”。合同书里没有写,说明贾某成或没有自己的房子。别人生活困苦是“家徒四壁”,贾某成家更穷,连“四壁”都没有,生活特别困苦。
第二,债主反复讨债,前几次可能是为了顾及贾某成母亲的生活,没有拿走“零星家倨(具)几件”,到了1929年正月,债主不愿再等,对贾某成一家进行“财产清算”,将其家中的所有物件都搬走,就连贾某成的母亲也被卖了。这就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首先,贾某成愿意卖他的母亲吗?合同的开头写着“立合同人贾某成”,看似是贾某成将他的母亲卖了,仔细一分析,就知道这种说法有问题。贾某成不是常年在外躲债,“不在家中”吗?如何能卖他的母亲?合同书的末尾没有出现贾某成的签字画押,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份部分伪造的合同,至少“立合同人贾某成”的字样是伪造的,未经过贾某成本人的授权和许可。
债主为何要伪造贾某成卖母的假象?这是因为,债主将贾某成的母亲卖了,等到贾某成回来,发现家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岂会善罢甘休?他要是闹事怎么办?债主有办法,那就是以贾某成的名义,将他母亲卖了,这就是“立合同人贾某成”七个字的深意所在。另外,即便知道是伪造合同,仍有多达六位“同人”来作证。
其次,贾某成的母亲愿意被卖吗?合同书中没有写,但是提供了足够多的线索:如果她是自愿的,那么立合同人里应该出现她的名字,写法为:第一个字是夫姓“贾”,第二个字是她自己的姓氏,第三个字是“氏”。从笔迹来看,立合同人的名字有模糊不清之处,但可以肯定不是贾某氏。这就表明,贾某成的母亲不是自愿的,起码不是她自己做主的。也就是说,债主才不管她愿不愿呢!她愿意也要被卖,不愿意也要被卖,不容得她自己做主。
再次,债主卖贾某成的母亲合法吗?合理吗?答案是不合法,也不合理。即便是在广泛存在人口买卖的旧中国,债主也没有资格卖贾某成的母亲。卖身契在旧中国是比较常见的事物,一般都是父母卖子女、兄长卖弟弟妹妹、丈夫卖妻子,也存在公婆卖儿媳、叔伯卖侄子侄女、舅舅卖外甥外甥女、主人卖奴婢等现象。总的来说,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旧社会里,卖身契往往是长辈卖晚辈、尊者卖卑者、亲人卖亲人、主人卖奴婢。贾某成欠的债是贾某成的,即便是要求子债母还,从合同上看债主也并非贾某成母亲的尊长或主人,无权卖贾某成的母亲。
债主无权卖,但他们竟然就卖了,只留下冷冰冰的几个字:“他母身价陆拾元。”在债主看来,贾某成的母亲不是人,而是冷冰冰的商品,是货币的等价物。他们凭什么这么做?他们主要依靠的,无非是八个字的古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或许还可以加上八个字:“父债子偿,子债父偿。”对这些冷血的债主来说,钱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为了要回钱,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思维和行为。
当然,债主也知道这样做不妥,因此就以“不在家中”的贾某成的名义卖。立合同人有两位,一位是挂虚名的贾某成,另一位是贾某某,这个名字中间一个字看不清楚,这个人从名字来看,应该是贾某成的同宗族同辈分之人,可能在宗族内有一定的声望,被认为可以替贾某成做主,甚至有可能就是债主本人。总之,贾某成母亲的命运不由自己做主,也不由自己最亲近的儿子做主,而是由外人贾某某实际上做主,岂不荒谬?
第四,贾某成母亲被卖的时间也值得注意,“正月二十二日”,用的是农历时间,而不是公历时间。俗话说,不出正月就是年,在正月的喜庆日子里,债主上门讨债,还强行将贾某成的母亲给卖了,岂不是很过分?
第五,贾某成的父亲没有出现在这份合同书里,大概是已经去世了。我们可以估算一下贾某成母亲的年龄。贾某成既然能欠债并且在外长期生存,当已经成年。我们假设他16岁以上,那么他母亲应该在30岁以上。从他母亲60元的“身价”来看,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我们曾介绍过一张卖身契,一位14岁左右的小女孩被卖了50元[1]),那么她的年龄也不应太老,估计很可能在30到40岁之间。
二、卖母合同与《白毛女》杨白劳卖女故事的对比
这份卖母合同与《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卖女故事颇有相似之处,共有多达13个相似点:
第一,时代相近。这份卖母合同发生在1929年,《白毛女》设定的故事时间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都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的民国时期。
第二,地点相近。这份卖母合同发生在河北省某县(文中合同为收藏者在河北某县发现),《白毛女》的故事设定在“河北省某县杨各村”[2]。
第三,杨白劳与贾某成的家庭经济情况相近。杨白劳的家庭状况是:“屋中穷苦简陋,内有一灶……柴火及盆罐散放在角落里,锅台上放一油灯。[2]”贾某成家里更为贫穷,首先是没有房子,其次是只有“零星家倨(具)几件”,属于艺术加工都没有写出的极度贫穷。
第四,极度贫穷的杨白劳和贾某成都欠了一笔他们还不起的债。杨白劳欠的“一共是二十五块五毛,一石五斗租子”[2]。贾某成欠的至少是60元,比杨白劳还要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杨白劳那么穷,黄世仁怎么会借给他那么多钱?其实,杨白劳欠的是10.5元,因为“利打利、利滚利”[2],硬生生给长到25.5元。同理,贾某成比杨白劳还要穷,明显没有偿还能力,别人怎么可能会借给他至少60元的巨款?这笔钱,很可能也是“利打利、利滚利”而来的。
第五,没有偿还能力的杨白劳为何会借到钱?黄世仁不怕他欠债不还吗?不怕,杨白劳有女儿喜儿,可以用来偿债。同理,没有偿还能力的贾某成为何会借到钱?债主不怕他偿还不了吗?难道债主不知道他家里只有“零星家倨(具)几件”吗?贾某成借钱的“抵押物”是什么?答案很明显,是他的母亲。杨白劳和贾某成在借钱时,债主在心理上都以其家中的女性为“抵押物”,而在事实上,他们都被迫用家中的女性来还债。
第六,还不起钱的杨白劳和贾某成都被迫外出躲债。
第七,杨白劳和贾某成签的合同都有严重问题。杨白劳签的合同并非出于自己本意,而是被强迫的。贾某成更惨,他很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份合同的存在,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被他人买卖。
第八,两份合同的内容高度相似。杨白劳签的合同内容是:
立约人杨白劳,欠东家租子一石五斗,大洋廿五块五毛,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与东家,以人顶账,两相情愿,决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约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智……[2]
将杨白劳的合同中的人名换成贾某成等人,或者是将贾某成的合同中的人名换成杨白劳等人,都毫无违和感。
第九,杨白劳和贾某成一家都是在大年正月里被人催债,也都是在大年正月里被迫出卖女人。
第十,被卖的女人都是被迫的,并不出于自己情愿。
第十一,债主之所以能够买卖杨白劳和贾某成家的女人,依据的都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偿,子债父偿”的传统思想。如果说,这种思想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将其发挥到卖人母、卖人女的地步,就属于十恶不赦了。
第十二,两家的家庭成员情况相近,都缺了父母双亲之一。喜儿死了妈妈,贾某成没了爸爸。
第十三,帮凶的名字都充满着仁义道德。黄世仁的帮凶是穆仁智,有“仁”有“智”。贾某成合同中的“中人”有贾某仁、张某智,也是有“仁”有“智”。如果说,《白毛女》故事中的有“仁”有“智”是出于艺术加工和讽刺,贾某成合同里的有“仁”有“智”则是来自现实的赤裸裸的嘲讽。当然,两者之间可能也是有差别的:穆仁智知道自己坏,003bd62fb4864548a371c5b1abd78da2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贾某仁、张某智则可能不知道自己坏,而是在维护自己心目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纯朴的道德感,否则他们可能也不会愿意当见证人。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杨白劳卖女的故事并非出于纯粹的虚构和想象,而是可以在旧中国的河北地区找到明确的相关事例,是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创造。而且历史真相可能比《白毛女》描写的更加残酷:真实生活中的贾某成比杨白劳更穷,也更惨——杨白劳卖女是被迫按手印的,他本身知道此事的发生,还有应对的时间和可能性;以贾某成名字签订的合同书则是伪造的,贾某成根本就不知道他母亲会被强卖,也就无法挽救。他回家之后,所面对的只有家破人亡的既成事实。
很显然,这份卖母合同会对一味为民国粉饰太平的观点造成强有力的冲击,让今天的人们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底层劳动人民的民国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不容任意打扮,正是因为有这份卖母合同在,有这类历史实物的铁证在,历史虚无主义才注定要消亡。
参考文献:
[1]衣抚生, 米龙. 一张卖身契[J]. 档案天地, 2021(8): 12-13.
[2]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 白毛女[M]. 北京: 新华书店, 1950.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近代发票与商业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