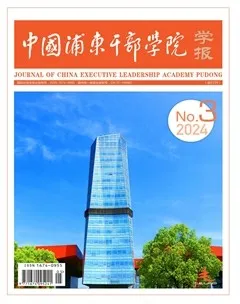走出“普世价值”的认知误区
2024-08-03陶富源
摘 要:关于“普遍”有两种理解:一是联结特殊于自身的“现实普遍”理解,二是与特殊对立着的或不含特殊于自身的“抽象普遍”理解。从“现实普遍论”的观点来看,人世间只存在“现实普遍”以及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价值,并不存在“抽象普遍”和“普世价值”。有些论者对“现实普遍”与“抽象普遍”不加区别,把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对人类价值的对象及主体之普遍性作了“抽象普遍”理解,进而为“普世价值”进行辩护,结果弄得谬误迭出。“普世价值”这一命题,不仅在理论上不能成立,而且在事实上也毫无依据,因而必须加以拒斥。
关键词:“现实普遍”;“抽象普遍”;价值;“普世价值”;人类共同价值;马克思主义
引 言
近年来,“西方普世价值论”在我国理论界遭到了批判。与此同时,却有一些论者站出来为“普世价值”本身的存在进行辩护。在他们看来,“西方普世价值论”把西方的特殊价值说成“普世价值”,这显然是不对的,对之进行批判是完全正当和合理的;但“普遍”毕竟是存在的,因而在价值论上,作为一种“普遍”的“普世价值”也必然是存在的。于是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拒斥“西方普世价值论”与承认“普世价值”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二者是统一的。
怎样看待这一观点呢?这里涉及对“普遍”的两种不同理解,即对“现实普遍”与“抽象普遍”的理解。这里要指明的是,“现实普遍”与“抽象普遍”区别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具体普遍”与“抽象普遍”。①尽管“现实普遍”和“具体普遍”都是相对于“抽象普遍”而言的,但它们在各自的相互关系中,含义并不相同。“现实普遍”与“抽象普遍”是就普遍与特殊是否联结而言的,而“具体普遍”与“抽象普遍”是就对事物内在联系的普遍性之理性把握是片面还是全面而言的。因此,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现实普遍”在德文中为“Universalität”。它是指与特殊作辩证统一理解的普遍。或如黑格尔所言,它是“贯穿于一切特殊性之内”,并“通过特殊性而给予自身以外在实在性”的普遍。[1]351,356“抽象普遍”在德文中为“Allgemeinheit”。它是指一种在想象中存在的“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普遍,[1]332即抽象共相,或“想象中的幻影”。[2]273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一论述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好极了!”[3]98
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来看,人世间只存在联结特殊于自身的“现实普遍”,并无与特殊对立着的或不含特殊于自身的“抽象普遍”。因而在价值论上,只存在与特殊价值相联结的“现实普遍”价值,即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价值,并不存在那种与特殊价值相对立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抽象普遍”价值,即所谓“普世价值”。
为什么说共同价值是“现实普遍”的?这是因为:其一,共同价值之“共同”,意味着它是以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为基本前提的,是使该共同体得以存续的一种价值。①其二,共同价值之“共同”,是相对于异在而言的异中之同。比如,“自由、民主、人权”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是通过不同国家的特殊GoFddK/iHo3anJJ2Kl7ghipZfXbR3jSqSDrPV920XYw=模式而存在和表现出来的。其三,共同价值之“共同”,标示着它是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共创共享的价值。
与之相反,“普世价值”是“抽象普遍”的。什么是“普世价值”?按《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普世价值就是指,在任何时空、任何条件下对每个人或每一群体都普遍适用的价值”。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普世价值是对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有相同价值的价值”。②我国有些论者进行了类似的解读,认为“普世价值”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永恒不变的、以普遍必然性呈现的价值。对此种解读,除不以为然者之外,还有论者持一种自以为的补正态度,宣称为了避免绝对化,应对“普世价值”加以某种限定。由此,也就有了“有限的普世价值”“一定的普世价值”“底线的普世价值”等言说。殊不知,这种加了某种限定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无普世性可言了。其一,“普世价值”不以人类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也不以全球交往实践为根据,故而在以往历史上,它是一种被想象为神赋的、或由人性赋予的、或由某种至上理性来设定的所谓价值。其二,“普世价值”是一种不以差异性为表现和规定的、抽象僵死的所谓价值。其三,“普世价值”与特殊性相对立,因而它似乎对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普遍适用,而实际上却是毫无用处的虚假价值,即价值虚无。
由于对“现实普遍”与“抽象普遍”的区别缺乏审察,因而我国有些论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抽象普遍”意义上来理解人类共同价值,从而对“普世价值”加以辩护,以致把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并用人类共同价值来为“普世价值”张目、站台。这是很不妥当的。鉴于这一情况,本文拟以“现实普遍论”为理论依据,对一些论者为“普世价值”辩护的理由进行具体分析。下面分八点来谈。
一、“普世价值”不能从“普遍人性”找到根据
有论者认为,“普世价值”存在的根据是普遍人性,因而只要能够证明存在普遍人性,那么就能证明存在“普世价值”。什么是普遍人性?有人说,普遍理性即公共理性,就是普遍人性,就具有“普世价值”。就此,这里谈三点看法。
1.普遍人性是存在的。普遍人性以人性的存在为前提。所谓人性,在人类学意义上,就是人类与物类相区别的特性。这里的特性,如果切换到社会哲学意义上,那么它就是与社会关系中的各个个体和各种群体的特殊人性相联结的一般人性。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性的普遍性。③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能把人性的普遍性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人性“抽象普遍性”;必须把人性普遍性理解为在社会实践中生成的,受一定时代性、群体性和个体角色性等特殊性制约的,通过社会性、能动性、历史性、意识性的行为活动来表现的人性“现实普遍性”。
2.人性普遍性无以证成其价值普世性。因为人性与其价值的性质不同。其一,在存在论上,如前所说,人性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体属性,而价值则是存在于主客体间的一种关系属性。其二,在价值论上,作为价值客体的人性,只是价值构成的一个要素,它的性质与由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价值系统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从人性普遍性来推断其价值普世性,这就如同不能用某种水果普遍含糖去论证它对所有人具有普遍价值一样。
3.人性普遍性与其价值普世性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以作为普遍人性的公共理性来证明普遍人性的价值普世性,这种论证是似是而非的。如上所言,意识性是人性的一种普遍性,但它并不是抽象存在,而是通过理性与非理性来表现的。就理性而言,其中有一种被称为实践理性,即对人的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的理性。而实践理性是分层的。比如,在国家层面,有国家公共理性与非国家公共理性。后者包括个人自我理性,即公民在自我利益盘算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福利理性。诚然,个人作为国家公民也会形成国家公共理性。这种理性在国家维度上就表现为维护和增进公众利益的制度安排和道德规范,在公民维度上就表现为维护和增进公众利益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来看,在人类整体层面上,一定的公共理性,是与文明发展程度相联系的全球性交往实践的产物。由此所决定,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公共理性,从世界公民的维度说,也就表现为维护和增进全人类利益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很显然,这种公共理性只对与时代同行、拥有和践行此种理性的人有价值,而对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落后于时代的人以及反对和漠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人,就没有价值。因此,作为人性普遍性之意识性表现的人类公共理性,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有价值普遍性,即共同价值,并无对所有人而言的价值普世性。因此,那种用公共理性来证明普遍人性的价值普世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总之,普遍人性是存在的,但它并非脱离人性特殊的“抽象普遍”存在,而是内含人性特殊的“现实普遍”存在。作为“现实普遍”存在,它只有相对于特定人群而言的有条件的共同价值,并无相对于所有人而言的无条件的所谓“普世价值”。可见,那种脱离人性特殊性对普遍人性作“抽象普遍”理解,并将其作为“普世价值”存在根据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二、“普世价值”不能从“普遍需要”获得论证
有论者认为,人类个体之间,必然存在许多基本的、普遍的需要,而与每一个普遍需要相对应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比如,含氧的空气是人之普遍需要,因而含氧的空气有“普世价值”。又比如,“吃”作为人的普遍需要,对人来说具有“普世价值”。对于这一观点,这里谈三点看法。
1.人有普遍需要。每个人作为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生命体,无疑有其自然、社会和精神的需要,不然就无以为生,也谈不上有其作为。在人的一切需要中,无疑有普遍需要。其中,最普遍的需要莫过于维持生存的吃、喝、呼吸,以及安全和繁衍后代等需要。
2.人之普遍需要不能证成其“普世价值”。因为对人的普遍需要,不能作抽象理解而须作现实理解。拿呼吸来说,呼吸氧气是人的普遍需要,但对这一命题不能作抽象理解。现代科学证明,在标准大气压下,如果空气中的氧气浓度低于19.5%,人就会感到呼吸困难。然而,呼吸氧气这一普遍需要,是通过处在不同条件下的人的呼吸来表现的。生活在不同海拔高度和不同气候中的人,乃至在高压氧舱中的高危病人,其需要的氧气浓度和呼吸的方式都是不同的。那种离开了特定环境条件和特定呼吸对象而抽象谈论呼吸氧气是人的普遍需要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另外,那种没有任何含氧浓度规定的抽象的含氧空气,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因而其对任何呼吸者来说,也就不成为价值对象,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所谓价值。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具有一定具体氧气浓度的空气对一定人群而言的价值普遍性,或价值共同性。上述推论之所以不妥,就在于它抽象谈论人的普遍需要,又人为虚设了一个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3.人之普遍需要可能引发价值冲突。这是因为,需要作为价值主体的根本属性,只是构成价值系统的一个要素,需FvWGU9DmKHuYTzYbtSIEuQ==要并不等于价值。要构成价值系统,除了要有需要,还要有满足需要的对象即价值客体。拿“吃”来说,这是人的普遍需要。但要实现“吃”的价值,除了“需要吃”以外,还须“有得吃”,即有吃的东西。不能因为作为吃的对象的X是人人需要的,便由此推断X具有“普世价值”。在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中,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其他所有人都得到X。在“吃”的问题上,阶级社会中的剥削阶级正是把饥饿作为压迫手段,而得以役使劳动者的。而从更高的立意来说,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人,即处在人与人关系中的个人,才能科学说明人的需要及其价值实现。
诚然,社会关系中的人之需要及其价值实现,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还拿人之“吃”的价值的实现来说,在未来的实现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撇开偏好性、丰富性和精致性等不谈,至少在维持生命的“吃”的意义上,需要和满足实现了高度融合。“满足了的要求不再是要求”,[4]43因而到那时,饥饿消除了,与之相应的维持生命的“吃”,也就不再作为需要存在了。
总之,那种脱离人之需要的特殊性,脱离人之现实需要满足的对象,以及脱离制约人之现实需要满足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引发的各种矛盾,来对人的普遍需要作抽象理解,并以之证成其“普世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三、“普世价值”不能从“普遍真理”求得支撑
有论者认为,人之需要,包括认知的需要;而作为科学认知成果的普遍真理,是有“普世价值”的。对此,这里谈三点看法。
1.真理有人类价值。真理是与客体相符合的认识,或曰对客体的正确认识。作为真理对象的客观事物,其外延有广狭之分。这样,就有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最普遍的哲学真理,也有以一定范围或领域为对象的各门具体科学的普遍真理,还有以个别事物为对象的个别真理。这里所言的普遍真理,主要指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普遍真理。
不管真理的普遍性如何,对人类来说,凡真理都是有价值的,都能指导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实践改造和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提升。也就是说,真理是改造世界、造福人类、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对整个人类实践和人类利益的发展来说,认识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追求认识的真理性和实现认识的价值性是互为前提的。人类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同时又在实践中实现价值。没有真理的指导,价值就不能被追求,也不能被成功地实现。没有价值的追求,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会丧失动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价值的成功实现,要从真理获得客观依据;真理的实际运用,要从价值获得意义说明。二是在人类利益上的统一。一切普遍真理都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趋势的揭示。人类作为上述关系中的一方和上述关系中的能动者,只有认知这些关系的普遍本质,才能确立自己的行为根据;只有把握这些关系的普遍趋势,才能找准自己的行为方向,从而也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不惜牺牲去追求真理,说到底是因为真理代表了人类的根本利益。
2.普遍真理无“普世价值”。普遍真理之普遍性,是相对于其外延中的个别而言的普遍性。对在其外延中生活的人来说,这种普遍性就变为了无例外性,或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平等,是指在真理的客观性意义上的平等。比如,水在一个大气压的条件下,达到了100℃就会沸腾,这是一个客观真理。哪怕将这一过程重复一万次,它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客观性。由此所决定,无论是谁,尊重真理的客观性就能获得价值,而违背真理的客观性就会丧失价值,甚至要受到惩罚。很显然,不能用认识的“普遍真”来论证其价值的“普世善”即“普世价值”。
普遍的真并非善。任何普遍真理只有与具体情况相结合,才具有价值。比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造福各国人民。反之,如果不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普遍真理就无价值可言,更谈不上有所谓“普世价值”。
“普遍真”的人类善,并非“普世善”。如上所言,对整个人类实践和人类利益来说,认识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是统一的。但这并不是说,一切真理包括普遍真理对所有人和所有群体都有所谓“普世价值”。这里有两点原因。一是,如果某个特定主体的思想和行动与人类根本利益和社会进步趋势相背离,那么反映事物普遍本质和规律的普遍真理就不可能符合其需要,对其就没有价值。二是,在阶级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普遍真理具有相对于一定社会主体而言的意识形态性。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普遍真理对不同阶级、政党、国家等社会主体就不具所谓价值普世性。应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自然科学普遍真理呢?有论者认为,作为非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普遍真理具有对所有人而言的价值普世性。其实,这也是不能成立的。
3.自然科学普遍真理不具价值普世性。
人类社会中,自然科学普遍真理并非是人人共享的财富,这是因为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普遍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除了由国家承担(比如普及义务教育)以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由个人及家庭承担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谁花费代价掌握了自然科学普遍真理,那这些真理就转化为了能够带来价值的知识、技能、技巧。
自然科学普遍真理的价值有两重性。其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如果被不同的主体所享有或承担,那就必然会引发价值冲突。比如,一家工厂的经营者把通过运用某种自然科学技术而获得的可观经济价值归自己所有,而工厂造成的环境污染却由周围的公众来承担。这就是当今许多地方发生生态冲突的原因所在。
自然科学普遍真理的价值是一种手段性价值,它要服务于利益主体的目的性价值的实现。在阶级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利益主体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分立甚至对立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科学普遍真理就不可能具有“普世价值”。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5]418使“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6]366由此可见,即便是自然科学普遍真理,其价值也并不具有普世性。
总之,那种脱离现实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对普遍真理的普遍性作“抽象普遍”理解,并以此来论证其价值普世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似是而非的。
四、“普世价值”不能从“普遍利益”得到确认
这里的普遍利益是指人类的普遍利益。有论者认为,“普世价值”关涉人类普遍利益。怎样看待这一观点呢?这里有以下三点需要澄清。
1.历史生成的人类普遍利益并非超历史的所谓“普世价值”。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交往水平低下,人类长期处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束缚下。在那时,还无所谓人类的普遍利益。直到近代,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才逐渐产生了人类的普遍利益。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逐渐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当今时代,才形成了由“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原则所标示的人类普遍利益,或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7]522也就是说,人类普遍利益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历史地生成的,是近代以来人类实践创造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与那种超历史的所谓“普世价值”,不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2.联结特殊利益的人类普遍利益并非凌驾于特殊利益之上的所谓“普世价值”。这里的特殊利益,主要是指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得以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利益。就一个国家来说,维护其主权、安全、国民福祉、道路选择、制度安排等,就是它的特殊利益。人们为了获得和增进自身的特殊利益,必然要与他者进行交往。随着交往的国际化、全球化发展,出现了各国家各民族间的利益交汇点和共同点,以及利益摩擦点和冲撞点。在扩大和增加利益交汇点和共同点、化解和消除利益摩擦点和冲撞点的过程中,形成了通过公共原则和规范来保障和体现的人类普遍利益。对各国家各民族来说,这种普遍利益是大家共同缔造、维护和享有的真正的普遍利益。它与那种脱离和凌驾于各国家各民族特殊利益之上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根本不相容的。因为对各国家各民族来说,后者是虚假的。
3.人类普遍利益所标示的人类系统的导向价值,并非对一切人而言的所谓“普世价值”。人类不是个体的叠加,而是世界人民通过交往所结成的以“人类”为指称的一个系统。由此所决定,人类普遍利益就是保障作为世界人民利益之集中表现的人类系统得以运行和发展的利益。人类普遍利益的维护和增进所指示的方向,是由价值维度所标示的符合世界人民期待的人类系统发展大趋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就是当今时代条件下,体现人类系统发展大趋势的导向价值,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追求合作发展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价值。为了实现这种共同价值,一切进步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与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以及恐怖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不难看出,就当今人类的普遍利益而言,不能脱离当代人类系统发展之总趋势以及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去作“抽象普遍”理解,更不能以此证成所谓“普世价值”。
总之,那种脱离人类普遍利益得以生成的历史条件,脱离与各国特殊利益的联结,以及脱离当代人类系统发展所指示的历史方向,来对人类普遍利益作“抽象普遍”理解,并以此来论证“普世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站不住脚的。
五、“普世价值”不能从“普遍规范”得以证明
有论者认为,世界性组织和世界性公约确定的原则和规则,作为一种规范,具有覆盖全世界的普遍约束力。比如《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等所规定的价值,就可看作全球所有国家或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普遍价值,这也是一种“普世价值”。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论述十分粗疏、笼统且混乱。
1.任何组织规范的价值普遍性只是相对于该组织的范围而言的价值普遍性,其价值并不是“普世价值”,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比如《联合国宪章》与《国际人权公约》在相应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或者说具有价值普遍性,但并不具备价值普世性。众所周知,联合国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而区域性组织是不能作为主体加入联合国的,因而《联合国宪章》对这些区域性组织就不具有约束力。《国际人权公约》也是如此。承认该公约并在该公约上正式签字确认的国家,才受这个公约的约束。
2.价值不同于价值认同。如前所说,价值是价值对象对价值主体的一种意义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客观性。而价值认同则是对这种客观关系的一种评价和态度,有其主观性。因而这里的认同,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上述论者把普遍价值说成是认同的普遍价值,也就是把价值与价值认同混为一谈了。这也是不妥的。
3.一切普遍规范都无所谓“普世价值”。这里的“一切普遍规范”,包括将来在全球一体化条件下所可能制定的那些规范,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有巨大价值,但规范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比较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因为有不规范的人和事存在,所以才需要规范。由此,任何规范都有两面性,既有维护守规者的一面,又有排斥和打击违规者的一面。否则,规范就不成其为规范,也就没有价值。不难理解,规范只对守规者有价值,因为他需要得到规范的保护;而对违规者来说,规范则没有价值,因为他无此需要,并根本反对规范本身。有论者大谈“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其实是误谈。从规范论的角度说,如果社会上不存在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人和事,那么也就不会产生“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和规范。另外,在阶级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从来不存在超阶级的、适合一切人的所谓“普世自由”“普世民主”“普世人权”。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所一再申明了的。
总之,脱离一定组织规范的局限性,脱离相对不规范而言的规范的比较性、针对性,来对普遍规范作“抽象普遍”理解,并以此来证明其具有“普世价值”的做法,是轻率的、不妥的。
六、“普世价值”不能从“普遍解放”寻得理由
有论者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但由于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跟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指向是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其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因而其包含了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普世价值”。这里的论证看似言之有理,其实牵强附会,甚为不妥。下面从人类解放的过程和愿景这两个维度来加以说明。
1.人的普遍解放过程所体现的并非超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人的普遍解放,是无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对其不可作“抽象普遍”理解。“普遍解放”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有条件的、现实的。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指出的,“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167也就是说,人的普遍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或者说,人的普遍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实现的”。[2]167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指无产阶级——引者注),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8]526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不然就会把人的普遍解放变成“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2]370这里是说,人的普遍解放对有产阶级并无价值,因为他们“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对它作抽象理解,那么人的普遍解放就成为了一句导致自我麻醉甚至忘却自身历史使命的有害的空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警示人们,不能脱离无产阶级解放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消灭,去空谈人的普遍解放,甚至认为其体现了超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
2.人的普遍解放愿景所代表的并非对每个人而言的所谓“普世价值”。人的普遍解放的愿景指向的是:人类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已从以往所经历的前两个阶段逐渐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从人类早期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原始融合阶段,发展到阶级社会中的二者片面对立阶段,最后进入通过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来实现的二者高度统一的历史阶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那样,在这个历史阶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53在人类解放愿景的意义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其他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已经根本不存在与“自由人联合体”利益片面对立的个人及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同样也不存在与这些特殊利益片面对立或有别的、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标识的所谓普遍利益。既然在这种融合中,特殊利益和与之相对的普遍利益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在最终的意义上,人的普遍解放也就是使人从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中获得解放,从而使人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人,并从而使社会成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因而作为历史发展愿景的人的普遍解放,也就意味着个体人再也不是以往那种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中的个别利益主体或个别价值主体,而成了个性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既然如此,在没有了上述个别价值主体的前提下,而去谈论对每个人而言的所谓“普世价值”,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那种无视剥削阶级消灭和阶级消亡的历史过程,无视人类历史发展愿景所标示的人类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高度融合,来对人的普遍解放作“抽象普遍”理解,并以此来论证“普世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七、“普世价值”的存在没有事实依据
由上可知,“普世价值”在理论上得不到任何证明,那么它在事实上是否存在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自阶级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上,一些人所说的“普世价值”,其实从不“普世”。也就是说,所谓“普世价值”只是一种口头宣称,从未真正存在过。
人们宣称的“普世价值”,大体说来有三种类型:一是古代西方基督教所高扬的神性论“普世价值”,二是现代一些神学家和伦理学家所倡导的伦理论“普世价值”,三是当今西方霸权主义者所强推的政治论“普世价值”。
1.关于古代神性论“普世价值”的批判。如上所言,这里的“普世价值”是指西方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在基督教看来,上帝至高至圣,至仁至爱,因而作为上帝意旨体现的基督教在世界上就具有价值普适性。也就是说,凡是皈依基督教的人,不受历史、地域、人种、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差异的影响,都能获得救赎,从而得享幸福。这就是基督教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从社会根源上说,是中世纪西欧封建主和教廷的特殊利益借助宗教这种形式所获得的一种虚假普遍性表现。因此这种所谓的普遍性,也就必然会遭到它企图凌驾其上的、拥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各民族各国家的拒斥,并最终走向破产。到16世纪时,随着欧洲出现反对罗马教会的宗教改革,以及其后的西欧各民族人民的觉醒和各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基督教宣称的曾作为西欧各国思想和政治主宰的所谓“普世价值”,也就逐渐退缩为一种个人信仰。
另外,神性论“普世价值”的所谓普世性,不仅在内涵上不真实,而且就其外延来说,也不具真实性。基督教所谓的“普世”,其所涵盖的只是其信徒,而非世界上所有的人。正如《圣经》所言,“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的最高刑罚就是“灭绝”。所谓“灭绝”,就是屠杀异教徒或通过宗教战争征服异民族。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发生的。不难看出,基督教宣称“普世主义”,实际只是以“普世”为幌子,去谋取特殊价值。
2.关于现代伦理论“普世价值”的批判。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普世伦理”一说,是从伦理维度所言说的“普世价值”。这里,在说明“普世伦理”有无的问题之前,首先要划清社会群体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与“普世伦理”的界限。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一开始就生活在群体之中。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使得群体伦理即群体成员的共同伦理逐渐形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际交往的扩大,人们生活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嬗变。与此相联系,相关伦理也在发生着生灭、变化。比如,一夫一妻制产生后,才有了“不要奸淫”的规定;私有制产生后,才有了“不要偷盗”的规定。在古代中国,封建婚姻的前提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道德风尚。
随着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随着世界逐渐从无序趋向有序,随着以联合国为首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及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初具雏形。由此,也就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伦理、科技伦理,以及多边共商、共担、共享等伦理。这也就是当今人类的共同伦理。
由上可见,任何伦理都是与时代条件、人们所生活的群体以及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相联系并由其决定的。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时代条件、特定群体及群体成员共同利益而以所谓上帝或理性的“绝对命令”形式存在的“普世伦理”。这种抽象的“普世伦理”似乎适用于任何时代,但实际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适用的。不仅如此,这种作为抽象共相存在的“普世伦理”,可能获得某种先入为主的解释。这些解释者自以为“上帝或真理与我同在”,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他者往往不是更平和、更讲道义,而是更专擅、更强暴。诚然,观念不等于行动,但二者之间存在联系。人一旦把自己倡导的伦理看成普世的,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和道德使命感,从而使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某种条件下就会对别人指手画脚,甚至不择手段地使他者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3.关于当今政治论“普世价值”的批判。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为维护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反对“专制主义”为旗号,在全世界所强推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是西方启蒙学者提出来的政治理念。他们对这一理念的信仰是真诚的。这种信仰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压迫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西方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沿袭了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做法,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阶级基础上所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原则,从其产生的条件和阶级基础中抽象出来,给其套上“普世价值”的外衣,进而对广大非西方国家和人民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剥削掠夺,以实现自身特殊利益的最大化。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武力崛起并称霸世界,同时对西式“自由、民主、人权”加以文化包装。而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和人民日益觉醒,对西方国家而言,发动武力侵略的代价太大,且可能在其国内引发广泛的反战浪潮。于是,这种被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就变为了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武器。这也就是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运用。实际上,其维护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指出的,“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10]45,286其实,何止是危险?近几十年来,西式“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在全世界的推广,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祸害。从更高的立意来说,不独西式“自由、民主、人权”是如此,世界上任何价值如果以一种单一模式来复制、推广,同样不会产生好结果。因为人世间根本没有一种价值是无条件的、普世的、绝对的。
总之,“普世价值”在学理上无从论证,在事实上也没有支撑,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八、消除关于“普世价值”的观念迷误
既然西方宣称“普世价值”的用心如此不良,影响如此恶劣,那么为何还有一些论者肯定“普世价值”本身的存在呢?在笔者看来,除了上述所指出的,在人类价值的对象及主体之普遍性问题上迷失于抽象理解之外,他们还陷入了关于“普世价值”的观念迷误。
这里的迷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认为,承认“普世价值”,有助于变被动为主动。这一观点可简称为“主动说”。二是认为,承认“普世价值”,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大道保持一致。这一观点可简称为“一致说”。三是认为,承认“普世价值”,并把中华文化中的某些优秀部分提高到“普世价值”的高度,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这一观点可简称为“自信说”。下面就这三种观点来作一些具体分析。
1.关于“主动说”的辨析。在这一观点看来,西方以“普世价值”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占据道德制高点,享有充分的主动权;中国则长期遭受压抑,被动挨批;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不妨接过“普世价值”的旗帜,用自己的观点加以解释,并批判西方“普世价值”,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殊不知,这样做,不仅不能变被动为主动,而且还会使自己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甚至从根本上丧失由被动变为主动的任何可能。这是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不管怎样解释,或由谁来解释,都不能把虚假的东西说成真实的东西。如果硬要去做,那必然会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为一个错误辩护,必然招致一系列新的错误。如此错上加错,还有什么主动可言,其结果只能是彻底的失败。面对“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挑战,唯一的取胜途径就是:彻底揭露其反科学、反时代潮流、反人民的本质,高扬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为世界人民服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2.关于“一致说”的辨析。在这一观点看来,承认“普世价值”,就是承认人类有其文明大道;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可能各有特色,但必须与人类文明大道相一致,即必须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然就会走偏方向,从而招致失败。这一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说通,因为它把“普世价值”与人类文明大道混为一谈了。所谓人类文明大道,就是指以科学、民主、自由、法治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旨归的康庄大道。承认这条道路的存在与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并无任何关联。因为人类文明大道不是按照某种超民族、超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走出来的,而是各民族各国家在各自的实践中,在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共同走出来的。每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大道的开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样,每个民族也在为开辟这条文明大道作出贡献的过程中获得了进步和发展。如果背离人类文明大道,把自己孤立、封闭起来,那么必然会走向愚昧、落后、衰败。而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如果自我矮化、自我轻视,把他者的某些东西视为“普世价值”,或听信他者所宣称的“普世价值”,对其顶礼膜拜,将其奉为圭臬,那么必然会走向失败。就吸收人类共同文明成果而言,一个国家要真正享受这种文明成果,还是要以我为主,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民族化重塑,才能真正使其为我所用。
3.关于“自信说”的辨析。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试图把中华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提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借以提升文化自信,并希望为增进世界人民福祉作出应有贡献。应该说,持这一观点的论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何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是很有讲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提升,源自三个方面。其一,在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走出了一条可以救中国和可以发展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其二,中国人民以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为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其三,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并在向世界回馈和贡献的过程中,赢得了尊重和赞扬。就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关系来说,唯一正确的取向,就是和而不同、交流互鉴。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应自我吹嘘、盲目自信,将自己的文化当作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人。既然是交流互鉴,如何借鉴、借鉴多少,都只能由借鉴国的人民说了算。如果强加于人,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遭遇抵制和反对。由此不难看出,那种给中华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戴上“普世价值”的桂冠,希望以此来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实乃南辕北辙。另外,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对外来文化抱有一种虚心学习、择善而从的态度,这本身就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把21世纪说成是所谓“中国世纪”,是不合适的;因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借鉴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就认为“世界将中国化”的观点,是不理性的。为了中国好,也为了世界好,必须与上述显虚荣而招实害的观点划清界限。
结 语
总之,人类共同价值非“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辩护者,对人类价值的对象及主体之普遍性作了“抽象普遍”理解,并以之对“普世价值”加以论证。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普世价值”这一命题,不仅在学理上无从论证,而且在事实上也毫无依据,因而必须加以拒斥。只有消除观念迷误,凝聚价值共识,才能沿着人类文明大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苏]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美]A.H.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程朝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十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J].求是,2017(1).
杨永建,郭澄澄.正确认清西方“普世价值”论的蒙蔽性和虚伪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3).
陈文旭,易佳乐.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4).
杨涯人,邹效维.“普世价值”考辨[J].哲学研究,2011(2).
鲁品越,王永章.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
陈慧平.普世价值问题的主体形而上学症结及其消解[J].哲学研究,2018(1).
[责任编辑 黄云龙]
Breaking Free from the Myth of “Universal Values”: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Universal Values” and Humanity’s Shared Values
TAO Fuyua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understandings of “universality”: the one is “real universality” that connects speciality with oneself, and the other is “abstract universality” that is opposite to speciality or does not contain speciality about one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er, there exists only “real universality” and common valu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within a certain rang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is no “abstract universality” or “universal values”. Some theorists do not distinguish them, confuse humanity’s shared values with “universal values”, understan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object and subject of humanity’s values as “abstract universality”, and then defend “universal values” but with the result of repeated fallacies. The proposition of “universal values”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untenable, but also has no factual basis, so it must be rejected.
Key Words: “real universality”; “abstract universality”; values; “universal values”; humanity’s shared values; 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