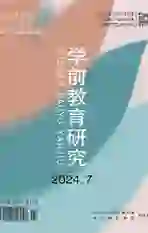以“否定性”为支点:儿童哲学的存在论辩护
2024-07-31韦恩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JJD880019)
**通信作者:韦恩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儿童哲学的存在论问题是儿童何以哲学的逻辑前提。既有论证方式难以建构有效辩护,继而造成了儿童哲学的身份疑案,主要表现为:理论构建和教育应用在立论前提下的定位模糊,一般儿童与个别儿童在研究对象上的层次混淆,权宜之计和普遍兼容在价值旨趣上的两副面孔。通过以否定性为存在论支点,揭示否定性奠定了儿童在“问题分叉”中的生成性,阐明否定性是开启儿童可能性的“众妙之门”,诠释否定性标识了儿童让“事情发生”的及物性,澄清了哲学是儿童个体成人的自发态势和固有动力。否定性的转化是儿童哲学生效的教育立场,这要求我们重视儿童身体价值,超越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避免儿童角色固化,提供多重体验的做事承担;厚植儿童生命力量,寻求自然与人为的相对平衡。
[关键词] 否定性;儿童;儿童哲学;存在论;教育
在现代教育的事项上,人作为教育对象的第一个阶段表征为儿童,儿童是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研究儿童是进入现代教育学的必经门槛。[1]历史上,通常将卢梭(Rousseau,J?鄄J.)“发现儿童”认定为教育学的“哥白尼革命”,尤其是经过“新教育”运动的洗礼,儿童逐渐走进教育的视野,并在教育理论体系与学校系统中拥有一席之位。[2]儿童得以“徘徊”在教育中央地带,既有生理性的考虑,也有社会性的承认。后得益于李普曼(Lipman,M.)和马修斯(Matthews,G.B.)的开拓性贡献,一种被称为“儿童哲学”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在成为教育哲学重要研究分支的同时,对推进基础教育改革也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上,没有儿童的存在,很难有底气说教育有地位和价值,勾连教育与儿童的联系,并不会引起质疑。但是,儿童如何能与哲学挂钩,形成儿童哲学的基本建制,却很难判定为值得信服的命题。困难在于,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语境中,儿童都和哲学格格不入。黑暗的中世纪,儿童甚至没有机会接触非自然符号记录的文化秘密;[3]在中国本土思想中,也不乏对儿童持有“不能比贤发其志”(《周易正义》)的看法。也就是说,儿童哲学确为略带牵强的“弱论证”,亟待成为拥有可靠支点①的“强论证”。因此,本文旨在以“否定性”为支点,为“儿童何以哲学”提供存在论辩护,并通过“否定性”的转化,明确儿童哲学的教育立场。
一、回顾与反思:儿童哲学的既有辩护
若以轴心时代为参照点,肇始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儿童哲学虽美名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华丽转身,但自李普曼20世纪70年代探索儿童哲学算起,也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也是晚近才有的现象。由此可见,儿童哲学无论在西方哲学史中,还是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中,都没有积淀已久的传统。事实上,儿童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普曼对当时美国学校教育的深刻反思。他认为,囫囵吞枣的灌输式教育对儿童思维塑造并无益处,儿童成年后容易思维定型和僵化,从而失去应有的创造能力。有感于此,李普曼认为,正如不存在补救性医学,形成良好思维也无法诉诸补救性教育,唯有通过重新设计,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4]
李普曼的初衷是“教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使其落实到操作层面,主要体现为帮助儿童掌握与哲学相关的思维能力。并且,他笃定哲学足以充当知识的内容和载体,“所谓的‘儿童哲学’代表一种努力,促使其承担作为教育的功能”。[5]对思维可教性的确信,是李普曼儿童哲学的辩护思路。经过长时间摸索,他在《教育中的思维》中形成了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创造性思考(creative thinking)和关怀性思考(caring thinking)的思维目标。在李普曼看来,“儿童哲学不是要把孩子变成哲学家或者决策者,而是帮助他们变得更有思想,更深思熟虑,更理性”。[6]如此,不仅能复归儿童理性发展的传统教育目标,并且,思维本质上是对话在心灵的显现,因而还能“全力帮助儿童去发现、获得与自己生活经历的意义”。[7]
与李普曼同处一个时代的马修斯,他试图改造哲学的刻板标签,认为儿童和哲学具有亲缘性,坚信“儿童有哲学”(Philosophy by Children),每个孩子都有萌发哲学倾向的天性。与李普曼儿童哲学不同,马修斯指出,儿童哲学的价值不能局限在开发思维的工具性方面,他更加强调“从关注儿童哲学对话的形式和结果到关注儿童哲学本身;从工具性的思维重新回到哲学的思维”。[8]在马修斯看来,儿童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构建的朴素观念,足够为儿童哲学辩护。成年人研究的所谓哲学,其目的是解决人类认知能力和道德能力遭遇的不同挑战,而这些挑战,在幼小儿童的思考中同样有所体现。[9]在马修斯眼中,这和哲学精神从根本上是相通的。
美国学者里德(Reed,R.)和约翰(John,T.)将李普曼和马修斯划分为儿童哲学运动的第一代人,接续他们研究的后来学者则被称为第二代人,当前儿童哲学的活跃研究者则自称为第三代人或第四代人。第二代儿童哲学试图在第一代人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主张塑造儿童健全理性失之偏颇,但也不能就此走向儿童天然有哲学的极端。由此,儿童哲学的辩护实现了某种转向,第二代人更多地基于伦理关怀,强调成人站在儿童立场替儿童着想,维护儿童利益,与儿童共同参与、平等交流,成人要和儿童共同“做哲学”(Philosophy with Children)。借鉴有学者划分的儿童哲学研究的基本层次,[10]我们认为,对儿童哲学的辩护思路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思路是关于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即将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主要是基于哲学立场对儿童和童年进行价值论辩护;第二种思路是为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for and with Children),主要是讨论成人如何将哲学教给儿童的认识论辩护;第三层则是儿童提出的哲学(Philosophy by Children),即儿童能够提出自己的哲学问题,创造非传统的哲学形态,成为儿童哲学家的方法论辩护。
在当代语境中,儿童哲学辩护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样态可谓百花齐放。在理论范式上,后续研究者倾向将儿童哲学视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形态,或者是当代哲学多元样态的一种。因此,他们批判性超越了前辈的分析框架,通过广泛借鉴后现代的哲学资源,形成了儿童哲学辩护思路的扩展。一是以福柯(Foucault,M.)、奈格里(Negri,A.)等人的生命政治学作为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的理性化水平越来越高,逐渐遮蔽了生活世界本来面貌。值此境遇,儿童象征着生命最本真的面目,因而儿童哲学构成抵制、防御甚至战胜权力支配的出路。二是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解读儿童,从而改变哲学中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转向将知识作为一种意义不断变更的文本,儿童哲学旨在引向儿童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构建。[11]循此取向,当前愈发强调儿童哲学不是让儿童掌握既定的哲学知识,否则,儿童哲学不过是成人强加给儿童的负担,并没有体现出儿童对自己的要求,遮蔽了儿童哲学的本真性。在这种价值诉求下,儿童哲学更多的是让儿童过上一种有哲学意义的生活。
在实践样态上,李普曼作为儿童哲学的公认奠基人,由他设置的儿童哲学科目是最初的实践模式。他将哲学看作可以利用的资源与手段,诉诸系统的教材编纂、配套的课程开发和相应的师资培训,用以提升儿童的思维品质。不过,这种想法附带浓厚的理想色彩,面临重重困境,难以实现。之后的研究者尝试突破儿童哲学的科目化倾向,开展了多元化、立体式的实践探索。在当下际遇中,国内外的学者都意识到儿童哲学的实践重心在于走本土化路线,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学校的特色开展儿童哲学。比如夏威夷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 Hawaii),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形成了温和的苏格拉底式探究、使用团体球探究、香草冰激凌和不急于到达任何地方的成熟模式。[12]在丹麦,丰富的童话资源是儿童哲学的天然文化宝库。在我国,儿童哲学经历了从“科目”到“方法”的转变,比如作为学科教学的方法,儿童哲学能够整合不同学科中内蕴的观念、现象和经验,使其上升到更为一般的哲学问题。除了渗透学科教学,有学校将儿童哲学耦合教育戏剧,通过隐喻与身体的双向互动,让儿童在戏剧体验中“做哲学”。[13]诸如此类儿童哲学的多元探索,正在越来越受到具体实践的青睐。
二、诘难与纷争:儿童哲学的身份疑案
以往对儿童哲学的辩护并非一无是处,不论是对思维可教性的确信,还是试图对哲学面貌的改造,或是承认儿童能构建自己的哲学形态,这些观点都是当代哲学和教育改革走向深化实践、回归生活世界的必然产物。然而,传统的辩护思路看似有理,实则存在漏洞,因为这些辩护统统只是回答了儿童哲学作为一个功能性概念的必要性,却没有能够解决“儿童何以哲学”的身份疑案。由这一疑案衍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引发了各种诘难与纷争。统而观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位模糊:儿童哲学的立论前提是理论构建还是教育应用?
20世纪末以来,儿童哲学研究异军突起。时至今日,其所能发挥的育人功能越来越受到实践工作者的认同。李普曼将理智能力的改善作为儿童哲学的目的,比较侧重于教育外铄论。马修斯则从有别于成人认知立场出发,凸显回归儿童本身的哲学价值,未曾脱离教育内发论的范畴。在后续发展中,第一代人开创的两种不同立论思路,又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域和价值链。然而,儿童哲学发展至今,这一概念本身却始终处于未定性认识和留白化态度的境遇。从知识考古学(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的立场分析,对儿童哲学的言说,从未实现将现实转变为语言符号,使语言符号真正契合事物本身的意图。[14]当然这种困境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儿童哲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含糊其词。因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儿童哲学都面临重要的挑战。
在理论层面,儿童哲学试图效仿哲学,却难以企及哲学立论的严谨性。与诉诸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澄清语言用法的分析哲学、聚焦人为秩序的政治哲学等哲学分支相比,儿童哲学不仅缺乏立足的关键论域,而且没有分析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导致其难以构建逻辑自洽的解释方式。在实践层面,儿童哲学有意拉拢教育学,却又和教育哲学暧昧不清,在现实中,其表征为一种哲学—教育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与实践,但又止步于将儿童哲学发展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校课程或科目。[15]质言之,在理论构建还是教育应用的定位问题上,儿童哲学依旧模糊不清、左右摇摆。作为后起之秀的儿童哲学,如果不解决这个前提性问题,就会陷入既难以寻求(教育)哲学的理论认同,又无法对接教育实践的“悬浮态势”。即使后来研究者将其视为“方法”,倡导成人与儿童共同“做哲学”,同样未能确定儿童哲学“事出有因”的“硬核”①②在何处,更无法判断儿童哲学“意欲何为”的“边界”在哪里。
(二)层次混淆:儿童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般儿童还是个别儿童?
“毫无疑问,孩子实际上并不从事任何哲学的工作,因为他从来没有试图将自己的思考编撰成一个体系。”[16]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哲学一向是理性的事业,思想的探索,智慧的寻求,但若以此为标准衡量儿童哲学则不够公允。其中的道理是,儿童哲学立论前提之所以受到质疑,错不在儿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混淆了儿童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确切地说,定位于(教育)哲学层面的儿童哲学研究对象,指向形而上学的“一般儿童”,它将儿童视为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在这里“存在”是主语,儿童则作为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且提示了澄明“存在”的道路与方法。通过解读儿童与存在的深层次关系,我们得以寻觅被遗忘和遮蔽的“存在”本身。用海德格尔(Heidegger,M.)的话来表达,即“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被规定,而同时却不必已经有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可供利用”。[17]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到尼采(Nietzsche,F.W.)再到阿甘本(Agamben,G.),他们不约而同地昭示出儿童的形而上学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将儿童视为成人的根据、世界的原型甚至时间的化身。
与此不同,定位于教育实践层面的儿童哲学对象,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体而生动的儿童,此时,若将“一般儿童”概念为参照系裁剪以“个别儿童”为单位的真实教育活动,难免会出现不同层面的儿童哲学研究,既无法“对号入座”,也不能“立即生效”,殃及整个儿童哲学,使其被诟病为劳而无功的“蹩脚程序”。[18]作为人类思维的定式,在经验生活中,我们更倾向以“个别儿童”为单位去理解儿童。但这种看待儿童的惯习,并不意味着开展“一般儿童”的研究是毫无建树的,更不是支撑我们选择对儿童形而上学视而不见,对儿童进行哲学刻画的不以为然的理由。原因在于,不同层次的儿童哲学研究都能切中对儿童真理性认识的一部分,但无论何种层次的认识,都不意味着等同于真理本身。在此意义上说,儿童形而上学与儿童真实样态之间的研究层次混淆,是我们误读儿童哲学的重要原因。
(三)两副面孔:儿童哲学的价值旨趣是权宜之计还是普遍兼容?
实际上,儿童哲学之所以能引起拥趸,源于人们试图探寻某种可以让哲学变得平易近人的、可供操作的“加工方式”,这使得理性尚未健全的儿童可以“轻易上手”。于是,未经认真推敲、匆忙登上历史舞台的儿童哲学,似乎提供了实现这种可能的路径操练。这是说,儿童哲学更多地蕴含着一种“权宜之计”的意味。其积极意义在于,让人们燃起破除教育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希望,或者说,它为教育拯救日益枯萎的儿童生活留有发挥余地。作为“权宜之计”的儿童哲学,敏锐捕捉到成人文明对儿童世界的“摧残”,提醒成人重视儿童地位。并且,这种旨趣的儿童哲学并没有偏袒其中任何一方,而是试图以儿童为突破口,呼唤对儿童本性的关注,改变成人对儿童的偏见和傲慢,旨在调和弱势儿童与强势成人的价值冲突,为教育尊重儿童的诉求筹划行动方案,在此基础上为拯救时代的精神状况提供处方。诚如雅斯贝尔斯(Jaspers,K.)所言,“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19]
继承浪漫主义传统的儿童哲学则不同,它并不满足于发现儿童,更为显著地包含着一种普遍的价值诉求,即儿童以及儿童所代表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最理想的、最好的生活方式。[20]其逻辑在于,我们如此强调儿童拥有和成人相等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是在指责成人是儿童失落的罪魁祸首。这一点不难论证,因为倘若成人文明不至于糟糕透顶,理应作为儿童的成长榜样,毕竟儿童无法更改通往成人的命运。问题在于,无论我们怎样承认儿童地位,儿童也不可能脱离成人去野蛮生长,甚至没有成人的参与,难以言说儿童的教育。所以,这种价值诉求的儿童哲学,其弦外之音更多的是在表达,儿童哲学拥有“普遍兼容”成人文明的能力,成人需要被儿童救赎,对儿童要放下身段并心怀敬畏。比较而言,它们各自诉诸的逻辑不同,前者偏重理性认同,寻求妥善的教育安排;后者因颠覆“成人霸权”的价值判断,更易引起情感共鸣。遗憾的是,这两幅不同面孔的儿童哲学,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儿童哲学的价值旨趣难免笼罩着层层迷雾。
三、否定性的支点:儿童哲学的存在论修正
儿童哲学的兴起有其深刻动因,它意图端正“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21]既然儿童哲学初衷是好的,那么它为何处于支离破碎的境地,说到底,是因为我们错失了对其的存在论辩护。所谓存在论辩护,指的是按照儿童与哲学本身具有的逻辑关系去理解,并非将其递归为训练思维或改造哲学等人为规定的方面。结合这一点,我们澄清“儿童何以哲学”的原因,其实是在考察哲学如何于儿童生命成长中呈现自发涌现的态势。也就是说,这种“原本如此”的态势是哲学在儿童个体成人历程中的固有动力,并不以人为因素为转移。明乎此,我们需要寻找贯穿儿童成人之路上“始终在场”的存在论支点,这构成“儿童何以哲学”的依据,这个支点我们将其锁定为“否定性”。
(一)问题分叉:否定性奠定儿童的生成性
将否定性判定为儿童何以哲学的支点,并非一个空穴来风的论断。实质上,否定性内蕴儿童个体成人的存在奥秘。思想史上,斯宾诺莎(Spinoza,B.)最早提出了“一切规定皆是否定”的命题,之后黑格尔(Hegel,G.W.F.)、马尔库塞(Marcuse,H.)等哲学家都曾挑明,哲学对经验世界概念化产物的思考是以否定(性)为依据的。[22]作为个体成人的重要阶段,本性的充分舒展与感性自我的发现,奏响了童年的主旋律。儿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会不断质疑周遭世界(自在存在)“是其所是”的规定,逐渐拥有一个精神世界,朝向自为存在迈进。自我意识根植于自为存在,一旦儿童拥有自我意识,即使相对微弱,他都不再只是机械地对外界作出反应,而是开始对一切实在和非实在的现象,产生好奇并进行思考。这种由好奇去思考而产生的疑问,通常在成人看来是幼稚可笑的“童言无忌”。但在存在论意义上,这些疑问的性质,原发于儿童在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将一切“是其所是”的自在存在,超越为“是其所不是”,也就是说,这确为儿童积极过问和主动寻觅自己存在的表现。
并且,最早的哲学确实出自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因好奇而思考的哲学家不是以某种实用性为目的的,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满足,仅此而已。[23]对于儿童而言,好奇是生命的感性冲动,并非后天的理性琢磨,所以“进行哲学思考是天生的本能,就与从事音乐和做游戏一样,这是人成长为人的一个重要部分。”[24]正是看到这点,马修斯的儿童哲学诉诸哲学并非成人特权,哲学起源于好奇,儿童好奇心更盛,所以儿童有哲学的论证思路。然而,我们不能因哲学始于好奇,儿童会因好奇而提问,直接将儿童和哲学画等号。[25]实际上,儿童有哲学的论调更多是为了赞美儿童的天性烂漫,经不起严谨的哲学推敲,并不能掩饰他将儿童有好奇心的论据偷换为儿童有哲学的结论。正如波兹曼(Postman,N.)所言,好奇固然是儿童天性,但其发展却有赖于清楚地揭示好奇所催生的问题之为问题的秘密。[26]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何由好奇而来的问题得以勾连哲学,进而在存在论深处观照儿童生命成长。
循此思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Sartre,J?鄄P.)为我们指明,“任何问题都假设了一个提问的存在和一个被提问的存在”。[27]自在存在“是其所是”的性质,决定它不能充当“提问的存在”,它对自身没有隐瞒,对外界没有疑问,这个“提问的存在”只能是人的存在。也就是说,问题只能由人来提出,提出问题是人独有的能力。但是,对问题的回答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但问题必定是分叉的,仅有肯定回答的问题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成立,问题也就消失,人也就退场了。这表明,问题内蕴对其“否定”的永恒在场性,反证唯有人的存在具有否定的功能。在萨特看来,人所拥有“否定”能力正是“虚无”的表现,“这意味存在先于虚无并为虚无奠定了基础”,[28]人借助否定的虚无才能降临世界。正因否定性的显现,儿童能够进入与现实处境的联系之中,将自身和周遭世界以问题的形式提出。这意味着儿童不会满足于只是肯定的答案,他不会被某种“实体”所规定,反倒是以否定的姿态去不断超越,从而获得对自身存在的领会,由此奠定了儿童个体成人历程具有持续生成性的存在论基础。
(二)众妙之门:否定性开启儿童的可能性
李普曼儿童哲学强调思维能力,其实算不上一件多么新鲜的事。杜威(Dewey,J.)很早就论述过,“如果我们的学校造就出来的学生,在他们遇到的各类事务中,其思维态度能有助于作出良好判断,那就比学生单纯拥有大量知识,或者在专门学科分支中具有高度技能要好得多”。[29]于是,他主张“做中学”,通过“经验的不断改造”,达到提升思维的目标。与此不同,李普曼则认为,哲学足以充当训练思维的工具,通过设立独立科目,开发相应教材,哲学可以直接教授给儿童。我们知道,李普曼本人提出三个C的思维目标,后续研究者又增添了合作性思维(cooperative thinking),由此四C思维成为其儿童哲学的代名词。尽管李普曼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对他的诘难却有增无gTdr5wtzUOqcLsYHRWuRQ50UZfgRTGa37T4PEyTSh1s=减:为何选择哲学而不是科学去塑造思维?选择四个C思维作为目标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如何证明四个C思维目标最适合儿童?拥有四个C思维究竟对儿童个体成人有何裨益?儿童在生活中有何种表现才算得上没有思维僵化?
事实上,哲学的确能训练儿童理性思维,但最显著的好处,莫过于能让儿童避免做错事。应该说明,理性在避免错误上的贡献和发现真理同等重要,遗憾的是,人们通常对理性的这种功能熟视无睹。货真价实的思维训练目标,定位在“启导”③孩子掌握哲学思维的功夫。因为哲学思维并非对任何事情都有用,有用的是揭示各种复杂观念背后的“元”(meta?鄄)思维。[30]按照中国的说法,元思维实乃“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它是贯通各种分门别类道理的“大道理”,得道者相当于拥有触类旁通的能力,而开启元思维的密码,实乃否定性内蕴的可能性,这构成四个C思维相通的底层逻辑。李普曼虽有所涉及,但更多地笃定思维的可教性,并没有更进一步。毕竟他当初提出儿童哲学,目光聚焦在如何解决大学生学习动力缺乏的问题,所以儿童哲学的存在论问题恐怕不是他的考虑重点。还有,哲学本身并非知识,“孺子可教”的不是知识,实乃思维的功夫,由哲学掌管的知识已让位科学,退化为哲学的认识论视域。企图将哲学作为知识去教给儿童从而训练思维,很大程度上注定是成人的美好想象罢了。
正因如此,赵汀阳指出否定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哲学词汇,[31]同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否定性是解码所有哲学思维的众妙之门。就此而言,既然哲学思维的用处,不能局限在发现必然性真理的部分,那么对儿童个体成人来说,它恰恰要立足于理性的另一面,即启导他们更为审慎地选择,而不是被本能冲昏头脑。毫无疑问,选择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时刻都在经历的问题分叉。在看似稀松平常的选择中,体现着思维的能力和知识的水平,构成生命的有限性在现实中伸展出无限可能性的路径。由存在论意义上来说,选择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选择需要理由,理由需要求证,求证即证明这个做法是更好的选择。由此挑明,儿童在选择中得以主动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求证意味着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复数可能性。论及至此,我们可以对否定性的功劳下个判断,它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同时,又通达每个儿童具体而生动的存在。这意味着,儿童本身没有什么本质可言,因而其成人历程并不服从既定的线性安排,既不是复刻过去经验的产物,也不为因果必然性所支配,而是始终伴随着否定性开启的可能性。
(三)事情发生:否定性标识儿童的及物性
马修斯指认儿童有哲学思考能力,但其证明方式却是动用哲学史的资源,与儿童貌似有哲学的各种表现进行类比,他记录在《哲学与幼童》中的案例就是这么操作的。实质上,马修斯的方向对了,但步骤错了,这种简单枚举的做法是一种成人伪造的儿童哲学,并没有撕下成人的商标,更没有体现成人的合理作用。换句话说,鼓吹儿童是哲学家之类的论调,其娱乐性超过了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儿童哲学的价值。此外,儿童哲学倡导者普遍主张设置课程或科目去发展儿童哲学思考能力,这对一线的教育实践者满足考核要求而言,或许打开了方便法门,但就儿童个体成人来说,这一方便法门却并不方便。一旦把握不当,还会弄巧成拙地导致儿童思维过度工具化,孩子在童心未泯之际,容易成为卢梭口中那些“年纪轻轻的博士”“老态龙钟的儿童”。基于此,凸显否定性的功能极其重要,以至于如果切断了这点,我们便难以判断儿童是否成为主体性的人,更难以处理儿童与成人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自为乃否定的涌现,是自我意识的基础,而意识只有通过主动揭示对象才得以确立。“它无影无象,却又不甘寂寞、四处游荡;它是无,却是个待填塞的空谷,总是对存在有所要求;它的神游,所到之处,全然没有任何企划,却又使世界生辉。”[32]意识的意向性原理表明,儿童并非受成人摆布的抽象名词,相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及物动词。其中,儿童的及物性由否定性所标识,因为否定性奠定了儿童在“问题分叉”中的生成性,而名词并不必然蕴含问题,动词则一定产生问题,[33]儿童哲学应始终粘贴在动词思维而非名词思维上。另外,儿童选择的自由同样由意向性赋予,进一步使得行动的可能性涌现。选择与行动之间不可割裂,如果否定性内蕴的及物性,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而不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不过是对儿童的生成性和可能性开具空头支票,否定性会沦为一无所有的空无,那么,儿童就和自在存在没有多大区别,相当于给自为意识戴上了镣铐。[34]在此意义上来说,儿童的自我意识尚未定型,自为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自在的界限,儿童自我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天性的无限。
在通往成人的道路上,儿童可选择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每一件事情,行动的作用即让事情得以发生。所谓让事情发生,它指向儿童立足行动或实践,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交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成人的世界是一个事的世界,若不是置于事中,物(自在存在)只是由知识封闭的必然性概念,仅仅是“事物”而已。它暗中屏蔽了某物置于事中,因人的参与而成为“事情”,所能显现“是其所不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某物的生活意义远远大于某物的知识论意义。[35]否定性是让事情发生的存在论宿命,更是儿童选择与行动的及物性规定。正是在事之境遇中,将儿童把握为动词的下一步还是动词,儿童得以在动词中实现存在,在动词中释放天性可能,象征永无止境的人生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否定性标识了儿童“做事成人”的及物性,它承认儿童“做”事情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有创造性的,不论“做”的事情是什么,儿童都能够从“做”的方式中领会“事情”的意义,并将自己作为意义的参与者加以肯定,达成对自身存在的认同。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纠正成人的傲慢与偏见,同时,在避免儿童出于本能而做错事的方面,为教育(者)促进儿童个体成长的使命留有发挥空间。
四、否定性的转化:儿童哲学的教育立场
以否定性为支点的儿童哲学,提供了儿童何以哲学的存在论辩护。这种“强论证”揭示了儿童生命中自发涌现的哲学态势,由否定性统摄而来的生成性、可能性和及物性,证明了哲学不是外在于儿童、提前预设目标的工具,而是构成儿童个体成人的固有动力。如此一来,引领儿童个体成人是儿童哲学确认身份的重要线索。如果这点成立,那么这种自发态势要想生效为儿童哲学,必须经由一定的中间环节。对此,无论从个体成人还是从公共生活的层面,教育都构成儿童利益或福祉的重要方面。[36]显然,儿童个体“成人”并非生理意义上的成熟,而是教育作用于这种自发态势的共同结果,以期造就“受过教育的人”(An educated man)。结果到底如何,不能完全指望儿童有限的自我教育能力,更多的时候是成人承担教育(者)的功能。这要求成人更加审慎地识别、呵护、培育儿童个体成人历程中的哲学态势。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否定性是进行这种转化的“配方”,由此才能明确儿童哲学的教育立场。
(一)重视儿童身体价值,超越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
自古希腊起,理性乃至高无上的存在。柏拉图认为,卑贱的身体欲望构成高贵理性思考的障碍,表达了对身体的古老敌意。近代以降,特别是“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原则,加剧了身体与心智的二元对立,身体更是在“我思”光环下难寻踪迹。受此影响,儿童的人性假设是尚未成熟的理性人,教育的任务是塑造其健全理性,由此儿童成为认识论的理性材料,身体价值逐渐退场。然而,儿童的及物性指明,生命和身体不分,乃意向性原理生效的前提,否则通过行动让事情发生的功能,将沦为纯粹主观层面的空话。身体缺位的儿童形象由来已久,它将理性主义抬高为唯一正当的认识方式,儿童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进一步催生“应试教育”。这种境遇在数字化时代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儿童与世界相处的意义探寻,由于技术物的控制,被降格为单方面信息接收的精神废黜。[37]结果正如杜威所言,儿童有了两个断片:一方面是单纯的身体活动,另一方面是靠“精神”活动直接领会的意义。[38]
进化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意识中凝聚着漫长生物进化遗存而来的本能趋向和普遍心理机制。[39]这种强大能量会激发儿童用身体表达自我,推动儿童积极地体验和探索,并且乐于和他者分享自己的发现。[40]身体现象学的研究同样证实,“儿童在任何逻辑构造之前,就已经理解了身体和使用物品的人类意义,或者语言的含义价值,因为他自身就已经开始了把他们的意义赋予语词和身势的活动”。[41]由此可知,身体是儿童认识世界的源初性规定,蕴含附加值的及物性力量,哪里有要做的事情,我的身体就出现在哪里。某种程度上而言,身体甚至是儿童作为“弱者”抵抗成人暴力的“武器”。[42]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蒙,人之初,非性之昧”。[43]“蒙”和“昧”不是同一个意思,儿童蒙而不昧,所谓蒙昧无知,实为成人自诩能对儿童化愚为智的优越。“蒙”通“萌”,儿童是生命的起点,天地的精灵,幼稚的身体内蕴生生之灵动,包含化蒙为圣的无限可能性。[44]在身体经验面前,健全的理性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休止于知识的必然性。相反,身体是儿童与世界相遇的开始,充盈着无限可能性的生命律动。
(二)避免儿童角色固化,提供多重体验的做事承担
在现代社会,儿童利益不仅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在成人观念中也日趋常识化。为了儿童成长而专门设计的学校,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育人功能,被视为儿童个体成人的最佳场所。然而,随着社会对儿童的照料走向制度化、同质化和规范化的轨道,[45]破坏了维持成人与儿童关系的张力,导致限制儿童的状况更为尤甚。在这方面,学校作为国家权力承认的教育机构,在性质上是对儿童施以标准化要求的合法场域。吊诡之处在于,以父母为代表的成人对孩子的爱与厚望,经过学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么被稀释为一种不够专业的教育,要么被催化为一种规范性质的支配性力量,造成儿童新的生存困境。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Ariès,P.)在《儿童的世纪》中指出,学校最致命的缺陷是将儿童与他们自然成长的社会环境隔离,由学校制定的良好教育的蓝图,“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死人打交道,而不是和活人打交道,和书本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和活生生的人生活在一起”。[46]言外之意在于,学校暗地里捏造了“与书本为伍”的教育标准。并且,这一标准有权越过边界去约束“非学校化”时空的教育生活,而由学校指派给儿童的学生角色,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由和载体。
“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7]当儿童个体成人历程受到学校意志的束缚,儿童的自我认同可能会因此收敛为学生角色。并且,该角色由国家“委托”学校指派给儿童,附带强制性质,除非违法辍学,否则难以抗命。作为隐而不彰的权力渗透,学校诉诸包括奖赏制度、纪律规章、仪式互动等在内的规范体系和价值期待,以便让儿童适应学生角色的要求。此外,通过同龄人聚集的机制组织儿童生活,不同个性的儿童得到相同的学生角色,但只有符合学校标准的儿童才是“好学生”。当固化的学生角色遮蔽了儿童生活中其他角色的典型性,就会催生被制度化学生人格占有的儿童形象。然而无论怎样,任何角色都不能和儿童的存在等同,儿童也无法永远只扮演一种角色。角色是经验的载体,不同角色意味着不同做事方式,儿童是从做事经验中不断习得向前的生成性力量,其个体成人历程是在不同角色的做事承担中实现的。正因儿童的最大特性在于未定型,具有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固化于一种角色,或许会在某些方面非常成功,但就个体成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桎梏。[48]
(三)厚植儿童生命力量,寻求自然与人为的相对平衡
卢梭指出,人的教育无外乎三种,分别是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和人为的教育。其中,“自然的教育完全不能由我决定的;事物的教育中人在有些方面能够由我们决定;只有人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地加以控制的”。[49]就此而言,所有儿童哲学的主张都属于人为教育。可是,人为教育想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儿童生命力量的丰盈与充沛,因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50]换言之,自发涌现的哲学态势根植于儿童的生命自然,“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因而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么遥远”。[51]当然,也不是每个儿童生来都是“天使”,还有可能存在“魔鬼”的一面,某些年岁尚浅的孩子作恶手段之歹毒,就连成人都难以想象。在这一点上,旨在改善或干预儿童成长的人为教育,起着关键作用。人为教育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其背后社会因素的强制性法则,会导致儿童过度地受到外来意志的围剿,其个体成人历程逐渐变得模式化、流程化、封闭化。对此,有先见之明的康德(Kant,I.)就说过,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怎样才能把服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52]
“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也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53]目前,被理性化和世俗化诉求过度渲染的教育,表面上对儿童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其实具有实足的封闭性。成人意志的教育设计过早地介入儿童生活世界,促逼着孩子从小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这导致儿童的生命褪去了自然的底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教育的牺牲品。然而,儿童终究无法抗拒成人的命运,抛去别的不谈,成人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意味着过一种公共生活,势必要对儿童提出社会化要求。但我们不应遗忘,这种社会化要求的目的是“让青年人懂得如何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只有按照自己的地位生活,才能保持自己原本的天性”。[54]那么,人为教育如何寻求自然与人为的平衡才是有效的呢?在此,否定性转化而来的儿童哲学提供了重要线索:一方面教育的合理引领构成儿童“适性扬才”的有效路径,能够改善儿童成长中的不良势头,为人为教育寻获儿童生命自然中的可能性拓展生长点;另一方面,人为教育作为沟通儿童自然与自由的桥梁,[55]不能扼杀儿童生命自发涌现的哲学态势,以期孕育儿童未来成人历程的多样性。这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儿童哲学成全自身、救赎教育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第一哲学”的问题,原指形而上学。在哲学发展历程中,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在寻找最可靠的(最好是唯一可靠)的第一哲学的支点,从而达到普遍有效地思考问题的目的。从古希腊的逻各斯到中世纪的上帝,再到近代的笛卡尔原则和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产生了轮流坐庄的各种第一哲学的支点。此部分可参见: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M].北京:三联书店,2017。受此启发,本文提出以“否定性”作为儿童哲学的支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图:其一是为“儿童何以哲学”提供一种存在论的解释。文章试图论证,哲学是儿童生命的自发态势和固有动力。只有将儿童哲学的论域与使命定位在儿童个体成人上,儿童哲学才能确认自身身份。其中,“否定性”是贯穿儿童哲学这一使命的有效支点,构成儿童哲学分析问题的独特立足点,也是避免“成人哲学”乔装为“儿童哲学”的内在线索。其二是如果我们确认引领儿童个体成人是儿童哲学成立的前提,那么,这种哲学态势就需要经过教育转化才能生效为儿童哲学。“否定性”正是进行这种转化的“配方”,由此得以明确儿童哲学的教育立场。
②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Lakatos, I.)认为,硬核(hard core)是研究科学理论发展的核心和本质,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是牛顿力学的硬核。一旦“硬核”遭到推翻和反驳,那么整个科学理论将要面临被彻底否定乃至退场的风险。参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③为了更好地体现教育的作用,这里参照彼得斯“教育”作为“启导”的理解,详情参见:孙嘉蔚,张晓月.“教育”作为“启导”——基于彼得斯(R.S. Peters)教育概念的考察[J].全球教育展望,2023,52(3):74-86.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儿童学:进入现代教育学必经的门槛[J].上海教育科研,2023(05):1-8.
[2]程亮.儿童何以成为“问题”[J].基础教育,2021,18(4):1.
[3][26][53]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3,122,2.
[4][6][7]李普曼.教室里的哲学[M].张爱玲,张爱维,译.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3,13,13.
[5]LIPMAN M. The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IAPC)Program[C]//SAEEDNAJI R.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New York: Routledge,2017:4.
[8]白倩,于伟.马修斯儿童哲学的要旨与用境——对儿童哲学“工具主义”的反思[J].全球教育展望,2017,46(12):3-11.
[9]马修斯.童年哲学[M].刘晓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80.
[10]梅剑华,张端.从学习来认识人工智能哲学与儿童哲学对话的三个层次[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3,40(2):9-16.
[11]王澍.儿童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以李普曼为起点[J].教育研究,2019,40(6):70-80.
[12]冷璐.夏威夷儿童哲学的实践模式[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34(10):29-34.
[13]张阿赛,谢延龙.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3,39(12):53-60.
[14]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63.
[15]程亮.儿童哲学:从“科目”到“方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2(2):171-179.
[16]MURCHISON C. A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M]. Worchester: Clark University Press,1931:534.
[1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
[18]孙蓉鑫,陈乐乐.儿童形而上学存在的实现道路[J].教育学报,2023,19(4):16-27.
[19]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
[20]高伟.浪漫主义儿童哲学批判:儿童哲学的法权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7,46(12):12-23.
[21][49][51]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1,7,75.
[2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70.
[23]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2.
[24]马修斯.哲学与幼童[M].陈国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1.
[25]杨妍璐.儿童有没有哲学?——儿童哲学的本真性问题考察[J].浙江学刊,2022(04):133-140.
[27][28]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9,43.
[29]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83.
[30]赵汀阳.思维迷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
[31]赵汀阳.四种分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2.
[32]李凤.萨特说人的自由[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3.
[33]赵汀阳.寻找动词的形而上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rnsigOj+sctA4wZCcUrp0cHWzhy4NfIX6sjEFAT3F1o=店,2023:87.
[34]韦恩远.萨特论人的存在与教育的三重意蕴[J].现代教育论丛,2022(03):34-41.
[35]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201.
[36]程亮.儿童利益及其教育意义[J].教育研究,2018,39(3):20-26.
[37]孙蓉鑫,陈乐乐.培养儿童的“沉思之思”——技术统治时代超越技术两重性的可能路径[J].学前教育研究,2023(02):44-55.
[38]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4.
[39]荣格.未发现的自我[M].张敦福,赵蕾,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312.
[40]贺刚,黄进.儿童的绝对他异性及其教育蕴意——基于列维纳斯“他者哲学”视角[J].教育学报,2023,19(4):28-39.
[41]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54.
[42]徐冬青.指向塑造心灵秩序的儿童哲学[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2(2):165-170.
[43]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8:442.
[44]唐艳.尊天性而施教化——蒙卦儿童哲学意蕴阐发[J].周易研究,2022(01):34-38.
[45]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M].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162.
[46]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M].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90.
[4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7.
[48]高德胜.沉重的学生负担:角色的过度外溢及其后果[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0(12):14-25.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
[52]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
[54]李平沤.如歌的教育历程——卢梭《爱弥儿》如是说[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20.
[55]李长伟.沟通自然与自由的桥梁:康德儿童教育思想概说[J].学前教育研究,2023(10):26-38.
Taking “Negativity” as the Fulcrum: the Ontology Defense of
Children’s Philosophy
WEI Enyuan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ontological problem of children’s philosophy is the logical premise of children’s philosophy. The existing argumentation is difficult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defense, which leads to the identity problem of children’s philosophy, whose main features are: the vague orientation of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in the premise of argument; the confusion of the levels between general children and individual children in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expediency and the universal compatibility in the two faces of value purport. Through taking negation as the existential fulcrum,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negation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children’s generation in the“Problem bifurcation”, and expounds that negation is the“Wonderful door” that opens children’s possibility, the interpretation of negativity marks the transitivity of children’s “Making events happen” and clarifies that philosophy is the spontaneous state and inherent motive force of children’s individual adults. The negative transformation is the effective educational standpoint of children’s philosophy, which requires u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children’s physical value, to transcend the cognitive mode of rationalism, to avoid children’s role stereotyping, to provide multiple experiences of doing facts, to plant the life force of children and seek the relative balance between nature and man?鄄made world.
Key words: negativity; children; philosophy of children; ontology; education
(责任编辑:刘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