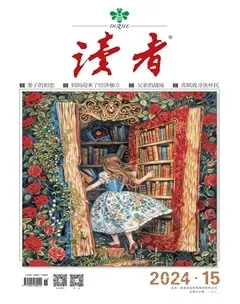妈妈迎来了经济独立
2024-07-29怀素

“我这个月的钱发下来了,一天没歇还比上个月少好几百块钱。夏天了,活少了,赚不到钱……”
微信消息提示音响起,点进去发现又是妈妈的多条语音“轰炸”。今天是妈妈的工资发放日,她详细地对我说着这个月的收入情况、工作感受,语气轻松而愉快。我也像以前一样,劝她多休息,身体不舒服就待在家里,不要和年轻工友们比工作量。当然,我知道这些话妈妈一句也不会听。
今年6月,妈妈迎来自己的56岁生日。她现在在我们市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已经一年有余,这也是她目前做过时间最长的一份有酬劳动。食品厂的主要业务是制作肉肠和淀粉肠,包括从鲜肉的加工处理到成品包装的全套流程。妈妈是包装工人,负责的工序是给肉肠串上木签。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工资计件发放,多劳多得,但单价极低,串完一盘香肠只能得到1.2元~1.8元,而一盘香肠足足有60个,还需要经过验收;虽然没有考勤要求,员工不来上班只需要在微信群里说一声即可,但也没有任何劳动保障,妈妈待了一年多,得到的唯一福利是过年时发放的一袋大米和50元红包;为了保障肉的新鲜,工作厂房的温度非常低,工人在其中长期劳作,嘴唇总是泛着紫色;尽管有员工食堂,但也只是每天中午提供两个馒头和一份炒素菜。正因如此,工厂常年处于缺人状态,包括妈妈在内,串签这道工序只有六七个人在做。
一年多以来,除非家里实在有事或者身体很不适,否则妈妈从来不休息,很多个月她都是满勤状态。为了抢到更多的活,她总是起得很早,早上六七点就已经到工作间了,晚上经常八九点才做完活骑车回家。工作时要穿防菌服,脱换很麻烦,为了避免上厕所耽误时间,妈妈很少在上班期间喝水,尿路感染和嘴唇干裂时常困扰着她,润唇膏用得非常快,隔段时间就会让我帮她购买。
但和手腕、腰椎的劳损相比,这还不算是对身体最严重的损伤。由于要不断重复串签的动作,妈妈才工作两个多月就患上了严重的腱鞘炎,不得不去医院做手术并休养。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站立,让妈妈在下班回家后总是连腰都直不起来,不停地贴膏药。长期与肉肠打交道,使得妈妈如她所戏称的那样“被腌入味了”,每天都要洗澡洗很久才能消除这种味道。
然而,对于这样一份工作,妈妈非常知足。我曾多次劝说她再去找份轻松些的工作,都被拒绝了。原因在于,在妈妈不惜气力的付出之下,这份工作每月能带给她三四千元的收入,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五千元,而同城其他的体力劳动者,比如包装工人,大多数的工资标准是70元一天。她愿意为了这份“高薪”的工作多吃苦,“能吃苦”是妈妈眼中自己具备的唯一优势。
妈妈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学会了一个时髦的词——经济独立。视频里的人总是语重心长地强调经济独立对女人的重要性,妈妈刷到的时候总是不停地表达着认同。这4个字,妈妈追求了一生,终于在本应该是女性法定退休的55岁时达成了。
我生在农村,自我记事以来,妈妈的身份就是家庭主妇,爸爸负责工作赚钱,她负责照顾我们姐弟二人,并打理家里的七八亩农田。之所以没有像村里其他家庭一样,夫妻二人外出务工,把孩子留给老人照顾,最重要的原因是,父母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而没有父母的监督,村里留守儿童在学业、习惯养成等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权衡再三,妈妈还是留在了家里,而爸爸的工作性质也使得他每隔三四天就能回家一次。
在这样的家庭分工之下,我和弟弟的学习成绩确实始终名列前茅,每次听到他人的夸赞时,妈妈脸上的骄傲都难以掩饰。但是,我们也能看出,妈妈对于工作赚钱是非常渴望的,她盼望着我们长大,盼望我们快点上大学,不再需要她的陪伴。
这份渴望背后的原因我们也是清楚的。首先,赚钱的人只有一个,却有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家里的经济情况一直都是非常窘迫的。看着邻居们建新房,甚至去市里买房买车,要强的妈妈也会发愁,总是反复盘算,家里的钱供我们上完大学之后,还有多少能用来支撑我们在工作地立足,乃至负担她和爸爸晚年的生活。
其次,妈妈是向往自由的。婚姻和育儿生活将她限制在灶台边和田间,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也不过是邻市。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到各处去看一看。与外出务工归来的其他街坊邻居聊天时,妈妈总是很羡慕她们有机会到大城市、到风景不一样的地方生活,哪怕到了那里,根本没机会享受生活。
多年来,妈妈对于新疆一直非常向往。每年一到棉花成熟季,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女性会去那里采摘棉花,勤勤恳恳地干上两个月,带回来数万元。妈妈不能去,不过她会根据其他人的描述,想象自己在那里劳动的情景。直到现在,妈妈仍然盘算着有朝一日到新疆去“狠狠地赚钱”,那也是在她的认知中,自己可能有机会去的最远的地方。
更令妈妈委屈的是,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爸爸的认可。
爸爸妈妈经常吵架,用“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来形容毫不夸张。在我印象中,吵到激动时,爸爸曾无数次对着妈妈吼“你吃我的喝我的,没有我,你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之类的话。
每到这时,妈妈的情绪都会瞬间被点燃,委屈而愤怒的泪水迅速流满她的脸颊,她也对着爸爸吼:“没有我照顾小孩,你能安心在外面赚钱?那你有本事请保姆吧,人家都能挣到钱,难道就我不能?家里的地每年还能收入一万多块钱呢。”可事态平息后,两个人又会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维持现有的家庭分工模式。
妈妈总说,她能看到爸爸的辛苦,爸爸却把她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因为工作性质,爸爸经常熬夜,当他回家休息时,妈妈会明令禁止我和弟弟打扰,甚至不允许我们靠近爸爸睡觉的房间。爸爸在外打来电话时,妈妈总是着急忙慌地赶着去接,说上许多句叮嘱的话,如果在约定的时间没有接到电话,妈妈就坐立难安。如果电话被我们接到了,事后妈妈就会详细询问我们,有没有说让爸爸注意安全和休息,如果忘记说了,妈妈就会念叨很久,要求我们下次一定记得说。
然而,在家的妈妈过得实在不轻松,除了总也做不完的繁重家务,地里的庄稼、人情往来也全都要她来操心。农忙时期,妈妈经常是天不亮就去了地里,到天黑透才满身灰尘地赶回家里,衣服都被汗水湿透,有时还夹杂着浓重的农药味和化肥味。没有作业时,我也会跟着妈妈下地,干上一会儿活我就觉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然而妈妈像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爸爸其实也能够意识到这些,可每次吵架,他还是会以妈妈没有“赚钱”而否定她的所有付出。
在这期间,妈妈也有过几段打工经历,但都没有维持多久,就总是因为担心我们的学业而中断。因此,妈妈格外不能容忍我们在学业上不上心。在她看来,我们的成绩就是她最重要的成就感来源,如果她受尽了委屈,我们却读不出名堂,那她的人生可谓毫无意义。从小听着这样的话语长大,我和弟弟也不敢不争气,因为觉得无法面对妈妈失望的眼神。
妈妈的记账习惯则始于我刚上小学时,同样是因为一次吵架风波。置办年货时,妈妈把那一年存下的钱拿出来,爸爸看到那薄薄的一沓钱,语气中带着指责和怀疑:“我一个月交给你几千块钱,到年底你却基本啥都不剩,你是咋花的?”
那次,整个春节期间爸爸妈妈都在冷战。过完年,妈妈就拿了一个厚本子,将每天的收支都记录在上面,无论数目大小。识字不多的她经常在记账时把我喊过来,让我工工整整地帮她记账,她要用白纸黑字有力地回击爸爸。她总是边记账,边感叹柴米油盐贵、人情重。
我们都上大学以后,妈妈也迈入了人生的第五个10年,家里的地我们不再自己耕种,而是承包给了种田大户。妈妈则见缝插针地开始了自己的务工生涯。
这时候,我和弟弟虽然还没有完全独立,但也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兼职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以减轻家里的压力。妈妈原本不需要那么辛苦,但好不容易自由来临,她绝对不愿放弃。工作对她来说,不仅仅是赚钱的手段,也是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你们现在也用不到我了,我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呢?”
时间最长的一次,妈妈跟随老家的几个熟人去了弟弟读书的城市务工。他们在工地上做小工,不仅工作强度非常大,而且收入不固定,有时候一天有几百元的收入,有时候则好几天接不到活儿。他们乘高铁来到务工地,每日出行则需要坐地铁,这是妈妈从未有过的经历。我也很难想象几乎没有出过远门的妈妈是怎样学会了过安检、候车、买地铁票的。当我问起来的时候,妈妈非常骄傲地表示,这没什么难的,自己跟在别人后面学了几次,就掌握了这些技能。
在这里,妈妈和一名女性亲戚合租,房租180元一个月,住了3个月。这么低的租金即使是在我的家乡,也很少听到,身在另一座城市的我无从得知妈妈住所的环境是多么恶劣。妈妈曾经给我发过图片,房间里除了一张床,没有其他家具,地上放着几个编织袋,装着她的衣物和其他行李,墙面和地面都非常斑驳,但被她打扫得挺干净,上厕所则需要到很远的公厕去。
由于距离近,弟弟去看过妈妈好几次。他非常难过,“难以想象在这座发达的城市里,居然还有这么破的地方存在”。透过妈妈的生活,我们认识到了繁华背后的另一面。
那3个月,妈妈一共攒下了近一万元,这是她省吃俭用,经常将一天的开支控制在10元以内的成果。当然,这些都是妈妈回来以后告诉我的。线上联系时,她对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就像我们对她一样。当面聊天时,妈妈也总是对这些辛苦轻描淡写,然而她大幅降低的体重和染得更勤的白发瞒不过我们。
生活虽然又累又苦,但是妈妈的精神状态好极了。在工地上有空闲的时候,她会拍一些视频,记录自己的打工生活,配文总是积极向上的。“只要心里有希望,再累也不算累”,妈妈总是这样说。
由于工地的收入实在不稳定,妈妈的常用药买起来也不方便,再加上挂念年迈的姥姥,妈妈的大城市之旅很快就结束了。她在年底回到了家乡,并且抱定要在老家找到合适工作的想法。
尽管如此,过年时,妈妈还是给她微信通信录里的包工头一个个发去了新年祝福,“万一来年我还去干活呢,发个祝福,叫人家想着还有个我,有活时叫我”,这是妈妈朴素的交际智慧。但是,消息发过去才发现,有几个包工头已经把她删除了,将近55岁的她已经属于“超龄农民工”。
过完年,妈妈每天念叨着要找工作,她实在是闲不住。于是,我开始陪着她“求职”。吃完早饭,我们带上身份证,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工业园区,看到厂房门口贴着招工信息就进去问,包括食品厂、玩具厂、药厂。大部分工厂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18岁~50岁之间,且不通融,尤其是工作强度比较低的。这是因为,这样的工作并不缺人做。
到了妈妈现在工作的这家食品厂,事情出现了转机。这是一家新办的工厂,非常缺人。看到妈妈身份证的时候,负责招聘的女孩还是有些犹豫。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妈妈反复向她说明自己“不怕吃苦”“干活麻利”,甚至提出可以试工一天。于是,女孩很快同意让妈妈入职。我们的找工作之旅,很幸运地半天就结束了。
回家的路上,妈妈显得非常激动,话特别多,一会儿担心后面来的人多了自己会被辞退,一会儿盘算着要把碍事的长头发剪掉。我也被她难得轻快的情绪感染了。办好健康证以后,妈妈很快就开始了自己早出晚归的务工生活。
第一天下班回来,妈妈感到了这份工作的不轻松,腰酸背疼的她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回到房间躺下了。一同去试工的同龄女性,有两个当即表示第二天不会再来了。然而当我建议重新找工作时,妈妈拒绝了,她觉得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且至少工资可观,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术,只要她不说不干了,老板也不会辞退她。她决定先干着,这一干就到了现在。
很快到了10号,妈妈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上面显示入账××××元。这个体验对妈妈来说新奇极了,人生第一次,她收到了工资汇款,满足感和安全感充盈着她的内心。她又兴奋地找了一个新的账本,这次是用来记录自己的收入情况。
虽然有了一份收入来源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一些习惯还是没有改变。妈妈还是非常节省,生活一贯简朴,由于大部分时间家里都只剩她一个人,于是她经常只简单吃点清粥和馒头。我教她学会了网购,但她很少在网上购物,衣服换来换去总是那几件,弟弟和我给她买的衣服、首饰,她总是放着不穿、不戴。
记得陪妈妈去找工作时,一个招聘经理以为我也是来应聘的,问我什么时候入职,妈妈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那可不是,这是我闺女,还在上学读书,和我不一样,她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来做这个。”跟在妈妈后面的我心头一酸。是的,妈妈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又像一根不停燃烧的蜡烛,榨干了自己所有的价值,只为了让我和弟弟变成和她不一样的人。
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萦绕在心头的愿望,我想带妈妈好好看一看辽阔而美丽的新疆,但不是以务工人员的身份,如今这个愿望,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大 浪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王 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