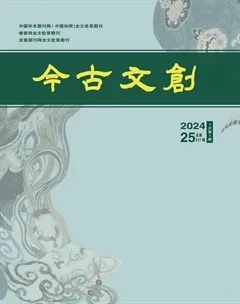氏、 氐考辩及相关字形的讹混
2024-07-25羊春秀

【摘要】“氏”之本义应为“根柢”义,《说文解字》对“氏”字的解释迂曲不可解。“响若氏隤”的本字应该为“ ”,“坻”与“坁”、“阺”与“ ”、“泜”与“汦”三组字存在着讹混情况,在修订第二版《汉语大字典》时应加以区分。
【关键词】氏;氐;讹混;《汉语大字典》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5-011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5.036
一、氏、氐关系
《说文》释“氏”为“巴蜀山名岸胁之旁箸落堕者曰氏,氏崩闻数百里,象形,乁声。凡氏之属皆从氏。杨雄赋响若氏隤。承旨切”[1]266。此说有几个疑点:第一,对字形的说解迂曲不可解。段注附会许慎之说曰:“谓 像傍于山胁也。”[2]628《说文解字诂林·氏》:“ 像岸胁之连于山者, 像旁箸之欲陊者,外像土石之边际,中像坼裂文也。”[3]5669此说不能令人信服。第二,“氏”字下属“氒”字,许慎解释为:“木本,从氏,大于末。读若厥。”从说解上看,“氒”字字义与部首“氏”没有任何关系,不符合许慎“以义系联”的原则。对此前人也有提及,如《说文解字诂林·氒》:“部属氒云大本,从氏,意于氏义无涉。”[3]5669第三,许慎所举例证不充分。《汉书》皆作“阺隤”[4]5122,李善注《文选》更作“坻隤”。[5]981段注引为“响若 隤”,我们认为此处“ ”为本字,为巴蜀方言词,本义为“大土山”,“山石欲坠者”应是许慎为附会杨雄文中用例而引申出来的解释,而“氏”字是作为“ ”的方言借音字来表“山石欲坠者”之义的,“氏”的本义为“根柢”。
《说文》中“柢”字释为“木根”,本字当为“氐”。《说文》释“氐”:“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凡氐之属皆从氐。”[1]266许慎所释为“氐”的引申义。关于“氏”“氐”的关系,前人也有不少认识,如章太炎《文始》曰:“疑氐本即氏字,旁转异音异形耳。”[3]5671《说文解字诂林·氏》:“氏当与氐同字,氏氐音稍变,故加一以别之。”[3]5670以上见解可谓精到,惜未能加详细论述,现将二字的源流论述如下:
从“氏”与“氐”的读音上来看,“氏”字在《广韵》中作“承纸切”,禅母支韵,“氐”音“典礼切”,端母脂韵,禅母字是从端组字分化而来的,二者读音在上古极为相近。从甲骨文字形上看,“氏”作 , ,可见“氏”字中间一横由增肥的指事符号演变而来,再看“氐”字金文作 ,正像“氏”字下增加一横。我们认为“氏”字甲骨文字形正像根柢之形,以指事符号指明本根之所在。正如《韩非》所言:“树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6]201“氏”的造意即为树木赖以生存的“直根”。而“氐”字则是为分担“氏”字负义而造出来的新字,下所增加的一横不表“地”之义,而是区别符号。在文字产生初期,祖先造字多以象形为主,随着语言的发展,文字的意义负担也越来越重,为了增加表义的准确性,古人往往在本字基础上增加区别符号或义符来表示本义,假借义或引申义,如“又”字本像手形,本义表示左右手,后来“又”又借来表示“再”这个虚词义,于是在本字的基础上增加区别符号“工”“口”而造“左”“右”字,表示左手右手,又引申为辅佐之义。“左”“右”又进一步表示方向义,则增加义符“人”而造“佐”“佑”二字专门表示“辅佐”之义。这种造字之例广泛存在于汉字之中,由此可见,“氏”与“氐”之间是存在着这种可能的,而且“氐”字一定是由“氏”字发展出来,这个契机当是“氏”字开始大量表示“氏族”之义时。这个时期应该很早,在现存文献中我们看不到“氏”用作本义的例证。很明显,“氏族”之义断不可能为其本义,按照许慎说解字形字义必有来历的传统,他只好迂曲其说来迎合杨雄赋中的例证了。
从“氏”与“氒”的关系来看,“氏”下属字“氒”刚好保留了“氏”字的本义。前人注意到了“氏”字与所属字“氒”意义的无关,因此认为“氒”字应该入“氐”部。许慎在排字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发现“氒”字跟“氐”部的字意义更近一点,况且许慎也并非死守字形之人,如日部“昏”字下许慎说解为:“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许慎正是发现了“氏”与“昏”义无关,才认定“氏”为“氐”之省。那么许慎完全也可以将“氒”解释为“从氐省”而入“氐”部,但他没有这么做,其后果是造成了“氒”字与“氏”部在意义上的矛盾,同时也给了我们发现真相的契机。“氒”字甲骨文作 ,应像木干与枝丫之形,故有“大于末”之说。下有增肥笔画以强调木干之所在,所以“氒”的本义是“木本”。“读若厥”注音兼含释义,容庚《金文编》:“氒为橛之古文。”[3]5671“橛”字本义为木桩,木桩舂物,正需要结实的木干来制作,与“氒”义相合。从甲骨文字形来看,“氒”字根本不从氏,而古人以会意之法造“氒”字,正说明“氏”字与木干义有联系。“氒”者木之本,“氏”者根之本,二者义通。
我们还可以从字族的比较中找到“氏”为“氐”的本字,本义为“根柢”的证据。《说文》中收录了十二个从氏得声的形声字,其中“祇”释为“地祇”,地神也;“芪”释为“芪母”,是一种根茎入药的植物。此二字正是“氏”为 “根柢”义的明证。由“地下之根”引申为止也,如“汦”释“着止也”;“坁”释“箸也”;“纸”释“絮一苫也”——按段玉裁之说,“苫”应为“ ”,“潎絮箦也”,“潎”者,“于水中击絮也”,可见“纸”的造法是将击打后的碎絮附着在 上,也带有“着止”义;“軝”释“长毂之軝也”,是一种缠缚在車毂上的装饰;“疧”释“病也”,带有病加于身的含义;“忯”释“爱也”,是情感的附加;“䟗”释“尌也”,“尌”者“树立”也,着于地面。以上几字都有附着义。“附着”义又可引申为“触击”义,如“扺”释“侧击”义,引申过程为:根柢义→着止义→触击义。由此可见,从“根柢”义出发,就能统摄从“氏”得声的整个字族,也反过来印证其本义不误。“氏”字的本义保留在从“氏”的字族之中,而“氏”字本身却专门用来表示“氏族”之义。“氏族”是靠血缘关系形成的组织,其成员都供奉同一个祖先,也体现了“根柢”之义。
再订正一下“响若氏隤”这句话。检索发现,除了在引用《说文》时作“氏隤”以外,其他古籍在引用杨雄这句话时可以写作“坻”“坁”“阺”“ ”四种字形。如《文选》作“响若坻溃”[5]981,《汉书》作“响若阺溃”[4]5122,《文字蒙求广义》作“响若 溃”[7]8,段注作“响若坁溃”[2]628。《说文》中有“坻”“坁”“阺”三字的释义,释“坻”为“小渚也”,释“阺”为“秦谓陵阪曰阺”,即大土坡,释“坁”为“箸也”,则皆可以排除,则“氏隤”之“氏”字应作“ ”,与其他几个字字形相似多误用。这一点《类篇·阜部》中有所谈及:“巴、蜀山名崖胁之旁欲堕者曰氏,或作 。”[8]2121根据字形规律,从“阜”之字与从“土”之字多为异体字关系,“坻”与“阺”,“坁”与“ ”有互为异体的可能,然而从《说文》的解释来看,“坻”“阺”“坁”为各不相同的三个字。“坻”“坁”为形声兼会意字,“氐”“氏”的“附着”义参与了字义的构建,而“阺”“ ”则为形声字,“氏”“氐”作为声符并不表义,二字都与“土山”有关,声符的不同彰显的是秦蜀两地方言音的差异,同时,这也从侧面说明,至少在《说文》时期,“氏”“氐”二字的读音已有不同。巴蜀之地多高山,土石自然容易崩坠,因此所谓“欲坠之山石”可能是许慎的附会。所以,“氏”是方言记音字,“ ”为后造本字,“大土山”即为“ ”的本义,“氏”与“ ”通用则可,但许慎以此来释“氏”之本义则非。《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将“ ”解释为“山旁突出势将崩坠的崖石”看到了“ ”的本字地位,但释义不够准确,应该补充说明“ ”的本义为“大土山”。①其后举颜师古注《汉书》曰:“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堕落曰 ”,今查颜师古注作“阺”,丁礼切[4]5122,《大字典》应在忠于颜氏原文的基础上征引,并注明颜氏误将“ ”作“阺”。另外《大字典》并未在“氏”字条下沟通“ ”“氏”二字之间的关系。原文第七条释义为“古代巴蜀一带称江边将要崩落的危岸为氏”,应将其改为:“方言借音字,古巴蜀一带称大土山为氏,或认为古巴蜀称江边将要崩落的危岸为氏,后造本字为‘ ’。”并在《说文》和《玉篇》这两条书证的基础上补充《类篇》的例证,且注明有“坻”“坁”“阺”
“ ”字形相混的现象。
二、“坻”“坁”“阺”“ ”“泜”“汦”讹混情况
“坻”“坁”“阺”“ ”字形相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响若氏溃”这一用例上,实际上四字在各自的义项上也常常相混,“坻”“坁”二字还常常与“泜”“汦”二字相混,现结合《大字典》对“坻”“坁”、“阺”“ ”、“泜”“汦”三组字相混的情况作一个梳理。
(一)“坻”与“坁”,“阺”与“ ”,“泜”与“汦”相混
“坻”与“坁”,“阺”与“ ”,“泜”与“汦”因字形相似而常常讹混,造成音义的混用。《说文》中“坻”字为“小渚也,直尼切”,“坁”为“着也,诸氏切”。段玉裁谓:“(坻)十五部,与十六部之坁迥别。”[2]688前者属脂部,后者属支部,二者不同音,然而在历代注释与字书中出现了注音和释义的混淆,如《字汇·坻》“诸氏切,音纸,止也。《左传》‘物乃坻伏’”[9]89。《广韵·坻》收“诸氏切”并释为“着也”[10]242。《正字通·坁》:“按《六书故》有坻无坁,《正韵》二纸坻,止也,三荠,陇坻也,二支坻,小渚也,据此说坻坁不分为二……坻偽省为坁。”[11]186段氏《说文解字注·坁》:“《左传昭廿九年》‘物乃坁伏,郁湮不育。’杜注:‘坁、止也。’此坁字见于经者。而开成石经譌作坻。其义迥异。楚金所见左传故未误。寻其所由,葢唐初已有误坻者。故释文曰,坁音旨,又音丁礼反。后一音则已譌为坻。凡字切丁礼者、皆氐声也。今版本释文及左传及广韵四纸皆作坻。坻行而坁废矣。”[2]687《大字典》在“坻”字下列“诸氏切”并说明了“坻”为“坁”的讹字,表“着止”义是有道理的,在“坁”字下也应该说明“坻”为“坁”的讹字。
“阺”与“ ”相混的情况较少,大概是因为“ ”出现的时间较晚。《说文·阺》从“氐”得声,段注曰“丁礼切”,而《字汇·阺》同时收有两音:“上纸切,时上声。岸旁欲落者。扬子云《解嘲》‘响若阺溃’。又典礼切,音邸,义同。”[10]493《字汇》误将“阺”作“ ”,才有了上纸典礼二切,对此《正字通》也进行了批驳:“《解嘲》本作‘氏溃’,今作‘ ’,旧本不考《说文》阺本训,又不考岸欲落本作氏,俗改为‘ ’,误以《说文》训氏者附阺注,兼上纸典礼二切。”[12]1234《大字典》在“阺”字与“ ”字条下都没有反映,建议应该简单说明“阺”混为“ ”的情况。
“泜”与“汦”的音义也常常相混。《说文·泜》:“水,在常山,从水氐声。直尼切。”[1]228《说文·汦》:“着止也,从水氏声。直尼切。”[1]234(按:此处应为诸氏切,段氏《说文解字注》曰:“按玉篇之是切,广韵诸氏切,十六部。大徐直尼切,误认为坻字耳。”[2]559)《说文》所释应为二字本义,然《龙龛手鉴·泜》“音迟,水名也。又音脂,亦水名也。又音纸,着止”[12]574中已将“泜”混作“汦”,其他如《广韵·汦》“水名,又音迟”[11]53,《类篇·汦》:“陈尼切,《说文》着止也。又掌氏切”[9]568,《字汇·汦》“直尼切,音持,着止也”[10]241也是如此。《大字典》并未注明二者相讹混的情况,可酌情补充。
(二)“坻”“坁”与“阺”“ ”相混
《说文》中“坻”字直尼切,本义为“小渚”,“阺”字“丁礼切”,本义为“土坡(陵阪)”。“坁”字为诸氏切,本义为“着也,止也”。“坻”“坁”“阺”与“ ”相混的情况前文已述。受到形旁的误导,“坻”字在表示“土坡”义上常常与“阺”相混,如《集韵》:“坻阺,《说文》秦谓陵阪曰阺,或从土。(笔者按:典礼切)”[13]717因此二者读音也常常相混,如《类篇·阺》:“典礼切,《说文》秦谓陵阪曰阺,又陈尼切。”[9]2123《重订直音篇·阺》:“音池,陂也,又音底。”[14]《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又音底,坂也。”[15]13而“坻”除了与“阺”相混而有底音之外,还增加了纸音,如《龙龛手鉴·坻》:“都礼反,陇阪也,又音纸。”[13]582《广韵·坻》表示“陇阪”之义的有“支氏”“当礼”二切。[11]271《类篇·坻》:“陈尼切,《说文》:‘小渚’,引诗‘宛在水中坻’。坻又掌氏切,龙阪也,又典礼切。”[9]2003“坻”与“坁”易相混,因此“坁”也可以表龙阪义,如《集韵·坁》:“秦人谓阪曰坁(笔者按:丈尒切)。”[14]651丈尒切为支部字,而典礼切、陈尼切是脂部字,“坁”字并非因为形讹而沾染上“坻”“阺”的读音,相反“坁”的这一读音又反过来混入了“坻”字,造成“坻”字在“山坡”义上也可读作纸音。综上三字的关系表述为:在山坡义项上:阺(换旁)→坻(形近而讹)→坁。[16]《大字典》可以在“坻”的“山坡”义项下注明“通阺”,并在“坁”下注明其“山坡”义是与“坻”相讹混而来。
(三)“坻”“坁”与“泜”“汦”相混
首先,关于“坁”与“汦”的相混,《说文》:“坁,箸也”“汦,着止也”。二者义近,常相混。如小徐本《说文解字》引《左传》:“物乃汦伏。”[17]223段氏《说文解字注》曰:“徐楚金引左传物乃汦伏。按左传自作坻伏。杜曰。坻、止也。寻其义当作坁。与汦义略同。”[2]559《集韵》中亦云:“坁汦,《说文》‘箸也’,或从水”[14]642,更是将二字当做了异体字。再者,关于“坻”与“泜”的相混,《说文》“泜,水名也”,“坻,小渚也”,二字都与水相关,在“小渚”义上也常相混,如《玉篇·泜》:“丈指切,水中丘也。”[16]69《重订直音篇·泜》:“泜,音池,水名,又水中丘。”[15]《大字典》可以在“汦”下注明:“有所附着而停止,也作‘坁’,讹作‘坻’‘泜’”;在“坁”字下也可以增加与“汦”的关系说明,例如:“止,也作汦,后讹作坻。”
据此,现将三组字的讹混关系表现如下:
注释:
①为了照顾古代字书的释义,可以保留“欲坠之山石”之义。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说文解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3]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 1988.
[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清)王先谦补注.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5.
[7](清)蒯光典撰,曹小云,方孝玲校点.文字蒙求广义[M].合肥:黄山书社,2020.
[8](宋)司马光撰.类篇(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9](明)梅膺祚撰,(清)吴任臣编.字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10]周祖谟.广韵校本(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明)张自烈著,(清)廖文英编.正字通[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12]鲁仁编.中国古代工具书丛编(6)·类篇·龙龛手鉴[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13]赵振铎校.集韵校本(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4](明)章黼撰.重订直音篇[O].练川明德书院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15](梁)顾野王撰.玉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6]李思含.“氏”“氐”互用校正[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3(01):90-95+102.
[17](南唐)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作者简介:
羊春秀,女,汉族,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古及近代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