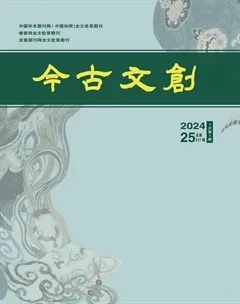《水经注》徵引汉晋时期汉水流域石刻文献及其价值
2024-07-25巫维薰
【摘要】郦道元《水经注》著录汉晋时期的金石碑刻众多,在卷二十七至卷二十九《沔水》中,收录了关于汉水流域汉晋时期的多处石刻文献,如司隶校尉犍为杨厥刻石、太尉李固墓碑、仙人唐公房碑等。这些石刻文献对研究汉晋时期的历史地理及地域文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本文探析《水经注·沔水》所收录的汉水流域汉晋时期的多处石刻文献及其历史文化、文学艺术价值,以求促进汉水流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郦道元;《水经注》;汉水流域;石刻文献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5-008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5.025
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大学2023年人文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水经注》与汉水流域文化研究”(项目名称:RWXYCX2301)。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从陕西宁强发源至勉县称为沔水,东去安康则称汉水,经丹江口为沧浪水,再过钟祥以襄江于武汉汉口汇入长江。郦道元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在《水经注》的序言中提到:“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1]44秦以前,已有许多地理类书籍,但当时国家诸侯割据、混战不休,极大地阻碍了地理学的发展,人们对地理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时之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普遍具有神话色彩。
郦道元极不认同这种神话虚构的性质,他主张:“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1]45强调野外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在为《水经》作注过程中,除广泛查引了相关地理文献外,还注重实地考察。对河流的源流、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古迹等都有所记述,对当地的碑文、石刻、墓志铭等也多有记载。
近年来,汉水流域内的石刻文献的挖掘与发展逐渐提上了日程,流域内的学者对汉水流域的碑石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冯岁平的《汉〈仙人唐公房碑〉研究》和《北魏〈石门铭〉刊刻现象再论》,李锐《石门摩崖石刻文化价值再认识》、孙丽娟《从碑刻资料解读清代汉水流域陕西段民间水运秩序》等论文,都对汉水流域的碑刻进行了一定考察与研究,为汉水流域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水经注》是古代地理学名著,其中《水经注·沔水》二卷记载了汉晋时期汉水流域的多处碑石,如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厥刻石、汉太尉李固墓碑、汉仙人唐公房碑等,这些碑石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及艺术价值。却鲜少人关注,本文从《水经注》徵引的汉水流域石刻文献出发,有效地拓宽了汉晋时期的汉水流域石刻文献研究的视野。
一、《水经注》徵引汉晋时期汉水流域石刻文献概述
本文对《水经注》徵引的汉水流域石刻文献进行考察,按时代顺序分为东汉与两晋两个时期,文章对墓碑或石刻的内容、功用、刊刻时间、流传、保存皆有提及,现将内容罗列如下:
(一)东汉
东汉时期,汉水流域的石刻文献有刻石和墓碑两类。刻石是为记载生人的丰功伟绩,表彰人物的优秀品质,墓碑是指对死者生平事迹与德行方面实行记载与称颂,二者均体现出了时人对于生命不朽、传扬后世的追求。刊石立碑不仅可以替人们延续声名,同时也可以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故立墓碑是东汉丧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厥刻石》[1]645
记功颂德刻石,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时刊刻,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后世多曰“石门颂”。由当时的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戎于石门内壁西方摩崖上以隶书刻写,历代皆享有盛名。据《读史方舆纪要》《方輿考证》《名胜志》记载,褒水即褒河。
2.《太尉李固墓碑》[1]646
记人述事碑,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立,据《方舆考证》记载,碑文乃由唐·韦皋隶书题写。李固,字子坚,东汉中期名臣,司徒李郃之子。他年轻时便博览古今、学识渊博,屡次不受辟命。历任将作大匠、大司农、太尉。顺帝崩后,他为梁皇后所重,但为奸人梁冀所忌,导致质帝晏驾。后李固与梁冀争论,不肯立刘志为帝,遂与其二子被冀诬害。太后嘉其义烈,特让其听归葬故里。太尉李固墓,在今城固县柳林镇李固庙村,但此处介于南郑与城固二县之间,地属何县,屡有变动,故文献记载不同。碑文内容漫漶,已不可辨识。
3.《仙人唐公房碑》[1]647
记功颂德祠庙碑,东汉末年以隶书刊刻,无撰书人姓名,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唐公房是西汉末年城固县人,传说他为避祸当时汉中郡吏,服用了仙人李八百给的丹药后,举家拔宅升天。升仙之日,婿出门未归,没能得以一起升仙,故约以此川为居,号为婿乡,当地的百姓为记载此事,在此刊石立碑,以传后世。人们对于碑的刻立者一直存有争议,陆耀遹《金石续编》认为是否是汉中太守郭芝倡率群义所立存疑。[2]560
4.《南阳太守秦颉墓北二碑》[1]668
记人述事墓碑,东汉刊立。据《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记载:“秦颉者,字初起。颉之南阳,过宜城中一家,东向大道。住车视之曰‘此居处可作冢’后丧还,至此处住,车不肯前,故吏为市此宅葬之。今宜城城中大冢,前有二碑是也。”[3]30洪适《隶释隶续》记载:“《汉故南阳太守秦君之碑》篆额,欧、赵皆云,文已磨灭,惟存其额十大篆。予所得者,犹有九十余字。”[4]174中平元年(184年)时,秦颉赶往荆州南阳郡上任,途径宜城县城,城中有一户人家,门朝东并有大道,秦颉停车看到后说这房子可以做坟墓。中平三年(186年)秦颉被杀,运送其尸体的马车路过此房屋时,马车不肯向前走,秦颉的故吏便将此房屋买下来,修做秦颉的坟墓,此碑已佚。
5.《冠盖里碑》[1]670
记功颂德祠庙碑,汉末刊立,洪适《隶释》《方舆考证》、杨守敬《湖北金石志》皆载,言此冠盖里碑,在宜城县太山,即今湖北宣城市西北。山下有一庙,聚集了许多汉末名士,一时之间,朱轩华盖,盛况空前。荆州刺史行部见此情景,雅叹其盛况,遂号曰“冠盖里”,并以刻石铭之,以传后世。后来,“冠盖里”就成了名臣冠族故里的泛称。
(二)两晋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争战不休,直到三家归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西晋建立以后,对于刊石立碑采取禁止的态度,流传至今的碑刻也比较少,直到南北朝时期才重新得到发展。晋人的墓碑显示出人们对功名的追求与向往,无论是替生人还是逝者立碑,都体现出对他们的美化修饰,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儒与孝的体现,也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1.《邹恢碑》[1]662
记人述事碑,据《方舆考证》《行水金鉴》记载,此为邹恢墓碑刻石,关于碑文的刻立年代、内容,郦注均未记述,后世亦不传,盖已佚。邹恢,史传皆阙,杨守敬《水经注疏》认为邹恢是郗恢之误。又据《晋书·郗鉴传》记载:“郗恢字道胤,东晋将领,太尉郗鉴之孙,北中郎将郗昙之子。”[5]1796曾镇守襄阳,在守卫襄阳期间,多次派兵保护洛阳,并抵御了后秦、西燕等国的进攻。郗恢被召回京城担任尚书,在返回建康途中被人暗杀,他的四个儿子也一同遇害,后朝廷追赠郗恢为镇军将军,葬于襄阳万山。鲁宗之,字彦仁,东晋大臣,鲁宗之曾州治襄阳,登此山,见郗恢墓,为其立《邹恢碑》。
2.《杜元凯碑》[1]662
记人述事碑,皆是晋时刊立,郦注文中两次提到杜预。杜预即杜元凯,魏晋时期的军事家、经学家,曹魏散骑常侍杜恕之子,事迹见《晋书·杜预传》。杜预曾自立二碑欲将己功传至后世。立碑时还思虑了沧海桑田的时空变化,遂将一碑立于岘山之上,另一碑则沉于万山之下。岘山,位于今襄阳城西南,东临汉江,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万山,襄阳境内名山,位于襄阳故城之南,即今湖北襄阳城西北,毗邻汉江。这样,将来即使山川巨变仍能保证有一碑矗立于山巅,自己的丰功伟绩将永传后世,“杜预沉碑”的典故即出于此。
3.《太傅羊祜碑》[1]663
记人述事碑,羊祜,字叔子,兖州泰山郡南城县人。西晋建立后,其累官尚书右仆射、卫将军,封钜平侯。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出任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襄阳。在荆州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据《晋书斠注·羊祜传》记载:“襄阳城南门道东有三碑,一碑是晋太傅羊祜碑,一碑是镇南将军杜预碑,一碑是安南将军刘俨碑,并是学生所立。《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一曰岘山在襄阳县东南九里,山东临汉水古今大路,羊祜镇襄阳与邹润甫共登此山,后人立碑谓之堕泪碑。”[6]971“城南门道东”是指城门道东。襄阳城,即今天湖北省襄阳市。西汉初置县,因居襄水之南,故曰襄阳。
4.《曹仁记水碑》[1]664
记功颂德碑,晋时刻立。据《金石萃编》记载:“城西南有曹仁记水碑,杜元凯重刻其后,书伐吴之事。盖古人简便不重烦如此。”[7]1238此平鲁城南即樊城西南,故知此城即樊城。曹仁,字子孝,沛国谯县人,三国魏初名将,魏武帝曹操之从弟,见于《三国志·魏书·曹仁传》。《曹仁记水碑》原为三国时期曹仁所立,碑文记载的内容是汉水围城、曹仁拒关羽之事。西晋初,杜元凯平吴之后,任镇南大将军,坐镇襄阳,于是又于此碑上刻写当年伐吴之事也,以述己功。今未见,盖已佚。
5.《桓宣碑》[1]664
记人述事碑,东晋时刻立。据《晋书·桓宣传》记载:“桓宣,谯国县人。祖父桓诩,义阳太守……朝廷追赠为镇南将军。”[5]2115桓宣曾收复并镇守襄阳,后在丹水之战中为后赵所败,坐罪贬黜,惭愤成疾,于建元二年八月,病逝,追赠为镇南将军。岘山位于襄阳城西南,东临汉江,羊祜堕泪碑、杜预沉碑皆立于此山上。
6.《征西将军周访碑》[1]664
记人述事碑,晋时刊立,已亡佚。周访,西晋名将。他曾平定江州刺史华轶及荆州杜曾叛乱,又协助平定杜弢的流民叛乱,对东晋能于南方建立政权甚有功劳,官至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封寻阳县侯。太兴三年,周访去世,年六十一,追赠征西将军。
两晋时期虽不长,社会动乱与黑暗的司马氏政权造成的历史影响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人不敢言政,文人专注于自身,士人则多趋附世族,保全自身,映射到当时的碑刻文化中,则是人们更加注重自身及后世的评判。时之儒家与道家相互影响,儒家的孝与义,道家的逍遥无为,很多时候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总之,两个时期间隔较近,内容多为记人颂德、记事述功,东汉时期的碑刻保存较为完整,而两晋碑刻则留下了较少的痕迹。
二、汉晋时期汉水流域石刻文献的重要价值
汉水流域是人类的古老发祥地之一,是以华夏民族为主干的汉民族重要发祥地,更是古老伟大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8]这些石刻文献,有的记录了中华文明该历史时代发展的印记,有的承载了人们渴望英名永存的念想,有的代表着人们心怀百姓,勇于创举的精神。石刻文献作为汉水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水流域永续发展的信心和力量来源。
(一)历史文化价值
汉水流域绵延千里,历史遗迹众多,留给人们宝贵的历史与文化遗产。1.保存历史,传承精神。这些石刻碑文虽时间久远,但为后世留下了历史名人的事迹以及历史典故的发展由来,不仅记录了流逝的历史时事,而且传承了中华几千年的儒家精神与信仰。2.绵延文化,源远流长。碑文的内容是时人思想文化的间接反映,是后世对做出卓越的成就与贡献人们的颂赞与歌颂,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3.寄托情怀,述说哀思。石刻和墓碑是亲人家属为追忆悼念、缅怀先人而立,他们的思念和敬佩之情绵延了几千年,流传至今。4.反映民俗,见证信仰。石刻是汉水流域民俗与信仰的载体,如《仙人唐公房碑》,时人为唐公房立庙树碑,并祈求保佑,反映出东汉时期的民间信仰。
(二)文学艺术价值
石刻文献是自然与人文内涵的结合,从自然到人文的转化,是因为历史人物将自己的一生刻于碑石之上,使得原本无情的山石变得有了生命。这些石刻文献默默矗立在自然山水之间,留存着过往的历史事迹,较于传统的纸质文献,要耐磨得多。在时代的更替中,述说着历史人物的传奇、功绩以及遗憾,引得后来者登高吟咏。汉晋时期汉水流域内的石刻文献独具特色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版式固定,风格特别。碑石由于自身的碑刻条件限制,决定了其大体的风格,汉碑是中国碑刻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东汉时,由于统治者的推行,人们大兴刻石立碑之风。此时的碑刻无论是从文法、书法及碑刻的形制都有了大致样式,并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发展。
刻辞语言优美,行文流畅。如东汉《冠盖里碑》其辞曰:“峨峨南岳,烈烈离明……德为龙光,声化鹤鸣。”《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厥刻石》刻辞曰:“君德明明,炳焕弥光……循礼有常。”字数工整,字句押韵,内容丰富,意境开阔,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方便人们口语相传及流传后世之用。
字体以隶书为主,美观大气。汉代的碑刻众多,字体以隶书为主,流传后世也以隶书作品较多。如《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厥刻石》《仙人唐公房碑》等,这些碑刻都极具艺术和审美价值,其独特的隶书书法、行文文法以及碑刻形制上体现出豪迈、自由以及俊逸,是东汉士人精神与面貌的体现,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至高造诣。
三、结语
石刻文献与纸质文献都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容小觑。碑石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源头,在千百年的斗转星移之后,它还承担着对纸质文献的对照、印证作用。汉水流域的石刻与墓碑是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珍贵的文学艺术价值,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全新的视野对汉水流域的各处碑刻文献进行集中整理与研究,学习并汲取前人对汉水流域碑刻文献的释读、历史文学、书法艺术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汉水流域石刻墓碑的概况与文献价值,进一步探讨其在各学科中的重要价值与地位。
参考文献:
[1]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清)陆耀遹.金石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3](晋)习凿齿撰,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8.
[4](宋)洪适.隶释隶续·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唐)房玄龄.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清)吴士鉴.晋书斠注·卷三十四列传第四[O].民国嘉业堂刻本.
[7](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二[O].清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
[8]潘世东.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光芒(五题)[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4(02):8-11.
作者简介:
巫维薰,女,广东河源人,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