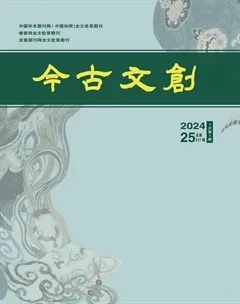论沈从文《夜》的隐喻书写
2024-07-25舒帆羲
【摘要】《夜》作为沈从文此前没有发表却收录在《沈从文甲集》中的一篇小说,隐喻思想深刻。《夜》隐喻的是“生命意象”,从根本上说“夜”的意象描写就是湘西边民在艰难境遇生存的顽强生命力。本文立足于“夜”的描写这根主线,探讨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异域世界,在景物描写和故事叙述中隐喻的是人在复杂心境中对生命庄严之美和人性诚爱之美的歌颂。老者“无故事”的故事隐喻的是人生之痛,更是沈从文在自我灵魂拷问下以普遍性的生命探讨人类共通的命运。
【关键词】夜;隐喻;生命;人性;命运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5-0007-04【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5.002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进入20世纪的文化标识,以乡土文学作为现实载体,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如果说鲁迅是‘写实派’乡土小说家的旗手和导师,那么沈从文就是‘写意派’风俗画乡土小说的扛鼎人物。” ①“乡土小说的外形和内核以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这‘三画’与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这‘四彩’所呈现,这便是现代乡土小说的精神和灵魂之所在。” ②“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交融一体的“乡土风俗”使得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异域世界,也是一种具有老庄哲学意蕴的田园诗风。
《夜》讲的是1919年在湘西边境的故事,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呈现此夜的所见、所行、所闻和所悟。
一、步行深山的黑色之夜
“我”是从槐化的正兵“高升”到榆树湾的司书,这为“我”之前擦枪、杀人的生活增添了写字作画的美趣,但也因需核实表册去到冷EpQiIdnOu4NX/SRs9P3p3g==僻岩崖上另外抄写一份资料。“我”和四个士兵开始了“黑夜之旅”。
黑夜是一种天地自然规律的现象,日落则夜黑。在一个阴郁沉闷的南方二月里,在一个刚上路就需火把的黑路上,在火把毕毕剥剥的燃烧声中,黑夜慢慢压下身来。虽是晚上又黑又冷,可却不失一种黑色的美感。“我们”在溪涧蹚过、深涧石梁上跨过,在蜿蜒变化的山路中降入夹谷,观赏高耸的石壁和树林。沈从文以朴实的描写带我们领略这黑色幕布下的自然之美。在不介入叙事的纯粹客观描写中,“我”同这黑色的自然融于一体,在这自然的黑夜中尽情享受夜行带来这空洞寥阔的畅然,为这动人的“黑”所陶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个体风格的呈现,乡土风景作为乡土存在的自然形相在创作主体进行的描绘中总是烙有主观情愫的因子。这个晚上黑色的夜不仅仅是我们同行人走过的地方对美的体验,更是沈从文个人人生经历所呈现的对美的感悟。这种风景如画的夜景描写更是作者在叙事功能中隐喻象征的“生活栖息地”。
可在火把燃尽的黑路上,黑色的夜像是张“会吃人”的大网,一不小心就会跌入荒山。在不安、恐惧的心理作用下,在幕布笼罩的深深黑夜里,靠着山顶的那点火光我们在这夜行之路上找到希望。沈从文以“我”的口吻对这地方地形的艰难进行直接描写,看似以一种记叙的态度对故事进行客观呈现,实则隐喻湘西山民在这艰难环境生存的顽强生命力。山顶的那点火光也更像是支撑底层人民生存的光亮希望。
二、围讲故事的漫长之夜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湘西人夜讲故事、抱团取暖的这种原始古老的民俗在湘西民间文化的久远中延续下来。在故事一环套一环的漫长之夜里,我们在沈从文充满想象与纪实性的故事记叙中更深入地走进夜的描写,深入古朴神秘的湘西世界。
几个士兵在“我”的提议下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消磨这漫长的黑夜。作者安排这样的“故事”为“外出执行公务宿于老者家”的“故事”增添无数情节。正如福斯特所谈到的那样:国王死了,王后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过度而死,这是情节。
作者安排的同伴叙述里,最爱谈到女人的黑小胖子说起的是与苗女恋爱的故事,自己的同伴却在一个黑夜中代替自己和那苗女死于其丈夫的长矛,还在那每夜幽会的林子里。我们在作者给的堆积事件中寻找故事的情节,在情节与故事的纠缠中推着逻辑和线索的发展。沈从文借助湘西故事、苗家人物形象让我们在这黑夜的世界里试探触摸。在这样的夜的故事里隐喻了湘西边地边民自然生命的神秘美和悲情美。
脸上有记号的兵士在其18岁大冷天的夜里,追赶着以为是斑鸠或山鸡的溪涧老虎。在这士兵的身上,湘西小人物的生存方式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彰显着生命顽强的底色,是一切湘西人的生活态式,所反映出来的是文化立场的阐释。黑色的夜不仅仅是一张会把人吞没的大网,更象征着一种强有力的生命张扬,是充满原始底色的小人物生存的生命力量。
第三个在夜里打鱼却捕到蛇的故事,更是展现了苗族血液在神秘古朴的湘西世界里存在的蛮横生命力。湘西男性的雄强进取在这原始的蛮性力量中凸显着人生生命张力的感悟。
作者安排的一个套一个的“夜”的故事,将民俗活动融入夜里,以风情画的形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最具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中隐喻朴素率真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并以生命的自然表达追求艺术的表现自由。在作者缺失的叙事声音中,默默地“消磨”这夜的“黑”。
三、“没有故事”的“隐者”之夜
我们常常在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的湘西世界中领略那似乎契合“老庄哲学”的思想意蕴。从悲剧韵律中解脱出来,追求生命底色的张扬,以一种生命蛮性的思维,在生命长河中高歌自然,自然的生、自然的死。
在这个漫漫长夜里,“我”总渴望能从老者的口中得到些趣事。老者像是独居深山的神仙,房里干净整洁有字画,桌上还有本《庄子》的“摆件”。“我”渴望和老者进行交流,似乎能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的情感共鸣。在“我”对老者住处的客观陈述中,以一种极简的朴素凸显人物的特性。朴素与自然是沈从文所追求的终极生命理想,在他的作品中无时无刻不存在一种朴素自然的生命观。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有所有事物淡然的纯粹和自然。“我”渴望能和老者有这种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沈从文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和追求。房间的字画、桌上的茶壶和《庄子》隐喻的是老者的生活,不是自由自在的神仙,而是有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的隐者,是向往脱离世俗的高雅情趣。“简单”即“自由”正是老庄思想追求的道法自然。“我”没有从老者的口中得知任何与他相关的故事,老者似乎只是这些故事中的看客,没有一丝参与,脸上那一份非凡的“神气”倒像是份保护色,只是淡淡地说道:“故事没有,天快亮了。”老者此时为什么不说说自己的故事,人生每天有故事和故事新生。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实则是隐喻老者自己的人生之痛。所以,在作者和“我”一样有着“不甘心”的心境下,最终还是以隐蔽的叙事声音走进老者那锁住的房间。
房间里除了大床上的死妇人,没有半分异于常人的奇特。可就是这样一个逝去的生命,在老者的眼中是沉入心底的冷静和自若。“没有故事”却一举一动都是故事,“若有故事”却一分一厘都在消散。“我”突然之间便懂得了那句“你们不来我也不睡的,你们到了这里,我倒很好过,好像不是我陪你们,是你们陪我!”这些话是当时的“我”和朋友都不懂得的,他们现在依旧不懂,只有“我”在老者的房间里见证了他本应怎样度过的漫漫长夜。“没有故事”隐喻的就是老者的人生之痛。老者和老伴从心而搬到这孤村,十六年的时间里恬淡自若的生活,老伴的离去像是失去光照的世界,在老者的生命中慢慢熄灭。“我”突然在老者这“没有故事的故事中”看到了生命“火热荒凉”的底色。
生命似乎总是这样美、悲交织,相融共生,缺其一样都不可称为人生。我们在“向生而死”“向死而生”的两种状态中追求生命的意义,却总忽略人生需经苦难的完整。在这孤寂的生命长夜中,“我”似乎明白了生命非传统意义上的优雅、宁静和淡泊。这种像极了偶然的生活方式赋予了生命形式不一样的色彩。沈从文曾说过:“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优势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 ③老者对待生死的态度像极了湘西山水的凝重和洒脱。在这样一个“夜”与“夜”包含的全部时间里,在这样“逝去”“现实”“隐含”的时空中,沈从文以生命的“原色”为“夜的故事”提供舞台框架,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从“我”对老者隐忍的好奇到由心而发的冷静,在这隐含的时空关系中达到精神容量的共鸣。
沈从文建构神秘而又平静的死亡描写,是夜的黑暗深化,引申的是生命的孤寂,这为亘古以来就无知无觉的死亡增添原色的描写。所以,沈从文笔下底层人物的情感共鸣并不来自所谓阶级意义的醒悟,也不仅仅是对生命真、善、美的追求,而是一种抒写原始自然所构造的蓬勃生命。
四、心灵拷问的永恒之夜
庄子在《齐物论》写道:“天地与吾并生,万物与吾为一。”在沈从文的人文世界里,也一生都致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完美契合。小说中“夜”的故事描写以本真生命的状态在“我”所见的人生际遇中,对人性进行深入的自我心灵“拷问”。
艺术评论家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曾这样提起沈从文的创作:“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 ④的确,对于这样一个“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⑤的沈从文来说满是人性的关照。无论是对自然景物还是风俗人物的描写,沈从文总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展露,以一种“乡下人”纯粹的视角进行美的构造。“沈从文的美学理念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面,那就是在酒神精神的影响下尽情地放纵自己原始的本能,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投入到原始生活中去,以求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 ⑥
大家好不容易找到深山火光的希望,可周围的环境和自我的各种可怕情感使得我们对这希望的火光高度警惕,“我”甚至坚定认为如果前去探路什长的火把熄灭那一定是遭到了不测,那“我”一定会第一个开枪打死那“强悍凶猛”的“匪头”。这也不难想象,沈从文在湘西土著军队担任司书时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厮混,也亲眼见证他们“反人性”的杀戮,这似乎成为他逆向思考人性和人类文明的一个“心结”。自然而然,明明找到了山顶灯火的希望,“我”却还是会想到之前营地捉到匪头是被破腹剜心的事,由此而联想到上前打探的什长会不会被破腔取心。“我”以自己枪法很好来宽慰自己的恐惧,却也还是在时间的流逝中遭到苦闷攻击。在这黑冷夜的包裹中,心上冰冷到极致。直到那一声狗吠声的出现,才完全打消“我”之前“恶劣”的想法。没有哪个土匪会饲养一条“无用”的小狗,仔细一瞧门口站着的是一位憔悴的老人,这更加证实“我”之前的想法多余且好笑。走进大门,小狗甩着它脖子上的小铃铛在我们的脚边嗅了又嗅,似乎接受了我们是好人的来意。“我”虽然很欣喜这不是匪头家,可“我”还是不高兴这老头脸上不欢喜的神气。“我”依然走在最后,想着若是“人肉包子迷魂汤”的故事便就可马上转身反击这老头。可当目睹了屋里的种种,“我”却变得很惭愧,怎么会将这老头想得如此罪恶。家中陈列干净整洁、墙上的字画、桌上的茶壶和《庄子》分明隐喻“这老头”是一位隐者。窗外遗留的残余火把声容不及我多想,迫使“我”马上出门用脚踹熄。在窗外瞥到卧房“睡梦中”的人更加使我安心这里的安全。“我”突然就来了兴趣,这老者一定有“我”很感兴趣的故事,“我”一卸之前的种种防备心理,表现出懂事的谦卑,那么老者一定会有“孺子可教”这样的话来展示自己的非凡。这个晚上,“我”曾自以为自己会是个对抗匪头的大英雄,却不曾想会变成这老者的“神仙”梦。默默观察的“我”,在什长和老者的对话中,总感觉老者有隐忍的神秘。“我”突然之间将老人的神情、家中的情调、谈吐的言语联想起来又归结到对老人的“厌恶”,他虽然款待了我们,可却把卧室的房门用铜锁锁着,这显然是一种戒备。好奇心迫使“我”一定要弄明白老者的故事,这样三番两次弄翻“我”心境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踏入房间看到床上的“死妇人”后,“我”惊讶到说不出话,连同初见老者的神气和悭吝的行为也都在这样一个“大的黑夜故事”中慢慢沉淀。“我”之前竟如此揣测老者,将他归为深山的匪头,或是杀人剖心的恶人,更是心有戒备的俗人,可这分明就是老者失去老伴的人生隐痛。
黑夜竟是像地球自转“太慢”这样的长,也像是同行友人接连故事讲说还没等到天亮的长,还像是生命亘古以来无知无觉的消失这样的长,更像是“我”作为老者及老伴故事看客视角的无关和相关的长……老者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我”在这余音绕梁的黑夜中留有太多的回味。“我”似乎在老者的“故事”中眼睁睁地看着这美好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消逝。在沈从文给的这种看似平淡却又深入生命探讨的设定中,给行文以一种悲凉伤感的气氛,今夜所见的种种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将是一个永恒的烙印。
回想起之前的种种情境,“我”竟还以一种“俗气”的眼光“恶意揣测”老者,却不曾想在今夜老者的家里竟发生了这么大的不幸之事。老妇人的死亡看似是老者个人生命的“插曲”,却也像极了老者人生意义的终结,更是“我”这个借宿的“小人物”在一个黑夜所拥有的人生震撼。连同沈从文都在那一声声的铁锹“咬地”声中慢慢接受这生命的沉重,以及“我”在这一声声的敲击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湘西人性的纯美怎会在“我”的这种“狭隘揣测”中变得如此“不堪”。今夜老者“无故事”的故事给“我”的心灵以沉重一击,让“我”思考这是与我们共通的生命存在。沈从文在“我”历经夜行的这个晚上、在山顶小屋见证生命“隐痛”的故事里、在冷夜和情热的环境中、在隐者外冷内热的人性里,歌颂生命的庄严之美和诚爱的善良之美。
作者设置“我”作为老者故事的看客,揭示小人物在底层生活的生命本色,以生命意识的“拷问”置我们从无关到相关的主体存在。所以,《夜》中的“我”绝非是纯粹的看客,更是在他者故事中渗透自我的“灵魂拷问”,在个体生命间的互相拆解和相互渗透。这种从无关到有关的自我渗透在永恒的空间范围里,实际上是沈从文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入思考,体现沈从文对生命的悲悯和人性的关怀。他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故事人物的情节中给予“我”从无关到相关永恒的印记。作者以这种象征隐喻的方式在思考生命普适性的问题,这是人生与境遇的思考,是湘西地域性与边缘化的思考,还是悲悯人性和人类大爱的思考。这种永恒性的自我拷问是对生命、人生和人性的关照,是立足于“生命诗学”维度的探析和绝对时空中的永恒。“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地对灵魂的‘拷问’几乎没有。深层意义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于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接受。” ⑦“应该说,在新文学作家中,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张扬人性并有理论自觉的人并不多见,沈从文算是一个例外。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沈从文的创作,不仅可以发现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而且可以发现其创作对展示20世纪人性主题的重要意义。” ⑧在“我”不断进行“自我拷问”的同时,展现的是沈从文对人类人性的深层思考和探索。
《夜》这篇小说的隐喻给我们以审美的启示,沈从文在生命长河中高歌的人性,以夜的隐喻探析了生命所谓的神性。在叙事和写意的笔调中深入一环套一环的人性解读,从自然到永恒的时空维度剖析生命意识永恒的价值。那个以山地为基础、坚石堆砌的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就是沈从文美在生命的人性论。
注释:
①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②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③沈从文:《水云》,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④苏雪林:《沈从文论》,载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⑤沈从文:《水云》,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⑥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⑧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3]李天程.美在生命——论沈从文的美学思想[J].东岳论丛,2002,(01):96-100.
[4]高小晴.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人性追寻[J].青年文学家,2020,(02):44-45.
[5]熊峰.沈从文短篇名作《夜》的隐喻内涵与叙事构成[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6,(01):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