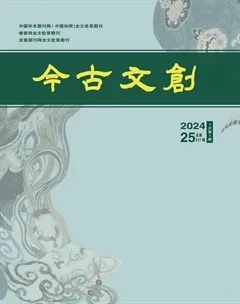元稹《莺莺传》张生形象新解
2024-07-25孔纤纤
【摘要】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主要讲述寒苦书生张生发迹之后抛弃没落贵族小姐崔莺莺的故事。当今许多人批评张生是位十足的负心汉,就连作者元稹也因《莺莺传》张生一角被质疑人品,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张生抛弃崔莺莺,真的算是始乱终弃的行为吗?本文就作家元稹的生平经历、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回归文章本身来进行探讨,以期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引起对“张生”形象的重新审视。
【关键词】张生;元稹;《莺莺传》;始乱终弃;负心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5-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5.001
对比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最终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莺莺传》里的张生抛弃崔莺莺之举可谓太过薄情,故今人大多以“负心汉”形象来描述张生,但事实理应如此吗?本文试图从对张生形象的解读、分析张生大变之故再到唤起对张生形象的再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希望提供一个新的关照视角,重新探讨张生形象的文本意义。
一、张生即元稹自寓
有关张生原型的问题,历来都是研究《莺莺传》的热点话题。自宋代王性之提出“元稹自寓说”之后,得到了后世许多学者的支持,像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卞孝萱等人,皆主张张生乃元稹自寓的说法。
(一)基于元稹自寓的前提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莺莺事虽元稹自述,犹借张生之名。” 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谈及:“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②肯定了张生即元稹的说法。后陈寅恪先生也明确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 ③除此之外,《莺莺传》中的许多情节与元稹所做的诗文多有交叉之处,像追忆往昔之作的《莺莺诗》,以“莺莺”提名,再如《会真诗三十韵》中所写的“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④,对比《莺莺传》原文中的“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 ⑤,画面尤为统一,此情此景,如此相似,如若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能够将张崔二人缠绵悱恻之时刻画的如在眼前?故此,“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说法大致成为学术界所共识,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以“元稹自寓说”为前提,通过元稹的生平经历来关照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为进一步研究张生提供了一个认识角度。
(二)通过元稹生平看张生
历史对元稹的评价似乎都停留在他对于名利的追求上,其实不然。在元稹仕途之初,因年少时的意气风发、光芒毕露得罪权贵无数,接连被贬的经历让他看透官场浮沉,其心态完全改变,因此他审时度势、攀附权贵,终仕运亨通,畅达无阻,于长庆二年官至宰相。纵观元稹一生,在追求文学和仕途的道路上充满矛盾,他一面针砭时弊,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一面又摆脱不了现实环境,最终被官场环境所裹挟。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反叛与乖顺在元稹身上就这样实现了矛盾的统一。
与曲折的仕途命运相似,元稹曲折的爱情故事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没有正式就职前,元稹停驻在浦州一带,当时叛军骚乱,社会局势动乱。元稹在朋友的帮助下,保护了落于危难中的贵族远亲,故此结识了表妹崔莺莺,两人结下情缘,彼此相爱。虽然,元稹对崔莺莺的感情不假,但他又意识到其仕途前程和婚姻的莫大联系,和文中张生一样,他最终选择放弃了不能给自己前程帮助的崔莺莺,迎娶了官位显赫的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根据卞孝萱《元稹年谱》中的说法,张生遇见崔莺莺是在贞元十六年,张生那年二十三岁,而元稹恰也是二十三岁左右,即便具体细节有所出入,但就整体故事情节而言,大体可以断定《莺莺传》就是元稹在过往回忆的基础上,对其加工、润色而改编成的一篇传奇故事。
二、张生之变
当下张生被今人大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看完莺莺回书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在《莺莺传》中原文如下: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比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胜妖孽,是用忍情。” ⑥
张生此番言辞犀利的“尤物论”,将女子视为妖孽,将美色视为祸患,并将其与国家兴衰命运相连,与文中言辞婉转、爱到卑微至极的莺莺形成鲜明比对。此举不仅伤了崔氏之心,更伤了万千读者之心,就连鲁迅都评价“文过饰非,遂坠恶趣” ⑦。世人便由此断定,这是张生为自己始乱终弃之举所作开脱之词,前文中的张生还对莺莺的情分依旧,为何突然性情大变?
(一)情感上的自我疗愈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张生态度的转变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尊的需要。“满足这种自尊的需要会产生一种自信的情感,个体产生相应的价值感、认同感和能力感。相反,这些需要一旦受挫,便会使人产生无力感、自卑感和渺小感,使人丧失基本信心,要求其他补偿或者一定的神经症倾向。” ⑧在张生和莺莺的交往过程中,张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受到传统礼教束缚的莺莺,其欲拒还羞又忽冷忽热的态度,让“未尝近女色”的张生总是摸不着头脑,在邀约被拒、索文被拒、听琴被拒,莺莺的种种行为,让身为男性的张生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甚至他的男性自信、自我认同都被逐渐磨灭。因此,他的改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自尊需求得不到满足后的一种情感补偿,这种情感补偿仅仅出于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是经受情伤之后的自我疗愈。
若非有情,何须忍情;因为有情,所以忍情。这种情感疗愈正是从反方面映现出张生对莺莺的情分。类比当今的男性在被女性抛弃之后,跟朋友肆谈诽谤抛弃自己的女性,仅是出于一种变相的自我保护、自我安慰行为。由此,张生才以“尤物论”“女祸论”为由,公开发表了“断绝书”。
(二)主题先行,作者有意为之
卞孝萱先生认为《莺莺传》大约写于贞元二十年。安史之乱后,国家迅速由盛转衰,经济衰退、时局动荡,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危机四伏的社会背景让文士们对中衰之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反思,由此,他们的忧患意识在诗文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元稹、白居易强调兴复儒学传统,领导了浩浩汤汤的新乐府运动。在此指导下,元稹创作了许多讽喻时事之作,像《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等等,作品中无不流露出讽谏意味和强烈的责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安史之乱的反思中,很多文士不约而同地将“女色”当作安史之乱的主要诱因,认为李隆基是因为受到杨玉环的引诱,因而终日不务朝政,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这种“尤物论”思想在当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尤物”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 ⑨,其大体意思是说,如果有了美丽的女子,那足以能够改变一个人,如果此人不是真正有道德和正义,那么其一定会形成灾祸。类比元稹在作品中大肆宣扬“女为尤物”的思想,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期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待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⑩,细致描绘了唐玄宗因贪恋美色而导致国破家亡的悲剧。无论是白居易从帝王宠色误国出发,还是元稹从普通男女进行描绘,都在无形中强调同一个思想论调,那就是“女尤物”论,通过在作品中否定此论调,来达到讽刺劝谏之功效。而文本中张生那番犀利的言论正是元稹以“女祸论”“尤物论”作为当时劝谏主题的切入口,来满足主题先行的需要。
(三)社会风气使然
从时间上来看,《莺莺传》写于元稹和韦丛成婚不久之后。一方面,他对自己抛弃莺莺,成功迎娶千金韦丛是极为认可的。他在《梦游春诗七十韵》中写道:“一梦合足云,良时事婚娶” ⑪“江花纵可怜,奈非心所慕” ⑫,尤为清晰地陈述了自己抛弃莺莺是因为“非心所愿”,而迎娶韦氏则是“良时婚娶”,即便他对莺莺的感情是真挚的,但在前程和功名面前,他将两人的曾经只形容成“良宵一梦”。元稹之所以会有这种思想,与唐朝当时门第等级观念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描述:“盖唐代社会呈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反婚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⑬莺莺虽不算布衣出身,但也算得上是个没落贵族,对比“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莺莺的存在,显然对张生的前途无益。而当时文士的仕途前程又与婚姻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张生在抉择之下选择了出身更加优越的韦氏。但另一方面,张生也深陷于抛弃莺莺的自责中。外在时局的压迫只能迫使他向内在传统伦理寻找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思想领域,儒学作为统治工具被重新推到前面,儒学一向重礼轻情,轻视“情爱”,将“人欲”当作世界原罪,将女子视为“红颜祸水”。历史上,前有商纣王因受妲己魅惑而丧国,后有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再者有武后乱政、韦后夺权、安乐公主毒杀中宗,此桩桩之事,无不是宫闱女祸之责,红颜祸水之过。因此,元稹站在儒家伦理的制高点,用“红颜祸水”理论作为对男权主义的合理解释,充满了男权至上的色彩,赢得了当时士人阶层的赞赏,故此,文本中张生的行为又被当时士人称之为“善补过”。
三、对张生形象的重读
对张生形象的解读,仅仅停留在作家的创作经历上,未免太过僵化生硬,容易失去文本自身的审美意蕴。因此,在基于作家创作体验的前提下,结合文章创作背景回归文本本身来探究张生形象的审美内涵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审美接受层次上对张生认知的偏差
除了文本客观刻画之外,读者在审美接受层面上对张生形象的塑造有一个二次创造的过程,其中不乏参与读者的主观认知、情感、经验等等,这些主观因素的参与,大大增加了对张生形象的认知偏差。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比起悲剧人们更加倾向于喜剧性大团圆的结局,无论是陈玄祐《离魂记》记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王宇和倩娘,还是最终成为汧国夫人的李娃,大团圆的结局往往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慰藉,更加满足读者的情感诉求。而《莺莺传》的张生作为这种传统美的反叛者,造成了美的幻灭,故此成为大众口中所谓的“负心汉”。基于中国式传统团圆心理,对于首先提起别离的一方,定多有责难,也就说,对于破坏稳定和谐的现状、违反现有秩序者,大都会被否定,不单单局限在爱情领域,张生由此被扣上“始乱终弃”的帽子,也可见一斑。
从心理上来讲,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弱者保护”,庇护“终弃之”的崔莺莺, 谴责“始乱之”的张生。“始乱终弃”一词最初借崔莺莺之口倾吐“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余不敢恨” ⑭,言辞婉转,柔软多情,激荡起读者内心阵阵涟漪。不仅如此,面对张生苦求已久的琴技,崔莺莺奏了一首意味深长的《霓裳羽衣曲》。传说中的《霓裳羽衣曲》本是唐玄宗亲作,杨玉环起舞主演,算是两人定情之曲,安史之乱后,杨贵妃被杀,两人未能终成眷属。而崔莺莺选择这首琴曲的原因,多多少少也在映射她与张生的最终结局。由此可以看出,她对自己与张生的爱情根本是不抱有任何希望的,甚至她已认定张生此去,自己便会被抛弃。次年,张生考试失利,于是便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再战,这时他还常寄信给崔莺莺,时时安慰,可崔莺莺回信中处处吐露悲观之情:“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 ⑮文中,崔莺莺以弃妇自比,语言婉转,处处伤情,锱铢之言,尽戳读者柔软的内心。正是通过文本塑造了这样一位柔情似水、顾影自怜的女子形象,对比决绝的张生,读者似乎更富同理之心,因此在心理上更加排斥张生。
(二)张生形象的重新审视
从深情款款到恩断义绝,张生性情之变虽不值后人效仿,但也不应遭受众人口中“始乱终弃”的苛责。回归文本本身对张生形象进行梳理:初遇莺莺,睹其仙容,张生惊,为之礼——后托红娘牵线,红娘惊沮,张生悔之——莺莺回诗,张生大喜,逾墙于西厢候莺莺——莺莺训斥,张生复逾而出,于是绝望——夜间莺莺携枕而至,张生惊而大喜——有过十日余,未见莺莺,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以思莺莺——莺莺至,其则心安——后张生即往长安,莺莺未语,离别之夜,也未能相送,旦而张行——后张生返还蒲州,知莺莺能文善琴,索求再三,但终不得愿——后张生又当西去,莺莺终弹一首《霓裳羽衣曲》,以当作别,明旦张生行。就两人的恋爱过程来看,崔莺莺在恋爱中完全占据主动权,张生的悲欢离合都与崔莺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息息相关,这样的张生,俨然是不符合大众口中的负心汉形象。反观崔莺莺,在张生多番示好后,并未给出明确回应,忽冷忽热的态度更令张生摸不到头脑,揣不透心思,致使张生抱憾而行,而后人仅凭张生一封斩断情丝的断绝书,就大骂张生始乱终弃,不免有失公允。
四、结语
就一般情理上讲,在古时男子想要彻底背弃女子,最简单、最合理的方式就是“不复相见”,对比《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张生在双方各有嫁娶之后,“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 ⑯,虽不敢直接断定张生是否想要“再续前缘”,但很显然能够感受到张生对崔莺莺仍是存有情义的。两人之初的结合本身就具有非法性,这种离经叛道的爱恋已然为悲剧性结局埋下伏笔,当张生选择皈依礼教,放弃自由爱情,便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两人的爱情悲剧,就此来看,两人的悲剧根源来自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因素,是文化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注释:
①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页。
②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第59页。
③⑬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2页,第116页。
④⑪⑫谢永芳编著:《元稹诗全集》,崇文书局2016年版,第578页,第561页,第562页。
⑤⑥⑭⑮⑯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14页,第4016页,第4014页,第4015页,第4017页。
⑧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⑨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33页。
⑩顾学颐、周汝昌选注:《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参考文献:
[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14-4017.
[2]卞孝萱.元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0:75.
[3]魏颖.性别视角中的女性形象和文化语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8.
[4]郭树伟.元稹《莺莺传》“尤物论”劝诫主旨与文本构建之关系研究[J].南腔北调,2022,389(11):67-73.
[5]林保淳.《莺莺传》中的张生不是负心汉[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1):102-107.
[6]李苑溶.元稹《莺莺传》张生“忍情”之小探[J].文教资料,2019,836(26):1-3.
[7]王昱.元稹《莺莺传》新解[J].名作欣赏,2019,668
(36):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