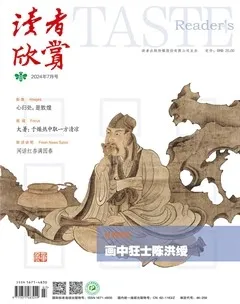心归处,是敦煌
2024-07-22王琳

奔赴:从北大到敦煌
黄昏时分,站在三危山向对面看去,夕阳照耀着整座莫高窟,那里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入口。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样错落地分布在崖壁上,好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沧桑而神秘……
这是樊锦诗第一次看到莫高窟的情形,也是电影《吾爱敦煌》的开场镜头。蓝天、大漠、洞窟、壁画……伴随着樊锦诗的扮演者——演员陈瑾的旁白,影片在敦煌苍茫而静寂的氛围中展开叙事。
在世人眼中,敦煌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敦煌石窟艺术历经1600多年绵延至今,是璀璨的文化宝库。在这样宏大的背景下,电影别出心裁地采用了纪录展现与剧情演绎相互穿插的表达方式,通过主角不疾不徐、质朴诗意的旁白,为观众营造出一个亲切坦诚的对话空间,如同翻开一本泛黄的樊锦诗手记,安静地诉说着光阴流转与人物命运。
时光的指针拨回1963年,镜头对准柳园火车站,24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服从国家分配,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当时,国家要对莫高窟实施抢救性加固工程。敦煌需要我,我就来到了敦煌。”从繁华的都市到寂寥的大漠深处,怀揣着对敦煌艺术的憧憬和报效祖国的理想,樊锦诗就这样,从此开始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穿行、成长。
彷徨时,她会在黄昏爬上三危山,凝望着对面那片戈壁瀚海中的奇迹,找寻坚守的力量。艰苦的境遇里,她常想到李商隐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还有李广杏,这是只有敦煌才有的人间美味。当香甜的李广杏入口,生活的苦也被渐渐融化。
奔赴,留下,相守。电影对于青年时期樊锦诗的勾勒诗意、干脆,只用了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让观众记住了这个系着红围巾,意气风发、扎根大漠的年轻女孩。
第一个场景聚焦于首任院长常书鸿对她的启蒙和点拨:“莫高窟饱经沧桑,它就像一位历史的老人。为了这样的老人,当一辈子儿女,不枉此生啊。”身处辉煌灿烂的第217窟,仰望着气象万千的巨幅壁画,聆听着常书鸿的介绍,樊锦诗的眼中满是崇敬与震撼。
第二个场景,寂静的洞窟中,樊锦诗独自一人凝视着第259窟的禅定佛。那一抹跨越千年的禅悦微笑,抚慰了每个来到敦煌的人,也同样令樊锦诗沉醉:“这里的一切让我着迷,让我痛惜。我愿用我的心来温暖这冰冷的洞窟,去承接这文明之火。”

第三个场景则是从山东来的李云鹤,为樊锦诗讲述自己当年是如何与敦煌结缘的。“这辈子就修洞子了,这辈子修不好就下辈子。”正是在常书鸿、段文杰、李云鹤等老一辈敦煌守护者的感染下,樊锦诗愈加坚定了守护敦煌的信念。她和研究所40多位职工一起临摹、考证、研究,700多个洞窟在他们的手中一点点地被清理、记录、修复,从满目疮痍到华彩重现。
时光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悄然飞逝。樊锦诗成为研究院的骨干力量,也成了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母亲。然而,她不得不和家人长期两地分离,丈夫彭金章在武汉一人带着两个儿子,樊锦诗则独自在敦煌守着莫高窟。她已经习惯了看着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洞窟,看着洞窟里的佛像泛出微笑,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冒出新芽,在秋天树叶一片片凋落……如何延续莫高窟的生命,也成了樊锦诗毕生的使命。
传承:从洞内到洞外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拥有735个洞窟、2400余尊塑像、45000平方米壁画、50000余件藏经洞出土文献的敦煌莫高窟,历经千年营造与传承。如此恢宏的背景下,面对浩如烟海的人物素材,如何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浓缩漫长的时间跨度,呈现一代代敦煌守护人“择一事,终一生”的默默奉献,对创作团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叙事构思上,《吾爱敦煌》选择了做减法。电影像按下了快进键,将漫长的人生经历和纷繁的人物故事,压缩到101分钟的影像中,勾勒出敦煌守护人半个多世纪的生存之苦、研究之难、守护之困,将叙事重点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
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相较于之前35年在洞窟中的埋首研究,此时的她不得不开始面对“洞外的世界”。
对樊锦诗和莫高窟而言,最难的并不是耐得住寂寞,而是与喧嚣抗衡,与时间赛跑。彼时,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参观游客数量的激增,洞窟内的生态环境日益严峻。如何长久保存这座独一无二的艺术宝库,解决旅游开发与修复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了巨大难题。
面对某些部门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经营的压力,樊锦诗力排众议,与涌向敦煌的各种力量进行博弈。年轻时不爱说话的她,在年过花甲后为保护敦煌四处奔走。为此,她频频在会议上直言不讳,为反对莫高窟上市经营跟人拍桌子发火。有一天,当她经历了一番据理力争,从市区乘车返回莫高窟时,第一次感到这条20公里的路是如此漫长。她想起了常书鸿、段文杰以及前辈们当年从这里走向莫高窟的艰辛,也深感守护莫高窟任重道远。
夕阳下,樊锦诗再次登上三危山山顶,凝望着对面如眼睛一样深邃的洞窟,往昔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她坚定地拨通了电话:“莫高窟请求国家保护。”终于,在她的坚持下,将莫高窟完全开放这种不顾未来的主张偃旗息鼓,“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也随之展开。
时代在进步,敦煌保护理念也要更新。20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去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电脑。由此,她想到为莫高窟每一个洞窟及其中的壁画、彩塑建立数字档案,为后人留存下完整精准的数字化资料。于是,她开启了敦煌文化遗存“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敦煌”工程,积极与国内外的技术公司开展合作,用数字技术留住莫高窟的原貌,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筹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在尽可能保护敦煌的同时,让更多人看到敦煌之美,探索出一条兼顾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还有一项工作樊锦诗始终不敢懈怠,就是莫高窟考古报告的整理与出版。“你是带着做考古报告的任务来的,莫高窟400多个洞窟都有壁画和塑像,考古报告至少要写100卷哪!”当初常书鸿院长的话还犹在耳边。
2011年,倾注了樊锦诗毕生心血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 6 6— 275窟考古报告》终于正式出版。她动情地抚摸着书页,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当年那个带着考古任务来到敦煌的少女,如今已经73岁了。诚如樊锦诗所说:“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守护:从青丝到华发
隆冬,雪花纷纷扬扬,三危山更显苍茫。敦煌研究院中,那座以樊锦诗为原型、名为“青春”的雕像也落满了雪花——一位少女背着挎包,拿着草帽,昂首向前,意气风发。干净利落的短发上,白雪飘落,如同华发。
朝朝暮暮中,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守护了6 0多年,如她所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敦煌的守护人。”面对这位老人6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电影并未将人物冠以“英雄的光环”,而是用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真实还原了樊锦诗的所见所感和人生经历,通过贴近生活的人物塑造,找到主角与普通人之间的共通之处,让观众自己在电影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
因此,我们在观看电影时,会不时被剧中人物生动鲜活的形象所打动:身为莫高窟人的一分子,樊锦诗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在洞窟里,她是安静谦卑的“敦煌女儿”,灿烂的石窟艺术让她着迷、让她痛惜;而在洞窟外,她又是倔强的守卫者,为保护敦煌而据理力争,让人惊叹她瘦弱的身体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身为院长,她低调随和,出差时健步如飞,白天在饭店和人谈合作,晚上却在北京四环边上的旅馆里煮方便面充饥;而身为妻子、母亲,她与家人两地分离长达19年,对孩子的愧疚和对丈夫的思念,并未被崇高的目标与伟大的事业所掩盖。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被她和爱人彭金章“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的相濡以沫所感动。影片中,出差在外的樊锦诗包里总会装着丈夫自制的酸奶;退休后,她会和丈夫一起喂养流浪猫,在散步时会看似不经意地拉住丈夫的手。而在丈夫离世时,她无限悲伤遗憾,言语中满是眷恋:“我的老彭走了,天上人间,各在一方。”却又觉得“老彭没有走,他还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
如同常书鸿所说,樊锦诗“让自己成为一道光,照耀着莫高窟”。纵观全片,简洁、平静的叙事中,始终涌动着一股无声无息的力量。无论是作为影片主角的樊锦诗,还是常书鸿、段文杰、李云鹤等老一辈敦煌守护人,或是不断来到莫高窟工作的年轻一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吾爱敦煌。
正是怀着对莫高窟的敬畏和对敦煌守护人的崇敬,主创人员在前期采访、实地拍摄、洞窟模拟、人物塑造、配乐设计等工作中下足功夫。通过诠释历代敦煌守护人对敦煌浓烈深沉的爱,影片让这一群体形象从大漠深处走进观众的心里,也让“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银幕上熠熠生辉。
电影最后,冬季的莫高窟恢复了宁静。北风掠过白杨,九层楼檐下的风铃叮当作响。宕泉河畔,一位身穿红色棉衣的老人背着双手,向着苍茫寂寥的莫高窟蹒跚而行——这位老人正是樊锦诗本人。“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望着樊锦诗踽踽独行的背影,时间仿佛在此刻凝固,电影落幕。在大漠中伫立千年的莫高窟,阅尽沧桑却依旧包容万物,拥有涤荡人心的力量。出现在影片结尾,源于樊锦诗自传中的这段独白,久久地回响在我心中—“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我想,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吾爱敦煌》想要呈现的不仅仅是通过樊锦诗的人生故事,为敦煌守护人这一群体形象书写“精神自传”,更是希望每一位观众能够透过他们的故事,思考自己的人生——在生活的喧嚣沉浮中,我们如同人生的过客,究竟应该心归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