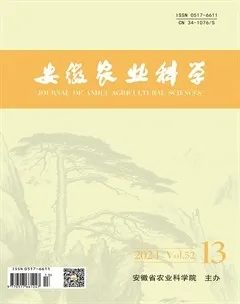内生发展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与路向选择研究
2024-07-22逯海勇胡海燕张成秀
摘要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过程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着保护与传承薄弱、过度依赖外部因素、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借助内生发展理论,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现状出发,以内生与外生的有效耦合为着力点,提出了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乡村共同体、构建内外资源统筹的网络结构、培养村民主体自发的主导意识、建立内生性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构建系统的新型“文化+”产业链、建立赓续发展的内生保障机制的新发展解决方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促进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传统村落;内生发展;保护与发展;路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 F59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13-0163-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13.04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Protection,Development and Route Sel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LU Hai-yong,HU Hai-yan,ZHANG Cheng-xiu
(College of Arts,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Shandong 271018)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weak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excessive dependence on external factors,and insufficient internal development impetus. In this paper,with the aid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starting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within the effective coupling of the birth and exogenous as main point,put forward the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buil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o plan as a whole network structure,cultivate the villagers body spontaneous leading consciousness,establish endogenous new villager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build the system of the new “culture +” industrial chain,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development solution with an endogenous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promoting the living protection,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Endogenous development;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Route selection
基金项目 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2023-WHLC-011);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L2021Z07070428);2021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项目“环境设计”。
作者简介 逯海勇(1971—),男,山东东明人,教授,硕士,从事传统村落及乡土建筑保护研究。*通信作者,副教授,从事视觉文化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 2023-12-03;修回日期 2023-12-25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基因库”,是乡愁寄托的重要载体,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正逐渐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2012年国家建立了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制度,至2023年,全国共有8 155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这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着保护与传承薄弱、过度依赖外部因素、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其中“内生”问题是制约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国家在2016年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其后党中央、国务院连续6年对农村内生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从内生发展视角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问题,对地方乡村建设和优化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内生发展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是针对外源发展模式忽视地方价值、限制地方自主发展的能动性以及发展中的持续性等问题,由瑞典Dag HammarskJld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报告《我们现在怎么办(What Now)》中正式提出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这一概念,强调从区域内部推动现有资源优势确定乡村发展转型路径。国外学者多从培养地方发展能力、保护生态环境等角度阐述乡村内生发展内涵。基于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本和市场如何促进地方生产力、本地“传统再造”及“多元主义”的问题,基于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价值、文化、技术和社会参与等问题。总之国外研究已将内生发展理论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逐步将视野拓展至地区的综合发展。国内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内生发展的诠释和内生发展模式探索,研究内容涉及内生式发展模式[1]、乡村发展模式[2]、理论基础构建[3]等。近年学界出现了“上下联动”和“内外共生”的混合路径新转向[4],但囿于干预路径依赖和发展经验不足,结果遭遇“外”动而“内”不动的窘境[5],这说明传统乡村发展障碍依然存在。基于此,该研究借助内生发展理论,深刻缕析现阶段传统村落内生发展矛盾根源,寻找内生与外生的有效耦合机制,尝试构建传统村落内生发展的能动性路径的逻辑框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促进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1.1 保护与发展目标缺失 自2012年传统村落名录建立以来,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趋势得到遏制。然而,将传统村落列入保护名录仅是保护工作的开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传统村落的赓续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尽管国家和当地政府反复倡导文化遗产的传承,但仍缺乏有效的保护与发展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在创建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模式时,仅将保护和传承方法纳入其中,缺乏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目标;二是现有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忽视了传统村落是由人、遗产、现代生活和环境生态组成的整体系统;三是对现有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多关注其过往文化遗产的保存、传承,而对于传统村落遗产、人的现实需求与未来生命力的共生性缺乏讨论[6]。
1.2 保护与发展价值偏移 地方政府对传统村落的价值认知不足,过于看重其商业价值,盲目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开发形式仅满足村容村貌“面子”的装扮,忽略了传统村落本体价值“里子”的深耕,造成传统村落“开发性”“建设性”“肌理性”破坏,或模仿其他地区将其当景区项目打造,造成传统村落“套餐化”“景区化”“同质化”,或把重点放在保留传统村落遗产价值的原始功能和单一功能的延续,而忽视对传统村落生产方式的保护和振兴措施,导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与居民生活生产需求的兼容性较弱,影响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1.3 保护与发展主体失位 现有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格局已普遍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的“至上而下”的外源式模式,这种模式忽略了村民的主体性。地方政府在立法条款中虽然明确规定村民和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条款,但这些规定缺乏实际功效。村民的参与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规划上,对保护和发展决策及管理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难以分享其收益和成果,在权利、义务和责任缺失的情况下,村民对参与保护和发展村落的积极性普遍较低。另外,居民对产权不清或产权分散,不愿对老屋进行维修和保护,无法通过经营增加经济收入,致使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7]。
2 传统村落内生发展实践困境
2.1 乡村共同体意识涣散 现阶段传统村落治理过程中村民的监督权、参与权等权利难以有效发挥,无法满足村民作为村落主体的诉求。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的系列农业改革和集体化政策使农村社会秩序和管理结构重组,同时也导致传统乡绅精英阶层解体。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剧了城乡不均衡。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老弱妇幼成为乡村的孤独守望者。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逐渐被半熟人社会所取代,农村社会个体原子化和关系陌生化趋势明显,乡村群体边界、利益边界和归属边界逐渐模糊,由血缘和地缘组合的乡村共同体正逐步瓦解。
2.2 内外资源统筹性缺乏 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实践中,由于长期寻求外部资源介入,逐渐形成亦如社会福利资源领域存在的“福利依赖”问题,而本地自身能力、资源条件等优势难以发挥,内生发展动力明显不足。这种长期靠外部力量扭转发展局面与村落固有的“内生堕力”形成拉锯,“外生动力”的过于依赖、“内生动力”的资源不足、“内生堕力”的疲于应付,构成了传统村落“外”动而“内”不动的深层困境。如何适当借助外部资源,统筹协调内外资源融合,实现优势互补,成为传统村落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2.3 地方自主性受到限制 虽然地方政府的政策强调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要以地方为主导,但依赖外生资源介入的现象仍然很明显。而当前外部资源的断续性与实际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难以实现和村落本地资源间的有效衔接。这种依靠外部资源不仅体现在个体行为上,在村落地方自主发展实践过程中,依赖外部资源发展问题仍很严重。在外生发展“自上而下”的主导地位模式下,地方原居民乡村发展行动空间受到制约,只能被动地按照上级政府的规定行动,地方发展的能动性和自主性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2.4 发展主体整合性不足 从发展的角度看,现阶段传统村落的发展缺乏整合性,影响了传统村落的内生发展和实践。具体来说,一方面,强调村落主体与个体发展相统一,但在实践中,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与个体诉求并没有有机地融合。村落主体发展与个体发展存在偏差现象,村落保护与发展成效不明显。另一方面,国家倡导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精准扶贫等政策并未纳入传统村落保护体系,传统村落的生存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传统村落的发展中,仍存在“重面子”“轻里子”、经济发展滞后、产业不明等现实情况。
3 内生发展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路径
3.1 信仰重塑: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乡村共同体
3.1.1
增强村民乡土认同感,重塑乡村信任。解决乡村人才紧缺以及培养新乡村精英的问题,特别是结合城市返乡的“新乡贤”或“能人”,打好“乡贤+”组合牌。他们根植于乡村社会,与普通村民相比具有娴熟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前瞻性的视野,可充当链接“乡城”之间的桥梁。认同为乡村内生发展注入精神动力,通过乡土文化基因的挖掘,重塑村民对寺庙、祠堂、花园等公共建筑空间的认知,唤醒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
3.1.2 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乡村服务体系。政府应改变“城市偏见”的观念,调整乡村内部的资源分配,以协调者的身份介入乡村,使资金和建设费用向乡村倾斜。完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建立与当地产业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和社会竞争力。
3.1.3 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增强乡村凝聚力。改变以往由政府单一主导的管理方式,实施以村民参与自行讨论乡建规划项目,邀请专业人士参与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建设投资的依据[8]。增强村民共享、协作的公共参与精神和责任精神,加强乡村凝聚力。
3.1.4 建立新型乡村管理体系,重塑乡村权威。完善乡村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制定乡村自治条例和村民规章制度,健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制度。
3.2 内外互补:构建内外资源协调的网络结构
传统村落的乡村性因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环境,已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传统结构秩序,这种稳定的“传统性”结构在当代语境下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显得极不适应,因此“发展滞后”与“惰性”在所难免,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撬动,唤醒传统村落的“沉睡”状态。Christopher[9]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纯粹”的内生发展而不依赖外部力量,仅依靠本土行动是不现实的,只能算是一种“理想型”。在激活传统村落的内生资源同时,还要掌控好外部资源的介入量,介入过度会造成创新能力不足、发展动力减弱,甚至出现污染环境、贫富差距较大的现象。外部资源介入主要以“唤醒”“激活”为标准,当内生资源形成持续动力后,外部资源还要以“旁观者”的身份关注内生动力,使外部资源成为内生动力长久的“加油站”。随着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推进,内生资源逐步替代外部资源成为主导村落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初期由政府主导的控制权、享有权逐步转归地方主导,实现从外生动力到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转换,形成“内”动的常态化。为打破“外”动而“内”不动的僵局,改变村民“等靠要”等依附性惯习和除能化心态,保持上下联动、内外协调的持续动力,还要防范“内生堕力”的滋生,通过鼓励村民参与以及“全民在场”的勤劳创新和锐意进取,强化内生主体的自我改变和发展意志,防止“内生堕力”与“外生动力”之间拉锯现象发生。
3.3 内生主导:培养村民主体自发的主导意识
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的关键是人才振兴,为此,必须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懂经营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村民。可通过网络资源、专家团队、地方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种知识平台展开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10],对不同诉求的村民进行不同形式的教育指导,提高村民的学习经验;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发展,加强对村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短期技术指导,使村民加快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提高村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帮助村民建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同时加强产品销售信息传输,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及时将信息传递到农村各个角落的村民手中,使村民的农产品销售到国内外,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财政投资,落实国家对涉农惠农的政策,保障村民的基本收入,扩宽村民致富渠道,有效解决村民面临的紧迫问题;结合国家“设计下乡”政策,针对传统村落规划设计、民居保护修缮、环境整治、运营管理、历史文化传承、乡村文创和产业培育等领域方面的知识,吸引更多的设计师和文创团队入乡,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陪护式服务;鼓励村民参与农村发展决策过程,引导广大村民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发展决策的权利,如进行选举、村务决策等活动,并在全过程参与中强化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意志,最终使每个村民达到在参与中发展、在发展中参与的有机统一。
3.4 三共协同:建立内生性新型村民自治组织
3.4.1 通过“共治、共建、共享”多元协同治理传统村落。政府应在财政、金融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简化审批程序,降低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准入成本,同时明确角色定位,合理划分管理界限,以平等态度支持村民发展自治组织;实施村企共建共治工程项目。结合传统村落实际发展,建立村级企业党建联盟,通过“村企联动”形式,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发展新格局;积极吸收社会成员力量,营造良性的管理秩序。社会力量的参与可有效弥补人口外流而导致的自治能力不足现象,并与当地留下的居民互融构成新的社会关系。培育村民的自主发展能力,帮助村民建立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产业合作等组织,以满足乡村多元内生发展所需。
3.4.2 加强对本土人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本土人才是振兴乡村的内在动力。要坚持村民主体原则,增强村民乡村自治的“局内人”意识,全面提高村民素质。有序引导大学生、“新乡贤”和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忧,留守创业。建立以青年自治合作社为主体,由村委会监督机构、专业团队提供技术援助的发展模式,引导企业家、设计师、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服务者、公益性文化组织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乡村文化建设队伍,以满足建设美丽乡村各类人才的需要。
3.4.3 明确村民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要宣传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高大家对“开发性”“建设性”破坏的防范意识,防止传统村落沦为“旅游胜地”;另一方面,村民的日常行为应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和导引,从而减少村民自治进程的随机性,通过法律法规澄清传统村落自治组织与村民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之间的关系[11]。此外,还要响应国家政策,定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焕发村民自治主体力量,把“话筒”移交给村民,真正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治理新格局。
3.5 创意引领:构建系统的新型“文化+”产业链
构建新型“文化+”产业链,就是要充分利用传统村落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遗存、传统民居、特色农业等资源禀赋,结合大数据、虚拟现实、5G+8K等新技术赋能历史文化遗产传播,创新性打造传统村落经济发展模式和振兴路径,围绕传统村落特色文化资源、特色文化品牌创意、数字文化、传统“手造”、有机农业等乡村经济,着力培育新型乡村经济新业态,以此实现传统村落文化振兴和村民富裕[12]。
第一,聚焦“传统村落文化+文旅”深度融合。在保护的前提下可通过探寻传统村落文化,将其打造成“可观、可游、可赏、可居”的文化主题空间,使文化遗产活起来,增强游客的体验性与获得感,体现传统村落精神文化内涵。还可通过建立“乡村群”,引导周边乡村协同发展,强化乡村区域性整体布局,实现联合产业的聚集发展。第二,推动“传统村落文化+特色品牌”融合创新。依据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禀赋,促进“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打造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生态文化旅游多业态融合的产业链条[13]。结合传统村落的特色民俗和历史文化价值进行品牌升值,对传统手工业产品进行品牌构建。通过创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唤醒村落文化记忆,重现村落公共文化空间,还原村落公共文化生活,使传统村落这棵“老树”再发新芽[14]。第三,开创“传统村落文化+数字科技”融合的新业态。通过借助人工智能和VR、AR数字化技术应用,还原传统村落的历史场景,形成实时互动和三维沉浸式体验,发挥其文化传播和资源共享作用。借助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传统村落进行数字化模型数据采集,建立完整、系统的三维数字模型库,完成对传统村落的数字化保护,同时建立数字化报警态势预测系统,及时发现并应对出现的危机。
3.6 和谐共生:建立赓续发展的内生保障机制
激发传统村落内生发展活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村民的民生保障放在首位,通过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使城市发展的资金、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特别是资本投资反哺传统村落,为发展传统村落铺平道路。在城市反哺的同时还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边界”,管理者身份不是以“他者”来管理,而是以“我”和“你”的身份形成平等关系,使村民主体真切体会到政府的帮扶支持。政府还要通过增权赋能赋予乡村基层特别是弱势群体一定的财政和行政权力,不断巩固村民的管理基础和能力,建立均衡的社会权力分配机制,优化社会秩序结构,同时,还要对村民的权力进行适当监督和约束,规范和加强村民的理性行为,防止权力过度使用[15]。建立内生保障机制还要尊重村民主体行动意愿,充分听取村民的诉求和建议,合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投票权和管理权,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发展环境改善等行动中的村民自治功能,确保乡村建设让村民满意。扩大农业保险覆盖率,提高风险保障水平,以此作为支持农业的重要手段,这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民生保障释放乡村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更是现代语境下传统村落有效保护和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在内生保障机制获得持续自主性的同时,要及时打破传统村落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度流向的“抽水机”效应,使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回归主体。明确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过程中所应承担的各种责任。建筑规划部门、文化旅游部门、文物部门等要做好监督管理,明确各部门保护权责,通过传统村落的主体责任落实和村民自治的整体合力,共同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61-68.
[2] 黄华,肖大威.基于内生理论的我国乡村发展模式研究[J].小城镇建设,2021,39(3):10-16.
[3] 章志敏,张文明.农村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转向、命题与挑战[J].江汉学术,2021,40(4):5-15.
[4] 文军,刘雨航.迈向新内生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J].贵州社会科学,2022(5):142-149.
[5] 王进文.迈向内生发展: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逻辑与路径选择[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1):93-103.
[6] 朱祥贵,张雯杏.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地方立法的新路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4):110-120.
[7] 陈淑飞,许艳.乡村振兴战略下山东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9(9):160-165.
[8] 刘祖云,张诚.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2-48.
[9] CHRISTOPHER R.Culture economies,centre for rural economy[R].Newcastle,England:Newcastle University,2012.
[10] 张慧,舒平,徐良.基于内生式发展的乡村社区营建模式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7(9):72-77.
[11] 林莉.振兴传统村落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其治理导向[J].探索,2021(6):58-69.
[12] 王院成.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三个重要逻辑[N].中国文物报,2020-02-14(05).
[13] 杨瑾,鄢金明,杨红.内生发展理念下传统村落保护与振兴路径探究[J].城乡规划,2022(2):39-50.
[14] 王院成.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34(3):37-40.
[15] 李伯华,杨馥端,窦银娣.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J].地理研究,2022,41(5):1407-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