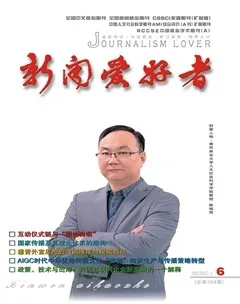培育“韧性”:返乡创业青年的平台想象与媒介实践
2024-07-09周孟杰
【摘要】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们难以彻底摆脱平台权力控制与算法支配,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会丧失韧性。聚焦返乡创业青年的数字媒介实践,探究他们在平台结构性控制的压力下所展开的具体沟通互动与韧性策略发现,返乡创业青年通过制造常态、锚定身份、替代逻辑和传播行动过程消解不确定性的算法想象。
【关键词】返乡创业青年;平台社会;韧性传播;数字媒介
一、问题意识:将韧性理论植入乡土中国
“韧性”被用来描述系统、组织或物质机体遭遇各种危机和外力干扰作用之后,展示出来的柔韧性、坚实度与恢复力。20世纪以来,各个学科逐渐将“韧性”一词不断概念化和可操作化,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在1973年发表的《生态系统的韧性与稳定性》中强调,“韧性”体现为抵抗而不自灭,且保持某种持久性的特征。心理学家们通过对“韧性”概念的讨论,细致考察了个体作为一个复杂生命系统是怎样与周围系统发生交互作用的。[1]进入21世纪后,韧性理论逐渐由生态学、心理学延伸至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
在传播学领域,国际传播学会前主席帕特里斯·布扎内尔首次提出了“韧性传播理论”,强调了韧性是通过五个阶段来抵御破坏性冲击和转变过程的。[2]尽管她对韧性的理解仅局限于人际传播、危机传播和健康传播,但给整个传播学界带来了新的理论对话可能。与此同时,国内外传播学界将“韧性”概念放置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语境下加以阐释,指涉因共同血缘、语言和历史文化团结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成功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甚至在面临压力和危机之后转变为新常态的聚合或集体互动过程的实践策略。“韧性”一方面强调了人或组织在受到打击之后的恢复能力,另一方面突出了主体重新融入和促进生产性变革的过程,体现出持续不断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在理论旅行的背景下,“韧性”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也被纳入对中国乡村社区恢复、乡村空间演变以及乡村地理的研究之中。韧性理论的系统化与非线性的演化观念,对解释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发展具有较强的适宜性和理论优势。[3]本研究进一步将“韧性”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审慎地将其引入到乡村传播领域,探究在深度媒介化时代,返乡创业青年在面临政府政策执行、生活文化融入、经济利益冲突等困境时所采取的回弹韧性和修复策略。其中特别关注当返乡创业青年陷入平台控制及危机困境后,数据或算法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以及韧性产生的过程和原因。
二、平台控制:返乡创业青年的算法缠斗
青年群体为何返乡,以及回嵌乡土之后会面临何种社会挑战与公共性危机?有学者表示,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一方面,返乡之前的工作经历所形塑的主体性建构和劳动观念转型构成了他们返乡创业的微观动因;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消费变迁、人口红利结构转型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积累效应成为该群体返乡的宏观现实条件。[4]而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青年群体不断面临政策实施、创业资源与人情关系的多重围困。[5]不过,以上讨论都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出发,忽视了传播学或人类媒介学的视角。值得关注的是,使用短视频或助农直播带货成为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的重要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之一。随着新媒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为代表的网络短视频浸入乡村后,对村民日常文娱生活、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和文化结构关系产生整体性影响。因此,分析青年群体返乡的创业原因与回嵌乡土之后的困境,就离不开短视频媒介的传播沟通和媒介展演。青年群体的数字媒介实践已经转变为一种勾连返乡生活、创业梦想和乡村人际关系重组的文化中介。与其说“在乡村拍抖音”是数字媒介实践的一部分,不如说“在抖音里观察乡村”悄然成为一种生活惯习与媒介景观。大多数传播学者在讨论“韧性”时,仅强调了“韧性”产生之后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却遗漏了“韧性”萌芽阶段的“社会—生态”语境或时空关系。返乡创业青年在开展韧性式沟通策略之前,大多遭遇了平台权力控制并与算法展开过缠斗,导致他们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不断异化。
第一,平台社会的权力控制。当返乡创业青年的数字媒介使用被平台资本和算法掌控时,处于一种垄断性地位的数字平台正在利用算法对青年用户开展数据指挥、督导与考核,并通过规则劝服、项目合作和推荐服务等策略将他们的行为痕迹转化为一串有关联的数据。有学者指出,在直播中,流量分化的马太效应尤为突出,拍段子和卡直播广场的策略很难使带货主播从流量池中脱颖而出。在平台资本的支配下,主播们很难单纯依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爱拼不能赢”成为他们在数字媒介实践中的常态。[6]数据已经转化为一种新的资本权力和行为准则。平台媒体的资本技术逻辑主要表现为平台资本主义的信息霸权与数据垄断,以及对平台劳动者的隐蔽性剥削和具身性异化,而且还辅以情感化操纵或权力控制。[7]这种权力话语纠缠或媒介信息遮蔽,促使返乡创业青年在平台社会中陷入困局。
第二,算法与主体的相互缠斗。在平台社会中,算法推荐和分发系统逐步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也形塑着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真实感知、态度观念和行为标准。然而,由于平台运作和算法推荐具有一种不透明性和不可见性,返乡创业青年往往被困于平台控制的牢笼中,即在平台资本的控制之下,返乡创业青年处于一种对算法规则认知较低且无法采取行动抵抗的中断状态。大多数返乡创业青年虽然有较强的商业意识、市场危机和平台运营能力,但他们仍然对平台规则较为陌生。因此,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算法黑箱导致返乡青年群体与短视频平台之间的关系越发失衡,这也是数字韧性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如果将算法视为一种主体,其本身会不断引导和操控人的主体认知,在人与算法的相互缠斗过程中,算法会逐步习得某种“反侦查”能力。当然,返乡青年也并不是一个被动且困在系统中无处可逃的人,虽然他们的认知力和行动力受限,但也会寻找各种隐性或显性的韧性策略去抵抗平台的支配和控制。
三、韧性策略:数字媒介实践与传播沟通
布扎内尔提出的“韧性传播理论”重点指出了培养韧性的五个过程。第一,制造常态。在灾难或混乱中保持旧的做事方式或创造新的沟通渠道,通过制造一种日常化的生活常态,来维系和保持与原有局面相似的状态,同时形塑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惯习。第二,锚定身份。增强某些身份认同和沟通能力,这种身份认同的确立建构与主体行动、媒介组织和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第三,使用媒体网络。着力增强通信网络和媒体的连接互动,数字信息技术与媒介叙事在培养韧性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可信任度较高的交流网络和渠道,以不同形式的媒介沟通与传播互动方式来重塑韧性。第四,找寻替代逻辑。在与外界压力共存的情况下,努力寻找新的替代方式和论述逻辑,促进创新与独创性。第五,合理化负面情绪,促使有效行动。在强调积极行动的同时使消极情绪合法化,通过淡化负面情绪,强化正向行为来提升韧性变革潜能。[8]因此,本研究尝试通过韧性传播理论的几个过程阶段来探究返乡创业青年如何冲破算法黑箱,增强媒介实践与韧性沟通的能力。
(一)制造常态:改造家屋及物质性交往实践
从城市空间回嵌乡土社区的返乡创业青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安家与何以安家的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群体常以改造家屋、种植及拍摄花草为交流实践,制造媒介化生活常态。多数青年返乡后,改造家乡老屋成为其改变生活方式与制造常态的重要调适性行为之一。返乡即寻找心安之处,而建设新家屋成为青年群体寻求身与心、工作与休闲双重平衡的具体行动。改造家屋不仅是返乡青年调适乡村生活方式的日常实践,更是他们建构“村里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在表达。返乡青年会通过直播、短视频的方式记录改造家屋的全过程,并在线上制造一个群体性的“云端之家”。这不仅获得了社群粉丝的打赏和支持,帮助他们以家为媒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而且还能把“家屋”空间转化为一种媒介记忆,通过对家屋劳作记忆、乡村景观记忆与童年生活记忆的话语呈现,适当抵抗与遗忘过往的城市生存伤痕,激发和唤醒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和交往情景。
在强调非媒介中心主义的传播物质性视野下,物在本体意义上的丰富性、有机性和能动性被忽视或低估。[9]“物”可被视为多元意义上的文化产物,它与人、其他行动者之间仍会产生复杂勾连,同样具有一种社会生命。在物质文化研究脉络下,自然界中的花草与家屋也被视为一种中介物。返乡创业青年在改造家屋的过程中,不断种植培育新花草,通过手机,在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或抖音短视频中进行拍摄、分享和转发,召唤对田园乡村有情感连接的群体,创造一种以家和自然为媒介的情感共同体。返乡青年将“城市与乡村”“规则与自由”“创业与倦怠”等认知寄托和投射在花草世界和自然身上。因此,在返乡创业青年重新发现自然与花草媒介,对其予以拍摄、触摸和培育实践时,他们正在通过改造家屋来重新与乡村的熟人亲友、社区组织建立关系,更是与土壤、花草、石头等自然景观媒介建立深度情感勾连。而这种与人及自然的深层次互动,是制造媒介化生活常态的主要方式。
(二)锚定身份:形塑“创业群我”的新农人身份
返乡创业青年利用抖音拍摄短视频,把助农直播带货这种数字媒介实践活动作为一种主要创业项目,是青年群体与父辈进城务工谋求生计的主要差别之一。短视频不仅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展演平台,更是构成其媒介化生存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基本要素。青年群体的返乡创业实践超越了以追逐自我价值为中心的“私人性”,具有一种天然的乡村“公共性”,在此过程中不断形塑某种新农人的身份认同。
一方面,返乡青年拍摄的短视频内容或助农直播带货摒弃了以低俗、荒诞或充满二次元亚文化为主的视听风格,着重以客观叙述的视角凸显乡村的质朴环境、物产富饶和欣欣向荣的社会变迁,而平台流量和数据点击量并不是返乡创业青年的唯一标准。这种充满公共化的记录言说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的可见性与文化公共性再生产。因此,返乡青年在媒介中不断彰显“乡土创业”标签,而非自媒体“网红”身份。这两种身份标签的差异与对立,正反映出返乡创业青年的乡村社会属性、阶层文化观念以及对直播带货媒介实践的态度认知。另一方面,多数返乡青年强调“不仅要自己创业,更要带着村民一起创业”,甚至有青年多次提到“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因此,“创业”原本只是一个自我追求事业发展的故事,却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演化成为新时代乡村社会群体谋求发展的生动实践。这种以直播带货为媒介的群体行动,将返乡青年“自我”与乡村社会的“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形塑出一种“创业群我”的新农人身份认同,并进一步强化了乡村社会的共同体意识。返乡创业青年的主体性与乡村群体的内生性互为映射和观照,作为青年返乡的“我”的社会价值在“群体”中展现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此语境下,“创业群我”所营造的情感连接与社会共识有助于削弱平台算法的权力控制和改变人与平台之间的异化关系。
(三)替代逻辑:以“学做直播”抵抗不确定性的算法想象
返乡创业青年们多次表示自己并不是“做主播”,而是“做直播”,他们以“学做直播”为替代逻辑,将“甘愿劳动”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希望实践。“做主播”意味着他们将被卷入更深层次的媒介化或情感化劳动,而“做直播”的本质是将乡村特色产品利用短视频或直播的方式销售出去,其中涉及用户、产品、直播间运营、产品供应链、物流运输、包装设计等“人、场、货”多个维度。作为刚接触短视频直播带货的返乡创业青年,从手机操作、福袋福利到产品链接、直播流程、产品介绍都需要从头学起,这种技术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主体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有返乡青年表示,直播时突然会涨粉数万,或短视频转发点击量超万次。这种“天降流量”会让他们不知所措,甚至出现恐慌、逃避的心理。一般情况下,多数返乡青年在当天直播后会进行复盘,总结直播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话术逻辑或回复态度、售后流程和平台规制等。但是主体与平台的不对等关系,以及平台算法的不透明性,仍然会导致主体产生一种“混沌无序”的算法想象。
尽管平台算法有着缜密而精细的规则,但返乡创业青年只能意识到平台算法的模糊性或不可确定性,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做数据”的必要性。于是,返乡创业青年开展了一系列甘愿劳动和理性劳动,包括学习直播流程,掌握直播间节奏,积极主动回应粉丝评论留言,组建多个平台粉丝群。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所经营的乡村特色农产品本身进行更为严格的把关筛选。返乡创业青年为了达成销售目标而不断自愿增加直播时长,这种甘愿劳动成为一种消解平台社会控制或算法不确定性的具身实践,也被形塑为一种技术化的希望实践,而希望本身则具有较强的韧性。希望是返乡创业青年在遭受平台困境或现实困境之后,能够通过实践来激发其内生性的策略和战术。面对一次次的挑战和失败,这些年轻人在“学做直播”过程中不断进行着甘愿劳动,并表现出强大的韧性。
(四)传播行动:连接社会多元网络及引导式嵌入治理
返乡青年群体借助短视频或助农直播带货展示一种乡村劳动化叙事,通过积累和建立粉丝社群,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市场用户。同时其媒介实践的过程也是扩展社会人脉与资源的过程,数字媒介实践为返乡创业青年建构了一个由市场资本、乡村关系和数字平台所构成的多元互动空间与情感连接场域。
返乡创业青年的韧性传播实践是聚集农村农业、文旅广电、文化宣传等部门,以及社会公益组织机构、影视传媒企业、数字算法平台等多元社会行动者的数字场域。返乡青年的赋权行动和韧性过程无法脱离历史语境、文化脉络与社会制度。例如,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与江西省浮梁县合作,成立浮梁乡创学院,并组建“乡创”特派员制度,有效推动了城乡资源有机融合,为返乡青年群体提供创业平台,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县域基层政府、农业组织协会、数字媒体机构等多方主体联合互动,通过组织电商直播助农带货来开展“数商兴农”工程,通过孵化、培训、指导等形式来建设电商供应中心、乡村数字仓储和数字乡村示范园区,提高返乡创业青年的经济收入,促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此,这种外部社会网络资源嵌入返乡创业青年的媒介实践之中,并通过技术嵌入、政策引导、流量补助和外援帮扶推动乡村产业再造。
返乡创业青年的数字媒介实践与参与式传播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赋权行动与媒体仪式,这种参与式传播行动构成了返乡创业青年提升个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条件,使得他们的劳动主体性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中得以增强,也进一步改变和形塑了数字乡村的内在结构。与其说返乡创业青年在媒介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韧性是依靠自身主体性而进行的自我赋权过程,不如说这种韧性策略是整体社会及各个系统部门协同进行的一次集体行动与传播仪式。
四、理论对话:数字韧性的建构与思考
本文通过借助韧性传播理论的五个过程和理论框架,聚焦从城市社区脱嵌出来并重新嵌入乡土空间的创业青年群体,一方面,尝试将韧性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乡村传播,乃至中国本土语境之中,并结合当下平台社会和算法制度的媒介生态环境展开细致和具体的讨论;另一方面,从制造常态、锚定身份、替代逻辑、传播行动等几个维度切入,进一步与韧性传播过程进行对话,并加以完善。在强调主体的韧性策略和传播实践的过程中,本研究特别注意媒介技术或数字平台对韧性的影响,把握“数字韧性”的内在逻辑。
首先,“数字韧性”所产生的时间或空间关系均被数字媒介技术所形塑。返乡创业青年不仅会入驻抖音、快手、西瓜等短视频平台,还会选择B站、美团、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网络。这种跨媒介的新媒体运营大量涌现,也暗含着当今媒介渠道和技术界面的多元性,平台不再是简单的传播手段或载体,而是一种维持社会运转的技术基础设施。其次,“数字韧性”包含着一种平台权力制约或自我甘愿劳动过程。这既是平台所引发的生活变革,也会导致一种媒介化生存危机,人类遭遇着平台的结构性约束。数字平台通过逆向时间、排名打榜、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策略吸引创业青年群体持续投入平台运营中,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并使他们获得一定的可见性。虽然在此情况下,主体会陷入自我驯化及甘愿劳动中,但他们通过极强的韧性行为来抵抗平台社会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最后,“数字韧性”是在主体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媒介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作为来自主体的内生性能力,数字韧性更多的是与主体惯习有关的诀窍技能、隐形知识或战术策略。随着媒介化的深入,韧性传播会越发成为一种与媒介纠缠的、与客体相关的实践,主体也会依靠数字技术的可供性恢复并超越某种平衡的状态。由此可见,数字韧性并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液态且持续流动的状态,更是主体与技术在“结构—能动”之间循环往复的、具有弹性张力的数字调适或抗衡过程。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视阈下返乡创业青年的数字媒介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3CXW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海垒,张文新.心理韧性研究综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149-152.
[2]Buzzanell P.Organizing Resilience as Adaptive-transformational Tensions[J].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8,46(1):14-18.
[3]李红波.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启示[J].地理科学,2020,40(4):556-562.
[4]梁栋,吴存玉.乡村振兴与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现实基础、内在逻辑及其省思[J].现代经济探讨,2019(5):125-132.
[5]王玉玲,施琪.县域视野下青年返乡创业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1(7):23-28.
[6]姚建华,张申博.“爱拼不能赢”:草根电商主播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探析[J].新闻爱好者,2022(11):34-37.
[7]陈文泰,孙仲伯.媒介遮蔽与行动纠缠:平台型媒体的权力控制机制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3(8):47-50.
[8]Amankwah A,Gyamfi P,Oduro A.Cultivating Communication Resilience as an Adaptive-transformative Process during a Global Pandemic: Extending the Purview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Resili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22(16):5626-5646.
[9]曾国华.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路径与分支领域[J].国际新闻界,2020,42(11):6-24.
作者简介:周孟杰,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长沙 410006),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副教授,长沙社科智库专家(长沙 410022)。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