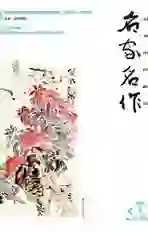水寒江静,载月明归:黄庭坚诗词中的禅意理趣及成因探析
2024-07-08许雯雯
许雯雯
[摘 要] 北宋时期,儒、道、佛三家思想呈现出深度交融的趋势,多元思想的融会贯通使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形成“以儒为本,佛道兼容”的思想体系和处世哲学,具体表现为其诗词作品呈现出的禅意理趣色彩。黄庭坚的诗学理论构筑和诗词创作实践是北宋“三教合流”趋势的有力佐证,对宋诗的变革与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黄庭坚的人生轨迹及其思想变化过程,能够探析其诗词中禅意理趣的形成原因。
[关 键 词] 黄庭坚;宋诗;宋词;禅意;理趣
一、“三教合流”的时代背景
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采取“重文偃武”的治国政策,通过改革科举制度笼络人才,儒士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以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名儒为首的士大夫集团顺势倡导儒学复兴,接续韩愈“兴儒抑佛”的主张,极力贬斥佛老思想。社会思想的单一或多元直接决定着时代文化的宽度,若佛道两家在儒家的浩大声势下悄然边缘化,那么不仅宋代文化的盛况将黯淡几分,华夏文明亦难造极于赵宋之世。因此,为顺应社会形势,符合统治者的“治世”需要,佛道两家的思想和处世态度逐渐发生了衍变,流露出与时世相妥协的意味,呈现出向传统伦理思想倾斜的趋势。北宋中期出现了三教交融的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契嵩禅师所著的《辅教编》;二是北宋理学的成熟。
宋仁宗明道年间,云门宗的契嵩禅师率先“广引经籍,以证三家一致,辅相其教”[1]。契嵩提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认为儒佛两家殊途同归,具有一致的“治世”功用,阐述其思想主张的《辅教编》一书在士林广为流传,引起强烈反响,仁宗皇帝褒赐契嵩禅师紫方袍,并赐予“明教大师”称号,准其书文编入《大藏经》目录加以流通。佛教自此开始得到北宋朝廷的重视,士大夫也由“兴儒抑佛”转向主动学习佛法,儒士与僧人互相交游的风气炽盛一时。
而后“北宋五子”开创的理学,即是吸收佛道思想对汉唐儒学进行改造后形成的新哲学理论体系,同样可以视为三教合流的思想成果。其中,北宋大儒周敦颐便借鉴了“气生万物”“无欲主静”等道家观念,将其对儒、道、佛三家的理解贯通并编撰出《太极图说》和《通书》,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儒、道、佛三家彻底打破壁垒,互融共通,使当时社会呈现出相当开明的思想氛围,也是北宋文学的深度和境界远超前代的重要原因。
二、“入世”到“出世”的人生经历
在儒、道、佛三教思想交融并行的宋代,文人的思想状态普遍呈现多元化特点,与僧人、道士相往来一度成为士林风尚。在三教思想的渗透下,北宋文学家黄庭坚逐渐形成“以儒为本、佛道兼容”的思想体系和处世哲学,其作品也因此具有超凡脱俗的禅意理趣色彩,进而对北宋文学的审美取向和风格衍变产生深远影响。
(一)家庭环境对诗人思想的熏陶
宋庆历五年(1045年),黄庭坚出生于洪州分宁双井村(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内)。北宋时期,双井村黄氏家族共出进士48位,名震朝野,人文底蕴极其深厚,被誉为“华夏进士第一村”。黄庭坚幼时便聪颖过人、酷爱读书,能够诵读儒家“五经”,得到其舅父李常“千里之才”的称赞。李常(字公择,官至吏部尚书)亦是满腹经纶的儒家学者,黄庭坚早年丧父后,李常在道德和学问方面均给予悉心教导,并携黄庭坚一同至淮南游学,结识了孙觉等众多名儒,对黄庭坚的人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皇祐四年(1052年),年方八岁的黄庭坚作诗《送人赴举》:“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归去明主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2]诗意简明质朴,稚气未脱,却鲜明地显现出幼年黄庭坚读书入仕的信心和做天子门生的远大志向。
家风熏陶和舅父教导使黄庭坚自幼便奠定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其也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浸染。北宋时期佛门兴盛,江西作为禅宗的起源地,境内寺院林立,礼佛之风浓厚。而当时声名远扬的黄龙宗道场正位于分宁境内的黄龙山。黄庭坚在《洪州分宁县云岩禅院经藏记》里写道:“江西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而洪州境内禅席居分宁县者以十数……分宁县中,惟云岩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为童儿时数之。”[3]444可见当时分宁县禅风之盛,尚为童儿的黄庭坚时常出入禅院,无形中加深了其对佛法的兴趣。再加之其祖母仙源君刘氏虔心信佛,舅父李公择对佛法亦颇有研究,环境与家庭的双重影响使黄庭坚亲近佛教。史料和佛门典籍中均有记载,黄庭坚与黄龙宗多位名僧交情甚笃,被视为黄龙宗的大居士、方外大弟子,也留有相当数量的参禅诗和与僧人往来酬和的诗作,例如《南山罗汉赞十六首》《观世音赞六首》等,但佛禅思想对黄庭坚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晚期诗歌中,后文将着重分析,在此不作赘述。
从早期诗作来看,黄庭坚少时深受《庄子》的影响,仰慕陶渊明,诗歌明显体现出对老庄逍遥之境的追寻,以及对陶渊明远离官场、回归自然的人生态度的认同。从其七岁时所作的《牧童诗》中,便可窥见其不俗的人格气质和思想境界:“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2]年方七岁的黄庭坚便已看透长安城内追名逐利的虚妄世态,流露出亲近自然、远离世俗的思想倾向,可以说道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已然根植在黄庭坚的价值观念中。
“短生无长期,聊暇日婆娑。出门望高丘,拱木漫春萝。……亦有好事人,时能载酒过。无疑举尔酒,定知我为何。”[4]从体式上看,这首五言诗初步体现出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的实践,即不追求情感上的强烈表现和辞藻的绚丽铺排,而转向素雅平淡、蕴含理趣的艺术境界。诗人于春日美景中感悟到放任自然、饮酒咏诗的乐趣,抒发了人生短暂、名利如烟的感慨,诗风平实,旨趣脱俗,深具陶诗之妙。然而我们皆知饮酒是佛门戒律,黄庭坚耽悦佛法,却以饮酒为乐;虽向往无所拘束的田园生活,却仍刻苦学习儒家经典,按部就班地考中进士、开启仕途。这并非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矛盾冲突,而恰是三教合流思潮对宋代文人处世观念和人格结构的改变。与前代文人“仕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5]的抉择不同,宋代文人不拘泥于“入仕”与“归隐”的对立,而是将“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4]。对于悟性极高、年少便参透佛道真谛的黄庭坚来说,佛道思想成为其涵养心性的途径之一,他仅仅是从佛、道两家汲取“由清静寡欲而达于逍遥自然的人生哲学”,“而统摄这一人生哲学的道并非虚无的主体,而是儒家的仁义之道。概言之:体儒家之道,达逍遥之境。”[4]
综上所述,黄庭坚早年受道家思想熏染较深,苏轼初读黄诗时的评价很能概括黄诗早期的意境特点——“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5]
(二)坎坷仕途对诗人性情的压抑
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考中进士后仕途不甚得意,在辞官归隐和为养家不得不留任的困境中彷徨,心情压抑苦闷,其间写有不少批判社会阴暗、揭露民生疾苦的纪实作品,如《流民叹》《上大蒙笼》等,现实意义深刻,但由于其官位低微,未能引起反响。任职地方期间,黄庭坚时常拜谒佛寺道观,听经闻法,对佛教思想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心境逐渐平静释然,同时更加坚定了其归隐山林的愿望,一些表达“出世”理想的咏怀诗境界不俗,颇有理趣。
元丰五年(1082年),黄庭坚于太和知县任上作《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首联诗人自嘲“痴儿”,诙谐地抒发了囿于官场的无奈之情,“了却公家事”一句言近旨远,近指诗人结束一天的繁忙公务,实指诗人期望早日脱离官场,与俗务彻底隔绝。颔联一句堪称宋诗状景之绝唱,描绘出晚晴时分登临快阁所见的自然美景,落木萧萧,青山连绵,澄澈的江水与静谧的明月交相辉映,意境空灵浑阔,显示出诗人开阔豁达的胸襟。颈联化用伯牙破琴绝弦以谢钟子期和阮籍青白眼的典故,流露出诗人没有知音相伴,只好借酒消愁的惆怅心绪。尾联直白地抒发了想要归于自然、与白鸥为伴的愿望,境界辽阔,堪与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句比肩。
元丰七年(1084年),黄庭坚于泗州僧伽塔作《发愿文》,起誓“不复淫欲,不复饮酒,不复食肉”[3]782,正式确立了佛教信仰,成为一名“在家僧”。对佛教也由从前的援引禅语、浅尝辄止变为深入研读佛教经籍,参悟禅门义理,标志着黄庭坚对佛教的接纳正式达到与儒、道两家等同的位置上,儒、道、佛三家圆融合一的思想体系初步成熟。
元丰八年(1085年)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方才回到汴京,与苏轼、秦观、陈师道等友人频繁交游,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吟咏书斋生活,书画、笔砚、茶食等蕴含文人气息的意象十分密集,风格恬淡雅致,反映出诗人愉快心境的同时也寄托着其想要归隐山林的愿景。为后世熟知的《寄黄几复》《双井茶送子瞻》便作于这一时期。《双井茶送子瞻》的尾联“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3]87一句,化用了春秋时期范蠡拒受封赏、弃官归隐的典故,暗示好友苏轼及时脱离党争旋涡,回到黄州时期悠然自得的隐逸生活,也显示出黄庭坚对政治的消极态度,虽身在官场却心向田园,是典型的“出世”思想的流露。
作于元祐三年(1088年)的《薄薄酒二章》,诗人更加直白地坦露出朴实无华的人生追求:“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无祸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富贵于我如浮云,小者谴诃大戮辱。……丑妇千秋万岁同室,万金良药不如无疾。薄酒一谈一笑胜茶,万里封侯不如还家。”用质朴的诗语抒发了最迫切的“还家”之愿。“不如无疾”一句是因为诗人当时患上头眩症,病情逐渐加重,来年甚至到了“不能苦思,因而废诗”[3]700的地步。进退不能的困境加之疾病的折磨使黄庭坚的意志急遽消沉,而元祐六年(1091年,47岁)母亲离世,其回到家乡分宁,在哀痛欲绝、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创作几乎停滞。元祐四年(1089年)至元祐八年(1088年)期间,诗人仅留下十余首诗作,而自元丰八年诗人进入汴京至元祐四年(1089年)患病前,存诗四百余首,可见诗人这段时期的低迷状态。
(三)谪居生活对诗人心境的涤荡
绍圣元年(1094年),以苏轼为首的旧党文人在政治斗争中黯然落败,黄庭坚虽未表现过明显的政治倾向,却仍被视为旧党文人而受到迫害,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晚年再次因“幸灾谤国”之罪被贬宜州,最后死于贬所。仕途受挫、接连被贬对苏黄等失意文人来说意味着后半生的跌宕不安,但在逆境中迸发出的创作激情却造就了宋代文学的璀璨光辉,尤其对厌倦官场、向往自然的黄庭坚来说,被贬至偏僻之地大大缩短了他与自然山林的距离,实现了无所拘束、纵情山水的愿景。因此,黄庭坚在晚年谪居期间达到了毕生创作高潮,并在延续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加深了对佛法的研究,频繁探访佛寺道观,与高僧名士往来论法,心境得到涤荡,诗词创作的技法、意蕴、境界在此时期均有极大突破,尤其在词法上摒弃以往“使酒玩世”的淫词艳语,而开始追随苏轼词风,尝试“以诗为词”的创作方式,流露出黄诗中特有的禅意理趣,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
被贬至戎州时,黄庭坚登临胜景,难掩喜悦之情,遂作《诉衷情》一词:“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3]406这首词描绘了戎州江边渔夫垂钓的图景,化用了唐代禅僧的《拨棹歌》,尤其末三句营造出的意境空旷辽远、宁静至极,直以诗家之化境写禅宗之悟境,用自然超妙之景象征自己觉悟解脱,由凡入圣的心志襟怀。[6]此外,《渔家傲·三十年来无孔窍》《拨棹子·归去来》等词作均援禅偈入词,使词具有了禅意境界和理趣色彩,对宋词的格调转变有较大影响。
而后,黄庭坚在春游中写就的《水调歌头》一词,词句隽永绝伦,思想境界再度跃升,展现出他对理想中的世外之境的追寻。“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 “武陵溪”代指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我欲穿花寻路”一句,与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有相似之妙,均有欲弃世归去却被现实所缚的无可奈何之感。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7]词中的“我”清高超逸,放浪形骸,要与谪仙人李白举杯共饮,“仙草”与开篇的“瑶草”呼应,“朱唇丹脸”象征桃花,桃花与仙草相比不免流于俗气,因此代指俗世琐事。“我”为寻仙草而来,却只见无数桃花,理想落空,但“我”却并未感到失落,长啸叹息有什么用处呢?且自斟自饮,伴着月光醉舞着下山。
遗世独立的桃花源是虚构的存在,黄庭坚并未执意寻找这一仅存在于理想中的仙境,而是畅饮一番,醉舞着回到俗世中来,心中也无甚遗憾。这表明在诗人心中,现实生活与“出世”理想达成了和解,诗人以更加坦然潇洒的态度面对生活,达到了“无山而隐,不褐而禅”“似僧有发,似俗无尘”的超然境界。
三、结束语
黄庭坚对佛道思想的融会吸收表现在其诗词的禅意理趣和旷远境界中,其作品可以视作文学艺术与佛道思想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结晶,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效仿者众多,加深了时人对佛道思想的接受程度,为儒、道、佛三家合流的趋势提供了有力的文学支持。佛道思想对黄庭坚人格气质的改造也使他形成了脱俗出新的文学观念,促进了宋诗审美标准的衍变,并纠正了晚唐以来的艳俗词风,使宋词有了清壮顿挫、意蕴深厚的一面。黄庭坚的创作实践不仅在北宋诗坛独树一帜,更对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循例,这是他能够立一派之宗、扛宋诗之鼎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释契嵩.夹注辅教编校译[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35.
[2]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416.
[3]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444.
[4]黄宝华.论黄庭坚儒、道、佛合一的思想特色[J].复旦学报,1982(6):89-95.
[5]苏东坡.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29.
[6]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黄庭坚诗文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95.
[7]周汝昌,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768-770.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