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想写出人的疼痛
2024-07-07舒晋瑜
舒晋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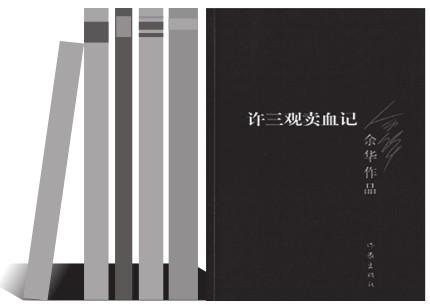
从余华的随笔中能发现他对很多作品的阐释,跟一般人的体会完全不一样。
故事人人都会编,都可以编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但是,同样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换一个人去写就不一定吸引人,问题在哪呢?问题就在于那些不经意的地方,没有被捕捉到。一个好作家,在我们认为不经意的地方,他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伟大来。就像鲁迅写孔乙己来的时候,他要是腿不断,就不用写他走来,他腿断了,鲁迅就必须写,那么怎么写,他就用这种方式写——原来是用那双手走来的。这一描述,表达了文学中的他异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阅读时,余华往往注重的是那些不经意的地方并以此判断大师的艺术水准。好比我们建立了一个故事大厦,那个故事大厦是怎么建立的?应该是用砖砌起来的。你用的是什么砖?你用什么方法去砌?有很多人砌得歪歪斜斜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作家,都是这样的,而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很多零之后的一,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读那些伟大的作品,经常在那些小地方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才是大师。
余华曾写过一篇随笔《我为何写作》,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功利的起点出发,最后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升华。他认为写作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一个人总会有很多欲望、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种种限制无从表达,但可以在虚构的世界里得以表达。
写作使余华拥有了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虚构的,另一条是现实的,而且随着写作的深入,虚构的人生越来越丰富,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他的写作,写出了个人的疼痛,也写下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阅读,在注解里发现“新大陆”
小学毕业的暑假,父亲给余华和哥哥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但是图书馆里的文学作品不超过30本,且多数都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题材的书。只有两本讲孩子的故事余华非常喜欢,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一本是《闪闪的红星》,另一本是《矿山风云》。
除此之外,余华能接触到的是父母书架上大量医学方面的书,以及《毛泽东选集》。
小孩子总善于在无聊中发掘有趣的事情。令余华惊喜的是,他在《毛泽东选集》的注解发现了“新大陆”。因为涉及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使他极为着迷。但是那些书籍常常是缺头少尾,这种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的状态令余华感到痛苦,因为没有谁可以告诉他结尾是什么,于是他开始自己给那些小说编结尾。一个一个编,觉得不好就再重新编。
多年以后,余华在一次高校演讲中回忆这段经历,感慨生活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人,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在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他以后成为作家有很大的帮助。他以余华式的幽默调侃说:
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20世纪80年代初,余华开始写作。那是文学杂志的黄金时代,很多文学杂志或复刊或创刊,如雨后春笋不断地冒出来。彼时,他尚是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完成一个短篇小说总是先寄往《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被退回来后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被退回来就再找别的杂志寄。他们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余华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这样的遭遇一直持续到1987年,《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一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发表后,引起文学杂志编辑的关注,余华从投稿变成应约写稿。他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父亲展示,父亲问:什么意思?余华说:我出名了。
永远做自己的先锋
在《北京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星星》后,1986年深秋,余华接到《北京文学》改稿会的通知,出门时他带上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初稿。
时任《北京文学》的主编是林斤澜,副主编是李陀和陈世崇。李陀对《十八岁出门远行》十分赞赏,不仅安排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北京文学》头条,还推荐余华的作品给《收获》杂志,此后,余华所有作品中,十之七八都发表在《收获》杂志。首选《收获》的原因有二:一是每次去《收获》编辑部,李小林都会对余华说:“你的小说不能寄给别的杂志,只能给我们发表。”二是他的作品在其他文学杂志未必能发表。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关于卖血的题材,在当时还是有些敏感。然而巴金的《收获》可以发。所以余华觉得自己很幸运,在需要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了李陀;在需要遇到一本杂志的时候,遇到了《收获》。
李陀和《收获》使余华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
余华曾将自己的文学起点定位在“先锋”时代。1987年至1989年,先锋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新的写作方式出现,是那个时代的特征。真正的先锋其实是一种敏感,回过头来看,一些先锋作家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启蒙还是在艺术启蒙上都高于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兴起的时候总会有群体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关心流派,群体中的作家也被遗忘,终究有几个会留下来,不属于任何流派,只属于文学。余华希望永远做自己的“先锋”,真正的先锋性,是保持写作生命力更长久的一个方式。
1995年完成《许三观卖血记》之后,《读书》杂志主编汪辉找到余华约稿。此后,余华发表了大量的音乐随笔和读书随笔。余华对音乐和书籍的迷恋找到了充分释放的平台。
其实,他对音乐的爱好在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仿佛在一瞬间,他被简谱迷住了,尽管对它们一无所知:
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我所熟悉的那些歌一旦印刷下来就是这副模样,稀奇古怪地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然后成了召唤,我确实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
余华没有学习简谱的想法,而是直接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写作”——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谱写成音乐。他先将鲁迅的作品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上面,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他甚至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也都谱写成了歌曲,为拥有整整一本作业簿的音乐作品心意满足。
很多年过去,余华真正爱上音乐,他喜欢肖邦、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海顿、马勒和布鲁克纳,在音乐中感受爱的力量,感受音乐与文学之间共通的叙述节奏,那些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带给他有力的震撼。毫无疑问音乐影响了余华的写作。他注意到音乐的叙述,思考巴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中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音乐是内心创造的,内心的宽广无法解释,它由来已久的使命就是创造。
《兄弟》使他精神上红光满面
《兄弟》的出版距上一部长篇《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间隔十年。此前,余华的所有作品加起来不过150万字左右,但《兄弟》足有51万字,且动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进入当下生活,颇有史诗的品相。这部长篇不仅使余华恢复了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而且让他发现自己新的才华。对作家而言,这的确是件美妙的事情。
任何艺术形式的创作对作家的要求都是苛刻的,才华、技术、修养、信念、体力……尤其长篇小说因为写作时间更长,叙述者会面临很多小说之外的经历和挑战。余华也不例外。《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写过长篇,三年只写了20多万字。问题不是字数,而是他没有找到叙述的快感。这一年他去了美国,在那里东奔西跑七个月回到北京,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他回看自己的小说,片段依然精彩,但却始终无法继续找到适合的叙述方式。
余华承认,自己低估了随笔对小说的影响,他决定先写短篇,慢慢恢复长篇创作的能力。没想到《兄弟》的写作使他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状态。起初构思的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只写了两三万字,他就被叙述控制了,篇幅越来越长。这是写小说最好的状态:开始是作者在控制叙述,写到后来叙述控制作者。
《兄弟》讲述了两个时代相遇生发的故事,前一个是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是一个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四十年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联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兄弟二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余华毫不掩饰对《兄弟》的喜爱。他发现了自己新的叙述能力,同时也使自己处理细节的能力得到强化,这对余华和他后来的写作无比重要。叙述的力量常常是在丰富有力的细部表现出来的,很多年前,他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表达杀人者内心的动荡,这个篇章让他阅读时十分震撼,那种精确细致的描写丝丝入扣。而在《红与黑》中于连勾引德·瑞娜夫人时,司汤达写得像战争一样激烈。当时余华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有力地叙述故事?《兄弟》的写作让他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
《兄弟》写完以后,余华仍有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想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再写一部,于是完成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部作品由十篇构成,以每篇分析一个汉语词汇的方式,对现代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日本汉学家饭塚容翻译了这部作品,觉得余华既有很“乡土”的一面,也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他可以用一种外国人都很容易理解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笔触非常公正而独到地分析中国的社会现状。饭塚容选择余华的随笔翻译,希望这些作品帮助日本人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倾听中国人的心声。这部随笔集在日本非常畅销,说明日本读者达到了译者的预期。
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哪里是一部非虚构能容纳得下?余华希望把它集中写出来,但是选择什么方式,他很难决断。突然有一天,灵感乍现:一个人死了以后接到火葬场的电话,说他火化迟到了。我知道可以写这本书了,写一个死者的世界,死者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也把自己在生的世界里的遭遇带到了一起。
余华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化解过长的篇幅,能把故事集中呈现出来。他虚构了一个候烧大厅,死者进去后拿一个号,坐在那里等待自己被叫号,然后起身去火化。
这并非余华第一次写生死交界的小说。多年前,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也是一篇有关亡灵的小说。他认为最能代表自己全部风格的小说是《第七天》。
“一个作家写作时间越长,野心越大;野心越大,可能风险也越大。”余华说,《第七天》以亡魂的视角回望人生。这是一部怪诞小说,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时代中荒诞的事情集中起来。这个角度在《第七天》里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从一个死者的世界来对应一个活着的世界。余华在写下自己疼痛的同时,也写下了中国的疼痛。
一向喜爱余华作品的饭塚容几乎第一时间翻译了《第七天》。因为对于日本读者来说,《第七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学习中国现状的教科书。即使对中国文学不了解,也可以把这部作品当作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饭塚容在“后记”中说:
余华在把这些年发生过的各种社会事件写进他的小说时,安排了一场主人公的意外死亡,他在死后的七天里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和走向另一个世界时的所见所闻构成了这部小说。情境亦幻亦真,笔触悲怆与幽默并存,其中还包含着神秘色彩。社会充满了丑恶,有时甚至是疯狂的,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的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和一对出身贫寒的恋人,他们之间的无条件的爱却让人感到一种无瑕的美。
人性的千变万化才是小说的基石
写作《文城》的想法由来已久。余华不否认那一代作家有挥之不去的一种抱负:总是想写一百年的中国史,哪怕不能在一部作品中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完成。
《活着》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余华想写写《活着》以前的故事。动笔是在1998年前后,结果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越往下写越困难,他马上停下来;2005年《兄弟》出版以后又重新写,2013年《第七天》出版以后再重新写。“文城”在小说当中始终难以寻找,但是又无处不在。书名并不是叫《文城》,而是《南方往事》。更名为“文城”,是来自其妻子的建议。
很多世界名著有这样的特点: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们并未能从中读到孤独,里面所有人都热热闹闹;马尔克斯还有一个著名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孤独是什么?马尔克斯把孤独的原来意义和概念完全扩充到开放式的,读者可以随便去理解。余华最终所以选择《文城》作为书名,也是因为它的开放性。这个城是不存在的,但所有故事都跟它有关系。
2021年2月,《文城》出版。作品继续围绕人生、命运、时代等主题,书写一个人在命运长河中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余华以时而细腻舒畅、时而勇猛锋利的笔触,以自己独有的黑色幽默,吟诵荒诞悲怆的命运史诗。
多年来,余华的作品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的短篇小说带有血腥和暴力,后期的作品相对增加了温情。余华因此常常需要向读者解释,那个记录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兄弟》出版后,余华自我调侃道:“《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而《文城》见证:读者熟悉的余华又回来了,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
《第七天》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如果说杨飞穿梭于阳间和阴间是为了寻找曾经失去的亲情和友爱,探寻现实苦难背后的真相,那么《文城》里的寻找,则是为了寻找人间的深情厚谊。当林祥福抛离殷实富足的北方之家,千里迢迢踏入溪镇,他的寻找是为了见证纷乱的世间,寻找情义、仁爱、谦卑等美好的人性。虽然寻找的故事不一样,寻找的意义也不一样,但是寻找确实成为余华写作中重要的故事内驱力。
余华在讲述小说故事时承续了民间叙事的风格,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从不同视角叙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在这个故事里,余华刻画了纪小美这个全新的女性形象,这个人物比他此前笔下的任何一位女性都复杂多面,柔软又坚硬,驯良却叛逆。她在命运推动下的每一次选择,她在那个慌乱时代的幸与不幸,更加牵动读者心弦。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余华曾表示,自己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回到南方”。故事里的小镇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在《文城》中,余华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还描绘种着高粱、玉米的黄河以北,在作品中展现了更广阔的图景。评论家丁帆评论《文城》时说,人性的千变万化才是小说的基石,余华很认同,因为所有的叙事都隐含了人性的不同向度。
(作者系本刊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