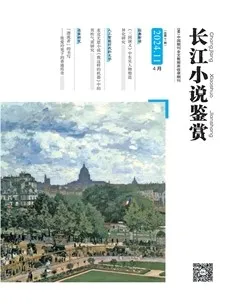从李寻欢看古龙武侠作品的当代接受
2024-07-04郑湑文
[摘要]《多情剑客无情剑》是新派武侠作家古龙的代表作品,塑造了性格复杂、极具悲剧色彩的经典浪子形象李寻欢,体现了浪子的精神漂泊与生命追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李寻欢的形象也从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逐步成为受人追捧的多情公子与备受苛责的情感不忠者的矛盾综合体。这与古龙作品的影视化、二次创作、网络文学发展带来的偏向传奇叙事而忽略人性书写,以及当代读者的认知转变密不可分。从李寻欢形象在当代的符号化、平面化变化中,可以看到古龙小说中繁复多维人性的失落,推及古龙笔下具有人文色彩的人物形象对于网络时代通俗文学阅读和创作的影响及启示意义。
[关键词]古龙 武侠 李寻欢 文学接受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26-05
一、古龙的江湖世界与人性之侠
1.古龙的浪子与侠义
不同于金庸笔下“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古龙笔下的“侠”,多是游侠,是浪子。
浪子之“浪”,在于四海为家,潇洒来去。浪子漂泊之源在于他们寻不到足以令其安定的归宿。《多情剑客无情剑》开篇,李寻欢坐在马车上:“车厢里虽然很温暖、很舒服,但这段旅途实在太长、太寂寞,他不但已觉得疲倦,而且觉得很厌恶,他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寂寞,但他却时常与寂寞为伍。”[1]彼时的李寻欢是自愿放弃曾经令他安定的归宿,选择成为一个“浪子”,于是他只得与寂寞为伍。
古龙笔下的浪子游侠们是自由的,他们出身神秘,没人道得出他们的师承渊源,他们的身家、武功仿佛天上掉下来的,光这一点,已然与传统江湖世界隔开了距离。游侠身在江湖,却又与江湖格格不入,他们更加自我,更加任性,真正称得上来去如风。因为他们来处成谜,去处同样未知,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知晓自己将要去往何方。这无疑造就了游侠浪子的迷茫,但同时,这种相对独立性也给了浪子游侠们更大的空间坚持自我与保持独立清醒的人格,因为他们本身与整个江湖体系便有一定距离。
由于跳脱世俗规矩之外,游侠们天生便具有一种更加理想化的人格,他们用自我的道德规范、广泛的结友论交重新建立起内心乌托邦与世俗江湖的联系,同时追求独立的个性与洒脱不羁的生命形态,将个体的生命价值抬到最高,有意无意中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和谐境界。
正因如此,这些游侠大都具备武侠江湖中少见的敬畏生命及人权平等意识。如楚留香不杀人的底线,在揭穿了无花面目后,楚留香没有同其他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一样惩处恶人,而是表示“武功不能解决一切,世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力夺去别人的生命!”[2]这样的言辞与人们通常认知中快意江湖的侠客以及所谓的“江湖道义”要求似乎格格不入,却恰恰可见浪子之真情率性。
2.人性之侠李寻欢
在古龙塑造出的诸多浪子形象中,李寻欢算得上是十分特别的一个。其身上异常纠结而复杂的人性,足够丰富的内涵与经历构建起一个多层次的人物形象。
2.1“浪子”李寻欢
毫无疑问,李寻欢正是古龙擅长塑造的于江湖之间肆意游走,任性自适却又与寂寞为伍的浪子。
古龙曾在《楚留香和他的朋友们》一文中这样形容胡铁花:“别人愈不了解他,他愈痛苦,酒喝得也就愈多。”[3]这句话用来说明李寻欢也是再贴切不过的。因为胡铁花是浪子,李寻欢也是浪子。自李寻欢将表妹林诗音同李园一起“送”给他的结义兄弟龙啸云之后,李寻欢就失去了他曾经可以依存的“根”,于是他只好浪荡天地之间,时常与寂寞为伍,怀抱着一种悲天悯人却无可奈何的沉痛心绪。所以他只有喝酒,哪怕咳嗽咳得要死了,哪怕喝酒叫他身中奇毒命不久矣也要喝酒。酒不但是李寻欢内心情感的外现,而且已经成为其浪子生涯的精神寄托。
友情和爱情是古龙笔下极其动人的两种感情,其中友情又往往比爱情深重真诚得多。对于一个浪子而言,爱情固然美丽诱人,却与浪子漂泊超脱的自由心灵相悖。因此浪子们往往宁愿选择友情,友情是一个浪子保持个性独立又不至落入孤苦寂寥的情感慰藉,这种感情是超乎了现实功利的心灵观照,远比会阻碍浪子追求自由洒脱的爱情重要得多。这也是李寻欢面对龙啸云的友情与林诗音的爱情时选择前者的原因。虽然这个选择令其落入浮萍般无根漂泊的浪子境地,但是促使他这样做的正是他作为一个浪子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由向往。
2.2“圣父”李寻欢
李寻欢出身于“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书香门第,不仅功名在身,还经历过官场,身上有一种古龙笔下其余浪子不具备的儒学色彩。
李寻欢受过完整的传统儒学教育,熟读经史,虽然最终辞官浪迹江湖,但是他所受的儒学教育无疑内化影响着他的行为,儒家所提倡的仁爱思想与克己复礼的规范令李寻欢拥有远高于江湖平均水准的道德底线,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上就是他的悲悯之心与博爱情怀。
对于他人命运的悲悯与顾惜在李寻欢与龙小云的初见时表现鲜明。面对初见就满口恶言并杀招相向的龙小云,李寻欢不仅不忍还手,甚至不曾感到生气。在龙小云搬出自己的父母进行威胁时,李寻欢动怒的原因也不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是龙小云极端的自私,以及将他人性命当做儿戏的轻浮态度,然而李寻欢依旧顾念龙小云年纪尚幼可以管教不曾出手,其悲悯情怀可见一斑。
儒家强调的克己,在李寻欢身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自我道德谴责。李寻欢将林诗音“让”给龙啸云之后,一直处于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源于他自愿背负起的对龙林二人的道德责任。李寻欢在兴云庄再次见到林仙儿时,林仙儿暗示李寻欢,龙啸云因为觉得对不起他,想要撮合他们。李寻欢却回答:“人都没有对不起我,只有我对不起别人。”[1]这当然不是李寻欢为了拒绝林仙儿说的一时气话,他是认真顾及他人情感并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感到自责。林诗音正是那个他自觉亏欠最深的人,因此面对林诗音时,哪怕他与龙小云的争端是他占理,李寻欢也感到深深的歉疚与痛苦。
2.3悲剧英雄李寻欢
故事开篇,李寻欢在关外漂泊十年后返回关内,古龙不曾交代李寻欢在关外的生活及入关原因,但是读者已经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深重的寂寞。
李寻欢的苦闷是他在情义之中抉择的结果,他是个多情的浪子,却有着比普通江湖人士都更加高尚的道德自律,因此他“自污名声”将林诗音推给龙啸云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痛苦。面对爱情与友情的两难抉择,李寻欢无法在现实中寻得两全之法,只得通过沉溺酒精逃避选择,这是他性格的缺陷,也是造就其身上悲剧性的重要因素。作为浪子,李寻欢实在太容易心软,也太“仁慈”,过度重视他人情感,以至于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然而若不是如此不幸的遭遇、出众的武艺、高尚的品格与“优柔寡断”的心肠构建出一个如此鲜活而复杂的形象,李寻欢便不会惹得读者如此怜惜又崇敬了。
二、李寻欢的当代接受与解构
古龙创作的武侠作品风靡一时,并被多次改编搬上荧幕,同时还诞生了大量以古龙江湖世界为背景或以古龙塑造的经典角色形象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的作品。影视作品与二次创作的解读与重构立足于古龙笔下各具特色的侠客构建起来的“江湖世界”,这个江湖世界有如泼墨山水一般,虚实结合,既给改编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内容支撑,又为认识这个江湖世界并想要进一步了解乃至参与其中的接受者留下足够的空白。
1.接受空间:原著的“留白艺术”
古龙的语言是充满诗意的,并非简单地将古典诗词化用其中,而是一种近乎现代诗的凝练简洁,富于生趣,长短句交错,富于节奏。这种诗化的语言使得古龙在描写冲突矛盾时更能营造出紧张肃杀的气氛。
小李飞刀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准和快。古龙这样描写李寻欢的出手:“鲜血一丝丝自诸葛雷的背缝流了出来。他瞪着李寻欢,咽喉里也在‘格格地响,这时才有人发现李寻欢刻木头的小刀已到了他的咽喉上。没有一个人瞧见小刀是怎么到他咽喉上的。”[1]三言两语间已将小李飞刀的厉害展现在读者面前,打斗过程的缺失并未减损武侠江湖气氛的营造,反而给读者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颇具镜头感的叙述更给文字的影视改编提供了借鉴,文字的二次创作也在此基础上有了发挥空间。
诗化的语言运用在环境描写中,仅寥寥数笔便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泼墨山水画般畅快洒脱的场景,令读者读到文字时即可嗅到迎面而来的江湖气息。
古龙于开篇写道:“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 视众生为鱼肉。万里飞雪,将苍穹作洪炉,溶万物为白银。”[1]干净利落的文字将肃穆雪景尽收笔下,更以景的寂寥点明了李寻欢心境的孤苦。而这雪景远不止如此用途,更为之后阿飞的出场以及李寻欢与阿飞的相识做了铺垫,同样是这场雪,也成为由金丝甲引发的江湖争端到引出梅花盗,将李寻欢卷入后续阴谋的契机。简单的环境渲染之中,古龙吸收西方侦探小说模式以变革传统武侠的“求新”创作笔法可见一斑。
剧情推进方面,古龙更大量运用人物对白,略去作者之言,将角色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身临其境,这样类似剧本的情节推进模式同样为影视化创作与改编提供了便利。
2.解读重构:影视改编与形象重塑
在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增多,影视作品的影响较传统文学作品更加广泛,引发诸多并不甚了解武侠文学的受众对于该题材的关注,而人们对于古龙作品乃至于武侠题材更大范围的认知也来自根据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
然而由于载体的不同,影视剧实际能够呈现的内容与原著一般都有一定差距,这种差异也是剧本改编者对于原著文本接受或解读的结果,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影视作品往往无法与读者阅读原著时的想象对应。古龙作品的影视改编大多在原著基础上有较大改动,角色性格、行为等也多因情节的删改与原著不符乃至矛盾,颇受原著读者的诟病。
尽管如此,基于影视改编而了解古龙笔下浪子形象的受众在新时代依旧具有相当体量。此部分受众或从未完整阅读过一本包括古龙原著在内的武侠小说,却从电视电影之中对武侠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乃至对其中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产生向往。
部分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武侠江湖、认识古龙笔下浪子的观众也会通过阅读原著继续深入了解人物。然而这些观众在阅读原著时往往面对一个问题:原著中的李寻欢与影视作品中的李寻欢不尽相同,比如影视作品中李寻欢的英俊帅气、潇洒多情在原著中极少被强调。这就涉及影视剧拍摄时为吸引观众会突出角色的特质。
3.强化符号:二次创作与人物符号
3.1人物特质强化
作为古龙笔下经典的浪子形象,李寻欢这个角色自《多情剑客无情剑》出版后就一直被反复解读、评价、阐释、演绎。为了还原古龙笔下的经典形象,编剧们不免要对古龙笔下角色的特点进行总结,将其突出特质在剧情中展现出来,以使观众们知晓这是古龙武侠作品的改编,是古龙笔下的江湖传奇。
在众多小李飞刀影视作品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台湾版电视剧《小李飞刀》,人们通过饰演李寻欢的焦恩俊认识了小李飞刀这个角色。这一版本的风靡当归功于剧中足够多的“美色”,毕竟单是电视剧剧情就与原著大相径庭。整部剧除了李寻欢的高颜值,其他角色也容貌姣好,第一时间抓住了观众的视线,进而引起观众的观赏兴趣。
当然,影视剧中的李寻欢形象能够得到广泛认可,也在于其将书中浪子形象的部分特质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如风流倜傥、多情温柔以及言语的风趣幽默等,如此潇洒英俊的形象的确比原著人物怀抱痛苦的落拓更讨喜。
3.2对人物符号的认知与接受
当原著中李寻欢历经世事的沧桑与情感上的痛苦被淡化,从其自我放逐中可以窥见的道德自律也随之被掩盖。李寻欢第一次出场时,古龙对其眼睛进行了描写:“这是双奇异的眼睛,竟仿佛是碧绿色的,仿佛春风吹动的柳枝,温柔而灵活,又仿佛夏日阳光下的海水,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活力。” [1]
这是古龙对李寻欢外貌为数不多的描写,由这一双奇异的眼睛中,读者可以窥得李寻欢的洒脱不是纨绔子弟的浪荡无羁,而是经历过艰难困苦,看淡了世事的超脱淡然,这正与其身上君子的一面相合。但影视作品中潇洒多情的浪子李寻欢倒不似原著中令人同情,反更叫人倾慕。
当然,李寻欢身上区别于其他侠客的儒学气质与内心愁苦并未被影视剧完全剔除,因而观众还是能够将其影视形象与书中的形象对应起来。影视作品选择塑造李寻欢这样一个复杂的悲情英雄,又将其放在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中,强调他恣意任性与风流多情的一面,使得这个半生漂泊的可怜人更能融入剧中江湖的传奇叙事。这样改编固然使观众的接受更加轻松,却削减了李寻欢身上的复杂人性,令只看影视而少读武侠小说的受众将古龙笔下的浪子如李寻欢之流视作风流随性的代表。
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古龙武侠小说用曲折的情节构筑起传奇江湖世界,身处其中的人物性格各异,善恶交织,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因而在脱离现实、远离朝堂、看似不合逻辑的武侠世界中,读者能够感受到真实的烟火气息。
但是影视作品往往很难以超脱现实的传奇情节,完整展现复杂的人心与人性。因此,现阶段的影视剧和观众都不再关注复杂多变的人性和人物内心世界,而将重点放在曲折离奇的故事本身,角色为了情节让步,变得扁平化。习惯了这种模式的观众一旦抱着阅读简单传奇故事的心态去阅读古龙的原著,自然容易忽略古龙掺杂其中的人性探索,以及浪子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因此,李寻欢的形象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具争议。
三、当代古龙武侠精神的失落
1.武侠类型的衰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带来更便捷的交流方式,却不知不觉令人们的精神陷入迷茫境地。哪怕古龙的武侠小说足够通俗,但是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交错复杂的江湖世界以及需要静心品味的江湖人物,都成为时刻匆忙的人群无法完整阅读一部武侠小说的理由。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既已有了那么多的影视改编剧与二创作品,人们通过快速翻阅、简单了解情节的方式就可知晓古龙笔下侠义故事的大致内容,根本无需去翻阅原著。
及至古龙金庸这一批新武侠的代表作家离开后,武侠小说的创作陷入困境。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离现代社会太远,没有读者基础,更少有人愿意去追寻那个与现实隔了些距离的武林,便也无人能构建出如古龙笔下那个充满诗意、脱离现实却又在细节之处可见生活实景的市井江湖。武侠类通俗小说在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今天逐渐没落。
2.当代武侠精神的失落
中国的侠义精神可上溯至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其吸收百家思想之长,形成了一套道德体系,诞生诸多向统治者发出挑战的“游侠”,而后这种游侠模式被不断发展丰富,在传承中不断归纳总结出扶危济困、信守承诺、舍生取义等“侠义精神”。传统的武侠著作多宣扬侠义精神的无私与仁义,至金庸为之一变,呈现出为国为民的广大格局,至古龙又为之一变,作为侠义符号的侠士们具有了更加鲜活的个体生命追求。武侠题材的式微,也是当代媒体商业化后侠义精神被异化、曲解的必然结果。
古龙之武侠精神,在于游侠浪子的个性自由和人性关怀。当代通俗文学,尤其网络小说,更关注个体,强调个人利益。因此,今人解读武侠作品时,也多从个体利益角度出发。李寻欢如今风评不佳,原因之一正是他看似痴情却没能设身处地为他的未婚妻林诗音着想,采用自污名声的方式“逼迫”林诗音选择龙啸云,这无疑是李寻欢将表妹视为其“所有物”可以随意让渡,而未将林诗音作为与之平等的人。这种说法初看颇有道理,却实在忽略了李寻欢也只是一个挣扎于友情与爱情之间的人,他身为浪子的自由向往使他更加偏向于能触及他灵魂的友情,并且这份友情之上还要加上一份救命之恩的重量。
如今人们对于李寻欢的解读,多基于网络时代网文代入的阅读习惯,对于其浪子的一面,只看重风流潇洒的表象,简单讨喜又便于代入。而在感情的一面,性别处境不同者所见又不尽相同,与前面的俊逸浪子符号又有冲突。这些接受与解读却都少有深入探求浪子孤苦内心之下的道德自律与侠义内涵,可见当代武侠精神的失落。
四、结语
通过探究李寻欢身上的复杂矛盾特质,读者可以看到浪子终身漂泊的寂寥痛苦与个体精神独立的自由追求;从李寻欢曲折离奇的经历中,读者可窥见古龙构建的超脱现实却又蕴含现实之“真”的诗意江湖;从李寻欢在这充满烟火气息江湖中的行止,读者可感受到古龙笔下更具人性的浪子形象——独立于天地之间,在虚无中追寻世界之真、人性之善,探寻到古龙对于理想精神家园的强烈向往乃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追求。
早期读者阅读古龙武侠小说,对于李寻欢这位悲情英雄充满怜悯、同情,然而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读者开始转向崇拜其外在潇洒形象,或批判其情感纠葛。对李寻欢这个角色的接受与解读,反映出时代发展下人们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武侠精神的失落。然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从古龙的作品中,尤其是其塑造的浪子形象身上,读者依然可在浪子们无根漂泊、空虚忧郁却行人所不能行的惩恶扬善之举中参悟出生命的真谛,从现实生活中寻得一隅精神归所。
参考文献
[1]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M].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
[2] 古龙.楚留香传奇[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
[3] 古龙.楚留香传奇1[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4] 曹正文.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5] 古龙.古龙散文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
[6] 朱嘉琪.古龙武侠小说的乌托邦建构[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6.
[7] 张志岩.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理念与创作实践[D].沈阳:辽宁大学,2019.
[8] 曹漾漾.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生成[D].合肥:安徽大学,2015.
[9] 景少峰.论古龙小说“侠精神”的现代转化[D].扬州:扬州大学,2016.
[10] 徐厚猛.论古龙小说中独特的江湖世界[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6.
[11] 徐清.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受到的中西影响[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2.
[12] 谢伟.论古龙小说的空白艺术[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13] 徐清.古龙武侠小说的创新性特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2).
[14] 曹燕瞧.古龙武侠小说的影像化叙事[J].青年文学家,2020(2).
[15] 王舜元.古龙武侠小说中的游侠心理[J].牡丹,2020(18).
[16] 方忠.繁复人性的多维凸现——古龙武侠小说的主题意蕴[J].台湾研究,1999(1).
[17] 曹漾漾.知人性者为侠——论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2(3).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郑湑文,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