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镜像:一场关于坍塌的象征性过程
2024-06-30杨小彦
1
美国城市学家林奇(Kevin Lynch)在他一本讨论城市的专著《关于美好城市的一种理论》中,给城市下了6个定义①,分别是:城市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城市是人类群体的生态学存在,城市是生产与物流的空间,城市是互有关联的决策系统,城市是竞争场所,城市是力场。这6个定义,其实是互为补充和相互解释的,并把城市这个复合体大致上给描述出来了。事实上,城市的确是逐渐形成的。人类居住在城市里,创造了各种不同的谋生方式,他们像自然界的不同生物,共同形成了一个生物圈。同时,城市也是个大仓库,存放与搬运成了城市运动的两种基本方式。城市也是政治的中心,所以许多重大决策都来自城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格局。而且,城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冲突远甚于和谐,冷漠远甚于热情。最重要的是:城市是多种力量的集合,有排斥的,有容忍的,也有落寞的。城市是激烈较量的场所,力量在这里获得了它永恒的形式。
在我看来,林奇的意思是城市创造了一种无法一语说透、类似生物变异般的存在方式;城市让生活其间的人们每天都滋长着尖锐而暧昧的思想,都创造着层叠交错的意识。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城市既是我们每天都摸得着的物质现实,还是我们每天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思想情绪。城市有它的视觉特征,更有它的心理模式。城市是现实的,更是视觉的和心理的。视觉城市和心理城市不是物质城市的替代品或描摹品。在物质城市之上,同时嵌合着一个视觉城市,凸显着一个心理城市。
事实上,从视觉城市到心理城市,呈现给我们的正是物质城市的一个镜像,但这个镜像并不像它所遵从的对象那样具有客观性。所有的客观性在城市镜像当中都受到了视觉和心理的双重打击。哪怕我们在这当中置入一个现实标准,也无法让视觉和心理按照物质的要求呈现自身。视觉城市造就了心理城市的外形,心理城市让视觉城市离开了物质城市。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发现,城市镜像包含了对城市的反抗和热爱。只是,这种反抗和热爱居然产生于对物质城市的高度依赖当中。
林奇在寻找一种美好城市的形式。他经过长篇大论之后,发现美好城市仍然离他的理想很遥远。林奇和另一个研究城市的学者蒙弗德(Lewis Mumford)②一样,在构筑理想城市方面遇到了困境。所不同的是:蒙弗德是个城市悲观主义者,而林奇则多少还保留了几分乐观的信念。然而,正是林奇的努力使我对城市学的理想产生了某种怀疑。如果我们只是以一大堆数据为规划的依据,美好城市也许还有希望。如果城市学家们也过分热衷于某种理想,以为城市可以按照这种理想重新加以塑形,那么,我则要指出理想城市将会抹掉生活本身的全部丰富性与独特性。
2
有意思的是:每当城市学家试图寻找与努力建设美好城市的形式时,敏感的艺术家们,包括那些文学家,一点也没有耐心去追随城市学家的唠叨絮语。艺术家面对城市寻找在视觉上可以表达自我感觉的风格,文学家则在物质城市当中发泄着狂喜或压抑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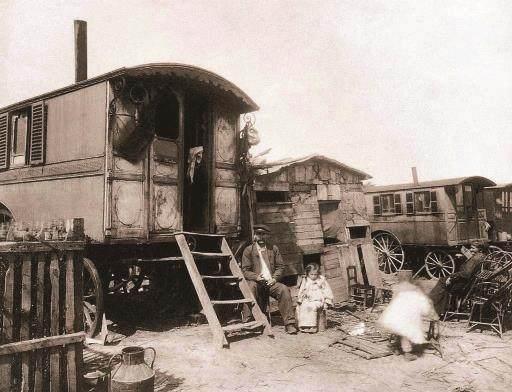
19世纪若干个文学家的叙述,可能是心理城市的一个浅显例子。
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雪莱(P e r c 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抒情是建基在对乡村的怀念和对城市的仇恨之上的。比如伦敦,在这个浪漫诗人的笔下,就成了“一座地狱般的城市!”③。雪莱的表达对于许多文学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心理的厌倦往往产生于所依赖对象的强大。况且,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反抗形式,总是以乡村理想化为主题的。有趣的是:同样是浪漫主义的诗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却对伦敦做了截然相反的评价。约翰逊坚定地指出:“一个人厌倦了伦敦,就等于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向你展开了生活本身。”④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城市的丰富性是滋养所有浪漫情怀的最好温床,一个人如果离开这张温床,浪漫就无所依归。约翰逊至少知道,是乡村而不是城市给平庸增添了各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尽管诗人仍然对抒情耿耿于怀,但他至少承认,并不是只有田园风光才让人激动。重复的乡村抒情已经造成了形式上的倦怠。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美国。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对纽约一往情深,在他眼中,“纽约是一只让人吮吸的橘子”。同为作家的菲莉斯·麦金里(Phyllis McGinley, 1905—1978)却厌恶纽约,她不无讽刺地说:“呵,巴黎有点可爱呢!帕杜也有点可爱呢! 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活像一个低智商的射手,一个胆大妄为、使坏的弓箭手,带着天真的同情。我就是这样去热爱纽约城的。”⑤
作家们的态度表明,城市的复杂性和城市的多样性是可以互为解释的。这种互为解释的方式同时又使城市变得格外的暧昧,难以定义。更重要的是:物质城市一旦进入作家的思索中,就会分裂成不同的词语板块,以指称彼此对立的情绪。当这种情绪转变成视觉时,城市就演变成一种独特的镜像。
3
文学家在寻找城市的心理表达式,艺术家们则用他们的手段建构城市的视觉外观。我们可以从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土鲁斯-劳特累克(Henri 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Monfa,1864—1901)和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1883—1955)等人的作品中看到艺术家的努力。关于视觉城市的建构,重要的还是艺术家,重要的应该是那些从事影像的人,他们丰富的图片库让我们产生了无比的兴趣。我总在想:这些人通过光学仪器所看到的,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物质城市?当他们自豪地举起照相机这种工业文明的精巧产品时,他们眼中所经历的,究竟是类似建筑外表所呈现的动人质感,还是梦幻中所体验的视觉历险?


我们马上想到的是法国摄影家阿杰特(Eugène Atget, 1857—1927),虽然他所拍摄的巴黎是一项被委托的项目,但难能可贵的是阿杰特却在工作当中,不时地把镜头对向不为人知的细节。显然,他是明确的,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为即将消失的巴黎留影,更重要的是:就他个人而言,是为眼前的旧物留下与心理密切相关的一份视觉记录。这样一来,他与其说是在客观拍摄,不如说他在重构一座属于视觉的城市;他的做法与其说发扬了摄影记录的长处,不如说他有意无意地颠覆了记录本身。敏锐的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nflies Benjamin,1892—1940)可能是第一个观察到阿杰特的这一份记录的价值所在,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复制。对此他如此说道:“机械复制却反映了某种新东西。……远在印刷术使手稿变得可以复制之前,绘画艺术就已通过木刻而成为一种能够机械复制的东西了。”“仅仅数十年后,平版印刷便被照相术超越了。在图像复制的工艺流程中,照相术第一次把手从最重要的工艺功能上解脱出来,并把这种功能交给往镜头里看的眼睛。由于眼睛能比手的动作更迅速地捕获对象,图像复制工序的速度更急剧加快,以至于它能够同说话相一致了。”“复制以一种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同时能使人欣赏,这导致了传统的崩溃。”“复制品能在持有者或听众的特殊环境中供人欣赏,在此,它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这两种进程导致了一场传统的分崩离析。”⑥
这说明摄影家的工作可以为从视觉城市走向心理城市的历险过程提供视觉证据,说明他们是如何通过拍摄去建构一座视觉城市的。摄影家们生活在物质之城和心理之城当中,同时被这两座既虚拟又现实的城市所挤压。物质之城就耸立在他们的前面,而心理之城则潜藏在他们的背后。在这样的挤压之下,城市就开始变形了,城市不再是简单的居所,城市充满了乡村所无法替代的快感,充满了文字所无法表述的复杂。城市变成一种幻觉,而且充分地视觉化了。城市空间不再是空间,而是凄厉的尖叫与嘶喊。城市经由视觉的指引而深入到无边的心理体验当中,冷漠的物质就被拍摄所创造的细腻触感所置换。
摄影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品无须我们多嘴多舌。从众多大师的视觉体验中,我们完全可以阅读到不同时期在不同城市的空间中对物质→视觉→心理转换时所产生的不同喜悦与厌恶。在这里,对情绪的风格分类很多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主义的分析也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城市镜像本身。城市镜像不仅是风格,不仅是形式;城市镜像是一种存在,它对应于城市,并折射出城市之光。
4
专门研究图像与视觉的学者米切尔(W. J. T. Mitchell)在《图像学:图像、文本和意识形态》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他所需要回答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图像是什么?二、图像和文字有什么不同?⑦然后,他又把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一、如何描述图像?二、图像说什么?米切尔指出:“研究‘图像(icons)的‘词语(logos),也就是‘图像的修辞学,涉及两层含义:首先,是研究‘如何描述图像,也就是传统所说的‘艺术写作(art writing),并追溯到哲学意义上的‘图像这一专有名词,以及它所指涉的视觉艺术的描述和转译方式。其次,是研究‘图像说什么,它指的是一种图像所固有的说话方式,图像是如何说服人、如何讲故事以及如何形容的。”⑧
米切尔的问题是当代任何试图回答图像及其意义的人所不能回避的。有意思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米切尔发现,传统学者把图像学定义为科学是有严重问题的。图像学不是关于图像的科学,而是关于图像的社会心理学。所以,图像的核心不是对图像的认知,而是对图像的恐惧。在米切尔看来,正是对图像的恐惧才导致了人们对图像的崇拜,这是偶像崇拜和现代拜物教的心理原因。米切尔对图像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图像的看法。也就是说,视觉艺术之所以产生力量,并不根源于让人感动的风格魅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由艺术家所创造的一种视觉说服方式,而是根源于对构成对象表面因素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惧怕。因此,偶像崇拜和偶像破坏不断交替出现在人类的图像史中。
显然,城市镜像也是图像的一部分。当影像工作者用相机面对城市按动快门时,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把物质城市置换为视觉城市,并通过视觉城市来提示背后的城市心理现实。关键是:按照米切尔的提示,城市镜像的力量源自对城市的惧怕。这种惧怕不是表面的、不是赤裸裸的,更不是那种过分文学化的,因而是无力的抗议;而是隐藏起来的,是一种对城市的整体畏怯感。城市比乡村更具有力量的原因也在这里。城市永远是一个超越所有个体而存在的巨无霸,它笼罩在城市个体身上,成为绞杀个体的有形机器。城市的生活方式作用在每一个居住其间的人的身上,把每一个人都作为自己的对应物,并成功地把一种只属于城市的意识形态植入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变成城市的因子,变成货真价实的城市人。
所以,从任何意义来看,城市镜像都是城市人的产物,是城市人对城市的自我评价,而且往往是一种疯狂的视觉评价。所以,绝大多数的城市镜像都具有颠覆的特性。如果我们明白了图像和恐惧的关系,明白了拜物教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我们就会明白:城市镜像只有通过颠覆的方式,才能达到克服畏怯建立信心的目的。因为,城市人必须依靠建立信心才能支撑自己每天去面对变化无穷的城市本身。
这说明,并不是所有城市人都能发现他所生活的城市的真正镜像是什么。甚至,更多的城市人并不愿意深入探讨他们所熟悉的环境。他们不愿意相信,城市镜像竟然充斥着如许的视觉疯狂。城市镜像和修饰无关,城市镜像是城市疯狂的一种对象化,同时也是镜像制造者自我克制恐惧的必然产物。当镜像从物质/视觉/心理三者不断置换的过程中呈现出来时,城市也就被定义了。城市镜像恰恰是这一定义本身。而一旦城市被定义,城市人同时也就被分裂为两部分:世俗与精神。世俗部分生活在物质城市中,享受着城市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精神部分则生活在城市镜像里,通过镜像寻找可能并不存在的自我。物质城市完全消失在欲望的海洋中,而城市镜像则生存在视觉与心理共同构成的虚拟世界中。于是,本来牢靠的城市就发生了动摇,甚至在某一层面上还会黯然坍塌,尽管表面仍然繁荣、一切如故。
注释:
① Kevin Lynch,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The MIT Press, 1981.pp 327-43.
②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1.
③ Shelley: “Peter Bell the Third,” Part 3, stanza 1.
④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entry for September 20, 1777.
⑤“A Kind of Valentine,”New York Times Magazine(February 1, 1953).
⑥《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 编,张旭东等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05、233、239页。
⑦ W. J. T. Mitchell,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 1.
⑧ 同上。
注:杨小彦,艺术批评家,视觉传播学者,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孟 尧 姜 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