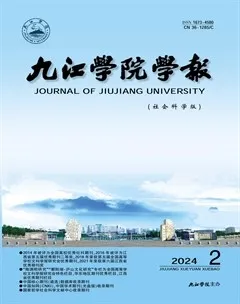鸿蒙初辟中的顽石与仙草
2024-06-28连超锋郭丹
连超锋 郭丹
摘要:《红楼梦》开首两回引出两位主人公出场:贾宝玉是一块顽石,林黛玉是一株仙草。这两回把主人公置于中华文明鸿蒙初辟时的神话传说之中,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一体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应理解为自然、人、社会的融合。两位主人公的人生阅历如同一个万花筒,他们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似幻非幻,这种自然、人、社会的一体化,又本质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并具有终极叩问、终极关怀的属性。它将烈焰般的感情喷发和语言叙述的零度幽默性巧妙结合,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社会关系;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似幻非幻;零度幽默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2-0048-(04)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2.009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中国古代的一本包罗万象的大书[1]。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红楼梦》熔铸了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冷峻的现实评价,从而表现了对人类生命存在的深刻洞察、哲理思考与终极观照[3]。其开首两回用神话故事引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构思巧妙,呈现别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一块“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顽石
高尔基把文学称为“人学”,这是一句极为深刻的话,为众多文人所欣赏。“人学”一词,含义甚为宽泛,革命导师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也即是说必须把人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总体中去考察,才能对“人”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在我们这样论述的时候,还应该对马克思的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理解要再宽泛一些,这里的“一切社会关系”还应包括“人”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把“人”放在自然的、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人际的、世俗的复杂交织的环境中,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这样复杂交织的环境描写是极不容易的,只有“大家”“巨匠”才能为之。《红楼梦》的头两回,便是这方面的范本。《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它以艺术的方式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5],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的各个方面。从中释放出几乎无所不包的信息:一个社会的信息,几百个人物的信息——活跃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大观园中的各色人等。它预见社会的未来和走向,也预见几百个人物命运。但这仅仅是预测,任何预测都有其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甚至有它的不虞性。《红楼梦》创作最大的悖论在于预测的准确性与模糊性同在;叙述的确立性与非确立性共存;发展的预定性和不虞性抵牾。这样一来,这部书的开篇便成了作者写作的第一个难题。“幸福家庭的相似性,不幸家庭的相异性”适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于《红楼梦》似乎很不相宜。人像展览式的开头,对于《红楼梦》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也未必最佳。在我看来,具有大智慧的曹雪芹,他别开生面地把作品的开篇和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神话相联系。女娲是中华神话的始祖,她的两项不朽的工作——“抟土造人,炼石补天”是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正面描写铺陈女娲这两项伟业不是作者的首选。作者的巧妙在于,既正面肯定女娲的伟业,又侧面选取其遗弃的一块顽石的风尘遭际进行叙写,从而完成了对一个社会从繁华到末路,从凯歌到挽歌,从欲补天到无材补天的社会异化过程的绘制。
作者把主人公定位为中国远古洪荒时期华夏始祖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之不用的一块顽石,叙述他在青埂峰下的一段精神历程,后又把这块顽石置于警幻仙子的赤霞宫中,取名为神瑛侍者,在无所事事之中以甘露灌溉绛珠仙草,此草后幻化人形,为报答神瑛侍者的雨露之惠从而演绎出天下第一爱情悲剧。《红楼梦》开篇的神话传说的传奇性、神秘性似乎和之后情节的世俗性、真实性不甚协调,但作者却用生花之妙笔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江南姑苏城的一个乡绅甄士隐邂逅从天边来的一僧一道,旁及葫芦庙寄居的贾雨村,后来甄士隐资助贾雨村应考,女儿英莲丢失,甄士隐看破红尘随着疯道人出家而去,后又叙贾雨村应试得官讨取丫环娇杏作妾,把两者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在第二回中,贾雨村同古董商冷子兴对贾府的一番介绍使得整个作品的脉络清晰起来。这开首的两回,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在世界小说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两回的总叙,使得整部作品显得气势若虹,条理清晰。把人物置于悠久的远古文化之内,又置于具体的典型环境之中,把故事和民族的源头联系起来,又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在人类生命之源的神话释解中对生命意义进行叩问,把人类发展中的动力和发展中的异化相交融,将对世纪末的恐惧和对盛世的留恋相混杂。这里既有凯歌高奏的余韵,也有挽歌吟唱的哀怨,还有葬歌吹响的预感。这两回神机妙算的开篇,吹响了东方第一巨著的序曲。
二、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与似幻非幻
“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是《红楼梦》诗美的基础,其中包含的审美理想与真挚情感是这种诗美的核心。具体来说,它表现在作品对宝黛爱情以及大观园其他女儿悲剧命运的深刻描写中。”[6]《红楼梦》开首两回,用神话传说做引子,使两位主人公登场,开篇伊始便吊了读者的胃口[7]。贾宝玉与林黛玉的亮相,一开始便不寻常:两位主人公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似幻非幻,在云雾缭绕中,开始了他们非同庸众的人生历程。
贾宝玉是女娲炼石补天弃之不用的一块顽石,天之将倾,女娲炼石补天,每一块石头都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栋梁之才。女娲独弃这一块不用,其用意深焉,不是所有的栋梁之才都可以发挥聪明才干,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才未展、情未了的干将们,必然会有不平之声、哀怨之情,做出有违常理之事。于是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批人便显出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似幻非幻的怪诞形态,贾、林都是这样的形象。贾宝玉对于自己不能补天,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8]。是空空道人把他携入红尘,看到人世间的一切幻象和丑陋,目睹仕途的艰险和龌龊,阅尽官场的无耻和黑暗,看清礼教的虚伪和残酷,使这位“顽石”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生理和精神时时在蜕变之中。从生理上来说,贾、林二人均非健壮之人,是一种病态之像;从形体上来说,贾、林都是飘逸风姿,如有仙人之体;从精神上来说,贾、林都有一种非常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和世俗礼教格格不入,被视为怪人,他们的精神和心理世界,呈现出似幻非幻的境界,具有庄子笔下“畸人”的病态美[9]。
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似幻非幻的主人公形象的开篇,奠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也为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应、不同于一般的开篇。作者用女娲炼石补天弃一石而不用的神话来营构作品的开局,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艺术的匠心独运[10]。不然的话,这部巨著的无比丰富性、巨大批判性、深刻叩问性、人性理想性、艺术感染性等都将无从依附。一个社会的末期,显示出它不可救药的丑陋性,破败灭亡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与之相应的是人在社会中的荒诞性与人性的异化性[11]。主人公显出病态是常态,因之,在荒诞之中显出真实才有可能。以荒诞寓真实,是一切反映社会大转型伟大作品的共性。贾宝玉生而衔玉便是病态,他对林黛玉说,为了林妹妹而弄出一身病,这是表层的表白。从深层来说,他的病体是社会造成的,是与生俱来的。他和林黛玉都是仙体—— 一为顽石化为的神瑛侍者,一为生在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但两人又都是肉体凡胎,似神非神的结合,使得主人公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融合中能演绎出感人肺腑的人生悲剧[12]。这反映了作者把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的非凡视野,也反映了作者的生命意识和生殖崇拜。人类来源于进化,生命诞生于自然,但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社会进步的动力却源之于异化。异化这种现象是一种非人间的自然之力,它的惰力和它的动力如影随形。有了惰力才有动力。也即是说,人类社会每一次进步中的异化是一种惰力,在惰力形成之时也就蕴含着动力。能够写出两者之间的相互颉颃,是一部巨著的标志。这种标志的外部表现形态,便是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似幻非幻。社会的异化中的非人化,以似病实则无病的怪诞形式显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病态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病,世纪末的心理病。以神话传说女娲炼石补天中一顽石无材补天的经历来结构作品,实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大寓言,似神非神是这个寓言的又一外部表现形态。《红楼梦》开篇的女娲、僧、道的出现,充满了浓厚的神仙道化色彩[13],表现了人生的虚无性和现实性相交织,人生命运遭际的虚幻性和现实性时刻伴随着每一个人,似幻非幻便是人生虚幻性和现实性相交织的第三个外部表现形态。
《红楼梦》开首两回,虽然以神话形式表现,但它的语言却是极为生活化的、活跃在人们口头上的雅言——俗化的文言,白话了的雅语。它的表现力是惊人的,以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片段来呈现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巨大生活内容及其蕴含的荒诞性,从而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及真实性。读荒诞之语不觉其荒诞,反而觉得是一种幽默,是一种反讽,是一种对生活的模拟。贾宝玉、林黛玉两个艺术形象如同两颗珍珠交相辉映,晶莹剔透,珠联璧合。这两回对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塑造采用的是互文、互现的修辞手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贾宝玉是一被弃的顽石,无材补天;林黛玉是一棵没有雨露将要干涸枯萎的仙草,是这个顽石对之施以甘露才得以延续生命。他们同时被时代所弃,但他们却相互依靠。这种语言叙述凝聚了华夏语言的高度智慧和审美特质。两个形象的互现性表现在叙宝玉时实则暗含黛玉,反之亦然。例如,作品详叙了宝玉来之于女娲炼石补天被弃的一块顽石,而对于黛玉作为绛珠仙草的来历却付之阙如。实际上,叙宝玉便暗含黛玉,留下一块空灵之地供读者想象。再例如,写绛珠仙草得了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恩,脱了草木之胎,幻似人形,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青果,渴饮灌愁水。但对于顽石吃什么,饮什么,却无有详述,这和上文的道理是相同的,黛玉之仙草与宝玉之顽石吃、饮之物都是相同的,写了黛玉就没有必要写宝玉了。对两位主人公用互文、互现的叙述策略是极为高明的,使得这两回的语言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三、感情烈焰喷发及零度语言叙述艺术
《红楼梦》头两回,感情烈焰喷发如同火山喷浆,烈焰滚滚,怒气如炽,势不可挡,但语言叙述艺术策略却是静如山林,淡如秋水。这两回的语言风格极为独特,把怒火般的炽情用恬淡的语言抒发出来,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红楼梦》的作者却巧妙地把两者协调起来,展现了一位语言大家的风范。
《红楼梦》绝对是一部烈焰喷发的作品,主人公空怀满腹经纶,但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看到了这个大厦将倾的必然性,不是他不想补天,而是不允许他补天。这是一种怎样的撕心裂肺的伤痛!他应该诅咒这个环境,但他却离不开这个环境,是这个环境玉成了他,又是这个环境毁灭了他。锦衣玉食,钟鸣鼎食掩饰不了他内心精神的苦痛,周遭是腐朽,是罪衍,是鸡鸣狗盗,是蝇营狗苟,是阴险虚伪;他想爱的却不能爱,他不爱的却如影随形,使他无法摆脱;爱他的人有时却是害他的人,在爱人的形式下吃人,在保护人的形式下毁灭人的意识,制约人的自由。礼教,使这个时代的弃儿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摧肝伤胆的情感!作品的叙述真是字字血,句句泪!正如《石头记》的缘起诗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14]但如果作者在创作时激情万丈,义愤填膺,充满了诅咒之语,处处都是谴责讨伐之声,恐怕这部书的艺术魅力便大打折扣了。在这部书的开首两回,作者的语言叙述风格是把烈焰喷浆的满腔愤怒,用近乎零度感情的语言进行叙述,有时还不乏幽默、谐趣,这两回的语言叙述风格奠定了整部书的叙述基调,成为经典性文学语言艺术。
主人公是一块被弃的顽石,有入世的心志,却欲济世而不能[15],他满腔的不平之气,满腹的怨恨之语,却被一僧一道用调侃的语言化解了:“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16]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诠释是蕴含血泪的人生体验,但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17]说罢甄士隐便同道人一块“飘飘而去”[18]。即使有一大缸的泪水,有一大车的怨恨,作者在开首两回奠定的语言基调却是以零度感情叙之,以幽默语调述之。这种语言是作者的鬼斧神工,寓泪水于轻快,蕴怨恨于幽默,抒忧愤于妙趣的语言之中,这是很难为之的。但作者做到了,这是一种灵气,是一种境界,是一座高峰。
四、结语
《红楼梦》开首两回以神话故事引出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似病非病、似神非神、似幻非幻的主人公形象,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反映了人在社会中的荒诞性与人性的异化性。这两回把烈焰喷浆的满腔愤怒,用近乎零度感情的语言进行叙述,奠定了整部书的叙述基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叙述风格。《红楼梦》足堪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范本,小说的评判与阐释、小说史叙述、小说创作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都离不开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19]。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更或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上,《红楼梦》都能经得起深层阅读[20]。
参考文献:
[1]樊星.《红楼梦》与当代文学[J].文艺评论,2003(2):28-36.
[2]鲁迅.鲁迅古小说研究著作四种: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382.
[3]杨海波.《红楼梦》“下凡历劫”“三大神话”及其他:人类生命存在的哲理思考与终极观照[J].名作欣赏,2020(4):9-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5]赵娟.《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J].学术探索,2013(6):77-82.
[6]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52.
[7]陈维昭.红楼梦·红学·经学:《红楼梦》研究史检讨之二[J].明清小说研究,1996(1):30-42.
[8][14][16][17][1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12.
[9]王子炫.试论“病态美”审美观在《红楼梦》中的价值[J].名作欣赏,2021(5):126-127.
[10]赵树婷.《红楼梦》“石头意象”考察[J].明清小说研究,2010(2):75-88.
[11]贾三强.论贾宝玉的双重异化[J].西部学刊,2017(5):5-11.
[12]程智江.冷月花魂 以泪偿灌:浅议林黛玉的悲剧美的意蕴[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2):121-125.
[13]梁婉月.《红楼梦》中黛玉困境分析[J].名作欣赏,2020(7):99-111.
[15]田霞.《红楼梦》开篇神话的叙事修辞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2019(2):152-165.
[19]刘勇强.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J].北京大学学报,2016(3):108.
[20]卜喜逢.析《红楼梦》前五回的纲领作用[J].红楼梦学刊,2022(5):164-179.
(责任编辑 程荣荣)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语文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编号2021-JSJYZD-052);河南省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大学语文”(教高〔2019〕671号);河南省高等学校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文学教研室”(教高〔2020〕393号)。
收稿日期:2024-03-16
作者简介:连超锋(1983—),男,河南信阳人,商丘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与中原地域文化;郭丹(1987—),女,河南商丘人,商丘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