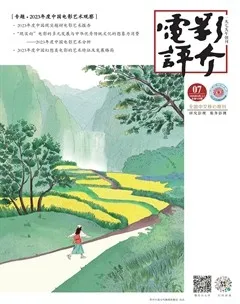错位时间·多重主体·历史谜因: 电影修辞学路径中的声音分析
2024-06-28张红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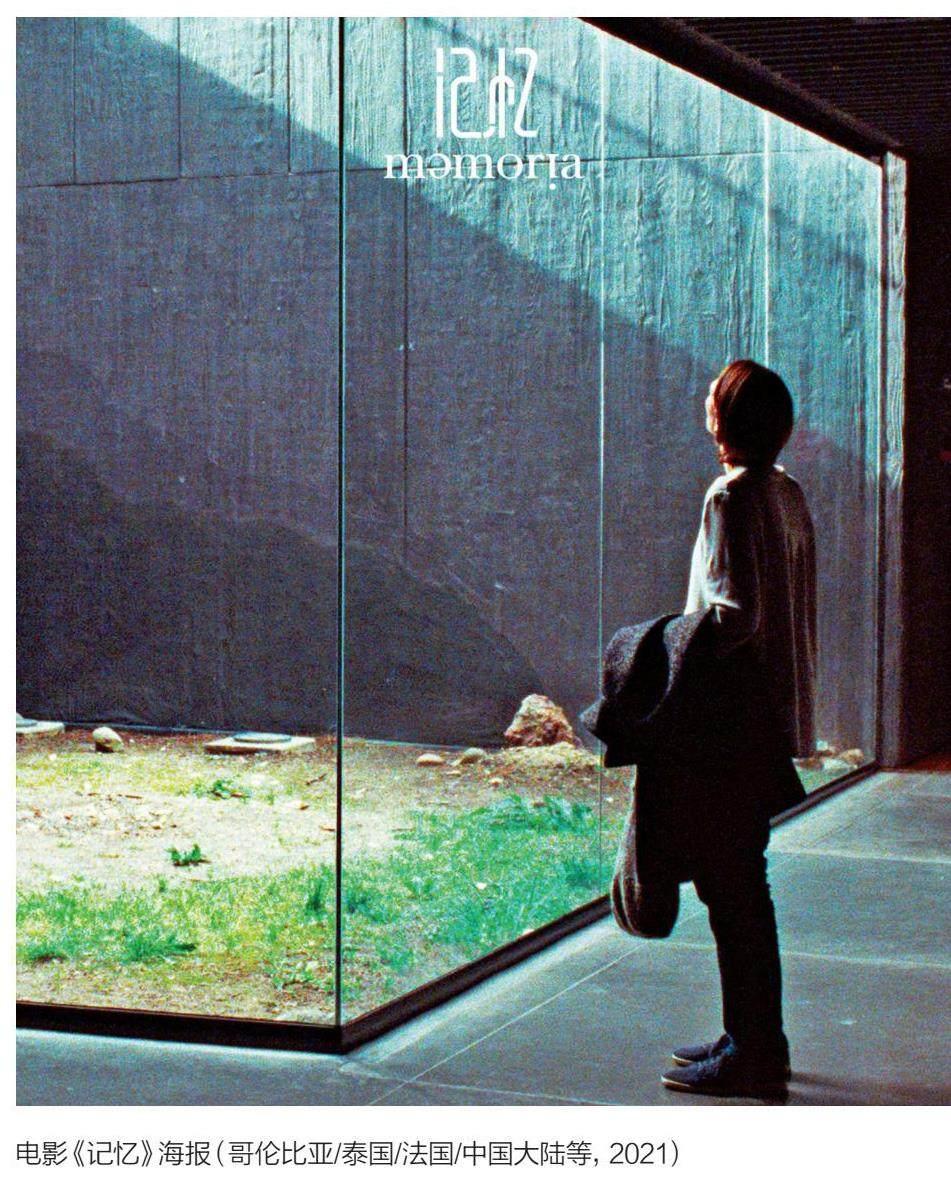

【摘 要】 电影中的声音在叙事性表意与意象性修辞两大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后者,电影声音经常以与现实拉开距离的方式对现实的表象提出质询与思考,在具有修辞性质的思想表达中挑战了完整统一主体的复现,包含将电影影像中的“主体”理解和展现为相互联系的多重主体的逻辑,在象征主义下直接与电影主题产生关联。作为电影修辞的声音表达可以构成疑问——解答体系中的观念性表述,通过提问和解答的方式揭示出整部影片历史谜题的“真相”。本文将从时间的错位、主体的分散与历史谜因的表达三个不同于现实的电影情景角度出发,结合实例探讨电影制作人员如何有效地运用声音来“修辞”电影文本,在相关视听意象蕴含的复杂性有所自觉的前提下,增强电影的叙事效果和观众的观影体验。
【关键词】 电影修辞学; 电影声音; 意象性修辞; 多重主体; 历史表述
电影修辞学是一个非常深入和复杂的领域,它涉及电影的各个方面,包括视觉元素、叙事结构、象征主义等。在电影修辞学中,声音是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参与到电影的叙事性表意与意向性修辞中,不仅可以基于电影影像的物象性传递信息,还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增强情感和气氛,是电影表达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叙事性表意”和“意向性修辞”中的错位时间
自有声电影发明以来,声音便在电影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可以传达信息和情节,还可以增强情感和气氛、转场和过渡、解释角色内心世界等。发展至今,声音已经成为电影表达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与画面一起构成电影的完整表达;但这些声音在其画面与影像情景中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电影记录的“可能的现实情境”中会发挥的作用,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情绪和氛围。在这些有别于现实声音经验的情景中,电影语言便可以通过修辞发挥其作用。在电影修辞学中,电影的声音不是仅仅在原有“词汇”组合的基础上加工美化、添加修饰,而是要根据影像主题在诸多可能出现在同一场景的声音与其他“语汇”中做减法,进行必要的省略等工作,用最精炼的声音表达主题内容。“因为影像的构成对象是现实外部事物本身(‘物象),现实物象本身并不是具有‘固定含义的‘词汇,而是多义的或者说是无意义的。只有通过影像的摄取和呈现,也就是说在影像画面的框定中,才使得现实的物象纳入电影表意的‘文本环境中,成为具有某种‘言说性(含义)的‘影像。”[1]电影修辞学基于这一原理,把电影表意的基本层面分为“叙事性表意”和“意向性修辞”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有别的层面。
“叙事性表意”指代电影叙事层面上的表意性,叙事性表意的声音也是电影情景性、故事性的最基本层面。电影声音在这一层面上的延长与缩短、显现或隐藏大部分依然是基于“声画同步”的故事原理存在的,尚未涉及电影作为“文本”的建构。例如,声音剪辑可以利用“捅音法”和“拖音法”加强反应镜头,让剪辑更加自然流畅。如果不使用这两种方法,画面之间的衔接就会稍显生硬——因此,导演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镜头与时间之间的断裂感进行叙事。例如在《我不是药神》(文牧野,2018)中,思慧和勇哥在小旅馆发生的对话,就是在不使用这两种声音剪辑的情况下完成的。勇哥送思慧回家后得知,思慧是一个病友群的群主,她的女儿罹患罕见的慢粒白血病,长期依赖特定的治疗药剂“格列宁”;而勇哥则有特殊的途径可以从印度以低价买到“格列宁”。为博取勇哥的好感,思慧只好硬着头皮与勇哥搭话,而勇哥在面对思慧的讨好时也显得手足无措,表情僵硬;干净利索的声音剪切配合不带角色关系的对切镜头在电影语言中完成一次“不动声色”的表达,让两人在旅馆中对坐的场景变得缺乏情感,给人一种僵硬的机械感,很适合表现勇哥尴尬的境地,以及二人之间互不熟悉的气氛。这样的声音修辞也可以看成广义上的修辞,“即建立在叙事惯例、情节架构层面上的表意性修辞。在这一层面上,人们通常把电影影像的修辞性(表意性)与‘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再现联系起来”[2]。例如文牧野在《我不是药神》中使用的带有语言修辞性的表达,虽然以有意的技巧省略赋予影像某种表意性,但此时传达和呈现的影像依然停留在较为基础的修辞建构层面,因为声音与图像的关系依然遵循着与现实物象相比较基础上的、可以识别的影像现实,乃至建立在现实事件的因果关系背景上的故事世界。
在更多时刻,电影中的声音还是要超越叙事性、超越与世界显而易见的近亲性才能制造出新的意义——这也正是电影修辞理论强调的“意向性修辞”层面:“倘若影像要表现特定含义,则必须与影像的日常‘近亲性含义拉开距离,而这种距离的拉开,常常是通过特殊(影像的变形、声画的冲突、格式的变化、幻象的构造等)的影像建构手法而得以实现的。”[3]“意向性修辞”手法是对前者叙事性的延伸和拓展,它超越了对单一现实情景与现实逻辑的复现,而将现实理解为深刻现象的表象,并尽力在形式上追求打破常规,对现实的表象提出质询与思考,在具有思想机制的内涵中更加具有文本性建构的特征和功能。以上文提到的“捅音法”和“拖音法”为例,这两种手法在电影中较为常见的用法还是制造意义:《万里归途》(饶晓志,2022)在展现中国人的归乡故事时,背景音常以一位努米亚小女孩吟诵的童话“人们紧紧搀扶着,凝望漆黑的海面”与画面进行对位,画面中的中国人相互搀扶着穿过努米亚无边的火焰与黑夜,而背景音中的歌谣飘散在黄沙大漠中。稚嫩的战争遗孤与众人一同经历回家的漫漫旅程,又仿佛这次伟大旅程的书写者与见证者;《潘多拉》(维吉勒·韦尼耶,2010)的结尾,随着酒店的关门场馆内回响起空旷的回声,音响系统和白噪音被空旷的场景放大了,变高的音量也意味着较高的能量,在心理上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和震撼性,简单直接地激发观众的情感。轰鸣的音响可能被用来营造一种紧张的氛围,增加影片的紧张感和戏剧性;或者是为了增强某种镜头的情感表达或为某种特定目的服务;在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克里斯托弗·诺兰,2017)中,拖音法的运用将人物的台词转换为蒙太奇的叙事,一名少年在火车上阅读关于士兵的报纸:“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土,将在沙滩上战斗……”此时,画面中显示沙滩边海水冲击着沙滩上的钢盔,一场残酷的战斗刚刚发生;一名英军飞行员焚烧了沙滩上的飞机,接着被德军士兵拖走,而这些士兵用生命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在这些场景中,声音的修辞在强化声音的同时用来强调诗句背后的含义,在电影的书写话语系统中发挥出“意向性修辞”的作用,把人物诗歌吟诵转化为画面蒙太奇,让影片内涵得到升华。
二、现实表象下的声音意蕴与多重主体
“意向性修辞”打破单一基于相似性的现实复现法则,将影片的叙事层面在电影语言上进行延伸和拓展,挑战了对完整统一主体的复现,包含了将电影影像中的“主体”理解和展现为相互联系的多重主体的逻辑。实际上,电影中的声音区别于画面,它在“叙事性表意”的层面上便包含多重主体的存在;越是先进的录音与放映技术,越能展现电影声音层次的不同层面。例如,不同景别与场景中声音强度与混响的变化不同,这是现实听觉经验所决定的,而电影声音也要尽量在技术上还原现实声音本身具有的穿透性,在均质的电影院空间里带来虚拟的“透视感”。在录音与放映时,技术人员会通过调整不同景别中直达声和反射声的比例,配合音量大小,从而产生“真实的”距离感。景别越大,收音器距离被摄物体的位置越远,声音强度也就越低,而回响更多,直达声更少;相反,越是小景别的特写镜头,声音的强度也就越高,混响越少,直达声音越多。除此以外,电影录音还要注意不同镜头角度对声音方向的影响。之所以能感觉到立体听感,是因为同一个声音传到人们的右耳和左耳时的时间和强度的差异而产生的。由于镜头角度不同,声源的水平和高度定位就会产生差异,声音的方向感便会随之变化。
然而,上述的“多重主体”依然停留在现实经验的层面,尚未与电影主体产生联系或涉及电影文本与电影修辞的表达中。电影修辞学中的声音更多指向带有“意蕴”或“气韵”的象征主义,换言之,便是以电影中的声音来象征或隐喻电影中的某些元素或主题。“从影像的这种赋予物象以灵气与韵味的意义上讲,影像修辞的表现力和创造活力似乎也可以借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的那种‘气韵生动之属性来加以描述。因为通过影像修辞‘心灵灌注同样可以使电影画面产生出一种如宗白华所说的‘流荡着的生动气韵。”[4]例如《刺客聂隐娘》(侯孝贤,2015)中曾多次出现古琴音乐,这是导演自出机杼地将聂隐娘与嘉诚公主,以及“青鸾舞镜”典故中的“青鸾”等多重主体集合在一起的声音修辞,欲说还休的声音心理蒙太奇将主体与客体、他者与自我、现实和想象的纠合与缠绕作为电影的主题之一。聂隐娘受命于师父嘉信公主前去刺杀表兄田季安,但在返回魏博母家后沐浴梳洗之时“回忆”起嘉诚公主的过往。伴随着以“捅音法”突入画面的古琴声,画面在展示隐娘心事重重的表情后展现出嘉诚公主远嫁魏博时,迎亲队伍从花树间出现,嘉诚公主抱琴居中而坐,弹奏着清润幽远又哀婉孤寂的曲子“青鸾舞镜”中。“青鸾舞镜”的典故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罽宾国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在古琴的独奏声中,独自一人远嫁藩镇的嘉诚公主以琴音状说内心、并借“青鸾舞镜”之说自比;而因为即将刺杀童年唯一玩伴表兄田季安而倍感孤独的聂隐娘,其自身也成为作为公主琴声倾听者、回忆者的隐娘的一面镜子,但镜中的影子公主又只是她自比自照的想象,一种与己无关但只有通过它的镜像才能确认自身存在的“理想化的自我客体”[5],越是追忆那远去的琴声越倍感孤独。
即使是在声音“缺席”的前提下,它也可以在主体与主体的感受之间制造裂隙,让画面中的主体体验“分裂的经验”。一部分电影从电影语言发明以来的复杂游戏中挣脱开,其中的意义与表象的关联不再依靠意指完成,而是依靠可以“听到”的通感。例如《记忆》(阿彼察邦,2023)中的声音元素与其故事表现的联系:这部晦涩的影片似乎总是不断地在记忆、声音、考古学、哥伦比亚历史、经验的传递等几个核心概念之间打转,每一个概念几乎都在电影中被具体的甚至经由台词直接抛出,将电影引向更深的谜题。在女主人公杰西卡深夜被一声巨响惊醒并陷入失眠症后,便陷入了“主体”构成的迷宫之中。失眠的杰西卡到波哥大探望病床上的亲人,也因此结识了考古学家阿涅斯和音效工程师埃尔南。但很快这些角色就展现出杰西卡与观众未曾预料到的另外一面:曾在录音室为她还原出巨响的埃尔南突然消失,而工作室的其他人却众口一词地说这个人并不存在;阿涅斯的行为将杰西卡与一个考古发掘现场中的骸骨联系起来;而另一个同样自称“埃尔南”的村民出现,与杰西卡相交似故人。两名“埃尔南”拥有迥然不同的种族、身份、能力与爱好,却同样神秘地出现在杰西卡身边,且仿佛能洞悉她的心思般还原出她的梦境或记忆。在这样不稳定的角色联系下,主人公杰西卡身边的一切都在逐渐变得抽离、神秘而失控,她看到越来越多的超自然现象,脑海中的声响也越来越频繁且剧烈。可以说,《记忆》中的角色通过感知、行动与其他角色发生互动不仅建构了基本故事,还颠覆了这个故事,以角色身份与角色关系之间的裂隙改变原本故事架构中的稳定性。《记忆》中存在不同的行动主体,影片通过暗示他们之间的神秘关系铺排故事,却并未给予一个完美的解答,观众只能与杰西卡一起“倾听”他们,感受世界的谜题。
三、历史记忆的钩沉与叙事谜因的呈现
电影声音是电影修辞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在构成电影修辞层面上形成一种常见的修辞体系——“疑问-解答”体系。①这种修辞内容更注重观念性的表述,通过提问和解答的方式,揭示出整部影片历史谜题的真相。声音在电影中所体现的信息,不仅有特定的思想情感和美学内涵,同时也是整部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电影中的声音与历史性表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现代叙事形式衍生于时间影像的类型和合成,其可读性并非仅来自影像的外观或外观的结构性效果,而是源自视觉影像与观念性影像自身的推论。这种推论是以它们自身定义为基础的,而不仅仅是作为外观的强调。本文此前讨论过的不同电影中种种声音呈现出的不同意义指向:《低俗小说》中的声音昭示着人与人之间难以泯灭的隔阂与陌生,以及他们不得不尴尬对坐的荒谬现状;《万里归途》与诺兰执导的美国历史战争电影《敦刻尔克》中的歌谣与独白仿佛是预言者或先知透露出“真理”与“结局”,超越人物当下的处境,对他的未来与宿命作出预示;《刺客聂隐娘》中的琴声就是一切的结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通过对电影声音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电影表现手法,同时也可以更好地领略电影的艺术魅力。在《双塔》(维吉勒·韦尼耶,2013)中,电影中的声音与历史性表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声音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语言元素,通过其独特的修辞手法,能够与历史性表述相互呼应,共同构建电影中的历史叙述。双塔的设定本身就隐喻了历史上的某种对立或分裂状态,双塔作为一种具有对立统一特性的建筑形式在空间上相互独立,但又通过某种方式相互连接或呼应。这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可以映射到历史中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或文化现象;同时,“双塔”对历史的隐喻或许还可以关联到双子塔作为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在911事件后的悲剧的象征。导演维吉勒·韦尼耶通过建筑物灯光的逐渐熄灭来呈现寂静而庄重的氛围,通过视觉和听觉共同作用,激发出隐含的历史表述,使观众产生深刻的感受。片中对歌舞厅的刻画通过高强度的镜头效果:星体之光及其多重变体、建筑空间的折叠/伸展、身体性的力量以及各种倒错等让观众沉浸在音乐和舞蹈的美感中,体验到不断向高潮涌动的热烈情感;舞女、双子塔、丽莎与乔安妮等元素之间似乎存在的神秘联系,又不禁让人产生对“双塔-纽约双子塔”等空间与历史坐标点的联想和思考。
声音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语言元素,通过其独特的修辞手法,能够与历史性表述相互呼应,共同构建电影中的历史叙述。在静谧之中,静态的图像与声音仿佛是向夜晚的诀别,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时间和历史终结的联系,它潜在地终结了坐标轴式的时间模式,以沉浸在静默夜晚中的双塔隐喻人类在面对历史灾难和悲剧时的态度与反思。
结合电影声音的历史表意来看,影像修辞的“减少”和“框定”工作显得尤为关键。声音作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影像共同构建了电影独特的表意系统。随着电影声音技术的发展,声音的表意功能也逐渐丰富和深化。在早期电影中,声音主要是辅助影像的存在,用以强化画面效果。这种初步的修辞性界定虽然赋予影像以表意性,但此时的影像传达与呈现仍然处于较为基础的修辞建构层面。例如在早期的无声电影中,尽管没有对白和音乐,但通过各种音效的巧妙运用,观众仍然能够感受到紧张刺激的追逐场景或温馨感人的情感交流。这些音效的选择和定位,为电影营造出一种特定的氛围和情感基调,使观众得以沉浸其中;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声音在电影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对白、音乐、音效等元素共同构成电影声音的丰富层次,它的核心功能在于在现实物象之外提供一种可辨识的影像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基于现实事件因果关系的故事世界,完成由叙事性表意向意向性修辞的转变。
在意向性修辞方面,电影的声音叙事成为建立在叙事传统和情节架构之上广义上的修辞手法,形成具有表意功能的修辞形式。例如《追月》(乔梁,2022)中的音乐元素为影片营造独特的情感基调,在展现越剧表演的场景时传统而悠扬的越剧唱腔与配乐相结合营造出充满艺术气息的古代剧场,在凸显越剧艺术魅力的同时也通过旋律的起伏变化传达出戚老师等角色内心的喜怒哀乐。戚老师年轻时曾凭借一出《追月》成为红极一时的越剧名伶,充满激情的音乐体现了她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在年老归乡后,戏剧令戚老师举手投足间展现出一种优雅得体的风韵,而教授越剧时更展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投入和执着,体现出她对戏曲艺术传承的严苛要求和深沉的热爱。此时的电影声音在与戚老师日常授课排练的情景之外,更具有另一种通过特殊影像建构手法而得以实现的含义,即她的艺术表现达到了忘我、无私和无情的境界;她咏唱的“空悔恨,碧海青天,夜夜凡尘心”不仅是戏剧唱词的一部分,还有她对自身生命的全部理解与追求。戚老师的代表作《追月》是她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类似于嫦娥的形象展现了戚老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纯净无瑕的艺术殿堂之中。尽管戚老师从不曾主观表露出因戏剧事业对家人的亏欠,以及家庭关系疏远的遗憾,但反复响起的吟唱声则流露出其幻想嫦娥在冷清而寂静的月宫之中,每个夜晚都深陷于孤独和懊悔之中,对人间温情和亲情的思念挥之不去的孤寂之情。低沉的音乐和哀伤的音效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角色的内心痛苦。
在电影修辞的层面中,现实主义辞格的巧妙运用并非是对现实物象的简单复制,它更多地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升华。“这一层面上的电影修辞,虽然不乏现实主义意义上的辞格运用,也可以是对现实生活——现实物象的‘艺术化升华,同样可以‘表述和建构出主体的修辞‘意向。但相比较而言,更多地与现代主义修辞的‘思考色彩或后现代修辞的‘非结构化取向相联系……脱离了现实背景本身的逻辑制约。”[6]通过这一过程,主体的修辞“意向”得以被表述和建构,旨在传达和表现具有特定思想情感和美学信息的含义,它常常超越了现实背景本身的逻辑限制。相较于意向性修辞而言,叙事性表意更多的是基于主体对外部现实的真实把握与认知,并通过既定的方式呈现于读者或听众前,因此它所具有的主体修辞性也相对较少;而意向性修辞则更为注重主体性建构与主体性情怀的表达,其更多地体现出主体在修辞过程中的主观情感倾向以及价值观念的抒发,从而更具有主体性特征。《追月》通过对声音元素的精心选择和框定,阐述戚老师如同“嫦娥追月”般对艺术超越性的执着和热情;哀伤的唱词不仅是对越剧艺术的再现与传承,也是电影声音对艺术生命的一种深刻诠释。
结语
在复杂文本场域中,电影中的“声音”既可以基于相似性表现现实的一个表层方面,又可以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进入文本深处,带动琴声与歌声勾连的深刻文化情结;当电影经由再现神秘的声音展开某种关于主体真相与本质叙事的时候,声音又作为一种直观可感的现象勾连起世界复杂构成的其中一面,开始以不可名状的笔法对历史的谜因加以描述。电影中的声音绝不是被给定的听觉外表,或强调符号性的结构性效果;声音的形式与功能对应着电影现代化形式的衍生,它是听觉表现和观念性影像自身的推论,因为它们首先是由自己定义的。
【作者简介】 张红霞,女,甘肃天水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
①参见:赵斌.电影语言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