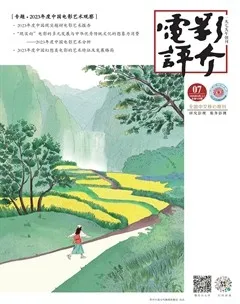电影人物的肖像化描绘: 一种现代性的主体逻辑及他者寓言
2024-06-28郭琳媛


【摘 要】 电影形象和肖像绘画在多个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肖像式的人物镜头在指涉性和非指涉性之间形成丰富的变化和组合,从而脱离单纯的现实模仿范畴,而在肖像化的形式中进入强调现实性和实用性的世俗状态时变为一种自我指涉的符号。电影作品对人物身份的特征的描绘与肖像画一样也是基于特定文化对人身份作出指涉的必然结果。在将人物处理为肖像的过程中,角色自主指涉性的身份与形象图像身份彼此之间逐渐靠近并融为一体。本文将从艺术史、电影史和身体美学的跨学科视野出发,以“面孔”“现代性身体语言”为研究横切面,结合电影肖像创作的社会语境、普遍作品特征,对肖像化的电影人物塑造方式进行分析。
【关键词】 人物镜头; 肖像化; 现代主体; 他者寓言
虽然电影形象和肖像在表现方式和手法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传达信息和表达情感方面的作用是相似的。电影形象和肖像都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形象,肖像通过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对现实人物进行捕捉和再现,通过捕捉人物的面部表情、神态、气质等细节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而电影形象则通过演员的表演、服装、道具等来表达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情感状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塑造人物形象。形象表达与感知方式的相似性使得电影形象和肖像都具有传达信息和表达情感的意义,部分电影甚至以电影手段将画框中的人物形象肖像化,以借鉴自美术学科的方式表达人物的个性、身份、情感等,继而通过肖像化的形象表达来传递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情感状态等信息。
一、指涉性与非指涉性之间的肖像化形式
肖像画(Portrait)是一种以人像为中心的绘画样式,其起源通常追溯到西方美术史中为贵族、上层阶级人士进行人像记录的传统。在中国古代,虽然存在肖像画的绘画样式,但没有“肖像画”这一确切的专门术语,仅仅是将描绘具体人物形象的绘画泛称为肖像画,包括头像、全身像、群像等。肖像画通过视觉手段与特定的人物相呼应,传达被画者的身份、性格、情感等个性特征,尤其描绘的人物穿着是反映社会习俗和身份地位的重要元素。[1]被画者的服饰、发型、配饰等细节都为观众提供了关于其社会背景和身份地位的信息。这些元素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而绘画的名称也证明肖像画所具有的这种指涉性: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描绘的是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戴尔·吉奥亢多的妻子蒙娜丽莎,而安格尔的《莫特西耶夫人肖像》则是安格尔为一位贵族妇女莫特西耶夫人所画,绘画的名称与画中的人物都显示出强烈的身份指涉性。例如在谱系化的肖像画系统中,画面的主人公是某个贵族家族的后代,他们的身份和形象特征被突出表现,以彰显家族的传承和荣耀。同样,人民肖像画和家族肖像画也是通过对个体的形象表现来指涉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或家族背景。但在对被绘画者身份做出明确的指涉之外,肖像画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所依靠的更多是绘画艺术中非指涉性的部分——正如《蒙娜丽莎》引人遐思之处并非画像与蒙娜丽莎本人的相似性,而在于绘画超越还原特征的神秘艺术表现一般。在肖像艺术的表现中,与现实相似的指涉性与潜藏在现实表象下的非指涉性构成一对彼此纠缠、相辅相成的概念,它们的此消彼长构成不同风格和流派的肖像绘画。
电影形象和肖像绘画在多个方面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捕捉和再现来传达信息和表达情感;同样,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展现也如绘画一般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历程。早期电影中的人物塑造依赖于导演或演员对现实人物的观察和描绘,并借鉴戏剧表演的方式,追求将人物的性别、年龄、职业等基本特征描绘出来。换言之,指涉性不仅是肖像画早期的核心概念,也是早期电影描绘角色的重要方式。例如改编自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的《火烧红莲寺》(张石川,1924),其中的主人公形象便以静态、单一、刻板的方式指向当时流行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强调正邪两派人物的二元对立和道德判断;而影片中的武打动作直接借鉴自京剧中的武生套路动作,具有强烈的符号性与程式化意味。美国经典喜剧电影《摩登时代》(查理·卓别林,1936)中的主人公查理也按照工人阶级的标准形象进行刻画,他被描绘为一名一贫如洗却勤劳、善良、正直的工人,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中所谓的“普通工人”形象。然而,电影角色与其“现实原形”相似的概念并不是像它听起来那样简单。在人物塑造的创作过程中,导演不仅要捕捉被塑造形象的外貌特征,还要理解和表现其个性、气质和情感状态,电影本身也需要像其他所有的文化产品一样遵循社会习俗和审美标准:《火烧红莲寺》中的流行武侠英雄形象及其源于戏曲的动作设计承担着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文化过渡任务,《摩登时代》中的查理与那些对查理进行剥削的资本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被描绘为为富不仁、缺乏同情心的象征,这种描绘方式强调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电影肖像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在指涉性和非指涉性之间形成丰富的变化和组合。当肖像描绘脱离单纯的现实模仿范畴,而在肖像化的形式中进入强调现实性和实用性的世俗状态时,它不再仅仅是表现人的形象,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表现,而变成一种指涉性的符号。这种转变使肖像画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原本的身份特征,而进入一种新的“肖像学”领域。肖像学(Iconography)是现代视觉研究中围绕肖像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也作为一种对电影视觉主题和风格进行归类和解释的方法,成为电影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2]在艺术领域中,这种世俗状态通常指的是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作为商品的价值。当肖像描绘进入这种世俗状态,这种符号性是指肖像所代表的人的身份和特征被明确地指出来,成为一种可以识别的标志。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人的身份发生变化。原本的个体身份被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或历史背景之中,成为某种符号的代表。而这种符号性的身份往往并不是由画家本人所赋予,而是由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绘画自身是它专有的‘世俗状态:绘画牵涉到它专有的世俗性或者社会性,而这也许并不在别处,而仅仅在绘画中,以及经由绘画主体们进入一种主体们之间的关系中,而不是有身份的客体。用另一种方式说,我们问题的视点也不是唯我论者式的;相反,它是这样一个视域:在这个视域中,肖像画总是那种他者的视域,然而另外,作为他者意义的面孔的价值,并不是在真理中被给予的,而是在肖像画中(在艺术中)被给予的”[3]。通过对形象的肖像化,人的身份处于在他之外,成为某种客观存在的符号。这种符号性的身份使肖像画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原本的形象特征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二、差异化与冲突性的现代主体建构逻辑
肖像化形式通过捕捉模特的个性特征和精神气质,将其表现出来并赋予一定的身份意义。这种身份意义并不是由模特的外部形象所决定的,而是由画家所捕捉到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因此,电影中肖像的本质在于通过电影语言手段将角色身上基于一定身份意义的个体精神和个性特征表现出来,肖像化角色被人所理解的状态就是它的形象状态。换句话说,肖像画并不是简单地描绘一个外部形象,而是捕捉这个形象所代表的个体精神和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可能是通过导演的观察和感受得出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对模特身份与外在形象的直接模仿。德莱叶在《圣女贞德蒙难记》(卡尔·西奥多·德莱叶,1928)中贯彻自己的现实主义追求,对一切演员都要求不化妆、不伪装和不使用假发,只依靠作为普通人的容貌和反应塑造形象。当剧本要求剪掉贞德的头发时,德莱叶真的将女演员法奥康涅蒂的头发剪了下来;在展现贞德的痛苦时,德莱叶要求奥康涅蒂忍痛跪在石头上,在设法抹去她的一切表情后试图冲突性地展现压抑的或是内在的痛楚。在演员的反复排练之后,导演对这一单一却蕴含深厚的容貌肖像进行反复拍摄,为的是能在剪片室里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微妙表情。罗伯特·布列松的导演风格与之有相似之处,1962年拍摄《圣女贞德的审判》(罗伯特·布列松,1962)时,他也让演员一遍遍地重复同一个镜头,直到他们完全融入角色本身,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展现以供解读的情绪中挖掘人类精神极限的状态。他在《电影书写札记》中提出,导演应该具备对现实敏锐的感知和识别能力,不要试图用激动人心的画面去试图抓住眼球,而要像画家一样,用画面中的微妙关系使普通的画面变得既生动又感人。“要孤立这些部分。让它们各自独立,以便赋予它们一种新的依赖性。只有使用你的清晰和精确,才能强制吸引人的眼睛和耳朵的注意力。一位高手不是让我们听到写下的音乐,而是让我们听到他所感受的音乐。对同一物品作多个取景,就像画家那样对同一个主题画几幅油画或画几幅素描,而画家每一次都会向准确靠近一步。要有画家的眼光。画家一边观察一边创造。画家眼睛那犀利的风钻,能拆开现实。然后画家会重新组装,用同样的眼光去组织,按他的爱好、方法和理想的美感去组织。”[4]这也是为什么绘画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标题为《一个年轻女子的肖像》《一个画家的肖像》等作品的原因。这些标题表明作品所描绘的个体身份和特征,但这些身份和特征并不是由模特的外部形象所决定的,而是由创作者所捕捉到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它也是理解肖像化形式的重要图景,也是基于现代文化对人身份作出指涉的必然结果。在将人物处理为肖像的过程中,角色自主指涉性的身份与形象图像身份彼此之间逐渐靠近并融为一体。
现代的主体逻辑与肖像化的逻辑一样,都是通过画面中的差异与冲突产生意涵与视觉张力的。即便在一部电影无人观看的情况下,其内在结构依然维持着为观众预留的空间,其中运动影像持续展现并流动不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与肖像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生》(吴天明,1983)和《黄土地》(陈凯歌,1987)中,高加林父亲高玉厚、翠巧爹的形象塑造就与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有着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外貌和神态上,还体现在人物的性格和气质上。《父亲》作为一幅表现中国农民的油画,通过极度写实的方式深入刻画农民的形象和性格,面容中黝黑的皮肤与洁净的羊肚毛巾、深刻的暗色纹理与汗水反射的光泽之间形成鲜明的冲突感,传达出中国农民当时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这种深入刻画的风格对后来中国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由其被捕捉到的个性特征所决定而非由角色单纯的外部形象所决定。人们可以清晰地在中国电影中辨认出其与人物肖像画的亲缘关系。“从常用的人物肖像、物品肖像等范畴中可以看出,肖像不是只表达人、事、物的存在,也不是只表达事物的外形,而是表达事物本身的、事物的现象与事物的本质的统一,是一种作为人类认知结果出现的形态。”[5]电影中的肖像画不仅展现了一种以人像为中心的绘画样式,通过视觉手段与特定的人物相呼应传达被画者的个性特征;还要展现出创作过程中超越画中人表面的形象以及真人与绘画相似性,在追求形似的基础上理解和表现被画者永恒的情感状态和气质。
银幕的注视构成真实的观看体验。这种注视使得银幕从原先的象征性符号转变为不可触及的真实。电影中的肖像与面容指向一个无法被占据的位置,并非源自电影理论所形成的无法实现的理想,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本质上的不可能实现的真实。在前者的情况下,人们期待在注视的焦点处找到一个明确的所指,而在后者中,即便是缺席的主体也是不存在的。简而言之,主体无法将自己置于这个注视点,因为这个点恰恰是主体身份的象征。当注视被意识到时,影像的视觉效果转变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差异,它失去了原本属于我的面貌,转而扮演起银幕的角色。
三、身份与媒介:他者身份与特征的建构寓言
指涉性的身份图像与其模特相关,而兼有指涉性与非指涉性的肖像画则与自身以及与作为他者的自身相关。肖像的绘画形式并不追求对形象本身进行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捕捉形象内在的精神气质和个性特征,将其转化为一种专有名字的形式。例如《燃烧女子的肖像》(瑟琳·席安玛,2019)中,影片以一位画家为爱人艾洛伊兹画下的三幅肖像展开,古典油画质感从颜色到构图屡屡让人屏息。第一幅画像由画家凭记忆作画,尽管还原了指涉意义上的容貌却有形无神,孤岛般的氛围仍显孤寂;在两人相互了解后,第二幅肖像画终于神情兼备;而第三张画作则是超越了二人短暂的恋爱关系、令片刻的激情成为永恒的创意之作:在母亲与主顾回家之前,篝火堆两侧的二人望向对方的目光专注到失神,被画者艾洛伊兹的裙子甚至被火焰点燃而不自知,只有在火光中注视画家的坚毅脸庞。他们通过彼此的目光与目光中蕴含的爱意确认此时自身的存在,既作为被爱者又作为爱人之人,爱情的火焰与生命的激情在这一场景中熊熊燃烧。对于形象自身的身份来说,“年轻女子肖像”或“艾洛伊兹肖像”在形象之外被给予的身份并不是最后或最初的定论,于平静中“燃烧”的冲突气质才是这幅肖像绘画的要旨,这展现了差异化与冲突性的现代主体建构逻辑;而二者辨认对方、建构自身的方式又是通过肖像画实现的。
在电影中,肖像画的本质脱离了对目标人物的相似描绘,通过绘画手段将个体精神和个性特征表现出来——尽管这些特征并不一定与模特的外部形象完全一致。观看的目光在影像的画框与肖像画的画框之间反复游移,让电影与绘画一起构成一个以他者身份建构自身的寓言。
银幕的真实注视不仅使观影者遭遇主体性解构,而且在本体论层面上是“显示”,同时“侵入”与瓦解。电影艺术的最终形成不是在于一个叙事性的虚构中重新创造现实,而是促使人们自身察觉现实自身的虚构面向,去体验一个虚构的现实自身。“电影实质上内含一个结构性的自我抗争,两股力量分别是一观影者头像,银幕的对象化注视于想象性注视与银幕返回来的真实注视,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这场对抗就是符号之域与想象之欲同真实之欲的对抗,使之变成符号之域的隐晦补充,并将重心转移到真实之域,意识形态现实秩序符号性秩序加以幻想地打开。”[6]电影拍摄和剪辑隐藏了摄影机与拍摄过程的存在,符号领域与想象领域两者的力量日渐增长成熟,通过技术进行缝合使银幕的注视不再能穿透出来。但电影中的肖像描绘却在将想象与符号加以缝合的过程中令实在界散逸而出。《爱丽丝》(杨·史云梅耶,1988)全片通过频繁展现爱丽丝的嘴唇特写与旁白中的自述来叙述整个故事,爱丽丝的行为在这个荒诞的梦境中变得毫无逻辑和随性,她不断地饮下墨水、食用可变大变小的饼干,似乎完全摆脱了常规的限制和约束。影片开始之前,爱丽丝作为影片中唯一真实存在的人物提醒观众要睁大眼睛观看,否则将“一无所见”;然而实际上是一句以符号否定象征秩序本身的“反话”,因为梦游仙境的爱丽丝与其所见梦境本身就是一种反现实的想象存在,预示着接下来荒诞不经的故事即将上演。为了避免对梦境世界的“客观”描述,影片中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在特写或者近景中实现。除了核心角色爱丽丝外,影片还展示了两个非典型的“人物”肖像:一只模仿人类婴儿哭声的猪,以及一个表现得如傀儡般的姐姐。姐姐与爱丽丝共同坐在湖边,然而她的行为却异常静止,甚至连手中的书本都未翻动。当爱丽丝完成扔石子的动作后,姐姐依旧维持原状,直至爱丽丝试图翻动她的书本,导演通过独特的切头画面揭示了姐姐的真实身份——她并没有头部,只是以僵硬的动作象征性地与爱丽丝互动。这一场景中的姐姐角色并未在影像中以常见的头部肖像形式描绘出来,导演对其“面容”的描绘却展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反应,在可见的容貌外为观众打开了一片空无的、令人不忍直视的领域;而“目击”一切的爱丽丝眼神中则透露出幽怨,本应投向湖边或姐姐的目光却异常地转向了镜头外的观众,以直接对镜头的凝视打破了影片“缝合”的叙事边界。随后,镜头转向爱丽丝的房间,继续以油画中景物特写般的方式对房间内的每一个角落进行详尽的展示:被啃食过的苹果核、散乱摆放的积木、破损的玩具、装有墨水的瓶子以及设置着奶酪的老鼠夹等,共同散发出一种衰败气息的物品与儿童房应有的活泼和色彩形成鲜明对比。镜头最终定格在两个与爱丽丝和姐姐外貌完全一致的洋娃娃上,其中一个洋娃娃的特写镜头揭示了其脸部特征以及裙摆上放置的石子,暗示着这个娃娃是“变小”后的爱丽丝的象征。此处外观完全一致的娃娃也突出了故事角色的“非人”特性,与他们重复的动作共同赋予角色一种僵硬的生命感,进而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梦境中营造出一种单调乏味的氛围。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一切传统的意义和价值观念都被颠覆,只剩下重复和混乱作为主导。作为杰克新浪潮的灵魂人物之一,杨·史云梅耶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隐喻性和象征意义而著称。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手法,他以荒诞和奇幻的形式表达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类内心的深刻反思。
肖像与电影的“他者”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在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与肖像画的关联之外,还有电影与绘画作为不同媒介画面风格与肖像画的相似性。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另辟蹊径从肖像学的角度找到中国导演与中国当代美术,特别是与人物肖像画之间的关联性,并提出新中国电影导演得以在艺术观念上获得成为“一代”电影新人的理由与当代美术的人物肖像画之间息息相关。在中国第四代与第五代导演创作的电影中,可以看到电影画面风格与西方油画肖像画的相似性。例如《老井》(吴天明,1985)中,剧中人物围坐桌前吃土豆的场面就带有肖像绘画的影子,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画面布局、色彩运用以及光影处理等方面。[7]油画的绘画风格以其独特的色彩运用和光影效果而著名,这种风格在《老井》中被巧妙地运用到电影故事中,在强烈的明暗对比与高饱和度的色彩下显示出西北农民强劲有力的身体与蓬勃待发的生命力。中国导演不仅成功地融入国际化视野和趣味,而且通过历史性的创作实践,自觉地总结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色彩运用手法,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对‘崇高和‘壮美的追求,也能在吴天明电影和长安画派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印证。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和刘巧珍确定恋爱关系后,曾一度穿上陕北庄稼汉的衣服,站在黄土高坡上远望,壮美的山川尽收眼底,其画意与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作于1959年的《转战陕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8]借助“绘画”尤其是“肖像画”中描绘人物的方式,一代代中国导演在继承传统绘画人物描绘方式的基础上与电影艺术相互对照,最终将这一“他者”形式以“形象”或“肖像”的方式应用于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之中。
结语
综上所述,从艺术史、电影史和身体美学的跨学科视野出发,电影中相对于那些将自己装扮成绝对理性或绝对意义的肖像形式来说,肖像化形式实际上是在自身的非意指性中那个专有名字的形式。在中国电影中,将人物肖像化后的形式是一种对具有领导力的“英雄式”的人物形象的召唤,展现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定的信念,并打破了对现代化转型时期审美理想的反思,引领时代向前发展。中国电影中的肖像式人像,实际也是对传统审美观念的挑战和突破,以及对新的审美标准的探索和尝试。
【作者简介】 郭琳媛,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口语传播、影视融媒与文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