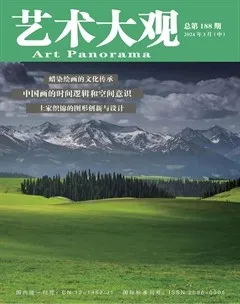中国画的时间逻辑和空间意识
2024-06-09姚煜
姚煜


摘 要:邓以蛰和宗白华分别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对中国画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炼出“体—形—意—理”“生动—神—意境—气韵”与以大观小的空间观照、书法的空间感型和诗性的空间。尽管两人的研究视角、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各自不同,但在最终又同归一处——指向心物交感和天人合一。
关键词:邓以蛰;宗白华;绘画美学;时间逻辑;空间意识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05(2024)08-000-04
中国画在世界绘画之林独树一帜。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中演绎出明确的时间逻辑;另一方面基于东方地域和文化土壤,形成了独特的空间意识。
一、邓以蛰:“画史即画学”的时间逻辑
“体—形—意—理”与“生动—神—意境—气韵”是邓以蛰立足于中国画史的发展形态,并汲取西方著名美学家黑格尔与克罗齐等人的美学思想,建构起的中国绘画美学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明确地揭示出了中国画发展的时间逻辑。
邓以蛰在《画理探微》中有一段论述:“艺术因自身之发展而有种类,大别之,有三,曰体,曰形,曰意是也。体者为一切工艺及建筑之领域也。以物质之体积、重量、颜色为要素造作之,以适合器用于美感者也。故艺术之体终非天然物体之体。形者脱于物质之拘束,而以物理内容(生命)为描写之对象者也。形者画也,欧阳之论画言难画之意,难形之心,是形与画相通也。画事异于体之造作而始于生命之描写,故形以禽兽人物画为始也,而雕刻为介在‘形‘体之间之艺术,因其描写生命而犹造作物质也;不过物质之诸种特性又不能拘束其形焉耳。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直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词之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胸具丘壑,挥洒自如,不为形似所拘束者为山水画之开始。至元人或文人画则不徒不拘于形似,凡情境、笔墨皆非山水画之本色,而一归于意。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此就艺术之发展以寻其根本原理而言也。”[1]在此,邓以蛰把中国画的历史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是“以物质之体积、重量、颜色为要素”而創作的“体”的艺术;二是“以物理内容(生命)为描写之对象”的“形”的艺术;三是“直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而又“不为形似所拘束”的“意”的艺术;四是“归于意”,以表现“气韵”为能事的“理”的艺术。[3]换言之,邓以蛰认为中国绘画在时间维度上大致经历了“体—形—意—理”四个不同的阶段。其中,“体”的艺术大约在商周时期,亦谓之“形体一致时期”;“形”的艺术大约在秦汉时期,亦谓之“形体分化时期”;“意”的艺术大约在魏晋到唐代,亦谓之“形净时期”;“理”的艺术大约在唐以后,亦谓之“形意交化时期”。
如果邓以蛰仅是从史学角度揭示中国画的发展轨迹的话,尚不能说明他在艺术美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真正使得邓以蛰的研究呈现出超越性意义的地方在于,他从史学视域总结出“体—形—意—理”结构的同时,还从美学视域提炼出了中国绘画不同时期的审美追求:“生动—神—意境—气韵”。
“生动”是邓以蛰对“形”的艺术时期的审美境界的概括。邓以蛰说:“六法首重气韵生动;生动,人之本体,若使生动能入画,必缩朝暮春秋之变动于一瞬之静然后可。得动之一瞬之静,画家谓之得神。”[1]因此,画家只有“得动之一瞬之静”,方能达到“生动”的审美境界。此处,需要注意的是,邓以蛰并没有从“体”的艺术时期就概括其对应的审美追求。因为在邓以蛰看来,“体”的艺术尚未摆脱器体的束缚,没有进入相对自由的境地,因此也就没有形成明确的审美追求和典型的审美境界。只有在秦汉时期,绘画艺术开始“体”“形”分化。进入“形”的艺术之后,画家多以人物与动物为表现对象,才出现了“因转而拟生命之状态,生动之致,由兹而生矣”[1]的境界。可见,“生动”境界的形成与人物画、动物画有着莫大的关系。邓以蛰说:“夫生动者,乃缘生类之有动作也。”[1]当然,除了艺术表现对象发生变化之外,造成“生动”审美追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楚风”的影响。邓以蛰说:“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1]
中国绘画发展到“形净时期”,艺术家开始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为旨趣,于是,对人物内在“神”的追求代替了对“生动”的追求。邓以蛰认为:“汉代艺术,其形之方式唯在生动耳。生动以外,汉人未到。故其禽兽人物,动作之态虽能刻画入微,但多以周旋揖让,射御驱驰之状以出之,盖不能于动作之外有所捉摹耳。又其篇幅结构,徒以事物排列堆砌,不能成一个体,虽画亦若文字之记载然,观于石刻中每群人物,注以名位,水陆飞动,杂于一幅可知也。汉以后乃渐趋纯净,虽曰佛教输入,于庄静华丽之风不无有助,但人物至六朝,由‘生动入于‘神亦自然之发展也。神者,乃人物内性之描摹,不加注名位而自得之者也。”[1]此处,邓以蛰准确地抓住了汉代到六朝时期,中国绘画发展的重大转变及其美学特征——“汉取生动,六朝取神”。如今,这一思想已成为美学界的共识。
意境的内涵要复杂一些。一方面与“神”一样,“意境”也是“形净时期”艺术家的审美追求。不同的是,人物画、动物画主“神”,山水画主“意境”;另一方面邓以蛰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认为“意境”是“生动”与“神”的统一。他说“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1]这就意味着从逻辑关系上讲,“意境”又在“神”之上。所以,“意境”的内涵既有与“神”平行的一面,也有超越“神”的一面。
中国绘画直到发展到“理”的阶段,追求“气韵”为目标时,才算是达到了“画事发展之晶点”。而所谓“气韵”到底所指为何呢?邓以蛰说:“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1]“艺术自其‘体逐渐以进于‘理;斯理也,实即气韵生动之谓也。”[1]综上,不难得出邓以蛰的观点:气韵即理,理即气韵。至此,两个表里相依的逻辑框架合流归一了。
概而言之,“体—形—意—理”是史学的,“生动—神—意境—气韵”是美学的,但两者又都是基于“时间”线索的,一体两面,互为表里。他继承前人从“时间”维度研究中国画的视角,又基于“时间”维度提出了美学层面的创见,并将两个维度有机统一,殊为难得。他用自己的理论表征出中国艺术美学的根本特质:“我们的理论,照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绝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1]这正体现出了邓以蛰学术研究的超越性意义。
二、宗白华:从以大观小的空间观照到诗性的空间
宗白华以象与数为经纬,建构了一个生生不息,异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本身就包含着时空的观念。此外,在《形上学》中,宗白华又专设“鼎卦:中国空间之象”及“革卦:中国时间生命之象”两节,专门讨论了时空问题。
由此可见,宗白华对中国画空间意识的研究,一方面是建立在其哲学探究之上的;另一方面他所探讨的“空间意识”始终伴随着“时间”的维度。但是比较而言,宗白华在中国画空间意识方面的研究,最为世人称道。宗白华通过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画的空间意识做了深入的探讨。
第一,以大观小的空间观照与焦点透视的空间观照。中西两域有着不同的宇宙观。西洋人重视宇宙形象里的数理和谐性;而中国人最根本的宇宙观是:“一陰一阳谓之道。”中西不同的宇宙观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家的空间观照方式。正如宗白华所言:“中画、西画各有传统的宇宙观点,造成中、西两大独立的绘画系统。”[2]在宗白华看来,西洋画家将焦点透视发挥到了极致。他说:“西洋人站在固定的地点,由固定的角度透视深空,他们的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2]但是,中国画家则用心灵之眼,笼罩全景,采取以大观小的空间观照方式。“画家的目光不是从固定的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全景的阴阳开阖、高下起伏的节奏。”[2]这种观照方式以“三远法”最为典型。“由这‘三远法所构的空间不复是几何学的科学性的透视空间,而是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2]中国画家通过“三远法”,视线由高而深,由深转近,再横于平面,流动转折,富于节奏,表现出“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2]空间意识。
第二,书法的空间感型与建筑、雕刻的空间感型。宗白华认为:“每一种艺术可以表现出一种空间感型。”[2]西方艺术的主要基础在希腊,而希腊艺术以建筑和雕塑为代表,两者共同追求“静穆的单纯,高贵的伟大”。这个因素支配了后来兴起的西洋绘画,所以西洋画表现的是偏于建筑、雕刻的空间意识。而中国画则是基于书法的空间表现力,因为书法的线条结构都会占据一固定的空间。作书时,各种笔画单元自然结成,字距、行距、气势、章法等应运而生,最终建构出一个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和空间单位。所以,“在这样的场合,‘下笔便有凹凸之形,透视法是用不着了。画境是在一种‘灵的空间,就像一幅好字也表现灵的空间一样”[2]。宗白华曾以八大山人的作品为例,说画面虽只用寥寥数笔表现了一条鱼,却觉得满纸江湖,烟波无尽,生动至极。可见,基于书法空间感型的中国画就像是一条生命之流,不仅具有形线之美,而且在笔走龙蛇的过程中,极尽生命的律动。是故,“而引书法入画乃成中国画第一特点”[2]。
第三,科学的空间与诗性的空间。中西两域不同的哲学文化基础,深刻影响了中西绘画不同的空间观照方式和空间感型,并最终铸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意识,即:西洋画的科学空间意识和中国画的诗性空间意识。西洋画以建筑和雕刻为背景决定了它特殊的路线和境界。就路线而言,西洋画重视理性与科学,力求合理真实的空间表现,强调透视学、解剖学的运用。画面在一个透视的空间里,由近至远,层层推出,趋于无限,却无法回环;就境界而言,“西画以建筑空间为间架,以雕塑人体为对象,建筑、雕刻、油画同属于一境层”。[2]但是这种科学的空间意识终究是物我两分,对立抗争的,所以西洋画“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如镜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则其真愈幻。逼真的假象往往令人更感为可怖的空幻”[2]。但是,中国画展现出的是诗性的空间意识。在中国画中,生命与物推移、纵身大化、血脉融入。画幅的意趣,是回旋往复的,画面的空间意识借助虚实而流动的节奏表达出来,体现出鲜明的音乐感和舞蹈感。正如宗白华所言:“饮吸无穷空时于自我,网罗山川大地于门户。”[2]因此,“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意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一境层”[2]。至此,科学的空间意识与诗性的空间意识在画面中的本质性差异得以体现:“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2]
三、殊途同归:心物交感与天人合一
邓以蛰和宗白华站在古今文化交汇、东西思想交融的十字路口,为中国艺术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和当代艺术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仔细分析,两人的研究视角、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有着鲜明的不同。邓以蛰出身于书香门第,其远祖就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家学渊源的优势使得他对中国绘画本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和深入。事实上,邓以蛰在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书画美学上。他早年受家藏的惠泽,晚年又以对完白山人的研究而结束自己的学术生涯。应该说,书画研究贯穿了他的一生。所以,他在书画美学领域用力最多,功力极深,见解精微。在研究视域上,邓以蛰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不同——都是在时间维度中对中国画进行考察的,但是他超越性的价值在于:他在美学的意义上,建构起了中国绘画美学的基本框架:“体—形—意—理”和“生动—神—意境—气韵”,就明确地揭示出了中国画发展的时间逻辑。比较而言,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则体现为一种对中国艺术的宏观把握,他学术研究的视野更加宏阔,其学术成就亦不局限于书画美学一域。也正是因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他才能抓住中国画的“空间意识”这一极其重要又特别新颖的研究视角,并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刘纲纪曾总结说:“宗白华主要从美的欣赏的角度对中国书画作一种感性直觉的把握,从体验中展现书画的美的特征,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揭示中国艺术同中国古代哲学的密切联系……邓以蛰在中国书画的史料考证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史与论要密切地结合起来,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优点在于‘永远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画史即画学,绝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同时,形成我们民族极深刻、极细腻的审美能力。”[1]概而言之,邓以蛰的研究得其专,能遵循前辈的脚步“照着讲”,更能超越前辈“接着讲”,体现为一种拓展之功;宗白华的研究得其博,在广博的视野中,寻求新视点,探索新颖处,开始“重新讲”,体现为一种开山之功。所以,两人的研究各具特色,各领千秋,此之谓:殊途。
而与此同时,两位学者身处相同的社会时代语境,耕耘于相同学术领域,都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都面临着中国传统学术现代性转换的重大命题。因此,他们的研究又在另一重意义上呈现出诸多的共性:如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研究对象都聚焦在中国艺术最具代表性的门类——绘画;在研究立场上,两人都立足于中国绘画的实际状态,注重挖掘自身文化与艺术的价值,洋为中用,又借古开今;在研究视野上,两人都融中西于一炉,汇古今于一体,采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而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探究出了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主客二分、物我对立的根本特质,即:邓以蛰绘画美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心物交感”思想和宗白华绘画美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4-5]。
王有亮在总结邓以蛰美学思想时,说道:“更为重要的是,从邓以蛰提炼出的理论结构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如果说邓以蛰的美学思想有什么‘完整的系统性的美学理论的话,那么,‘心物交感就是邓以蛰美学思想之根本。邓以蛰的美学是‘心物交感论美学。”[3]也就是说,邓以蛰美学思想的根本特征是“心”与“物”能够彼此感应,达到统一。借蒋孔阳的话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的创作,就是要沟通‘心与‘物,把‘造化与‘心源统一起来。在统一当中,关键在画家的‘人。”[6]这种思想,在宗白华那里也能找到相近的表达:“中国画的作者因远超画境,俯瞰自然,在画境里不易寻得作家的立场,一片荒凉,似是无人自足的境界。然而中国作家的人格个性反因此完全融化潜隐在全画的意境里,尤表现在笔墨点线的姿态意趣里面。”[2]宗白华的这段阐述,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人合一。但不管是邓以蛰的“心物交感”思想,还是宗白华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实质上都是对西洋画中主客二分、物我对立的超越,进而揭示出了中国画与物推移、纵身大化、物我浑融的合流境界。此之谓:同归。
四、结束语
无论是邓以蛰提出的“体—形—意—理”和“生动—神—意境—氣韵”,还是宗白华提出的以大观小的空间观照、书法的空间感型和诗性的空间,都在不同维度上对中国画本体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但是,研究中国画,时空两维,缺一不可。因为中国画的本质属性和审美特质,是在流动的时空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只有综合邓以蛰与宗白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加全面和立体地把握中国画本体。而在梳理两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也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两人绘画美学思想的异同——尽管两人的研究视角、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研究的落脚点,又同归一处:那就是呈现出了“心物交感”与“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从根本上区分出了中国画与西洋画的不同,深得中国画的本质特征,从而彰显出了两人在中国画领域研究的典范意义。
参考文献:
[1]邓以蛰.邓以蛰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2]宗白华.宗白华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3]王有亮.“现代性”语境中对的邓以蛰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冯晓.中国画艺术的宇宙意识[J].文艺研究,1998(04):107-113.
[5]张生.“领悟”中国文化的“最深的灵魂”——宗白华的“空间意识”与李格尔的“艺术意志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04):65-82.
[6]将孔阳.将孔阳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