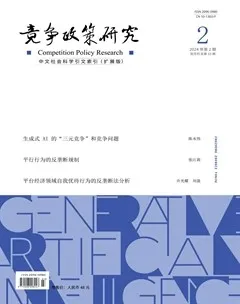平台经济领域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
2024-06-07许光耀刘盈
许光耀 刘盈
摘要:平台经济领域的自我优待行为因其呈现出的新颖外观而备受关注,但目前学界并未能就对其采用何种分析方法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通过分析谷歌比较购物案和亚马逊黄金购物车案中自我优待的行为方式发现,该行为只是在歧视方式上与传统的差别待遇行为存在不同,本质并未改变,因而反垄断法中关于差别待遇行为的理论与规则仍然适用。欧盟委员会对这两个案件的调整过程也印证:(1)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传统的需求替代性标准并未受到挑战;(2)在支配地位认定方面,以市场份额为首要因素的传统方法仍然适用;(3)在竞争效果考察中,仍需要关注优待行为排斥下游竞争的效果;(4)在行为效率考察中,仍由当事人提出合理理由进行抗辩。
关键词:平台经济;自我优待;差别待遇;双边市场
一、引言
平台经济的兴起给反垄断法带来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已成为各国反垄断法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平台经济领域出现的各种所谓新型垄断行为,人们在其定性和分析方法上都存在严重争议,其中平台企业所从事的“自我优待行为”是最受关注的类型之一,针对其调整方法的讨论始终无法达成有效的结论,甚至对其性质亦无法达成共识,有学者将其定性为拒绝交易行为,有学者将其定性为差别待遇行为,也有学者主张将其定性为新型垄断行为。但这些讨论大都脱离了反垄断法上既有的理论与规则。如果紧密依托当事人的行为过程,以及反垄断法的基本法理进行深入分析,则可以发现这些行为大都属于传统的行为类型,其中自我优待在性质上属于传统的差别待遇行为,应适用关于后者的调整方法,反垄断法的传统规则与理论并未受到挑战。而国内外现有研究大多过于关注行为在外观上的特点,将讨论引向非本质的方向,相比之下,实务反倒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欧盟委员会的谷歌比较购物案(以下称“谷歌案”)和亚马逊黄金购物车案(以下称“亚马逊案”)不仅很好地展示了自我优待行为的运行方式,而且其处理结果及论证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比较的良好素材,应当认真进行研究,并从中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
二、自我优待行为的运行方式及性质
(一)从典型案件看自我优待行为的运行方式
欧盟委员会有关平台经济领域自我优待行为的执法实践,始于谷歌案,发展于亚马逊案。在这两个案件中,当事人的行为过程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自我优待行为的运行方式。
1.谷歌案中的自我优待行为
谷歌通过其搜索引擎平台“Google Search”,为内容提供商与终端用户提供一般搜索平台服务。作为平台内的下游经营者,内容提供商借助谷歌平台,将其商品或服务以文字、图片等形式呈现在网站上,供终端用户搜索和浏览。当用户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谷歌会迅速索引相关内容,按一定标准进行打分排序后,再以蓝色链接反馈搜索结果。由于用户通常只会点击搜索结果第一页上排名前十的链接进入网站浏览所需内容,因此排序的先后直接关系到内容提供商们获得交易机会和潜在收益的数量,所以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排名顺序。
谷歌在2011年以前主要根据商家的网页被链接的得分情况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其打分的基础是该网页被其他网页链接的次数,同时还考虑对其进行链接的其他网页的质量,并据此赋予不同的权重。后来,谷歌引入熊猫算法(Panda algorithm),又增加以下考察因素,包括网页内容的原创性、网页内容与搜索指令的相关性以及网页内容中广告的占比等,其中最重要的考察因素是其原创性。有些网页的内容是由网页所有人自己创作,比如生产商介绍自己产品信息的网页,其内容均由该生产商所填充,此类网页被视为具有原创性;而有些网页的内容主要来自对他人网页内容的复制或转载,则被认为原创性低。依熊猫算法,对非原创性链接,降低其分值。因此在被链接的次数相当的情况下,非原创性网页的得分较低,在搜索结果页的排名靠后。
在线比较购物服务(以下称“比价服务”)位于一般搜索平台服务市场的下游。这种服务主要是將同类商品的不同经营者的信息(包括价格信息)汇集在自己的网页上,便于消费者进行价格比较。由于这些信息大都来自对各该经营者网页内容的复制,因此比价服务提供者的网页原创性较低,得分不高。但对于其自营的比价服务,谷歌却不采用熊猫算法,其后果是,谷歌的比价服务网页被看作是原创性的,尽管这些网页与竞争者的同类网页一样,其内容主要来自对他人信息的复制。这使其得分远远高于其他比价服务提供商,在搜索结果页上长期居于第一位。
谷歌的自我优待行为还不限于此,在搜索显示方面,它还为自营业务在搜索结果页的顶部或右侧的空间中预留可以附带图片、价格等丰富信息的突出显示位置,以更好地吸引用户注意力,而其他人的比价服务则不享有此项待遇。
基于谷歌在上游搜索平台服务市场采取的上述自我优待措施,下游比价服务市场上的用户流量大都流向了谷歌自营的比价服务,其在欧盟各国的用户流量分别增长了14倍至45倍。
2.亚马逊案中的自我优待行为
亚马逊经营着“Amazon Marketplace”电子商务平台,为在线零售商和终端消费者提供虚拟交易场所及附属的平台服务。亚马逊在其平台推出黄金购物车(Buy Box)计划、特定推荐(Featured Offer)计划、Prime会员计划,这些计划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的购买条件,被纳入计划的零售商将得到消费者优先选择。根据调查,亚马逊平台上超过90%的销售额来自消费者对黄金购物车中商品的购买,其中,超过70%的销售额来自消费者对黄金购物车中特定推荐商品的购买。此外,“Prime”会员买家作为购买主力,超过70%的平台销售额是由“Prime”会员买家创造的。因此,所有零售商都希望加入上述计划,目的是使其商品被纳入黄金购物车,成为特定推荐商品,并获得“Prime”标签,以吸引“Prime”会员购买。
然而零售商加入上述各项计划的条件是,必须同时使用亚马逊自营的物流服务。亚马逊将其平台内的零售商区分为两类:(1)AFN零售商,指使用亚马逊自营物流服务的零售商,包括其自营的零售业务,也包括第三方零售商;(2)MFN零售商,指不使用亚马逊物流服务的第三方零售商。对AFN零售商,亚马逊不仅始终默认其有进入黄金购物车的资格以及获得“Prime”标签的资格,而且为其设置的进入特定推荐计划的门槛更低;对于MFN零售商,则采用更高的门槛,也就是说,亚马逊作为平台经营者对MFN零售商与AFN零售商实行差别待遇,使得后者在下游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使前者受到严重排斥:2017至2020年间,在亚马逊平台内所产生的零售额中,AFN零售商的比重超过90%,而MFN零售商只占不到10%。
(二)自我优待行为的定性
有学者认为,自我优待行为有两个核心特点,其一是双重身份下平台自治权的扩张,其二是数据市场竞争优势的跨界传导,这两个特点导致该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涉及平台竞争优势利用和经营自主权的边界问题,因此需要以审慎态度对其进行处理,而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方法存在适用困境,应借鉴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第19a条的思路,增设独立条款,围绕“平台是否将其市场势力传导至另一市场来排除或限制竞争”这一核心命题建立新的分析框架。但这一观点并未对德国法的上述规定进行必要分析,也没有阐明传统方法在分析“传导”效果上存在怎样的缺陷。实际上,传统反垄断法对于各种传导型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如搭售、拒绝交易、差别待遇均有成熟的调整方法,未必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
也有学者将其定性为拒绝交易行为,并认为谷歌不向竞争性比价服务提供与自营业务同等的条件,应视为谷歌拒绝与第三方交易的行为。这也是谷歌案中,谷歌公司本身的抗辩思路。但反垄断法上的拒绝交易是指行为人不向相对人提供交易机会,从而阻断相对人进入下游市场的途径,后者并不在下游市场出现,而在谷歌案中,谷歌并不试图阻止比价服务商们进入该市场,它只是抑制其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平台运营的特点决定了其经营者一般不会产生拒绝的企图,因为只有容纳大量商家,平台才能对终端消费者产生吸引力。既要将竞争性比价服务的商家留在平台内,又要对其进行排斥,那么平台经营者选择的手段只能是差别待遇,而非拒绝交易。这两种行为均旨在对下游竞争者进行排斥,以使其在上游的支配地位传导到下游,其区别主要在于排斥的程度不同。
从两个案件所展现的行为方式来看,自我优待行为存在三个明显的特点:(1)行为跨越上下游两个市场;(2)对同等交易中的不同客户采用不同的交易条件;(3)其竞争效果是对下游市场上的竞争者产生排斥。这正好对应着差别待遇的构成要件,因此并非新型的行为,也不是拒绝交易,而应当采用差别待遇行为的反垄断分析方法。
1.行为跨越上下游两个市场
自我优待行为跨越两个市场:当事人自身是上游平台服务市场的经营者,在谷歌案中,是指一般搜索平台服务市场,在亚马逊案中,是指在线零售平台服务市场;而下游商家则在这一平台内从事下游业务的经营,这些下游业务构成下游市场,在谷歌案中,指比价服务市场,在亚马逊案中,指在线零售市场。一般说来,平台希望下游商家之间存在有效的竞争,而不希望其中一部分商家拥有市场力量,从而对平台自身造成威胁。因此平台通常没有对下游经营者即商家采用差别待遇的动机。
但如果平台本身也进入下游市场从事经营,其下游业务将与商家之间相互竞争。这种情况下,对下游商家进行排斥可以使自己受益,因为这可以为自己的下游业务获得更多交易机会,并由此获得在下游市场上的支配性力量。在谷歌案与亚马逊案中,当事人的行为动机便是如此。
2.对同等交易的不同客户采用不同交易条件
首先,差别待遇的对象是“同等交易”的不同相对人。所谓同等交易,归根结底是指交易成本相同。平台经营者的交易相对人是下游业务的经营者,包括其自营业务以及独立的商家。平台对二者提供平台服务的成本相同。谷歌和亚马逊作为平台经营者,提供平台服务的成本主要由前期建设和后期维护的投入所构成,这些成本并不由个别交易单独承担,而是由所有的交易分摊,因此每一笔交易所承担的成本相同,即单位成本不因相对人的身份差异而有所不同。
其次,平台对不同相对人采用不同的交易条件,这将导致他们在下游市场无法拥有平等的竞争条件。在传统產业中,歧视待遇大多表现为价格歧视,即对同等交易的不同相对人采用不同的价格,由此导致在下游的竞争中,受到歧视的相对人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但这两个案件中,当事人所采用的则是价格以外的歧视方式:谷歌案中,歧视的方式主要是计分方法上的差异;亚马逊案中,则对不同零售商采用不同的进入门槛,最终使其所获得的经营条件差异巨大。
3.对下游市场的竞争性结构产生破坏
差别待遇可能产生的主要反竞争效果,是行为人利用其在上游市场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在下游市场排斥竞争者,最终破坏该市场的竞争性结构,为行为人带来支配地位,即将其在上游市场的支配地位传导到下游市场。由于同平台交易的成本相同,得到偏袒的经营者将在下游市场获得竞争优势,而受到歧视的下游经营者则将受到排斥,并且一般来说,这种优势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因此后者最终将无法在该市场上生存下去,或最多维持边缘化的生存。比如在谷歌案中,搜索结果第一页之外的搜索链接所能得到的交易机会只有不到5%,而在亚马逊案中,MFN零售商的交易机会也仅有4%。如此有限的交易机会无法对谷歌或亚马逊造成竞争压力。可以看出,采用差别待遇的调整方法完全可以容纳对于“传导效果”的分析,并不需要借助新的条文设计,而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关于优待行为的规定也应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该条并不是新的设计,它只不过是对传统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分析方法的重申。
综上所述,自我优待完全符合差别待遇的构成要件,并不构成新型垄断行为,与传统的差别待遇相比,其主要差异在于歧视的方式不同。在传统产业中,差别待遇主要体现为价格歧视,但也并不排除在其他交易条件上制造歧视,例如在付款方式上,只允许某一买家分期支付,而要求其他买家全款支付。但线上平台的出现给当事人提供了新的歧视手段,例如在商品排名或者图文显示上歧视相对人。这些手段在传统产业中不会出现。以亚马逊案为例,传统的线下商场对商品进行展示的方式是将同类商品陈列在同一货架上,线下消费者通常可以一览无余,其购买意愿并不由商品陈列的先后决定,在同一排货架上,哪一种商品摆放在前并不带来交易机会上的明显优势,因此经营者无法采用排序的方式来排斥竞争者,为下游自营业务带来优势。而线上平台则不同,由于终端消费者的注意力通常只停留在排序靠前的网页上,因此排序先后可以构成不同的交易条件。自我优待行为的新颖性仅在于这种技术性的外观特征,而这些技术性特征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而无须将其定性为新型垄断行为。
三、谷歌案和亚马逊案的处理结果及其论证过程
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分析过程一般有三个步骤,即支配地位的认定,当事人行为竞争效果的考察,以及行为效率的分析。在该案的审理中,欧盟委员会的分析过程遵循着这一框架,并在这一基础上,企图顾及这两个案件中当事人的“平台”特征。通过对其论证过程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些考虑并无必要。实际上在这两个案件中,并未出现主流研究中赋予平台的那些特点。
(一)谷歌案的处理结果及其论证过程
1.界定上下游两个相关市场
本案中,欧盟委员会依据需求替代性标准,界定了上下游两个相关市场:将上游市场界定为一般搜索平台服务市场,将下游市场界定为比价服务市场。每个市场的界定过程中,首先明确需求的内容,然后对类似产品进行考察以判明其替代性状况,这与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并无差异。
2.支配地位的认定
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在上游一般搜索平台服务市场拥有支配地位,理由如下:
(1)谷歌在这一市场上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从2008年起,无论是按页面浏览量还是按网站访问量计算,谷歌在大多数欧盟国家的市场份额基本都保持在85%以上,微软旗下的必应搜索服务作为唯一值得一提的竞争者,在任何国家的市场份额均未超过10%。
(2)市场进入和扩张存在重大障碍。首先,搜索引擎的开发需要大量数据以改进算法,优化搜索结果的相关性。潜在竞争者尚未进入市场,并不拥有大量数据,这成为其进入市场的重大障碍;现有竞争者们的用户数量均不大,难以获得足以支撑搜索的大量数据,因此也无法迅速扩张。其次,谷歌资金实力雄厚,从2006年起,其用于一般搜索服务的投资便高达19亿美元,到2015年,更是达到了99亿美元。其竞争者们均无可匹敌的能力,即使是主要竞争者雅虎,2006年至2015年间最高的投资也不过7亿美元。此外,谷歌基于提供一般搜索服务和在线广告服务而形成的双边平台所产生的正反馈效应,也为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制造了障碍。这说明谷歌的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均无力大量增加产能,因此无法对谷歌形成竞争制约。
(3)用户的“多归属”频率低。所谓多归属,是指用户同时使用若干个平台的搜索服务。同时使用多种服务来满足同一需求,可以表明这些服务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多归属的用户越多,表明与谷歌的一般搜索服务互相具有替代性的同类服务越多,这些服务的存在可以构成其拥有支配地位的阻碍。但欧盟委员会经调查发现,多归属用户最多占比不过21%,对多数用户来说,除谷歌的搜索服务外别无选择。
(4)用户没有对抗能力。终端用户对谷歌搜索服务的依赖性很强,且每个用户的查询量只占总搜索查询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其对谷歌的行为没有对抗能力。
3.竞争效果的考察
在本案中,欧盟委员会虽然区分了两个相关市场,但并未对谷歌的行为进行精确定性,而只是将其称为“一个市场上的支配企业以扭曲竞争的方式,将该支配地位扩展到另一个独立的市场”,因此其分析过程比较含混。将市场力量扩展到另一市场,通常被称作市场力量的“传导”。传导型支配地位滥用行为主要有搭售、拒绝交易和差别待遇三种类型,但不同类型的传导方式不同:拒绝交易旨在阻止其他人进入下游市场,从而获得下游支配地位,其效果可以立竿见影;而差别待遇在外观上并不拒绝与相对人进行交易,但使其处于不利的竞争条件,同样可以达成传导效果,只是见效尚需要一定的时间。二者均属当事人利用上游支配地位来排斥下游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同时是当事人的交易相对人,差别仅在于排斥的具体手段不同。手段通常并不影响性质,但不同手段的运行方式不同,因此仍然需要进行必要的定性与区分,才能准确把握行为的过程。搭售行为则呈现出不同的外观:搭售行为人强迫交易相对人购买其被搭售品,导致被搭售品市场上的其他经营者因缺乏交易机会而被挤出市场,该行为直接作用于相对人,但排斥对象却是提供被搭售品的其他经营者,而不是相对人本身,这与拒绝交易、差别待遇存在区别。对拒绝交易与差别待遇来说,其行为作用于相对人,而其所排斥的竞争者也正是相对人本身。
事实上在亚马逊案中,同时发生了两种排斥性行为:亚马逊对不同零售商采用不同待遇,可以构成差别待遇行为;而其采用不同待遇的目的在于迫使零售商接受其自营的物流服务,因此又可以定性为搭售行为。这两种行为排斥的对象不同,因此并不构成竞合:差别待遇行为排斥的对象是其他下游零售商,而受到搭售行为排斥的则是其他物流服务提供商;其他零售商可以基于前者对亚马逊提起诉讼,而其他物流服务商则只能基于后者起诉。欧盟委员会的处理结果则没有注意到搭售行为的存在。
4.行为效率的考察
欧盟委员会认为谷歌的优待行为产生了以下消极影响:其一,削弱了消费者福利。竞争性的比价服务退出市场后,谷歌对自营比价服务网站内的商家将收取更高的费用,最终导致消费者购买价格提高。其二,削弱创新动力。一方面,由于不再有望提高用户流量,竞争性的比价服务通过创新来吸引用户流量的动力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不再需要努力吸引用户流量,自营比价服务通过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动力也降低。
基于以上论证,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的行为构成滥用行为,且不能产生增进效率的结果,因此是非法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在相关市场的界定、支配地位的认定还是在竞争效果的考察上,欧盟委员会完全套用传统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分析方法,并没有针对人们所说的双边市场交易模式、平台服务零价格属性等特点进行调整。
(二)亚马逊案的处理结果及其论证过程
如前所述,谷歌案中没有对行为进行具体定性,而宽泛地将其称作传导型支配地位滥用行为,而在亚马逊案中,欧盟委员会则将亚马逊的行为定性为《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c)款所规定的歧视待遇,这比谷歌案推进了一步。同时,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谷歌案中并未表明所谓的平台经济给反垄断法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因为在其分析过程的每个步骤或环节上,传统的规则与方法均仍然是适用的。但在审理本案时,欧盟委员会观念中显然更认同目前国内外研究中普遍的觀点,即平台经济在相关市场的界定上给传统反垄断法带来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试图将关于这些特殊性的考虑纳入其分析过程中。这主要体现在其决定书中相关市场界定部分,认为应当从消费者、商家两个视角来界定相关市场,但又并未将这一想法予以落实,因而自相矛盾。
1.试图根据双边平台特性界定上游相关市场
本案中,欧盟委员会同样认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及上下游两个市场,并将上游市场界定为在线零售平台服务市场。但与谷歌案不同的是,欧盟委员会注意到亚马逊在上游采用的是所谓的双边市场经营模式,并试图根据这一特点对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作出调整。
对于双边平台经营模式,学者Evans认为平台的角色是连接双方或多方用户并促使他们进行交易的中介,学者Armstrong进一步补充道,其中一方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另一方用户加入平台的数量。欧盟委员会基于这一认识,认为亚马逊平台既然存在零售商与消费者两端客户,并且零售商的收益取决于消费者的数量,因此其所从事的属于双边市场交易;平台两端连接着不同的市场,因此需要从两端分别界定相关市场。而在谷歌案中,欧盟委员会则没有考虑这一因素,它只从比价服务提供商这一个角度来界定相关市场。
本案中,欧盟委员会首先从零售商角度界定相关市场,在明确零售商的需求后,依据需求替代性标准,对各品牌自营的在线商店、社交平台、购物比较平台、线下实体店的替代性进行考察,认定它们无法替代亚马逊的在线零售平台提供服务,最终将相关市场界定为“为在线零售商提供电商平台服务的市场”(本文称“在线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欧盟委员会认为,亚马逊对消费者提供的平台服务也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但同时指出,由于本案考察的重点是亚马逊相对于零售商而非消费者的市场力量,因此欧盟委员会在决定书中放弃从消费者端对相关市场进行详细界定。这与其对双边市场的认识有些冲突:一边认为需要从两端界定相关市场,另一边又放弃其中一端,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隐含着如下可能,即欧盟委员会关于平台特点的认识可能是不正确的。
2.支配地位的认定
多数研究认为在平台经济领域,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也存在特殊性,即市场份额作用弱化,网络效果与锁定效果构成支配地位的主要成因。但亚马逊案的处理结果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该案中,欧盟委员会仍然采用传统的支配地位认定方法,并据此认定亚马逊拥有支配地位:(1)当事人市场份额巨大。亚马逊平台的零售商数量占市场总额60%以上,消费者数量占市场总额70%以上。(2)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无法有效增加产能。竞争者们不仅资金和技术实力无法与亚马逊相提并论,而且也无法挑战其基于数量庞大的零售商和消费者形成的强大网络效应。(3)零售商没有对抗力量。零售商依赖亚马逊提供的平台服务开展经营,且大多规模较小,无法对抗亚马逊。
3.竞争效果的考察
亚马逊的优待行为使MFN零售商受到歧视待遇,导致其在竞争中受到排斥:由于无法加入黄金购物车,也无法获得“Prime”标签,他们很难得到交易机会。在特定推荐商品的总访问量中,亚马逊自营商品所占份额高达80%,使用其自营物流服务的零售商品占16%,也就是说,AFN商品共占据了96%的访问量,而MFN商品的访问量只有不到4%。如此微乎其微的用户流量必定无法支撑MFN零售商在下游市场的经营。因此,欧盟委员会认定亚马逊该行为扭曲了其平台下游市场零售商之间的竞争。
鉴于亚马逊在2022年12月为解决以上竞争问题提出了有效承诺,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些承诺可以消除竞争风险,因而予以接受,并结束了本案的反垄断调查,而没有对其合法与非法作出认定。
四、谷歌案与亚马逊案评析
(一)相关市场界定过程中并不涉及双边市场问题
谷歌案与亚马逊案之所以引起世界反垄断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是由于人们认为这两个案件体现着平台经济领域的特点,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案件的分析,明确对平台经济领域自我优待行为的有效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问题达成规律性认识。但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在这两个案件中无论当事人的行为方式还是欧盟委员会的分析过程都没有呈现出多少特殊性:自我优待行为完全符合传统的差别待遇的行为方式与构成要件,而关于差别待遇的传统分析方法也仍然适用,反垄断法理论与规则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挑战。仅有的例外是在相关市场的界定上,亚马逊案针对双边市场经营模式的外观特点,试图说明有必要从两端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但接下来又放弃这一想法。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将加深人们对于平台特征的如下常见误解:平台普遍具有双边经营的特点,因此在界定平台所在相关市场时,需要兼顾双边不同用户的需求。
但从这两个案件来看,谷歌平台与亚马逊平台并不采用双边市场经营模式。实际上它们与消费者之间并无交易关系,因此消费者并非平台的客户。消费者进入平台的目的是购买商家的产品,而商家进入平台的目的则是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为此商家不仅要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本身,而且需要提供进行交易的条件,包括交易场所与手段,因此消费者的需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产品本身,二是购买环境与条件。但商家自身只生产产品,满足消费者第一方面的需求,而对于第二个方面的需求,则需要从平台那里购买,再向消费者提供。因此这里并存着两笔不同的单边交易:一笔为商家与平台之间的服务购买协议,其中需求者为商家,相关市场为所有能够满足商家同一需求的平台服务;另一笔为商家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商品买卖协议,相关市场由所有互相具有替代性的商品组成,商品的交易成本中包括其生产成本,以及提供购买条件的成本。这时消费者得到的购买条件服务本质上是商家所提供,平台已将这些服务出售给商家,只是仍然由平台来具体操作。无论谷歌还是亚马逊的优待行为均只有一类交易对象即商家,因此在相关市场的界定上并无特殊性:该项交易中,商家是需求者,其需求是能够满足消费者购物需求的购物条件,因此相关市场由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平台服务所构成。
即便不采用上述思路,從两端界定市场也并不必要。商家对于平台的需求,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购物条件的需求,因此能够满足商家需求的相关市场必定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商家的需求,从两端界定市场的结果必将是一致的,没有必要再从消费者角度界定一次。
總而言之,至少在自我优待案件的相关市场界定上,平台的出现并未给反垄断法带来挑战。在界定该类案件的相关市场时,只需要着眼于优待行为双方当事人,查明需求者及其需求的内容,依据需求替代性标准对上游相关市场进行界定即可。
(二)市场份额在支配地位认定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主流看法,平台经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要挑战,是在支配地位的认定上,市场份额的作用被削弱。但人们一直未能对此提供论证,也并不能够清晰回答市场份额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
在传统产业中,支配地位的获得主要是基于对产能的控制:支配企业之所以能够有利可图地提高价格,是由于竞争者们缺乏足够的产能,无力大量增加产出来满足消费者的转向需求。这通常要同时满足四个要件:当事人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现有竞争者没有能力增加产能,潜在竞争者无力进入市场,买方缺乏对抗力量。其中市场份额巨大是拥有支配地位的基本条件,只有如此,竞争者们才有可能缺乏扩大产出所需要的产能。但尽管如此,市场份额巨大只是支配地位的构成要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
而互联网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以各种杀毒软件、即时通信工具为例,用户可以无限量下载,经营者并不为此增加成本,因此每个竞争者的产能均无上限,可以无限量地增加产量,来满足消费者的转向需求。经营者若想拥有支配地位,必须能够阻止消费者的需求转向,而阻止其转向的主要原因主要是转向成本。这种情况下,支配地位的取得与产能的控制能力无关,因此市场份额对于支配地位的认定并无意义。
在谷歌案与亚马逊案中,平台增加产能是有成本的,其产能并不是无限的。以谷歌为例,其产品的外观表现是一般搜索平台服务,但商家入驻这一平台的动机,却在于获得该平台所能提供的交易机会,一般搜索服务只是提供交易机会的手段,而不是商家需求的本质。因此商家所需要的真正“产品”是平台所能提供的交易机会,而制造这种产品的“产能”则是平台的流量,流量的增加不仅需要加大广告投入、技术升级、用户维护等成本,也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其边际成本巨大,因此各平台的产能均有局限,在支配地位的认定上,以市场份额为首要指标的传统方法仍然适用。在两个案件中,欧盟委员会经审查后均认为,当事人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既有竞争者无力大量增加产能,潜在竞争者无力充分进入市场,买方没有对抗力量,因此认定其拥有支配地位。传统反垄断法理论与规则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挑战。
五、结语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自我优待行为并未给反垄断法带来新的问题,其所呈现的特殊性仅限于外观与部分具体实施手段——在这两个案件中,体现为差别待遇的具体实施方式,而不关系到行为的性质,因此没有对反垄断法理论与规则构成挑战。不仅如此,从这两个案件的分析过程也可以发现,人们对平台一般特性的认识也发生重大误差,比如无论谷歌还是亚马逊都并未采用双边市场经营模式,其交易对象是下游经营者,并无第二类客户,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欧盟委员会原本没有必要分别从两个角度对相关市场进行两轮界定;而在支配地位的认定上,两案中仍然采用传统方法,这也是对于学界主流观点的直接否定。也就是说,国内外研究中对于平台经济领域特殊性与规律性的认识中,有相当多的部分经不起这两个案件的考验。
随着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垄断行为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些新颖的外观,带来或多或少的复杂性。面对这些复杂性所带来的困扰,不宜过于轻率地倡导标新立异,而应首先对当事人的行为过程进行细致解剖,然后努力回归传统反垄断法的理论与规则,捕捉其本质特征,才能发现真相,并沿着正确的方向追寻下去,最终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脱离专业基础知识的创新努力不仅无法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而且将落后于实践的进展,谷歌案与亚马逊案的结论即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Anti-Monopoly Law Analysis of Self-Preferencing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bstract: The self-preferencing in the field of platform econom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due to its novel appearance.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appropriate analysis for it. By analyzing the self-preferencing in the Google Shopping case and the Amazon Buy Box case, it is found that this behavior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treatment only in terms of discriminatory methods, but its essence remains unchanged. Therefore, the theories and rules regarding discrimination treatment in the Anti-Monopoly Law can still be applicabl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handling of these two cases further supports this notion, as it confirms that (1) when defining relevant markets, the traditional standard of demand substitutability has not been challenged; (2) in determining dominant position,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using market share as the primary factor is applicable; (3) the examination of competitive effect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self-preferencing on excluding competition in downstream markets; and (4) the parties involved still ne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s for their actions when assessing behavioral efficiency.
Keywords: Platform Economy; Self-preferencing; Discrimination Treatment; Two-sided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