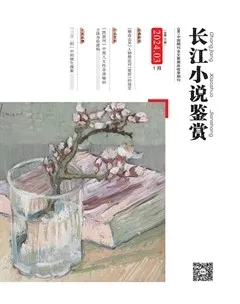后殖民女性主义视域下《雪花秘扇》中被边缘化的女性
2024-06-01李雅雪
李雅雪
[摘 要] 《雪花秘扇》是由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在书写“女书”与“老同”这一已经近乎消逝了的中国传统女性文化中,展示了19世纪的封建中国、闭塞的瑶族村落、奇特的社会习俗、神秘的女书文字、有着终生誓约的老同、小脚的东方女性等种种异域风情。这部小说试图刻画和呈现当时的女性命运、心理特征和时代价值观,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视为边缘化的“他者”的悲惨遭遇。本文拟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解读《雪花秘扇》,揭示在此作品中所体现的在父权话语下被边缘化的女性境遇及成因以及边缘化女性社会身份的重构。
[关键词] 后殖民女性主义 边缘化 女性形象 身份构建
[中图分类号] I247.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3-0032-04
一、被边缘化的“他者”女性形象
1.女性遭受的身体上的伤害
在父权制思想的支配下,妇女被看作是男人的附属物,受到家族和社会观念的双重压力。作为封建时代的深闺妇女,百合的母亲和婶婶坚守着传统观念,从女儿五六岁的时候便开始为女儿缠足,来塑造女性的美丽和纤细。她们相信,只有通过束缚女性的脚部,才能使其表现出娇小、柔弱和优雅的特质。这种传统做法在当时被广为接受,虽然现在已被视为残忍和剥夺自由的做法。当时的母亲都希望借此为自己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夫婿。但是,要想得到“三寸金蓮”,就必须要承受缠足之苦。虽然百合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想要装出一副坚强的模样,然而双脚传来的疼痛还是让她难以忍受,她还被母亲赶着在地上走来走去。久而久之,她的脚趾骨折,肌肉溃烂、化脓。缠足不但会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会造成残疾,严重时会危及生命,书中的三妹就是这样死的。这是令人叹息的遭遇。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公。女性生来的意义好像就是为了嫁人,身体的掌控权也不在自己,完全在于男性的审美和喜好,那个时代的女性的地位低下,生命的存在也是没有价值的。
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生育子嗣对于家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可以传承祖先的香火,同时也给予母亲社会地位和荣耀的认可。甚至当百合听说雪花在婚姻中受到虐待时,她的家人鼓励她再生一个孩子,安抚她的情绪,希望以此来提升她在婚姻中的地位。可是,在意外流产的时候,从她体内流出的血,却是黑色的,黏稠的,还带着腐臭的味道。雪花最终沦为了封建大家族的生育工具,无休止地孕育子嗣,正是因为当时对于“母凭子贵”这种荒谬思想的盲目追捧,这给雪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由于她的身体负荷过重,最终导致她病重并去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容器孕育家族的接班人,可见女性受封建礼教思想的荼毒之深,让自己的身体承受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2.女性忍受的心理上的折磨
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一个脱离了时代的落后村庄,那里的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女人们没有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还会用缠足、结老同等方式来满足男人的审美需求。小说中,“婚姻,是传统观念和封建社会赋予女性的一种宿命”[1]这种观点多次体现。男性和女性都没有权利自主选择婚姻,因此夫妻间的感情和默契难以达成。男性随时可以丢弃妻子,纳妾,而女性则可能因不幸的婚姻而遭受毁灭性打击,无法弥合一生的伤痛。
小说中,相较于身体上的伤害,雪花遭受了更多心理上的折磨。雪花原本是富有家庭的小姐,博学多才,举止优雅,凭借这些优势,她完全可以同另外一家门当户对的公子结婚。但是,因为她的父亲做生意失败,又吸毒,所以她的家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逐渐没落,雪花也从大家闺秀变成了连一般人家的闺女都不如的落魄小姐,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她被迫放弃大小姐的身份,学习家务劳动,还去侍奉他人,这令人悲哀又心疼。更令人震惊和同情的是,媒人告知雪花,她将要嫁给一个屠夫,从此以后,她将过上卑微又贫穷的生活。平时,雪花受尽了婆婆的白眼和丈夫的打骂。她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当容器,以免被遗弃,她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下,拼命生育,让自己沦为生育机器。在雪花的身上,体现了旧社会女性遭遇的不公,妇女完全丧失做人的权利和追求,完全沦为家族和男人的附庸。正如雪花母亲所说:“命运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命。”婚姻、性别和权力结构的不对等,造成女性处于社会边缘,导致了无数女性的悲剧命运[2] 。
3.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妇女在社会中的生存是一种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妇女的话语权缺失。小说开篇就写道:“时代变了,我也可以把这些都说出来了,以前我是靠父母把我抚养长大,后来是靠婆家养活,因此,我也不好说什么。如今,我想要把我这一生的遭遇都吐露出来。我已经一无所有,也不会得罪任何人了”[1]。这折射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在男性统治话语权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并缺乏话语权。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力,说话人话语的地位。谁有话语权,谁就能掌控舆论。男性主导的社会就是通过对话语权力的支配来实现对社会权力的支配。福柯“话语权力”理论指出,话语权与权力密不可分,只要有话语权,就会产生权力,而权力又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对话语的支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妇女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了妇女社会地位处于“缺失”状态,作为被男性操控的客体,妇女的沉默和容忍既是话语权的缺失,也是妇女权益的丧失。
在封建时代,女人依赖男人生存,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翼翼,没有任何话语基础,处于话语权无根状态,最终被男权话语体系所吞没。在男权价值系统中,妇女总是处于次要地位,是一种被异化的自然物,是男性欲望的客体。“裹小脚”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它决定了女性的美学特点和行为准则。男人视自己为“主体”,并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对女人的期待,将其塑造为拥有“善解人意”“谦恭温顺”“相夫教子”等人格特质的客体观赏物,甚至连后世的妇女都认为这些特性是与生俱来的。作为被压制的妇女,在男权统治下,妇女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妇女被置于社会边缘,没有一位真正的独立女性。小说中的百合成为八十岁的寡妇的时候才敢说出这段往事,这象征着女性开始觉醒并对自己的话语权做出反思。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觉醒和反思是在百合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当时,大多数女性仍然处于男权话语的统治下,一直被边缘化并成为被动的“他者”。
二、女性身份被边缘化的原因
1.父权制对封建女性的压迫
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的社会地位很高,有着支配女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女性则成为了被支配、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成为了“他者”。后殖民女权主义认为,在第三世界中,妇女不仅仅是性别的“他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他者”,处于被双重边缘化的地位。身处男权文化之中的妇女,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由两性差别所造成的歧视、偏见与不公。19世纪中国妇女深受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为了取悦异性不断改变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这一点可以从“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中看出来。女性缠足正是对这一观念的深刻体现。但是,由于受中国古代傳统儒学的熏陶,男尊女卑、重礼轻爱、三从四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已深入人心。
百合成为地位崇高的卢夫人之后,她就已然变成了以男性凝视为中心的理想女性。她跃升成为那个时代妇女的标杆和榜样,也是男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驯服模范。她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主导的文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规范和驯化自己以及身边的女性,即便这些都是她以前最深恶痛绝的。百合的思维早已被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同化,所以她对于自己,对于其他女性,都有着与男性对于女性同样的要求。她既要让自己顺从于社会对妇女的期待,又要让其他妇女顺从,把这当作评价女性是否称职以及衡量女性价值的尺度。时间久了,百合就失去了心灵上的知音,与昔日的好姐妹们也有了隔阂。
2.家庭内部的隐形伤害
女性在家庭之中被赋予了理所应当的责任,这种责任则变成了对女性无声的压迫。百合渴望着爱,但对她来说,爱是如此遥不可及。甚至当她的母亲给她一个耳光时,虽然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她都不会感到愤怒,因为百合认为这就是母爱。她的心灵已经变得扭曲,她觉得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然而,在和母亲的分歧和争吵中,她忽然想起了自己被裹脚的那段日子,那种痛让她撕心裂肺,一直无法忘怀。她忽然清醒地发现母亲从来没有对她有过哪怕一丁点的爱,只有无尽的要求和无尽的责备。这令百合非常失望,她不能原谅和释怀母亲对她所做的一切,包括她的自私行为。她试图将母亲从自己的生活中剥离,却使自己陷入深深的悲伤中,永远无法忘却。这就是家庭对百合造成的隐形伤害,使她一辈子生活在阴影之中。
雪花一直向往着自由,也曾借助女书给他人写信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渴望得到同情和关注。但她的好友百合首先向她施压,要她遵守家规,当个乖乖听话让夫家满意的合格媳妇,“顺从,顺从再顺从”,要靠生个男孩来提高家庭地位,从而改变命运。作为女性的典范,百合的婆婆卢夫人因为雪花家族的衰落以及其杀猪丈夫的缘故,嫌弃雪花的身份,断绝了百合与雪花的交往。那些恪守妇道和三从四德的女子,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封建制度对自己的残害和压迫,并将之前自己弃之如敝履的规定作为自己现在的行为准则。她们沦为了旧习俗的受害者,最终也成为了压迫别人的人,作为曾经伤害自己的人的帮凶,她们把他人也变成了牺牲品。这都是家庭内部对于女性的隐形伤害,女性并没有从自己的家人和姐妹那里得到安慰与支撑,无处诉说自己的无奈与苦闷,相反受到最亲近的人的背叛以及不信任[3]。
三、边缘化女性社会身份的重构
小说中的女性从老同的姐妹情谊中获得精神慰藉以反抗父权压迫;构建以女书为核心的女性话语系统来打破父权压抑下“缄默”的失语境况;以“双性同体”的形象来颠覆父权社会所建立的不平等的两性关系。
1.老同的姐妹情谊
“老同”是中国南部一种古老的风俗,有这样一种传说,即年龄相仿、相貌相似、性情相近的姑娘会对彼此发誓,互相爱护,永远不分开。结“老同”是一种神圣、吉祥的喜事。这是女人与女人间最亲近的感情,比丈夫与妻子、姊妹之情更甚。她们使用一种名为“女书”的独特女性语言进行沟通。这不是同性之间的恋爱关系,更像是心灵上的伙伴,生活上的朋友。“老同”与欧美文学史上的“姐妹情谊”有很多相似之处。“姊妹情”是一种由妇女联合起来的力量,它是由被男权社会所排斥的女性力量组成的反抗势力。与此类似,“老同”也是“妇女们在共同被压制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感情联系,是对妇女感情世界的一种温柔的救赎”。“百合”与“雪花”是经媒人介绍而结成“老同”的,并以独特的女性文字——“女书”的形式“互诉衷肠”。在困境中,她们分享彼此的情感,鼓励对方勇敢地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在幸福中,她们分享彼此的喜悦,为对方的快乐而感到开心,共同分享喜怒哀乐。
小说中的义姐妹也如此,性格相合的几个女孩会自动结成义姐妹。在女性遭受压迫、迫害的情况下,妇女的命运、人身自由都会被种种条条框框所制约,身心俱受摧残。因此,女性们会寻求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结盟,彼此帮扶鼓励,一起直面艰难的人生。根据《道县志·社交习俗》所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在乡村中的未婚女性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风俗习惯。她们大多是正值青春妙龄的大家闺秀,由于对传统的包办婚姻感到不满,又惧怕自由恋爱,不敢与异性交往,结果就是同性相爱,结为姐妹。”[4]义姐妹处于同一生活层面,共同的经历和情感让她们彼此靠近,惺惺相惜。这是一种淳朴的人际关系,不掺杂利益关系,给予对方日常生活中的陪伴以及苦难中的精神慰藉。
父权制社会中,女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她们也在极度压抑、身不由己的处境中结成了老同和义姐妹关系,这是独立于男性之外的人际关系,她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一束光,陪伴彼此,给对方重获新生的力量。
2.用女书文化构建女性话语权
江永女书是湖南省西南地区的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字。它在女性中间流传了上千年,是世界上唯一基于性别的书面文字。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常常陷入“失语”的境地。但是,女书却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女书既是女性的智慧,又是一种文化的联系。仔细阅读女书中的故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时女性的人生境遇。
百合与雪花之间有许多书信都是用女书所写,其中一封这样写道:“我的丈夫对我很好。我从来不知道我家的那些地在什么地方。我每天都要非常努力地工作。婆婆一直在旁边监督。我们家的女人对女书都很有研究。我婆婆也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女书的新字体。回头我再写给你。我每天都要缝补衣服,做针线活计,做鞋子,还要纺织,做饭。如今,我有个儿子了。我向上苍祈祷,希望有一天能让我生下另一个儿子。你也得听我说,要听你老公的话,听你婆婆的话……”[4]这封女书简单明了地描述了女性生活的日常情况。从女性的劳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勤奋、能干;她们对公婆、丈夫百依百顺,并以自己有个男孩而自豪,表现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卑微与她们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从来不知道我家的那些地在什么地方”揭示了女性生活的封闭,认为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女人是围绕着她的丈夫,从丈夫那里获得生活来源。
“女书”是一种以女人为载体的象征代码,传达着女性的讯息,对女性有着特殊的意义。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对女性施加了种种限制与约束,旧时代女性只有借助女书来表达她们内心深处的苦闷与压抑,她们的情绪借此得到了短暂的释放。在女书中,女性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特有的个性魅力。女书有其独特的书写规律,“每一种女书字体都要回到原文中去解读”,这既体现了女性对女书的独特运用,又体现了女性独特的感情世界,以及女性建构自身世界的方法[5]。
四、结论
在压迫和失语的状态下,写作行为承担着巨大的责任。《雪花秘扇》通过独特的叙述话语,让读者了解生活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处境,刻画了被边缘化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受苦受难的女性的关爱。邝丽莎对男权意识和男性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使女性叙事主体成为叙事的主要声音、女性角色成为了故事情节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而男性角色被描绘成叙述者的对象。
总有一天,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女性和人们将重新书写自己的社会身份,不会被视为“他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书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女性身份,即“强调尊重女性个体的差异,不再有削弱、国家、民族和阶级的界限”。
参考文献
[1] 邝丽莎.雪花和秘密的扇子[M].忻元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张艳.论《雪花与秘密扇子》中百合的多重身份与焦虑[J].山花,2013(2).
[4] 范若恩.全球姐妹情谊的幻与灭——《雪花秘扇》的后殖民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解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2).
[5] 莫秀云.《雪花秘扇》的女性独立意识解读[J].电影文学,2013(1).
(特约编辑 范 聪)